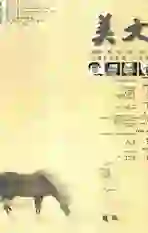巴恪思与《太后与我》
2015-06-25罗宾·吉尔班克
罗宾·吉尔班克
慈禧太后不仅喜欢人家把她画的像观音菩萨,也把自己打扮成观音菩萨,让宫女装扮成金童玉女,太监头李莲英扮成依怙尊。她让宫里的画家把前后背景画好,然后宣她的御用摄影师,年轻的裕勋龄为她照相,让阳光这个伟大的画家照射出她的光辉。
一天,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参观琉璃厂的一家古玩店时,玩家手里慈禧太后画的四小幅黑白梅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四幅画以前一直挂在她陛下颐和园寝宫两间房子的过道里,能得到这几幅画我自认为很荣幸。
“你注意看,”那人说,“这画上的每一笔都是一气呵成,此举实乃不易。她的笔在用墨上,既要线条分明,同时还要达到期望中明暗的渐变。要是线条有瑕疵,无法重画;要是明暗不到位,也无法加减,这是书法和绘画中的大忌。一笔下去,落地生根。此乃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
得到这几幅画后,我曾让当代北京的几位大画家看过,他们都说这几幅梅花是单色水墨中的上品,与缪嘉慧的看法一样,认为要是慈禧太后一辈子作画,她就会成为历史上当朝的大画家之一。
有天,慈禧太后的一位御用画家来访,我让他看这几幅画。他赞同其他几位对慈禧作品的评价,但却让我看其中一幅画上的菱形交叉枝叶。
“这个,”他说,“能证明是她的画,”
“何以见得?”我问。
“因为职业画家的笔下枝叶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不是这样?”
“画家不这样画,”他说,“没有美感。”
“那太后的朋友为什么不提醒她?”
“谁敢那样?”他反问道。
节选自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著
《中国的宫廷生活:首都的官和民》 1909年出版
虽然慈禧太后作品的审美意识常常有点差强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绘画和书法中的笔画苍劲有力,绝对的泰然自若。几年前出去旅游时,我在陕西的党家村初次看到了慈禧的作品,党家村位于临近山西的小山里。沿着古镇挤满了人,凸凹不平的青石板街道走进去后,主街忽然成了一个小广场,人们站在那里可以欣赏镇里最宝贵的艺术品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恐落入敌手逃离北京。党家村成了逃亡西安避难路途上的歇息驿站。慈禧太后留下的纪念之一就是她御笔钦赐的一个巨大的“福”字,象征她永远感谢这些忠实臣民的款待,祝愿他们能继续发达昌盛。慈禧赐福被雕刻在墙上,现在到此旅游的人都挤着在那里照相,并伸出手指摸“福”。毫无疑问,人们期望能沾一点吉祥福传承下来的福气。
但在我眼里这字一般,人能感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即便沮丧这位老妇依旧大权在握,然而我欣赏的不是这。这个“福”字的一笔弯曲,像一只鹤扬嘴吞食,要是进一步想象一下这只水鸟的寓意,后面的几笔就更有问题了。人好像是被赋予了X光的功能,能看穿这只鸟,看透它的内心。而下面出现的“田”则意味着内心的不爽,“田”对这只可怜的鸟肯定是个威胁。
慈禧太后喜欢人吹捧她的作品,且特别看重外国人的评价。要是人能与早亡的人联络,我肯定自然会不慌不忙地把我对她这幅书法“大作”的真实评价告诉她。上面何德兰的这段话就更有趣了,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大家都在追求静怡的花卉创作,但太后身边的人却时刻不敢忘记她身上散发出的独裁和威严。许多奉承慈禧太后的描述是外国的一些娇生惯养的权贵写的,因为他们曾有幸获准短暂的入宫。相形之下,何德兰的描述听来更真实。何德兰是美国人,他是传教士,在北京汇文书院任教,他的汉语很流利。在结发妻子去世后,他和自己的同事玛丽亚姆·辛克莱(Mariam Sinclair)结了婚。他夫人一直是慈禧太后和其女家眷的西方御医。何德兰及其夫人的回忆录重点不在解构这位“龙夫人”的神话,不谈政治动机,而是专注于细节,更谈不上有自我炫耀,令人耳目一新。从这对夫妇的描述中读者看到许多平常事,如光绪皇帝十分渴望有自己的一辆自行车。不过他对这新玩意的钟爱好景不长,在自行车的后轮缠住他的辫子把他绊倒后,他就把它扔到了一边。所幸的是,这对夫妇没有试图用文学色彩来渲染类似这样的逸事,他(她)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转喻为光绪试图为古老的中国引进外国科技和改革,但却失败了。
有关此话本文就到此打住。在写给外国人看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多少“真相”?不得不忍受多少文字上的发挥呢?近来,有关慈禧太后的形象、性格以及身后事,再次成为人们热议和重新评价的主题。这里不适合对清朝灭亡的原因提出新论,也不会对任何有影响的大问题给出己见。我主要想说的是为什么慈禧太后会成为越来越有争议的人物,我的文章也许会让清水更浑。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历史小说作家中就出现了一种思潮,有意揭掉其表面的光环,企图发觉慈禧太后人性的一面。美国画家柯姑娘(Katherine Carl ,1865-1938),著有《慈禧写照记》(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译者注)曾在紫禁城呆过几个月,她后来抱怨说自己无法抓住慈禧太后的精气神,因为她必须遵守中国宫廷画的要素,不能有阴影,像是在透视,比如不能显示太后让人恐惧的“阴阳脸”,否则就认为是不祥。这些限制的确让太后的画像显得很庄重,但也让柯姑娘的每一幅画像都很平淡,即便是主人公身着华丽的黄袍和紫裙。
诸如这样的描述在闵安琪等作家的笔下屡见不鲜,暗示公众不了解慈禧太后人缘好的一面。遵循自己在书写历史人物传记时一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写《赛珍珠传》和《江青传》时都是如此),闵安琪在《兰贵人——慈禧太后》(2004年)和其姊妹篇《末代皇后》(2007年)中,试图挖掘女主人公从被册封为咸丰皇帝之妃,到1908年驾崩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闵安琪作品的前提是,现代读者(既对过去的解读者和作者本人)和前朝之人是有渊源的,而人性的光辉可以超越时代、文化,甚至是语言。虽然皇妃之名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神秘莫测,但闵安琪强调的是在男权社会里,慈禧做为一个女人所经受的创伤,以及自己体会到的慈禧的女性本能。虽然人们说慈禧是一个由底层爬上来的暴君,甚至是十恶不赦,但对她的描述是她内心深处亦有柔情,这一点宫廷里的政客从没否认过。在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的同情心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在当时于公于私都不允许她有此举动。面对知己似的读者,慈禧悲叹道:
太阳正在升起,皇儿却命丧哀家怀中。迟来的霜降扼杀了庭院中的栀子花,花枝枯萎黝黑。林间的松鼠不再跳跃,蹲在树上,大声喧哗。一行大雁从头顶飞过,羽毛从天而降。
哀家记得怀抱同治,感到他的心跳渐弱。依稀记得坐着昏睡了过去,故哀家确实不知,何时皇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节选自闵安琪著《末代皇后》第92页
此类散文式的段落在风格上是下了功夫,谙熟文学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其中运用的写作技巧。闵安琪又一次玩的是“感情误置”,也就是说把书中主人公的感情投射到了外部事物如天气和环境上。作家为何要选择这样写,看透这点并不难。“感情误置”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莎士比亚对此就很在行,其力道在于能穿透文化障碍。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可以理解《李尔王》所说的“荒凉的田野”或《麦克白》中“有人说大地都发热而战抖起来了”,那也就可以理解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其他运用这种技巧的任何中国经典著作。闵安琪的用意在于想驾驭对“感情误置”的运用,至于她是否成功尚有争议。她不断地借用明显具有“东方”特色的动植物,给人的感觉就有点是在拉清单。
《兰贵人》及其姊妹篇实话说乃中产阶级的娱乐口味,英国人(不论喜不喜欢)会根据这本书在国内所得到的喝彩给出自己的评价。著名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理查德·马德莱(Richard Madeley)和朱迪·芬尼根(Judy Finnegan)认为第一部作品“非常精彩”,并把它加在了夏季好书榜之列。我不是有意苛刻,但爱新觉罗家族的苦恼常常会成为白天电视节目中无休止的个人问题探讨。当慈禧太后发觉同治懂得了“风情”并在外面“寻花问柳”时(见该书第83页),她的反应恰似二十一世纪的一位母亲发现儿子在浏览黄色网站。在肉欲色谱的另一端,得宠的太监小安子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只能靠崇拜声名遮住了太监身份的英雄人物来排解自己的困苦,如探险家郑和。闵安琪简洁的文风有时也会变得很迂腐。在李鸿章进贡了一套西方的洗漱用品后,慈禧柔声细语道:“哀家特喜欢李大人手书的使用方法。现在哀家要防牙衰落,还要想着防国家衰败。”(见该书144页)看到这人不禁诧异,作者是否拿了“高露洁”广告团队的好处。
读《兰贵人》和《末代皇后》,让我更加渴望了解人的内心深处。这在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1874-1944,史学界通译为白克浩司,英国人——译者注)的回忆录《淫乱满洲》(《淫乱满洲》英文原名Decadence Mandchoue ,中文版译名《太后与我》——译者注)一书中有不少描述。该书作者所言被认为是描写慈禧个人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因为作者声称他是慈禧的情人,抑或用“老佛爷”自己的话来讲是个被“驯服了的洋鬼子”。除了简短的外出,巴恪思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他去世一直寓居北京。在其人生末年,他成了一个小名人。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对西方人避而远之,喜欢把自己藏在飘逸的白胡子(就是现在任法融和张至顺道长的那种胡子)和中国传统文人的马褂后面,但遇到自己特别赏识的人,他就会大谈世纪之交时清朝皇宫里的趣闻逸事。其中最离奇的(不用提最淫秽的了)都保存在他的传记手稿里。这部传记是他在年轻的瑞士朋友,医生贺普利(Dr. Reinhard Hoeppli)的鼓励下,在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完成的。该书和讲述其在英国淫乱生活的前篇《黑暗的往日》(The Dark Past)一起构成了一部性学大全,一直被认为过于直白而不能出版。《黑暗的往日》中涉及一连串的“恋人”(大多数是男性)包括奥斯卡·王尔德,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和至少两名英国首相。
很多人初次听到巴恪思的大实话肯定有疑问,但有位学者后来评价说,他书里的一些东西如此“详细”,很吊人的胃口。在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方面,他也许就是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笔下那个老船夫的活化身。然而涉猎一下《太后与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做作。巴恪思出身贵族,二十多岁时离开英国到中国,他的语言天赋显然为他打开了美轮美奂的成功之门。
巴恪思宣称第一次见到慈禧是在1902年秋,当时他想转达的一个愿望就是归还紫禁城被掠夺的一些艺术品。起初的交往彬彬有礼,慈禧特别感兴趣的是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君主和寡妇,刚刚驾崩的维多利亚女王(1826-1901)。显然都是在探询世界上有关女王们的逸事,她打问寡居的英国女王和其信赖的苏格兰仆人约翰·布朗到底是啥关系。问他是太监(这个问题很可笑),还是女王的精神恋人,或亦是个面首?巴恪思只能是讲一些老掉牙的逸事,说女王坐马车到爱丁堡旅行时,有人开玩笑喊她的绰号“布朗夫人”。对这样的轻蔑,慈禧说要是她就会血腥的报复。她诚恳的感谢这位外国客人归还爱新觉罗家族的珠宝,这种尊人之道引发了两人对遵守孝道之重要的探讨。慈禧给巴恪思讲到了光绪皇帝的爱妃珍妃的命运。两年前,当朝廷的其他人准备逃往西安时,珍妃被投井杀害。这并非像有些历史学家如作家张戎所臆想的那样,是为了甩掉累赘,怕珍妃难捱长途跋涉,但把她留下来又怕遭洋人侮辱。而是慈禧为了个人恩怨除掉了一个无所事事、图谋与其做对的人。巴恪思在听慈禧太后说话时一直呆若木鸡,用他的话说“就好像一只被眼镜蛇吓呆的兔子。”(见《太后与我》第39页)他窘迫不安到了极点,太后看了他一眼然后问道:“你是外人。你说,哀家是对是错?宫里的规矩,有妃子犯上不敬,罪及至诛。”话到此足矣。
不知何故,两年过去了,巴恪思才接到了觐见诏书。他知道慈禧太后不点检的名声,故在他看来慈禧的召见就是在诱惑他。他刚一到慈禧的住处,李莲英就开始在他的身上涂香膏,然后再让他服了一剂春药。除了威严依旧,慈禧脱了衣服,也放下了让人生威的面具。书中的描述如下:
太后的寝宫点着十几盏灯笼;宽敞的大殿排着两列镜子,令我想到凡尔赛宫的镜厅。镜中反射出相貌平平的我,因兴奋而满脸通红,渴求一见。李引我至凤椅之前,太后唤道:“霜重衾冷,盼一解寂寞。”李道:“跪在垫上,让太后好好抚慰一番。”“胡说,”太后道,“他跪着怎么好为所欲为!让他脱干净了,我愿饱眼福。”李告退,只留太后和我二人。她披着一件湖绉轻袍,前身洞开……屋内放着几架电扇,还以精致的景泰蓝小橱储了冰块,清凉无比。我就不用担心汗如雨下,亵渎了她。我此刻就像身处干燥的沙漠,欲念焚心——为什么?为了这个正等待我的六十九岁的妇人,还是因为她是一个象征,是我心爱之人的替身?
“不要想着我是太后,把我当杨贵妃,你就是那多情天子唐明皇。”
“我又怎敢,老佛爷?对我而言,您是大慈大悲观世音,永远年轻美丽……”
——节选自巴恪思著《太后与我》第70-71页
巴恪思的文风清新轻快,饱含文化韵味,处处显示出其谙熟中国的一切。在写到朦胧的(常常是淫秽)的当地话时,他就会在手稿里给出汉语原文,再配上英文。其用意在于让读者觉得是在读宫廷秘闻,这样的事只有像大使和外交官级别的外国人知晓。比如,他写到太监和世人心目中讨厌的对象不同,不是人们嘲笑的那样有臭味,阴阳怪气。倒是很注重个人卫生,用省下来的钱买最好的香水和香油。李莲英视巴恪思为自己的知己,毫无顾忌地让他看自己皱缩了的“净身宝物”,这东西在他死后会重新缝到他的身上。有的太监透露自己是徒有虚名,大都是混进宫里的正常男人,沉迷于色情和金钱。除了用铁腕统治皇室,慈禧太后蔑视宫廷礼仪,身边猛男如云,但却坦然处之。
巴恪思谙熟多种语言,善于制造八卦,故通常其读者的反应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他是个知晓底细的权威,不知何故被当时的历史资料漏载了;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巴恪思在一篇文字中解释说,他从慈禧太后的心腹中被驱逐是因为自己伸手过长,甚至不经过老佛爷的允许就在紫禁城里胡作非为。他让读者相信,慈禧太后生气嗜血的脾性有所收敛,是因为她一直留恋他的魅力,愿与他同乐。说到底,他书中的老佛爷把色欲和报复把握得很到位。
这一切是否牵强附会得让人难以置信?有评论家注意到,巴恪思的回忆录与古董商和考古学家维克多·谢阁兰 (Victor Segalen)所著的法语小说《勒内·莱斯》颇为相似。谢阁兰的故事说在清末的时候,有位比利时教师好像与年迈的慈禧有染。他的故事比巴恪思的简单,渲染的主要是作者营造颓废情绪的能力。另外,作者说这就是本虚构的小说而已。在我看来,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两本作品的不同之处比其相似之处更显眼。除了模仿《勒内·莱斯》,我更倾向于一种被忽视了的阐述。作为临终前的遗言,我的假设是:巴恪思选择的是彻底满足自己愿望的意淫,而且是身不由己地参考了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的记载。慈禧对猛男的渴望,危险得超越了理智。听来很离奇,有点像司马迁笔下秦始皇不检点的母亲。大清帝国的太后被嫪毐那样的人引入了企图,老佛爷不但有被驯服了的洋鬼子,还有一大群和嫪毐本事相当的太监。早在明朝,就有类似《太后与我》这样的小说了。巴恪思和《金瓶梅》的作者如出一辙,尽力在详述上流阶层嗜好的每一桩风流韵事。他提到的有些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性虐待(他自己最初意识到这一点还要归功于公立中学校长对他过分热情的鞭打),用目前中国最新杜撰的一个词来说就是“第四爱”。
要是我们认为《金瓶梅》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是世情小说,而非简单的色情小说,那二者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巴恪思不敢想象惩罚或摧残自己的放荡伙伴。这位英国入侵者既没有被野蛮地杀害,也没有像西门庆那样暴死于过量的春药。他只是被秘密地放走了,悲泣失去了自己的宫廷之乐。这种缺乏悔过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对贺普利的做法算是一种解释。作为巴恪思作品的遗嘱执行人,他除了写了篇序言介绍《黑暗的往日》和《太后与我》的创作背景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做。
贺普利财产的继承人则完全不同,但其朋友的晚年作品需要有人来审核。人们觉得应该找一个专家来决断出版的这部作品到底是学术性的还是娱乐性的。文稿的交接安排在瑞士的巴塞尔机场,巴恪思的书稿被转到了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手中。特雷弗·罗珀在多个领域都可能是数得上的高手,他只是在1965年随“英中了解协会”访问过一次中国,后来就成了该组织的几位主要推动者之一,该组织的著名人士还有他认为在“冷战”期间带有反西方偏见的李约瑟。虽然如此,但值得一提的是休·特雷弗·罗珀宣称自己的公允任由大家评说。也是在1965年,他评价说:“世界史从其近五百年的意义来看就是欧洲史”。他的这一论断似乎和他世界史学者的声名不符。他对巴恪思手稿的第一反应是不屑一顾地退避,即便是选择通过调研来撰写一本这位汉学家的小传,而不编辑和出版其作品后,他的不满依旧未减。在名为《北京隐士: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的神秘生活》(该书1976年出版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译者注)一书中,这位历史学家写道:
“呜呼!当说的是,巴恪思的‘回忆录非有益之作……写作风格中的气韵无法弥补其病态的淫秽。但吾辈当仁慈,将所有现象看作是老糊涂的一种病态宣泄,当记住一个性格变态的隐士所承受的心里压力。”
——节选自休·特雷弗·罗珀著《北京隐士》第274页
要是他想在二十一世纪出版《北京隐士》,诸如“病态”和“变态”这样的形容词早就会以超越了政治正确的界限而被删除。
休·特雷弗·罗珀不愿让巴恪思的作品直接面对没有疑心的大众可能有其个人复杂的动机。书中对男女艳情的描述似乎有悖于他性格中的清教徒特性,即反对(如果不是蓄意的)性爱的多样化。他的弟弟帕特里克·特雷弗·罗珀(Patrick Trevor-Roper 1916-2004)是位有名的眼科专家,在“沃尔芬登委员会”于1954年成立,经过调查准备使男子同性恋合法化时,( 沃尔芬登委员会the Wolfenden Committee,英国有关同性恋和卖淫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1954年成立,以议员沃尔芬登为首组成,故名。主要任务是调查同性恋和卖淫行为是否不应再被视为犯罪,并提出法律改革意见——译者注)他是仅有的几位愿意用亲身经历作证的人之一。休· 特雷弗·罗珀对自己的弟弟卷入同性恋权力之争的态度有所不同,当然他的弟弟并非巴恪思那样的好色之徒,但人们都知道当他的弟弟与一位男同伴在伦敦开始同居时,他的反感并不强烈。而更有意义的是,那时休·特雷弗·罗珀已经是英国最著名和言辞被人们引用最广泛的一位历史学家了。在出版的许多学术大作,以及在牛津大学的学术机构活动中他一直保持自己的这种立场。实际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当选为首相后,就认为他是自己学界的最佳智囊人物,他是撒切尔第一个授予终生贵族头衔的人。出版巴恪思那样的色情作品,肯定会使他面临和其观点不同的对手们的抨击。
同时,他心里也拿不准这些资料是否具有权威性。对巴恪思的欺世盗名外界颇有争议。巴恪思曾经与濮兰德(J.O.P. Bland)合作,后来两人闹翻了。他们二人合著的畅销书《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又被译为《慈禧外纪》——译者注)使这位汉学家在有生之年声名鹊起。做为慈禧传记的一部分,该书的第七章是清朝重臣景善的日记。书中的三处重点引起了休·特雷弗·罗珀的怀疑。其一是朝野大事,包括光绪皇帝的驾崩,都与《太后与我》中的描写有出入,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两本都号称为第一手资料的作品的可信度。其二是巴恪思不止一次地篡改景善日记手稿被偶然发现的经过,这让濮兰德觉得巴恪思是个骗子。其三是巴恪思虽然号称“隐士”,但后来却想方设法巴结牛津大学的上层。他曾夸口说要为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赠送上千本中国古典作品,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当然是很珍贵的)被运到了英国。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北京隐士》出版后不到十年,休·特雷弗·罗珀 (当时已是格兰顿·戴克男爵)的声誉遭到了一次重创。在经过草率的鉴定后,他认为六十多本被重新发现的手稿是阿道夫·希特勒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斯图加特的康拉德·卡尧(Konrad Kajau)被捕入狱后,供认他用榔头捶打普通的学生练习册,在封面涂上茶渍伪造了这一切。康拉德·卡尧被判刑,坐了三年半监狱。这刚好相当于他伪造这些作品花费的时间。而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其名声也上到了顶点,国际上的媒体奚落他,并把这改编成了电视剧。
休·特雷弗·罗珀对《太后与我》的高压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一位香港出版商颇有勇气,全文出版了《太后与我》和新版《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厄恩肖书局(Earnshaw Books)圆滑地避开了该书的权威问题,而是从猎奇上推广此书。我朋友从上海给我搞到的这本书是人见人爱。该书和张戎的《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有天壤之别。张戎的书据说是基于作者十五年来对鲜有人问津的档案研究。在张戎看来,慈禧太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勤于朝政,诛杀得当。要不是风流的儿子、几乎神经的侄子和一帮幕僚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性别而中伤和阻挠她,她也许早就成功地把清廷带进了改革的航道。
要是人们觉得巴恪思有关宫廷嗜耄癖的故事比张戎颇有同情心的阐述更有意思,那是否意味着读者肤浅、愚昧和好色呢?我是坚决否认这样看的。慈禧所在的空间独一无二,摄影技术的进步,使她可以把自己标榜为观音菩萨那样的女人,使她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接近现实。她愿意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到虚构的故事中去,实际上也就是同意别人也可以仿效。张戎愤愤不平地认为慈禧一直受人诋毁,但我们应该清楚性别歧视、反清宣传和文学描述是有区别的。我们每个人也许对此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毕竟是慈禧本人的性格以及所作所为,打开了人们从多个方面批评和描述她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