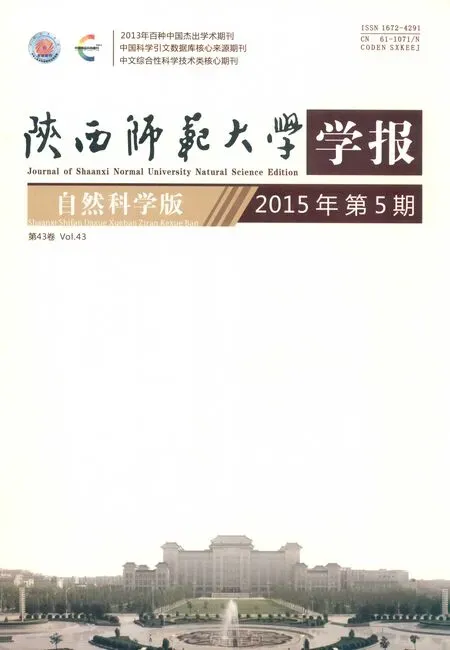1761—1780年极端气候事件影响下的天山北麓移民活动研究
2015-06-05李屹凯
李屹凯,张 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1761—1780年极端气候事件影响下的天山北麓移民活动研究
李屹凯,张 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以1761—1780年新疆天山北麓的移民活动为研究对象,讨论移民政策、移民高潮与移民迁出地极端气候事件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761—1780年间有3次移民高潮,分别发生在1764—1766年、1772—1773年和1777—1780年。1761—1780年,天山北麓的移民政策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1763—1765年、1771年、1775—1778年移民迁出地——河西走廊发生了3次极端干旱事件,揭示1761—1780年的3次移民高潮受极端干旱事件的驱动,且移民高潮的出现滞后迁出地极端干旱事件1~2年。第3次干旱推动了第3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使得当时的清政府于1780年转变了移民政策。1775—1780年河西走廊极端干旱事件—天山北麓移民高潮—政府移民政策转变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成的气候变化-社会响应链条。
极端气候事件;天山北麓;移民;政策转变;河西走廊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气候变化是重要的自然背景[1-2]。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作用关系复杂,因气候变化而致的资源和灾害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最终作用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及其所采取的响应行为[3]。历史时期曾发生多次规模或大或小的移民活动,人口迁移成为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调节机制[4]。
以过去气候变化为视角,研究者对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活动已有很多讨论。从宏观层面探讨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活动的关系有:许靖华[5]通过检视全球过去一系列不同气候背景下的人类活动,认为历史时期发生的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异常气候变化造成的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引起。Pei与Zhang[6]则通过定量计算的方式,认为降水的变化导致历史时期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迁移。也有关注微观层面上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活动的关系,其中Fang等[7-9]以过去华北向东北的移民活动为例,讨论人类活动对过去气候变化的响应,认为17世纪中期的东北移民与垦殖是社会层面上对华北灾害的异地响应,其后政府的封禁政策是对大量移民的政策响应[7]。而18、19世纪之交的气候变冷,迫使华北地区的移民再次进入东北,且政府在解决问题上的无力和相关政策上的摇摆,导致社会动荡,也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水平[8]。Xiao等[9]认为社会因素和旱涝事件共同影响了1644—1911年华北人口向东北的迁移。由此可见,旱、涝等极端气候事件对华北移民活动的影响明显[7-9],而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案例进行分析,能够深入认识过去气候变化与移民活动之间的作用关系[3]。
有清一代(1644—1911年),不仅东部地区有向东北的移民潮,在西北地区也同样存在人口迁移[10]。其中18世纪中期从甘肃迁往新疆的移民,促进了新疆的区域开发,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1119]。移民活动的大致过程为:1761年起清政府为安置甘肃无业的贫民和充实新近收复的新疆,决定从河西走廊组织招募大批移民前往新疆开展民屯,这部分移民主要安置在天山北麓;为顺利实施移民,清政府给予各项优惠条件,如提供移民经费和生产资料;1780年清政府转变移民政策,停止组织招募,不再资助移民,移民开始自行前往[11-19],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发生在1761—1780年的移民活动。
关于引发移民活动的社会因素,研究者已有深入的讨论。有研究者认为,经济利益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华立[12]认为,移民愿意迁往天山北麓的原因是其地连年的丰收;Millward[15]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经济的原因引来移民,其中以商民最为明显。此外,有研究者注意到在移民活动中河西走廊的“推力”,张丕远[16]认为生计无着的内地贫民和灾民是在清政府优厚条件的吸引下,踊跃迁往新疆的;阚耀平[17]认为甘肃人地矛盾是移民的原因;贾建飞[18]认为迁出地不利的自然环境迫使内地人离开,迁往边疆地区。可以看出,研究者已经关注到迁入地有利经济因素的吸引和迁出地不利因素的推动。最近,刘超建[19]讨论了1761—1780年天山北麓移民活动的灾害背景,半定量地描述了灾害对移民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1761—1780年河西走廊移民天山北麓的活动中,清政府移民政策支持、天山北麓连年丰收和河西走廊极端气候事件等都是引发移民活动的重要因素。
同样,研究者也关注了1780年清政府移民政策转变的原因。华立[12]认为,自1761年在政策支持下开展的移民活动,经过20年的发展,在1780年之前已经颇具规模,所以清政府的移民政策发生转变,不再给予资助。路伟东[13]认为新疆农区已经形成、资助移民花费巨大和移民数量已成规模是使清政府结束资助的3个重要原因。已有研究表明,招募移民后期,移民数量众多、巨大的财政投入使得清政府转变移民政策。
综上所述,天山北麓1761—1780年的移民活动研究大多从社会层面进行,较少从自然层面入手。本文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时的气候背景,关注气候变化和移民活动的相互作用过程,尝试定量地分析1761—1780年河西走廊向天山北麓的移民活动过程中,气候变化-移民活动-政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作用的过程。
1 数据与方法
由于存世历史文献的限制,目前很难找到1761—1780年迁出地移民数量的系统记载,仅能根据移民迁入地相对系统的移民数量统计,来重建1761—1780年间的移民数量。至于极端气候事件的统计,已有的研究表明,1761—1780年甘肃受灾726次[20],其中干旱367次、洪涝97次,这说明旱、涝是甘肃较为频繁的灾害。河西走廊生态脆弱,极端气候事件在过去2 000年影响巨大,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为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是干旱[21],所以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统计分为干旱和洪涝。
1.1 天山北麓移民数量统计
张丕远[11]、王希隆[14]、华立[12]等已经重建1761—1780年清政府组织前往天山北麓的移民数量变化。结合本文的研究特点,在前人基础上,需重建系统而合理的移民数量变化指标。
1761—1780年进入天山北麓的移民众多,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民户、商户、兵屯眷户、安插户和遣户。不同类型的人口统计途径不同,其中民户是1761—1780年政府组织移民的主要对象,其数量也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历史文献中,保留了较为系统而完整的记录[22]。此外,政府招募迁移户民的迁出地比较一致。需要说明的是,不少商户、安插户又与内地招募的民户有相同或接近的迁出地,且文献记载零星。所以本文所有涉及的非民户,在文献记载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将会视为民户的一部分。
另外,需要注意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1761—1780年,清政府在招募移民时,一致认为移民天山北麓“事关充实户口”,担心单身前往者没有任何牵挂,有可能只是为了贪图一时利益,很难保证能够在新疆长久定居,精心耕作,迁移单身者不利于长治久安,因此,力主“就近招有携带眷属之人”[23]。也就是说,此次移民活动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文献中关于移民的统计基本以“户”为单位,本文同样遵照文献记录,不将其换算为人口数量。因此,本文以尝试重建民户移民户数的变化,来反映气候变化-移民活动-政策三者之间移民活动的波动变化。
为准确了解招募移民期间(1761—1780年)移民户数的变化,本文补充查阅了相关历史文献[2326],重建了1761—1780年迁入天山北麓移民迁入户数数量的逐年变化(见图1a)。
1.2 河西走廊极端气候事件统计
文献[27-28]对1761—1780年河西走廊的旱涝状况有所涉及。本文利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29]和《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甘肃卷》[30],选择其中隶属于河西走廊、可以明显分辨出旱涝状况的相关记载,重建1761—1780年河西走廊的旱涝序列(见图1b)。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河西走廊包含安西州、甘州府、凉州府和肃州,按照清代的行政区划,其下尚有多个县、厅,还有次县级的分县[31],文献中提到的移民迁出地众多,共计有13个地点,其中有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张掖、山丹、玉门、敦煌、高台10县,抚彝和庄浪2厅以及东乐分县,文中对以上府州县厅及分县的旱涝灾害均进行统计分析。

图1 1761—1780年天山北麓移民迁入数量(a)和河西走廊旱涝序列(b)Fig.1 The number of immigration to the North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number(a)and the series of drought and flood in the Hexi Corridor(b)from1761 to 1780
1.3 气候变化-移民活动-政策之间的互动分析
本文在重建1761—1780年移民数量和极端气候事件数据的基础上,采取对比分析方法,将极端气候事件与移民迁移数量进行比较,分析招募政策下,不同移民数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及其移民政策的转变,探讨气候变化-移民活动-政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作用过程。
2 结果分析
2.1 移民数量变化特征
由图1a可知,1761—1780年共计迁入19 294户,接近于1782年乌鲁木齐都统明亮所奏报1762—1781年安置的“民户一万九千七百余户”[24]。这说明本文基本准确重建了1761—1780年户民移民的总体数量。在招募组织移民期间(1761—1780年),明显存在着3次相对的移民迁入高潮时期(图1a所示阴影),即1764—1766年、1772—1773年和1777—1780年,其他时段是相对的移民低潮时期。移民高潮中以第3次迁入数量最多,占到全部迁入户数的41.04%;其次是第1次移民高潮,迁入数量约占全部迁入户数的22.32%;最后是第2次移民高潮,约占全部数量的10.52%;其他年份每年的移民基本保持400或500户左右。就移民数量最多的第3次移民高潮而言,贾建飞[18]的研究也表明1777—1780年人口增长率较高,数量近乎翻了一番,与本文的研究基本一致。
2.2 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特征
图1b反映出1761—1780年河西走廊存在着3次灾害频发阶段(图1b所示线框),即1763—1765年、1771年和1775—1779年。其中3次大规模的干旱分别在1763—1765年、1771年、1775—1778年3个时间段;洪涝则相对较少,集中发生于1771年和1779年。
2.3 极端气候事件与移民高潮的相关分析
极端气候事件会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引发粮食减产,受灾贫民衣食无靠,且流离失所。如1765年,“经春不雨,麦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种,旬日来街市米价暴贵,群情忧惶”[32],可见干旱造成粮价暴涨,粮食安全受到影响[33]。这对清政府压力巨大,故将河西走廊灾民移往天山北麓便成为解决灾民生存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从1761年实施人口迁移活动起,清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对招募、转送、安置移民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十分强调移民的“自愿应募”前往、出资将移民从河西走廊转运到天山北麓、借给移民籽种、代建房屋进行安置、划拨土地等[12]。基于解决内地“无业贫民”生存难题的移民目标,自1761年开始招募移民,清政府就有着积极的愿望,认为“必生齿日繁,田土日辟,而腹地无业贫民亦必闻风接踵前往”[23]。但1761—1763年,年均只有274户迁往天山北麓,而在1764年迎来了一个高潮,说明招募移民最初并没有得到河西走廊贫民的响应。
与图1b所揭示的3次极端气候事件相对应,清政府都有相关的将河西走廊受灾贫民迁往天山北麓的计划与方案。第1次干旱期间(1763—1765年)的1764年8月28日,乾隆帝根据陕甘总督杨应琚的奏报,针对受灾的地方,下旨要求赈恤,同时认为灾民生活拮据,而近来天山北麓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足,将灾民迁往天山北麓可以缓解内地赈灾压力,也可以充实边地[34]。第2次干旱的1771年7月23日,面对甘肃“灾民流移甚多”,乾隆帝同样下旨,要求地方官员积极组织移民,因为受灾面积广大,让灾民自力更生困难,而天山北麓一带,水利和土地资源充足,如果灾民勤加耕作,不但可以糊口,还将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34]。在第3次干旱期间(1775—1778年)的1776年7月27日,所颁布的圣旨与前两次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即“乌噜木齐(乌鲁木齐)一带,地皆沃壤,可耕之土甚多,贫民果能往彼垦艺,不但可免于饥窘,并可赡及身家”[34],均强调移民天山北麓是解决甘肃河西走廊受灾贫民生存的有效措施。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乾隆帝认为“且此时多送一人往外耕作,将来边内少一人待赈之人”[24]。这亦与最初商定迁移甘肃贫民前往天山北麓,解决生存难题的目的一致。由于极端旱灾气候事件的发生,河西走廊贫民(灾民)的数量大增,形成了移民迁出的有力推动。可见,1777—1780年天山北麓移民高潮的出现是受1775—1779年河西走廊连年干旱的推动。
据1761年杨应琚所奏,为了“料理省便”,移民招募的来源地是河西走廊,此后多年也是按照这个方案实行,但是到了后期,也出现了河东移民[12]。根据相关记载,第3次移民高潮期间河东的极端气候事件也普遍存在[35],说明河东移民的出现也是对灾害的响应,如1780年5月28日“平番、中卫、静宁等州县愿往民户一百三十一户,俱系无业贫民,恳请携眷前往种地”[23]。可见,1777—1780年甘肃的干旱时间较长,干旱发生的地域范围较广,河东灾民亦加入移民的队伍,共同推动了第3次移民高潮的形成,这也是第3次移民高潮的规模大于前两次的原因。由此可见,在移民政策的支持下,天山北麓良好农业气候条件的吸引,河西走廊移民不断迁移到天山北麓,而3次移民高潮(1764—1766年、1772—1773年和1777—1780年)则是在迁出地极端干旱事件的驱动下出现的。
综合以上社会背景,结合图1a和1b所示可以发现,1763—1765年3次移民高潮出现的时间恰好对应于3次灾害频发期,但同时存在着明显的滞后现象,即存在响应的时滞性[7]。这是因为移民从河西走廊迁出,到达天山北麓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12]。前两次灾害发生后的1年即是移民高潮,而第3次移民高潮发生在第3次灾害发生后的第2年;而且灾害结束后1年,移民高潮也随之结束;另外,只有少量迁入的移民低潮年份对应的就是灾害低发的时段。由此可见,天山北麓移民数量的增加就是对河西走廊极端气候事件的异地响应,即移民活动是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响应。
2.4 极端气候事件-移民高潮-政策转变
在1781年清政府不再资助移民出关前,移民政策基本没有大的变化[36],也没有增加移民资助额度,甚至在后期减少了移民资助额度,最初资送每户移民平均拨银90两,在1777年将资送费用减半,每户约为50~60两,1780年之后,再次将资送费用减半[36]。结合前文对天山北麓移民户数复原结果进行分析,移民资费的不断下降,并没有影响第2次(1772—1773年)和第3次(1777—1780年)移民高潮的出现。
在1777—1780年河西走廊极端干旱事件的影响下,天山北麓第3次移民高潮的规模远远大于前两次。第3次移民高潮(1777—1780年)的最后1年,清政府不再资助移民,招募移民的工作便停止。大规模的移民高潮让清政府以为达到了移民会“闻风接踵前往”的原计划,1780年5月28日陕甘总督勒尔谨奏“镇番县、平番、中卫、静宁等州县民户呈请愿往新疆垦种……查乾隆四十二、三(1777年、1778年)等携眷前往贫民俱赏给一半盘费……即或念该民户等口食无资,亦止应照给一半之数再减一半赏给,已属格外优恤。至将来四五年后,此等闻风愿望民户日多,即此再行减半之数亦无庸给发……山东、直隶等处贫民各携眷属出口种地者谋生者甚多,俱系自行前往,又何尝给与盘费耶?”[24]。可见,清政府认为不再给予资助,移民也会自行前往,而且组织移民无疑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1780年以后,清政府不再组织、资助移民迁往天山北麓。
正是第3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促使政府改变了移民政策,天山北麓的移民以政策性移民为主转变为自发性移民为主。当然,同期的财政压力也很明显[20],社会背景也不容忽视。可以说,移民政策的转变是对河西走廊1775—1778年极端干旱气候事件的间接响应,而政策的转变滞后于移民高潮,也滞后于极端气候事件。1775—1779年河西走廊的极端干旱气候事件-天山北麓的移民高潮-政府的移民政策转变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驱动-响应链条。
3 讨论与结论
在移民政策执行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内地贫民或灾民的生存问题,1761—1780年这20年间,清政府从甘肃河西走廊招募为数不少的移民充实新疆天山北麓。实际每年移民数量并不是很均匀,且存在着明显的3次移民高潮时期,即1764—1766年、1772—1773年和1777—1780年,其中尤以第3次移民数量所占比例最大。通过对移民产生条件的探讨,分析移民高潮的出现原因,认为移民高潮与灾害的频发存在着响应关系,存在3次频繁出现的极端气候事件——旱涝灾害,即1763—1765年、1771年、1775—1778年,尤以干旱为主。进一步分析认识到,3次灾害是3次移民高潮的诱发条件。1761—1780年清政府的政策、天山北麓的丰收和河西走廊的极端气候事件共同驱动着移民活动的进行,而移民高潮期主要是在极端干旱事件的驱动下出现的。
旱、涝灾害的出现降低土地生产力的效用,进而影响农业的收成。移民迁往天山北麓有效地解决了河西走廊地区因灾无靠贫民的生存问题,缓解了清政府赈灾的压力。第3次移民高潮期间河东贫民的出现,壮大了移民的规模。地方官员为缓解财政压力,减轻清政府的负担,决定转变移民政策,减少移民“盘费”。同时,清政府认为即使不再资助河西走廊民户,他们也将自行前往天山北麓。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之后出现了移民政策的调整,1780年之后,清政府不再给予资助,移民数量逐渐减少,自此只有少量移民进入天山北麓。可以说,移民高潮的出现是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同时存在着1或2年的滞后;1761—1780年甘肃到天山北麓的移民高潮响应滞后于气候变化1~2年,而政策响应滞后于移民高潮。
本文论述了移民活动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响应,但仍不可忽视政府移民政策和天山北麓连年丰收对于移民活动的作用。在1761—1780年的移民政策鼓励下,河西走廊移民不断迁移到天山北麓,政策对移民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贾建飞[18]研究表明,1777—1783年天山北麓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1.45%,而在移民资助政策终止之后,1783—1793年的年均增长率仅2.54%,以后渐趋于平稳。天山北麓连年丰收也是推动移民的重要因素,利用树轮重建的PDSI显示18世纪40—80年代,天山北麓处在一个较为湿润多雨的阶段[37]。此背景下,天山北麓自“开辟以来,田地多系膏腴,渠流足资灌溉”[24],“岁获丰稔”[24],移民的农业开发顺利进行[12]。同其他过去气候变化影响下的人类活动一样[34,33],1761—1780年的移民活动正是在自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1780年移民政策的转变,也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移民数量增多和同期财政压力双重作用下发生的。
[1]Zhang P Z,Cheng H,Edwards R L,et al.A test of climate,sun and culture relationships from an 1810-year Chinese cave record[J].Science,2008,322:940-942.
[2]Büntgen U,Tegel W,Nicolussi K,et al.2500years of European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human susceptibility[J].Science,2011,331:578-582.
[3]葛全胜,郑景云,郝志新,等.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新进展[J].地理学报,2014,69(9):1248-1258.
[4]葛全胜,刘浩龙,郑景云,等.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J].自然杂志,2013,35(1):9-21.
[5]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1998,28(4):366-384.
[6]Pei Q,Zhang D D.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nomadic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China[J].Ecology and Society,2014,19(2):68.
[7]Fang X Q,Ye Y,Zeng Z Z.Extreme climate events,migration for cultivation and policies:A case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f China[J].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Earth Sciences,2007,50(3):411-421.
[8]Fang X Q,Xiao L B,Wei Z D.Social impacts of the climatic shif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J].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2013,56(6):1044-1058.
[9]Xiao L B,Fang X Q,Zhang Y J,et al.Multi-stage evolution of social response to flood/drought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during 1644-1911[J].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4,14(2):583-595.
[10]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1]张丕远.清朝乾隆时代新疆屯垦统计数据的探讨[J].历史地理,1998,14:155-157.
[12]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M].修订版.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3]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14]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15]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1759-1864[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6]张丕远.乾隆在新疆实施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J].历史地理,1990,9:93-113.
[17]阚耀平.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3,26(4):379-384.
[18]贾建飞.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9]刘超建.异地互动:自然灾害驱动下的移民:以1761—1781年天山北路东部与河西地区为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28(4):58-66.
[20]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21]郑景云,郝志新,方修琦,等.中国过去2000年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若干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1):3-12.
[22]路伟东.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23(4):81-90.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徙民屯垦新疆史料[J].历史档案,2002(3):9-31.
[2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5]和宁.三州辑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6]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27]郁科科,赵景波,罗大成.河西明清时期旱灾与干旱气候事件初步研究[J].干旱区研究,2011,28(2):288-293.
[28]董惟妙,安成邦,赵永涛,等.文献记录的河西地区小冰期旱涝变化及其机制探讨[J].干旱区地理,2012,35(6):946-951.
[29]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30]董安祥.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甘肃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
[31]胡恒.清代甘肃分征佐贰与州县分辖[J].史学月刊,2013(6):57-65.
[32]慕寿祺.甘青宁史略[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33]方修琦,郑景云,葛全胜.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的过程与机理[J].地理科学,2014,34(11):1291-1298.
[34]中华书局.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升允,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36]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J].西北史地,1987(4):119-131.
[37]Li J B,Gou X H,Cook E,et al.Tree-ring based drought reconstruction for the central Tien Shan area in northwest China[J].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2006,33:L07715.DOI:10.1029/2006gl025803.
〔责任编辑 程琴娟〕
Study of migration into the North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from1761 to 1780
LI Yikai,ZHANG Li*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China)
Considering the immigration from the Hexi Corridor into the North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during 1761—1780,the relationship among migratory policy,the migratory peaks in the North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the extreme climate events in the Hexi Corridor were discussed.There are three migratory peaks which occurred in 1764—1766,1772—1773and 1777—1780.The migratory policy had not changed much during 1761—1780.The three migratory peaks were driven by the extreme drought climate events.There are three drought events occurred in 1763—1765,1771and 1775—1778.Migratory peaks lagged behind of the extreme drought climate events about 1~2years.Among them,the third drought event pushed the last migratory peak,which made the Qing government change migratory policy in 1780.It was formed a complete chain of effects-feedback among the extreme drought climate event in the Hexi Corridor,the migratory peak in the North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the government′s migratory policy changes during 1775—1780.
extreme climate event;the North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migration;policy change;the Hexi Corridor
K928.6
:A
1672-4291(2015)05-0084-06
10.15983/j.cnki.jsnu.2015.05.452
2014-11-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271159)
李屹凯,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环境变迁。E-mail:ek199105@163.com
*通信作者:张莉,女,副研究员,博士。E-mail:zhangli20130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