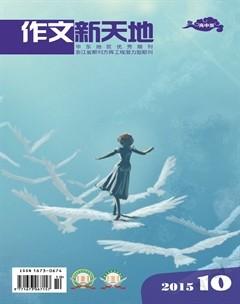一棵树一个家
2015-05-30李晨阳
李晨阳
我家附近,原是一片村庄,有一片老房子,房子是两层的,砖木结构,前面是菜园,后面是房舍。我入住小区已经数年,这片老屋一直存在着,每次路过只是与它照个面,不曾细察,心中却温暖无比。
有一天,蓦然发现这片老屋已经七零八落,只剩孤寂的两三间还在风中飘摇,大有随时倒塌之虞,我这才细细地打量。老屋有点老,不见主人。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摧残,梁柱上积满了岁月的沧桑,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腰杆弯了。
周围,江南民居传统的庭院消失了,只有杂草在疯长着。被推土机推倒的老屋垃圾遍地,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尘埃味。在我满目失落之际,一棵光秃秃的不知名的树吸引了我的目光。细看,树有碗口粗,直直的,树枝散漫地舒展着,在冬日的暮霭中清朗而有诗意。
于是,以后每一次路过,我都要向它行注目礼。我在寒冷的冬天里感受到了春的讯息。早晨,冬阳初升,炫目的光直直射来,枝丫沐浴在金色的世界里,绽放着。我在想,这棵活了数十年的树,当初是谁栽下的?是谁为它浇水,带着怎样的心情,又有多少期许?这些年来,原本住在这片老屋里的一户户居民们,是怎样见证它的稚嫩与成长?
树与房,树与家,两个原本不相干的物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却糅合得水乳交融。
相传,元末战争,经济破坏严重。明初,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下诏迁移山西民众于京、冀、豫、鲁、皖、苏、鄂、秦、陇等十余省,故土难离,无人响应。明政府无计可施,就设了一个骗局,贴出布告说:“不愿迁移者,于某年某月某日到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登记,否则视为同意迁移。”于是,民众成千上万聚集在大槐树下,早已埋伏的大队官兵包围了前来签字登记的人们,并命令“所有人等必须外迁,不得抗命,否则格杀勿论”。霎时间,大槐树下妻离子别,哭声遍野。很多人被迫远离故土,踏上异乡,家乡,成了一个概念,一种传说,最后附丽在大槐树上。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成了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是“家”,是“根”,一个伤心地,因了大槐树,成了海内外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精神故乡。
山西洪洞大槐树,成了故乡的代名词,早已经超越了大槐树本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其实,这种文化的积淀在中国人心里根深蒂固。传统村落里,有几样东西常常是标志性的:庙宇、戏台和大树。庙宇,代表着信仰;戏台,代表着文化;而大树,则见证着这方水土的生机和村庄的历史。有些是有形地表现着,有些则以无形的形式存在着。在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里,也有一棵挺拔的樟树,估计有数百年的历史,三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记得我们小伙伴经常在树下玩耍。夏日,树荫下,凉风习习。冬天,许多的树都枯了,樟树依然枝繁叶茂。春日,嫩芽初上,我们每天观察着叶片的颜色由嫩黄转成青色,再渐成碧绿。秋天到了,樟树的种子掉在地上,我们把它们种在土中,等待着来年长出苗子。我童年的许多欢乐都与这棵樟树相连。后来,听说村民以极低的价格把这棵樟树卖了,我突然感觉到我的故乡变得无根了,只成遥不可及的记忆。
对树的眷恋,其实是一种对故乡的怀念。当我见到这棵不知名的树,我心中莫名地想起山西洪洞大槐树和我故乡的大樟树。我庆幸,这片曾经的老屋还幸存着这棵树。我暗暗地计划着拍下它一年四季的模样。过了不久,城市环境整治,这片废墟围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上写满了红红的宣传语。唯有这棵树高高地昂起头,似乎在向我诉说着这里曾经升起的袅袅炊烟,洒下的欢笑,还有孩子们闹腾的声音……
春天到了,这棵孤零零的树长出了一片片嫩叶。我想,什么时候,我把它拍摄下来,以记录这个春天。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树不见了。越过高高的围墙,我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树,枝叶枯了,树干失色了。刀斧最后带走了这片居民区仅有的记忆。我迷惘了。
当现代化势如破竹,当城镇化成了这个时代的宣言,我看到了一片片挺拔的高楼,一条条华美的大街,一辆辆喷着尾气的汽车,伴之而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村庄消失,还有曾经绵延了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基因的裂变。我心中常常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我站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却发现回不了家,回不到精神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