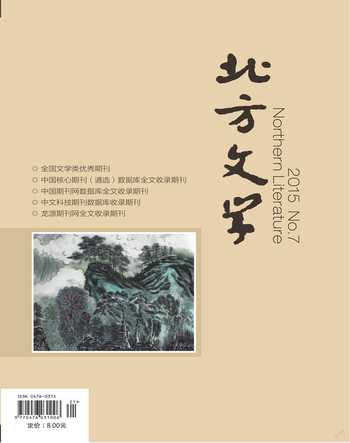他者的想象
2015-05-30米丽娜
米丽娜
摘 要:作为美国主流文学中的一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成名作《喜福会》中描写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异域民俗。这样的描写一方面吸引了美国本土读者猎奇的目光,让小说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另一方面,也由于对中国文化在空间上的疏远以及对中国信息了解的断层和局限,使得作者笔下的民俗描写无意衬托了美国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的价值观,这种书写所蕴藏的中国形象走向了意识形态的倾向。
关键词:喜福会;谭恩美;他者想象;中国形象
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一支蓬勃发展的研究分支,其主要是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以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亦国家的“他形象”(hetero image)和 “自我形象”(auto image)。形象学的重点不是探讨‘形象“的正确与否,而是“形象”的生成,发展和影响;或者说重点在于研究文学或者非文学层面“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发展过程及其缘由。[1]在这段被誉为欧洲比较文学形象学之父的德国学者狄泽林克给出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纲领性勾画中,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范围首先被锁定在了“他形象”即异国形象上。那么什么又是”他形象“呢?法国比较文学领域著名的教授巴柔给出了以下的描述:“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2]而这种总体认识会导致一种有关异国的固定模式,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性表现[3]这种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所构筑的异国形象包含了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4]换言之,异国形象是由某作家由于其特殊的感受和背景所创作的关于他者的形象,而这种形象虽由某位作家创作却不可避免的包含了本国对他者形象的集体想象。
作为美国主流文学中的少数族裔作家,谭恩美收获的成功是巨大的。她的成名作《喜福会》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美国主流读者的热烈追捧。不仅在当年长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更在随后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的巨大荣誉。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作家独特的叙事手法,更得益于书中关于中国的种种异国情调的展示。通过阅读这部小说,美国读者眼前不仅能浮现出有关中国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别样风俗,也能了解到中国人独特的处世之道。总之,《喜福会》为美国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关于中国形象的立体画卷。然而这样立体的中国形象,虽出自于流着中国血统的美籍华裔女作家之手,但其仍是实实在在的他者想象。作为第二代移民,中国这个谭恩美眼中的故国对她而言是作为他者出现的。没有在中国生活成长的经历也没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置身其中的系统了解。谭恩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较少的。谭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事大都来自于其母的口授,作为生活在美国文化历史语境中的个人,谭恩美对中国形象的解读仍然摆脱不了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形象认识的轨迹。
一、《喜福会》中的中国民俗折射出的中国形象
(一)他者的娱乐——麻将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将其从父辈了解到的中国民俗和盘托出,用一幅别样的异域景象牢牢抓住了美国读者的心。故事首先从吴精美接替母亲在喜福会打麻将开始。小说中的麻将不仅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更是中国女性消除内心沉闷的方式。为了分散思绪也为了将自己从这种战时苦闷的心境中抽离出去。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精美母亲生出了组织喜福会邀人打麻将的想法。母亲精心挑选了志同道合的牌搭子,每个星期她们轮流坐东,东家则需要准备一些讨口彩的食品比如烧饼,长寿面,落花生和橘子等。通常打了八圈后,大家会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然后便谈天说地。这种嘻嘻哈哈的聚会遭到了人们的非议,母亲的行为被看作是麻木不仁,中了邪。然而,对母亲这样柔软的战时女性来说为数不多的选择只能是与其痛苦清醒的熬过每一天不如开心热闹地忘掉苦难。麻将就这样成了柔软女性困难时的寄托。从中国来到美国后,物质生活的提升没能排解母亲精神上的苦闷感。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鸿沟和移民的身份都让母亲们成了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精神上的孤立感让精美母亲想起了喜福会的传统,而麻将则成了苦闷母亲们寻求精神寄托的最佳途径。在喜福会里中国母亲们可以随意地用自己的母语拉家常说闲话,喜福会成了她们在异国他乡找回自我的场所。可是这个在母亲们精神世界中如此重要的娱乐方式,女儿却没有同样的认同。喜福会和麻将在女儿眼里是以他者的身份出现的。对精美来说喜福会是一个类似美国三K党的中国人的秘密集会,或者是一个展示中国人陈规陋俗的社团。而这或许也是众多美国主流读者对这两个具有浓厚中国色彩的词汇最初的理解。可以说正是麻将的奇异性让这种传统的中国民俗成功地博得了美国主流读者猎奇心态的关注。
(二)他者的饮食
不同的文化滋生不同的饮食习惯,而不同的饮食习惯又成了展示不同文化的一扇窗口。中国相异于美国的饮食文化在小说中也有浓墨重彩的描写。说到中国最特别的饮食传统,大多数美国人恐怕都能随口说出中国人吃饭不用刀和叉而用筷子。这两根小小的棍子让很多用贯刀叉的西方人窘迫不堪。《喜福会》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描写:美国女婿里奇拜见中国丈母娘时坚持用象牙筷,“当他笨拙地夹起一块浓油赤酱的茄子往嘴里送时,这块汁水浓浓的可口之物,竟滑落到他两腿的岔开处。”[5]这样滑稽的情景一定会让吃过中国菜的美国读者产生共鸣。除了饮食工具的不同,中国菜常常用油炒的方式烹饪。这一点也与吃汉堡的美国人完全不同,在精美接替母亲参加喜福会的故事里,谭恩美借精美之口这样写道“许家的公寓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原先香气怡人的气味渐渐沉积成重重的油气”[6]这短短的几行字或许让美国读者生出中国人的厨房都是油污笼罩油气冲天的联想。
《喜福会》中有一个集中展示中国传统饮食的场所——唐人街。作为美国排华政策的产物,唐人街就像一个自我封闭的华人社会。这个中国文化的迁徙地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中国风俗和文化。美国民众对唐人街并不陌生。它是充满异域风情的华人聚居区,更是许多白人作家灵感和素材的来源。他们笔下的唐人街大都是一个神秘,肮脏,充满罪恶交易的地方。而鸦片,娼妓,暴力等贬义词也成了述说唐人街的传统套话。落后,阴暗,罪恶组成大多数美国人对华人聚居区的集体想象。小说中薇弗莱·龚一家住的唐人街的拐角处,有一家叫“宏新”的小餐馆。由于地处偏僻阴暗之地。薇弗莱·龚这样的小孩都相信这是一个强盗出没的地方,一个旅游者不会光顾的地方。由此可见为了照顾主流读者的阅读期待,谭恩美还是以隐含的方式呼应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唐人街的集体想象——一个强盗出没的地方。但是毕竟与华人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谭恩美对唐人街的描写却并没有过多地延续同样的套话。在她的笔下唐人街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美食街。小说中薇弗莱·龚一家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他们的公寓下有一家传统的中国年糕店,而在晨曦尚未散尽时街上的中餐馆常常会飘出甜烂的煮豆沙香和油氽麻球以及咖哩鸡饺的香味。一次,一个高加索旅游者来到了“宏新”餐馆的橱窗前要求薇弗莱和同伴在以浓油重酱的烤鸭为背景的橱窗前摆姿势拍照,之后,更是向薇弗莱询问店中有什么菜,薇弗莱就大声数说着:“猪内脏、鸭脚掌,还有章鱼肫……”[7]。中国人食用动物内脏的传闻在这里得到了印证。那些不可能进入美国人食谱的动物内脏竟是中国餐馆的招牌菜。虽然谭恩美笔下的唐人街少了罪恶和肮脏,但是与白人作家一样,谭恩美所写到的唐人街也因为饮食的奇和异成了美国社会名副其实的他者,《喜福会》就像一本散发着异族风情的中国饮食百科全书,一方面用奇和异的夺目光芒吸引了美国读者的目光,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奇和异巩固了有关中国形象的异质性。中国的饮食尽管丰富,尽管独特却在主流文化的衬托下始终摆脱不了他者的地位。
(三)他者的节日
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所描写的中国传统民俗都突出了奇和异的特点。这显然是为了迎合主流读者猎奇的心态。另一方面由于和中国文化的空间疏远,谭恩美对中国文化常常是一知半解。谭恩美有关中国形象的描述大都来自母亲的叙述。缺乏亲身的体验,这样的二手资料常常是脱离现实语境的。《喜福会》中节日这种民俗文化的描写正是如此。位于大洋彼岸的古老中国没有美国人庆祝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却有自己独特的民俗节日。为了突出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在母亲们命运多舛的中国生活中,作者提到了许多中国传统的节日。龚琳达是在清明节这个中国人纪念先祖的日子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行为。映映.圣克莱尔是在中秋节这个中国人举家团圆的节日因为溺水而对这个节日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总之《喜福会》就像一个介绍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窗口。向这个窗口望去,美国读者窥见了一些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奇异风俗。对个体生命而言,结婚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节日。婚姻是神圣而令人向往的。对女性尤为如此。然而小说中的婚姻在母亲们的眼里常常是苦难的代名词。《喜福会》中,美国读者读到的中国婚姻并非是两情相悦水到渠成。而是由媒人牵线,靠推算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和五行然后由双方父母决定的,龚琳达的婚姻就是如此。在媒人提亲的时候,龚琳达只有两岁。而她将来的丈夫还要小她一岁。小说后来对婚礼的描写让美国读者看到了一个与他们婚礼完全不同的婚俗。与纯白的婚纱不同,中国新娘出嫁穿的是红色的裙子。不仅如此,头上还会蒙上大红绣花绸巾。这种异国情调的描写深深吸引了结婚风俗完全不同的美国读者。但是同样的词汇场也不难让美国读者产生这样的语义反射即:传统的中国文化对女性存在着很深的压迫。中国的女性没有决定自己幸福的权利。婚姻不是自我个性意愿的表达。而是父母的媒妁之言。这种勾勒从反面烘托了美国平等,自由的主流核心价值观。谭恩美选择这样的素材在笔者看来并非是要刻意丑化中国形象。而是由她独特的华裔身份造成的。母亲的存在是作者和中国文化相联系的主要原因。和小说中的母亲们一样,谭恩美的母亲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移居美国的。对中国的记忆被永远定格在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维度。她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因此显得古老而落后。所以谭恩美试图重塑的中国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强化了相异的特质。
二、结语
《喜福会》中大量中国民俗的描写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由于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民俗文化始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异质性和他者身份。又由于作家对中国信息了解的断层和局限,作者笔下的民俗描写无意衬托了美国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的价值观,这种书写所蕴藏的中国形象走向了意识形态的倾向。异国形象自上世纪在法国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研究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文化命题。由于这些书写者接触中国文化的方式以及其文化身份的不同造成了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免不了以他者的眼光折射出集体想象。谭恩美亦如此。作为在美国出生和生长且对中国故国的生活没有实际记忆和感受的华裔作家,她笔下的中国大多来自于父辈的记忆和传授,为了迎合美国主流读者的期待视野和猎奇心态,她笔下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就像一面镜子反映来其对故国和宿主国复杂的文化心态。
参考文献:
[1]泽林克著,方维规译.比较文学形象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7,03:153.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
[3][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
[4][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5.
[5][美]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62.
[6][美]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
[7][美]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