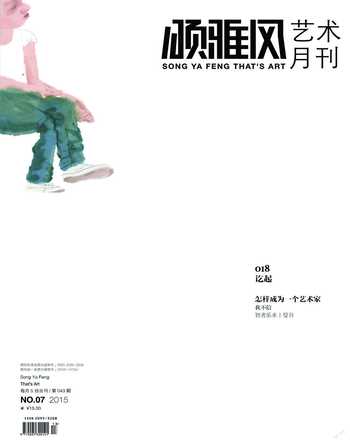纪念碑
2015-05-30杨亮

我创作中的主要材料——木屑,基本上是在木雕创作的过程中所摈弃的。我通过粘合的方式,继续创作,赋予了其新的形式和生命力,同时也为传统的木雕艺术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杨亮
杨亮
1986年 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2007年 中央美术学院
2008年 进入雕塑系第三工作室
2012年 被推免攻读硕士学位,从师于凡教授
研究方向为古代传统与当代雕塑研究
采访时间/ 6月15日
采访形式/邮件采访
你是如何理解“讫起”这个主题的?
刚开始看到还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讫”是结束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一些。我的理解就是结束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同时每个新的开始也要面临最终的归宿。我本人还是挺喜欢这个词的,虽然是两个点,但是这两点画出了一个圆,周而复始。
为何会选用木雕过程中的会被丢掉的木屑作为创作材料?
这个跟我的生活背景是有关系的,我来自农村,生活贫苦、拮据,知道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拥有,要节俭。我在大五的时候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不断地创造、生产,与此同时无形的制造出很多垃圾,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些所谓的艺术家思考和反思的。我经常看到这些木屑,我就觉得它们是可以用来做些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我的实验。
要毕业了,在结束学业,身份马上要转换为艺术家的时刻,你的状态是怎样的?
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已经毕业了,只是肉体上在美院又待了3年。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做过一些优秀艺术家的助手,也算见识了一些世面,这经历使我成长了许多,也打消了我之前面对艺术时的徘徊和不安,现在心更安定了。毕业了,应该说是我的肉身也解放了,开启我新的旅程。
自述中你谈到了身份的问题,你是如何理解艺术家这个身份的?
艺术家,起初是没有这个称呼的,达·芬奇他们也只不过是“巨匠”而已,后来随着个人意识的加强,慢慢地形成了个人的体系,从匠人的体系之中独立出来,艺术家的这个社会身份也就诞生了。
我认为艺术家跟医生、科学家、哲学家等等这些“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并且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我认为在不同领域做出相应的贡献和业绩的,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家。
是否会坚定地走艺术创作这条路?
我不喜欢“坚定”这个词,我觉得我的艺术创作不是坚定,它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它就是我生活的营养,让我活得充实、有意义。
如何看待毕业创作对你个人的意义?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我的作品被别人称之为毕业作品,我只是在毕业的时候展示了它们,从2013年我就开始做这一系列的作品了,这几年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使我很愉快,也很充实。我也不是专门为毕业而创作的,我在积蓄一些作品,是为之后的个人展览所准备,此次毕业展只展出了我作品中的小部分而已,我一直都在不断地思考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