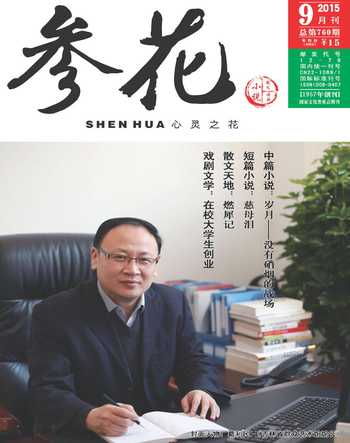浅析唐代诗歌意境的空间意识
2015-05-30张俊丽
张俊丽
诗歌意境与空间感互相交织,“意境是人们阅读诗词作品过程中在脑海里产生的整体美感,具有多维的空间感的描写, 方能构成诗词的意境。”[1]意境的产生以空间建构为主要基础。诗歌意境中的空间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移远就近,由近知远
中国的传统诗歌、绘画、书法、园林等艺术在审美诉求的某些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苏轼论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一斑。而网罗山川大地于门户,吸引无穷时空于自我的“移远就近,由近知远”则是中华民族最具有特色的审美观照方式。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提出“三远”说,其云:“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缥缥缈缈。”[2]107画家观察欣赏的视角不断变换,“目光自下而上,自前而后,自近而远地移动,试图展示画面空间的‘极人目之所旷望也”[2]15。
可见画家画山水,并非如常人站在平地上一个固定的地点,仰首看山,而是用心灵之眼,用流动的视点来欣赏上下四方,一目千里,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观照山山水水。笼罩全景,把全部景象组织成一幅气韵生动、有节奏的、和谐的画面。这是中国画里的空间意识,唐代诗歌意境里的空间意识亦与此相通。例如:“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杜甫)、“江山扶绣户,日月近雕梁”(杜甫)。
《中庸》上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3]诗人用流转的眼光绸缪于身所盘桓的形形色色,以“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游心太玄”。他们用心灵的俯仰的眼光来看空间万象,天人合一,容万物于心中,写出万物皆备于我的光明俊伟气象。凄凄檐角,摇摇珠帘,读者的目光也随诗人在渺远山亭,或林间小径,或扁舟一片中徘徊,在这一片阔大广远的自然山水间愈走愈远。心灵由近至远,由远消失于无限,由近走远,走到心灵最深的宁静,达到心灵虚无的极点,晋人主张艺术境界要“锤神”,广阔的天地,飘远的空间正好颐养了诗家的性情,也提供了观者存养心灵的场所”。
二、间隔化
“隔”是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隔”有这样的论述: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埘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4]63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阏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4]65
王国维先生并没有对“隔”的概念做抽象的理论概括,但从他所举诗句、词句,诗人、词人的例证中可以看出,“隔”与“不隔”主要区别在于语言是否自然。但我们这里所说的“间隔化”的“隔”却与王国维先生的“隔”略有不同,主要是指“阻挠”“障碍”等以及由此诱发的特殊的审美感受。
宗白华先生在谈艺术的空灵时指出,“隔”是构成审美的重要条件,所谓“摊烛下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他认为,“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在美感上很重要,常会给人一种深静、朦胧的美感,“风风雨雨也是造成间隔化的好条件,一片烟水迷离的景象是诗境,是画意”。“凡是能够‘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之物,都是创造‘隔之美的外界条件,如夕照、月明、灯光、帘幕、薄纱、轻雾等。这些事物创造出距离化、间隔化的美景,使得物象拥有了不同于往常的意境,在这种审美观的影响下,唐代诗歌意境里的空间意识既有此间隔性,例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
在这里,烟雨、风帘、清霜、漳河等等都成了间隔化的工具,红楼、残烛、佳期、梦思,因隔而变得朦胧、遥远、神秘。同时语言的遮蔽性也决定读者不能从语言中获得直接的视觉享受,而只能突破语言之隔,借助联想和想象获得虚在的视觉影像,使有限的文本获得无限的可开拓审美想象空间。在这种“隔”所造成的层次化、距离感、朦胧化和神秘感中古人间隔化的空间意识发挥到极致。
三、“以大观小之法”
在道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自然是一个万物一体的大宇宙,而人就是一个与“天地运而相通”的小宇宙。这种观念转化为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思维意识,而在诗歌意境中主要体现为“以大观小之法”的空间视角。
“以大观小之法”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出自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其文曰:“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低,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5]沈括在批评画家李成“仰画飞檐”的画法的同时,点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中“以大观小之法”的空间创作认识。
“以大观小之法”要求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关于本体、关于存在、关于宇宙生命的主观性领悟,诗人要在构思中“神与物游”,从精神上达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力求获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创作状态,创造出源于自然物象而又超越自然物象,既“随物宛转”又“与心徘徊”的象外之象,使人性和物性、主体生命和宇宙精神相互感发、融合,以领略天地无形之大象。
庄子在《庄子?天下》中提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追求,也可称之为“乘物以游心”的精神追求。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诗人所体现的心灵境界是一种与“节奏化了的时间空间”相协调糅合的、充满生命情思的境界。因此,诗人在体察自然万物时,不仅仅以身体之眼去观摩认识对象的外在形状和颜色,更以心灵之眼去“澄怀观道”,领悟的对象的内部生命规律、本质和情思。这时诗人的眼光是变换不定、游动不居的,超越一草一木、一山一隅的局限,超越有限的自我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样的艺术世界便呈现出了独特的空间感。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些诗歌的意境,处处显现着“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无论月夜、春山、青苔,还是幽径、江水、碧空,都已沾染上主体的心绪情思、生命感悟而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念、空间意识。正所谓“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这些诗歌里,诗人和宇宙完全合而为一了,诗人的眼光是宏观的,环视宇宙时空,俯瞰万物自然,诗歌意境的空间也是宏观的,充满画家心灵节奏和宇宙生命节奏,体现出超越万物之外的空间意识。
参考文献:
[1]张晶.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空间[J].文学评论,2008(04).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2.
[4](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
[5](宋)沈括.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2-183.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2013级文艺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