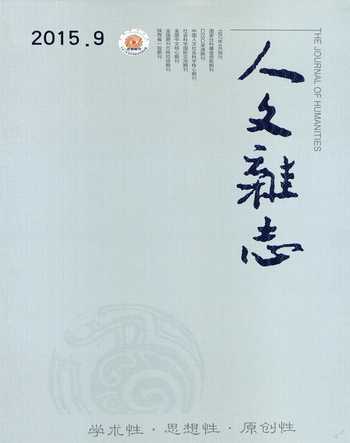地图所见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规划学分析
2015-05-30臧公秀
臧公秀



内容提要根据宋《平江图》和历史文献研究苏州古城以三横四直为核心的水陆双棋盘空间格局,是学界研究苏州古城的共同思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苏州古城图为依据,以现代城市规划学的视野,通过对苏州古城田园分布的分析,说明苏州古城空间结构的特点,揭示苏州古城生命力的基础和中国传统城市的历史特征。
关键词苏州古城图城市田园空间结构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K9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9-0091-09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要素的组合状态,可以分为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两大类,是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空间投影。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是了解城市发展特点的重要途径。考察现代城市如此,考察传统城市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对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资料: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城市遗址。就目前研究来说,人们大多是依据现存古代建筑、考古遗址,对照历史文献关于城市建筑、道路、河流、桥梁等的记载,判断其方位和距离,复原城市空间。因为古人对方位、距离的记载不够精准,据此作出的空间判断与实际存在必然存在距离;而古人记载多偏重于“建筑”,集中在城市建设的“点”或者“线”,而对处于“点”与“点”之间、“线”与“线”之间的城市空间则缺少记载,这些“点”“线”之间所包含的城市要素也就无从了解,而这些空间内涵恰恰是把握城市结构不可或缺的内容。和传世文献相比,地图自然具有其丰富、直观的特点,根据地图了解古代城市城市空间结构无疑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只是传世古代城市地图较少,就现有某一城市地图而言,大多不具有系统性,人们据以探索古代城市空间结构就有孤证的嫌疑;又因为古城图的绘制缺少现代的测绘标准和技术工具,所绘地图内容不太精准,据以研究空间结构时难免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是,近年来古代地图陆续出版,弥补了这一不足,苏州古城图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标本。
一
目前所见苏州古城地图最早的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平江图》,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城图,学者们曾予以充分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苏州古城三横四直水陆双棋盘格局的空间结构及其城市肌理。这是我们根据地图认识苏州古城空间结构的起点(见附图一,《平江图》)。
《平江图》是南宋绍定二年由平江府太守李寿朋主持绘刻在石碑上,石碑通高279厘米,其中碑额高76厘米,碑心高203厘米,宽138厘米,图中记述的各项建筑物之间的距离比例尚不一致,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精准的比例概念,另一方面是李寿朋根据城池、衙署等重要性的不同有意为之,以示区别。但是,平江府城内的各项要素则一一反映出来,可以使我们对平江城内的空间结构有直观的了解。该图绘刻内外二重城垣及水陆五门和水陆平行、河街相邻、前街后河的双棋盘城市格局,城垣呈不规则长方形,大约按照一比两千的比例制图,南北长约九里,东西宽约七里,周长约三十二华里。城内刻有大的河道六纵十四横,而以三横四直为核心,总长度约82公里,均为水陆并行、河道相邻、前街后河的水陆双棋盘结构。城内刻有大街20条,巷264条,里弄24条,标出坊表65座,桥梁314座,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67座,官府衙署38所,建筑物43座,其中的众多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众多学者曾对这些内容有过丰富而深入的研究。《平江图》碑刻现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其拓片和线描图收入《苏州古城地图集》,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出版。关于《平江图》绘刻时间和绘刻人,古今学者有不同意见,目前比较通行的看法是王謇在《宋平江城坊考》中考订的绍定二年即1229年。张维明先生力主绍定三年1230年说,见《宋〈平江图〉碑年代考》,刊《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本文采用通行说法。图中所反映的内容,笔者除了根据原图之外,还参考了以下学者研究成果:杜瑜:《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汪前进:《〈平江图〉的地图学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张勇坚:《〈平江图〉与古代苏州》,《档案与建设》1999年第12期。本文列举这些内容的目的是讨论苏州古城空间结构。
2015年第9期
地图所见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规划学分析
附图一《平江图》
若就《平江图》而论,平江府城可谓规划严整,功能分区明确,衙门官署、寺院道观之外,就是市肆与居民区,各种建筑栉次麟比,为水陆并举的河流和道路区分在不同的空间,而又形成完整的有机体,既是一幅繁华的市肆图,也是一幅优美的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画,是别具特色的江南都市景观展。这是现代学者一致的看法。这个看法当然有其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苏州古城的认识。但是,从中国城市发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我们对苏州古城的空间结构还要多一层思考,还不能完全按照根据《平江图》来解读苏州古城的空间结构和历史特点,因为《平江图》有其局限性,这就是虽然详细描绘了平江府城的河流、道路、官廨、寺院以及其他建筑的空间布局,我们从中可以清楚水陆双棋盘式的城市水陆交通系统,但是还不能进一步说明城内空间结构,不能据以说明社会经济情况。因为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根据现代城市知识解读《平江图》的城市内涵,面对《平江图》时,不自觉地联想到当时的衙署、市肆、宫观、寺庙、民居等栉次麟比的城市建筑,想象着摩肩接踵、挥汗成雨、挥袂成幕的繁华景象,不由自主地认为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体现。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城内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地块,没有任何标志,尤其在城图南部即今天的十梓街、道前街以南的大片地块都没有任何建筑物和其他标记,在北城墙、东城墙内侧也有相连的大片地块。这些地块被河流和道路分割成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或不规则方形,其用途和性质模糊不清。如果追问:这些地块所承载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建筑,如果有为什么没有在图上标明;如果没有,这些空间是如何产生的,意义何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此深究。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从《平江图》和传世文献不能获得明确说明的问题,需要根据其他资料予以探究。
苏州古城图,除了《平江图》之外,现存的自明代至清末的共有九幅,分别是崇祯十二年(1639)《苏州府城内水道图》、乾隆十年(1745)《姑苏城图》,嘉庆二年(1797)《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同治年间《苏城地理图》(同治三年至十二年,1864-1873年)和同治-光绪年间的《姑苏城图》(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七年,1872-1881年,下文简称同光《姑苏城图》)、光绪年间的《苏州城图》(光绪六年,1880年)、《苏州城厢图》(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888-1903年)、《苏城全图》(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1896-1906年)、《苏州巡警分区全图》(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博物馆、苏州碑刻博物馆、古吴轩出版社:《苏州古城地图集》,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这些古城图不仅记录了苏州古城的水、陆交通和建筑分布,还比较详细地描绘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苏州城内土地分布情况,为我们了解苏州古城空间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为以往研究所未见,通过对这些地图的比较分析,可以了解苏州古城空间结构的特点,丰富我们的认识。
明崇祯十二年的《苏州府城内水道图》由四幅组成,是城内主要水道示意图,分别为:《苏州府城内西北隅吴县分治水道图》《西南隅吴县分治水道图》《城内东北隅长洲县分治水道图》《东南隅长洲县分治水道图》,记录水道同时,同时也记录了陆路交通布局,其三横四直的水陆双棋盘格局和《平江图》完全一致,所绘水道较《平江图》则多出五千米左右。比较两图不难发现,《苏州府城内水道图》显示交通最为集中的区域是中部,大约相当于现在桃花坞大街-西北街-东北街以南、干将路以北地区,说明明代苏州城的空间结构变化较大的也是在这一区域;其他区域的水道与空间结构和《平江图》基本相同,说明其空间结构没有大的变化。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在干将路以南、桃花坞大街-西北街-东北街以北都有大片地块,没有被水道隔开,其性质从《平江图》和《苏州府城内水道图》无法显示,而清代的苏州城图则提供了说明。(附图二明崇祯十二年《苏州府城内水道图》)
清代八幅苏州城图中以乾隆《姑苏城图》和同光《姑苏城图》最为详细。乾隆《姑苏城图》中可辨的地名,有街巷620条、桥梁256座、寺庙128座、祠堂28座、衙署25座、仓库11处、城门6座,营寨、学校、会馆、园林、码头、坊、坛等总计1200多个,用文字注明为耕地、田园的地块有130余处,另有数10个池塘。虽然因为边界节点的模糊和缺乏,无法精确计算出当时苏州城内农田园地面积,但根据图中标注的农田、园地、荒基地地块,可以判定当时城中用于农业生产的农田、园地面积要超过城内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现在的葑门-十全街-胥门以南地块的五分之四是农田、园地和荒基地;现十全街以北、凤凰街以东、干将路以南地块约百分之六十是农田、园地;现在苏州大学十梓街校区及天赐庄以西地区全部是农田;现在的娄门-东北街-西北街-桃花坞大街以北地区约四分三是农田、园地和荒基地;东北街以南、平江路以东、干将路以北地块内约三分之一为农田和园地;在现在的观前街以南、十梓街以北、锦帆路以东、凤凰街以西地区也就是现在最为核心的地块也主要是园地。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小块园地、池塘散落在其他地块内。
附图二明崇祯《苏州府城内水道图》(根据四幅原图绘制拼接而成,原图见《苏州古城地图集》)
同光《姑苏城图》记录的内容稍简于乾隆《姑苏城图》,但是其标明的高墩31处“高墩”,则是乾隆《姑苏城图》所无,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墩是城市建筑和河流疏浚、池塘清污的产物,中部和西部是衙署、市肆和人口聚集地区,建筑密度和水网密度远远大于东部和南部地区,高墩自然多于其他地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政建设的需要,高墩的数量、分布也处于变化之中。光绪《苏州城图》标出的高墩为15个,《苏城全图》记录的高墩则为23个,这些高墩在民国时代依然一直存在。民国十年(1921年)的《最新苏州城厢明细全图》尚有高墩23个,主要集中于城市中部,见苏州历史博物馆、苏州地方志办公室编:《苏州古城地图集》,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根据笔者走访调查,古城内的高墩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有保存,其构成内容多样,有的是一般的土堆,有的是建筑废弃物,有的是兼而有之。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人回忆,高墩附近一般都是荒地,有的还是坟地,在民国时代,苏州城内就有好几处大片坟地,位于现在市中心的体育场、大公园地区就是较大的坟场。至于农田、园地、荒基地的面积及空间分布和乾隆十年《姑苏城图》比较,只是在面积上有盈缩,空间位置没有变化。(附图三同光《姑苏城图》)
附图三同光《姑苏城图》
高墩形成时间,无从查考。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可知,这些高墩的形成,是城内建筑需要、土地开发的衍生物,自然是因时而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墩的存在,由来已久,并非清朝末年才出现,只是因为绘制地图的人以为是临时堆放物而没有标注而已。所以,我们有理由推论,这些高墩由来已久。除了高墩以外,苏州城内还有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水塘,这些水塘在清朝的八幅地图中标注的并不详细,而在民国时代的地图中有部分体现。根据老人回忆,民国时代苏州城内大小水塘20余处。笔者先后访问一直居住在苏州古城内的75岁老人两位、72岁老人一位、81岁老人两位,他们均对民国时代苏州古城内高墩、池塘记忆犹新,这些高墩、池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还保留了一段时间。这些水塘并非私家园林的附属物,而是生产资料的组成部分,用作水产养殖,如现在的东采莲巷、西采莲巷就是因为该区域水塘盛产莲藕而得名。又如现在苏州大学本部西北角的读书湾就曾经是一个面积开阔的水塘,相当于一个小的湖泊,现在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痕迹。这些水塘、高墩、荒基地一般情况下都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
二
明确记载城内农田、荒基地、园田、水塘空间分布的地图都是清朝绘制的。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追问:这些地图固然表明了清朝苏州城的空间结构,可否据此推论以往苏州城的空间结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清代苏州城的肌理是历史的延续,清代苏州城的水陆交通系统与《平江图》有着一致性,以三横四直为核心的水陆双棋盘格局、城墙周长、形制都没有变化,起码说明苏州古城的物理空间完全均延续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逆推苏州古城空间结构的历史形态。
城市空间是一个生产过程,经济发展、政治变动、文化发展都影响着城市空间的生产,不同组织、不同集团、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因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力量的不同均会导致空间生产的变化。反过来,我们通过变化了的空间结构即可逆推其历史形态。乾隆时期的苏州是苏州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是学界关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是商品经济的核心城市,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起码高于以往,其城市建设最为发达,其城市建筑密度也远远大于以往,其时的苏州城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和以往相比都要复杂得多。地图表明,乾隆时代的苏州城内有大面积的农田、园地,说明当时苏州城内的产业结构和人口构成是以手工业、商业和工商业者为主的传统认识是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乾隆时期苏州城内居民有相当比例是以农为生的。乾隆时代如此,社会生产、在商品经济落后于乾隆时代的过去更是如此。由此上溯,时代越早,苏州城内农田所占的空间和农业人口的比例越大。这为我们认识苏州古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
现代研究苏州古城历史均以《吴越春秋》记载的伍子胥修建阖闾城开始,阖闾城是苏州古城的基础,苏州古城的繁华就肇始于阖闾古城。现在,对这一流行认识需要重新认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对伍子胥修建城池情况有详细记载:
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制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舆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相天法地,造诸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曰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鳐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吴越春秋》成书于东汉末年,距离吴王阖闾的时代已经七百余年,记载的内容有些是后世的附会,有的则不合逻辑。如“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鳐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读来就很像小说。小城在大城之内,周长十里,只开了三个城门,唯独东城不开门,原因是“欲以绝越明也”。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小城既在城内,与越之间有大城相隔,小城无论是否开门,都不存在“绝越”的问题。所谓“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恐怕不是伍子胥的设想,而是后人的附会。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相天法地,造诸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聪”作为苏州古城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结构,为历代所延续。唐人陆广微《吴地记》记载:
罗城,作亚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迄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城南北长十二里,东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七县八门,皆通水陆。郡郭三百余巷。吴、长二县,古坊六十,虹桥三百有余。地广人繁,民多殷富。陆广微:《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0~111页。
周敬王六年即吴王阖闾元年为公元前514年,到唐乾符三年即公元876年,距离1390年,《吴地记》谓“凡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系传抄刊印讹误。这儿的罗城就是伍子胥所筑的苏州古城,形状为“亚”字形,也就是南北长、东西窄的矩形,南北长12里,东西宽9里,周长42里,比《吴越春秋》记载的“周回四十七里”少五里。这个数字差别,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记录或者传抄讹误;一是唐朝苏州城垣有调整。陆广微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说的苏州城规模和结构是其亲眼所见,我们应当以陆广微记述为是,说明到唐朝后期,苏州城基本上呈矩形,东西九里,南北十二里,八个水陆城门,均沿用旧名;城内有大河,三横四直;街巷三百余,大小桥梁三百多;有居民六十坊,分属吴县、长洲治下。“地广人繁,民多殷富”,这是自阖闾以来最为繁华的时期,关于阖闾城和平江城的周长,文献有不同记载,学界有不同理解,详细研究见杜瑜:《从〈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布局和规模》,《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9年第1期。其空间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
唐末五代时期,因为战乱,苏州城损坏严重。乾隆《苏州府志》卷三《城池》说至乾宁五年也就是898年,“十余年间,民困于兵火,焚掠赤地,唐世遗迹殆尽”。五代时期,苏州处于吴越钱氏治下,相对中原地区来说,虽然战火较少,但是,处于兵争时代,苏州城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残破状况没能得到大的改善。到了北宋,苏州才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经济繁盛,人口稠密,为东南之冠,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将苏州升为平江府。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曾攻占平江府,烧杀掳掠,居民四散,建筑毁坏。政局稳定以后,因为苏州地理位置特殊,是临安北面最为重要的军事屏障,加上原来经济基础雄厚,南宋政府自然着力经营,一方面加固城防建筑,完善市政设施;另一方面发展经济,苏州城再度成为繁荣富庶之都。郡守李寿朋为形象直观保存平江府城风貌,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绘刻《平江图》。
如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指在交通便利地区、以非农业生产和非农业人口为主体、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有不同于农村的管理制度、有一定规模的居民区。人们在讨论苏州古城演变时或多或少地受到现代城市概念的影响,以为苏州城的建立起码在一定意义上表示着苏州地区经济的发达特点,显示了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城市是个历史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城市的人口构成、产业结构有着特定的内涵,体现在空间结构上也有着特定的特征。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特点和空间结构的认识也离不开这个历史基础。中国早期的“城”和农业是合一的,并不是为了适应手工业发展、商业贸易的需要而建立,而是为了安全防卫的需要,最初是为了防卫猛兽的袭击,后来则是为了防止临近部落的攻击,再后则是为了防止敌国军队的进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城的设立最初是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而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结果。以此作为出发点,考察阖闾古城的出发点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阖闾建城,是为了和越国战争的需要而兴建,首先考虑的是对吴国人力物力的保护,居住在城中的是阖闾治下的吴国国民,主体是农业人口,而不是现代理解的工商业者、官僚等非农业人口。当时吴地的经济水平落后于中原,还谈不上商业生产,手工业、商业均以国营为主,工商业者隶属于官府,人口有限。伍子胥建城是要通过“设守备,实仓廪,制兵库”,以实现 “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的目的,“相土尝水,相天法地,造诸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聪”是为了“天气之数以威邻国”,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分工根本没有关系。因为城内居住的主要是农业人口,城内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农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和平时期,农民出城农耕渔采;在战争年代,城内大片的土地、池塘、排灌系统,可以保障城内军民的生产生活,可以抵御敌军的长期围困。同理,也应该从这个角度考察宋代苏州城的性质,宋代的苏州当然有着发达的手工业、商业,是当时地方经济都会,但是农业在平江城内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内水道系统怕不是为了交通的便利,而是有着排灌的意义,有着满足农业生产的目的在内。这些在《平江图》内没有显示,是因为《平江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地图,是为了表达其时城市发展的示意图,着眼于城市建筑主体结构,而不是为了完整、直观地记录当时经济情况,在当时的历史观念中,也不存在记录社会经济的土壤,其对城市空间的展现与实际存在有距离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推定,南宋加强平江府城建设的原因固然有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因素,衡以当时宋、金对峙的历史条件,更多的是出于军事和政治需要,不能以后世的工商业城市形态考量其性质。就目前所见从《平江图》分析苏州社会的研究成果来说,虽然直接叙述苏州市民社会的论著不多,但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认为《平江府》反应了苏州市井的繁华,说明当时商品经济发达,而乌再荣先生则通过对《平江图》的市坊制度的空间分析,论证当时的苏州已经“城市化”,表现了“市井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参见乌再荣:《从〈平江图〉看南宋平江府之市坊制度》,《建筑学报》2009年第12期。
三
通过对上述苏州古城空间结构的历史考察,明白了即使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乾隆时期,农田、园地所占空间依然在城市物理空间的三分之一左右,另有一定数量的荒基地、高墩、水塘,不仅为我们理解苏州古城空间结构提供了新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一般特点打开了一扇窗户。
首先,苏州古城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华的工商业都会,更不能以《姑苏繁华图》为依据理解乾隆时代的苏州经济结构和城市空间。《姑苏繁华图》是歌颂乾隆盛世的艺术品,并非当时社会的真实描摹,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使用,不能视为苏州古城经济发达、市井繁荣、民生富足的真实写照,与《姑苏繁华图》同时的乾隆《姑苏城图》才具有历史价值。《姑苏城图》告诉我们,古代的苏州城,居民生活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都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农业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中居民,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种植、水产养殖业和园艺业,其时苏州城内的经济结构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并举的格局。尽管无法对三者的比重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比重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空间结构上看,农业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只是在清朝社会最稳定、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农业生产的比重小一些而已。也就是说,从物理属性考察苏州古城空间结构,农业空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苏州古城研究中,运用《姑苏繁华图》说明苏州商业繁荣的学者以范金民为代表,参见范金民:《〈姑苏繁华图〉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清代苏州城是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史林》2003年第5期。
其次,丰富对《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记的营国制度的理解,即营国制度只是说明西周建城立邑有着等级限制,并不能说明城市兴建以工商业发达为基础,等级规定的是城邑空间范围,而没有考虑到其空间结构的经济属性的历史特点。《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国”即城呈正方形,边长九里,每面三个城门,四面共有十二个城门,周长三十六里,总面积为八十一平方里。国内分为九经九纬,呈方格网状结构,官署区、贸易区、祭祀区等各有专属空间。所谓“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就是在“朝”——朝廷的左面为周天子祭祀祖先的地方、右面为周天子祭社神的地方;朝在南面,市在朝北面,祖、朝、社在东西中轴线上,市、朝在南北中轴线上,市、朝的面积均为“一夫”——一百亩。按当时度制,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一步宽、百步长为一亩,三百步为里,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当时的尺是周尺,一尺约合现代23厘米强,一步约为140厘米,一里约为420米。也就是说,周天子的国——都城,在设计上边长是3780米左右。这是当时能够允许的最大的城池,其他诸侯国的都城要根据身份高低依次缩减。《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国大夫祭仲对郑庄公说过这样的话:“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谓“大都”是指大的诸侯国都城,不能超过周天子都城的三分之一;中等诸侯国国都大小只能限定在周天子都城的五分之一;小的诸侯国国都只能是周天子都城的九分之一。祭仲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22年,这里的“先王之制”是西周制度。这说明,西周到春秋初年,建城立邑,都是按照身份高低确定规模的,经过严格的规划,有明确的等级限制,而不是根据经济发展、社会分工需要进行。当时城中的居民,手工业者、商人是少数,农业人口是多数,所谓的城实际上就是有围墙的农村,和现代意义上城市的性质是不同的。苏州古城空间结构为我们这一理解提供了实例。
第三,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建城思想多样性的理解。人们研究古代城市时,往往不自觉地把《周礼·考工记·匠人》的营国制度作为建城立邑的标准思维,实际上没有注意到其适用范围和地理限制,忽视了其他建城思想的实践意义。营国制度是以西周分封制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是礼制秩序的物化反映,在等级变动的条件下,其秩序的权威性必然改变;若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在水网、丘陵地带建城立邑,这种以王宫寝殿为核心的以中轴对称为特点的设计理念显然难以变成现实。有学者曾经根据《匠人》的营国制度解读《平江图》,认为平江图是中华王都的体现,既不符合营国制度的礼制内涵,也不符合《平江图》的历史实际。曹林娣先生认为阖闾城是按照周天子的营国制度规划设计的,是“礼制”的体现,明确以“王都文化”代指阖闾古城,见曹林娣、殷虹刚:《中华王都文化的化石——苏州古城文化的价值》,《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其实,除了《匠人》营国制度的设计思维之外,《管子·乘马》还有另一种设计思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里说的“国都”是诸侯国国都。诸侯建城考虑的是依山就水,因地制宜,安全第一,建筑方便。用现代通行的观念表述,《匠人》的营国理念是宇宙思维,城市建筑模仿天地四方的对称与尊卑,《管子》所述是有机思维,因地制宜,为我所用。就实践而言,像后来作为王朝都城的偏重于宇宙思维模式,而地方性城市,特别是因为经济发展由小到大形成的地方性城市则偏重于有机思维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无论什么级别的城市,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苏州古城初建之时,作为吴国首都,自然有其礼制色彩,但是坐落于水网地带,面临着越国的军事威胁,显然不能照搬“营国”的理念,而需要因地制宜地灵活应用。以《平江图》而言,既有规划的对称性,以官府衙署为核心,但更具突出的有机性。苏州古城如此,其他同级别的城市也是如此。
第四,有机性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苏州是水城,水是苏州古城有机性的根本,赋予了苏州古城不解的生命力。人们之所以重视水陆双棋盘格局的城市架构,不仅仅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更主要的是因为水给苏州带来了舟楫之利、景观的活力,孕育了风格独具的文化特色,是誉满天下的园林文化的保障。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还不够全面。因为人们把苏州古城作为工商业都会,没有看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也就看不到水给苏州城带来的灌溉之利,看不到水在苏州古城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如上所述,苏州城内起码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农田、园地、水塘、荒地,在多雨的江南亚热带地区,农作物的生长既需要足够的灌溉用水,也需要相应的防涝设施。城市居民既然要以农为生,自然要有排灌系统,而越是精耕细作,对排灌系统的要求也就越高,需要精心维护。维护越好,越能保障农业生产、园艺培育、园林绿化,形成良性循环,保障经济供给,这是千百年来水陆双棋盘式的城市格局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苏州古城在唐末五代时期、两宋之际、元末都曾遭到过长期的围城和兵焚之灾,之所以战后能迅速重建,除了政局的因素之外,与苏州城内有自成系统的灌溉系统、大片的农田是分不开的,即使兵临城下,亦可生产自给,不必要依赖城外的供给,不会因为围城、封锁使城内民众无以为生而陷落;即使失陷,城内建筑破坏严重,城内农田、水道还在,排灌系统还在,就能在短期内恢复。这是苏州古城两多年以来历经战火而生生不息的内在保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