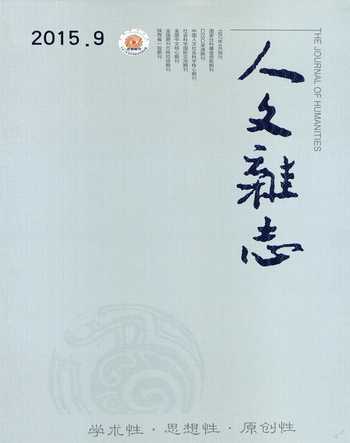触觉与视觉之间的传统与现代性?
2015-05-30陈昊
陈昊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学术史语境下,反思中国历史和社会中身体感研究的基本问题:如何探索中国历史中人们的身体感觉?中国视觉的现代性与殖民化身体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触觉是理解中国古代医学传统的关键性感觉因素吗?在中国的身体研究中,身体感的语言表达特别受重视,描述身体感的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可能展示出多种身体感官的互动关系。身体感及其语言表达被放置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之中,即社会和文化及其物质形式对人的塑造,以及人对社会和文化的调适和表达。知识和言语会重新塑造身体,并通过知识的再生产与规训,重新造成身体的行为和感觉方式。如何在被语言再现的观念、感觉和社会行为之间找到一个讲述的平台,成为重要的问题。
关键词感觉史日常生活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9-0082-09
在关于18世纪德国医家Johann Storch的论著中,Barbara Duden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我们如何重构历史中人们对身体的感知?在她看来,这种重构最大的阻碍也许是“现代身体的诞生”。她引述Michel Foucault的观点,认为这个身体诞生于“医学的凝视”与这种凝视所编织出的对象之间的互动,它带着相关的科学与社会话语,宣称自身才是“真实”的身体,直到现代医学中才被“发现”,因此是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在Barbara Duden看来,要追寻过去人们对身体的感知,就需要在方法上,将现代身体展开的问题与之区分开来,理解现代身体的诞生,只是重构过去身体感觉的第一步,虽然这是甚为关键的一步。Barbara Duden, Geschichte unter der Haut. Ein Eisenacher Arzt und seine Patientinnen um 1730, Stuttgart, 1987. Thomas Dunlap trans., 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 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Cambridge and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49.Barbara Duden的问题,对中国身体史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系列的问题随之在中国学的领域里展开:中国的历史中是否也有“现代的身体”诞生的问题?在反思中国现代身体的时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社会中的身体感觉和体验?
一、范式的移植与选择的差异
受栗山茂久之邀,Barbara Duden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更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问题:她希望探讨不同文化差异下的人们是如何感知自我身体,并将其变成一个知识的体系?如果不同的文化系统创造了不同的经验系统,那么一个文化系统下的人如何理解和感知另一个系统下的身体观念和感觉?文化差异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同地域,也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段。她认为在西方历史中,现代身体的出现,造成了“传统的”基于知觉的身体感与“现代性”的基于视觉的身体感的区别。Barbara Duden, “Images and Ways of Knowing- The History of Pregnancy as an Example,” Kuriyama Shigehisa 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History of Bodily Experience, Kyo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2001, pp.119~136. 其中论述问题的进一步展开请见Barbara Duden, Der Frauenleib als ffentlicher Ort. Vom Missbrauch des Begriffs Leben, Frankfurt, 1991. Lee Hoinacki trans., Disembodying Women: Perspectives on Pregnancy and the Unborn, Cambridge and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dem, Die Anatomie der Guten Hoffnung. Bilder vom ungeborenen Menschen 1500-1800, Habil.-Schr. 2003.这样的论述源自于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Lucien Febrve,他在讨论不信教的心态基础的时候,将视觉的不发达和其他感觉的充分使用作为证据,显然在他眼中,视觉与现代的思想世界之间有着种种联系。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ⅩⅥe siècle, Paris, 1942. 此据《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赖国栋译,三联书店,2011年,第434~447页。虽然支持他论点的一些证据受到质疑(见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Polity Press, 1999. 此据《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但此研究传统在年鉴学派内部一直延续,重要的作品包括Robert Mandrou, Introduction à la France moderne. Essai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1500-1640), Paris, 1961. Jeal-Paul Aron, Essai sur la sensibilité alimentaire à Paris au ⅩⅨe siècle, Paris, 1967. Max Milner, La Fantasmagorie, Paris, 1982.感觉史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参考Leigh Eric Schmidt, Hearing Things: Religion, Illusion, and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2000, p.18.Alain Corbin延续这个传统,在对法国18至19世纪的研究中,他重新将感觉的重要性放回到历史当中,从最容易被忽视的嗅觉开始,讨论从18世纪以来城市卫生与嗅觉感知之间的权力互动。他强调通过追踪味道的历史,可以研究历史被制造的过程。这种研究需要把不同的感觉模式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他指出,与其说嗅觉在现代社会重要性逐渐减低,不如说自18世纪中期开始,巴黎社会中对嗅觉的感知发生了变化。Alain Corbin, 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 Lodorat et limaginaire social, XVIIIe-XIXe siècles, Paris: Flammarion, coll., 1982.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重构西方历史中逝去的知觉世界,需要先反思现代视觉的身体感觉世界是如何展开的。视觉在现代社会逐渐建立优势的论述见于多位学者的观察,综述性的讨论请参见Mark Smith, Sensory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7, pp.8~11. 近来对其他感觉与现代性之间联系的研究也对此模式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听觉与现代性的研究,参见Joy Damousi and Desley Deacon eds., Talking and Listening in the Ag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Sound, Canberra: ANUE Press, 2007. Janet Stewart, Public Speaking in the City: Debating and Shaping the Urban Experi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Barbara Duden的问题显然源自此传统,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中,现代的身体是否与视觉相联系?这种视觉经验如何与现代中国面对西方的种种体验相联系?
2015年第9期
触觉与视觉之间的传统与现代性?
不过,在受Barbara Duden的启发之前,一个关注宗教与身体的传统就存在于中国研究之中。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开创性的研究中讨论了多个层次上的道教的身体,包括物理意义上的身体、神化中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但是他对身体关注的核心,却在于宗教仪式中身体的实践及其如何造成了宗教共同体。Kristofer Schipper, “The Taoist Body,” History of Religion, 17, 1978, pp.355~387. 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Le corps taost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2. Translated by Karen C. Duval, The Taoist Bod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只是之后的道教研究者,却更多地将道教中的身体看作一种与宇宙论相连的身体观念,特别是一种区别于“西方身体”的替代性身体观念模型。科恩(Livia Kohn)认为,在道教中身体与精神虽然有区分,但却不对立。长生技术中将人的身体看作长生的主要载体,通过自己的身体体验,而成为宇宙神圣的复制物,将身体-精神的统一体转化到一个更高的阶段。Livia Kohn, “Eternal Life in Taoism Myst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110-4, 1990, pp. 622~640. Idem, “Taoist Vision of the Body,”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 1991, pp.227~252. Idem, “The Subtle Body Ecstasy of Daoist Inner Alchemy,”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59-3, 2006, pp.325~340.Idem eds., Daoist Body Cultivacation: Tradition Model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Magdalena, NM: Three Pines Press, 2006.Michael Saso将道教仪式中的身体与密教仪式中的身体加以比较,认为道教仪式和存思使身体与外在宇宙的运转成为一个整体。Michael Saso, “The Taoist Body and Cosmic Prayer,” Sarah Coakley eds., Religion and the Bo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31~247.
这样的路径也遭遇到挑战和反诘,司徒安(Angela Zito)和白露(Tani E. Barlow)在1994年主编了《中国的身体、主体与权力》一书,其中体现了对中国身体历史探索的集体努力。Angela Zito and Tani Barlow eds., Body, Subject & Power i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这种努力基于一种反思,即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所言,之前宗教研究创造出的中国身体史叙述是一种与西方相反的身体形式的想象,而非东方历史和社会中的身体:“在任何一本著作中,中国医学的身体观都把身体看作整体,体现心身一体的完美结合,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传授了西方男女所不熟悉的自我治疗和内心平和的秘密,但所有这些观点都被相反的事实萦绕着:西方的身体观存在身体和精神两种解释思路,客观表现为通过现代科学的摄生法所体现的物质形态主体,并与达尔文的观点密切相关——竞争、独立、人类统治自然、欧洲统治亚洲。”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165,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见《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甄橙主译、吴朝霞主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那么如何才能将中国历史中的身体不再泛化为神圣的理念图景,而是看作一种主体参与历史与社会的实践过程。白馥兰(Francesca Bray)重视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对性别与身体的权力结构塑造的过程,在研究明清与生育相关的医疗技术时,认为在这个时期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在其生命历程中更加凸现出来。生育技术与女性母亲身份的互动展示出复杂的权力关系。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3~286页。费侠莉和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则更重视身体感觉如何为语言所表达和建构的过程,比如费侠莉分析宋代产科是如何在家庭语境下展开,及其与新儒家“家国”观念的关系,也讨论了生育与女性身体建构的问题,栗山茂久分析《脉经》中书写脉象的语言形式。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165,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 1999. Kuriyama Shigehisa ed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History of Bodily Experience, Kyoto: Uno Printing, 2001.在这里,进入中国的身体史范式已经出现了歧路,围绕身体展开的社会权力与身体感觉的语言再现成为了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区别,集中体现在“黄帝的身体”(Yellow Emperors Body)这一概念的争论中。费侠莉发明了一个词汇“黄帝的身体”来说明中国古代医学经典和宇宙论中阴阳同体(Androgyny)的身体,宋代妇科继承了孙思邈的思想,强调“妇人以血为主”,使女性身体差异的话语对这种阴阳同体的阐述形成一种挑战。明清以后的医生则以儒家经典重新强调“气”对所有人的重要性,妇科的领域逐渐缩小。这一论点一方面来自于Thomas Laqueur研究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白馥兰和瑞丽(Lisa Raphals)的研究。在对此概念的反思中,呈现出两种取向,一种试图指出,“黄帝的身体”是对于文本语境的误读,典型的例子可以参见李建民:《考古学上の发现と任脈学说の新认识》,《中國——社会と文化》第18号,2003年,第84~101页;又《督脉与中国早期养生实践奇经八脉的新研究之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2005年,第249~313页。一种则试图展示,女体在社会与历史中的遭遇种种,不能简单被模式所涵盖。李贞德:《唐代的性别与医疗》,第415~446页。参见Suzanne E. Cahill, “Discipline and Transformation: Body and Practice in the Lives of Daoist Holy Women of Tang China,” Dorothy Ko,Jahyun Kim Haboush and Joan R. Piggott ed., Woman and Confucian Cultures in Premodern China, Korea and Japan,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51~278.如何理解女性身体,是语言的再现,还是被层层包裹的自我身体经验,已成为争论的焦点。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关注社会权力对身体塑造的研究者忽视了语言的意义,费侠莉强调自己与栗山茂久的观点差异不在于是否重视语言,而在于如何理解语言,将其看作社会意义的塑造,还是话语以自我规则的演生。费侠莉:《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蒋竹山译,《新史学》1999年第4期。语言对身体及缠绕其上的权力意义颇重,但如果循着之前“视觉现代性”的讨论,也许需要花些时间探寻,西方医学的传入,是否向近代中国移植了以视觉为中心的身体感?视觉是否提供了语言之外的权力载体?这个外来的“现代身体”进入之前,中国的身体感知是怎样的?
二、现代中国的身体感:视觉再现与被传译的身体
韩依薇(Larissa N. Heinrich)对中国近代病理学文献和图像的研究也许会提供一些线索。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当她选择图像作为其讨论的对象时,韩依薇并非想论述视觉造成了中国身体的现代性,而是认为,中国身体的现代性是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与身体病理学联系起来的过程:早期医学传教士通过言辞和图像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形象传到西方,同时又通过他们的传教活动、对西方医学文献的翻译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学将这些观念传递回中国。这种身体的传译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现代性在文学中的体现,已有相当多理论化的研究。比如韩依薇与马嘉兰(Fran Martin)曾专门分析性别化的身体、民族主义和现代性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中体现的相关研究著作,见“Introduction to Part Ⅰ”, Fran Martin and Larissa Heirich eds., Embodied Modernities: Corpore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19. note 18.因此韩依薇试图另辟蹊径,讨论西方病理学是如何通过图像再现传递到中国,以及这些图像对中国种族、病理学、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接受所造成的影响。中文界对韩依薇此书的介绍可参郭彦龙的书评,见《艺术史研究》第1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9~525页。
当然她所提供的旅程并非全是图像,也涉及文字。她从韩国英神父(Father Cibot)关于中国天花的论述开始,然后谈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及之后通商口岸建立的背景下,林官[或关乔昌,当时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称之为啉呱(Lam Qua)]的一系列描绘中病人的图画,以及林官和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的关系。之后再讲到19世纪中期,照相技术引入医学之中,对中国病患身体的记录。最后回到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体新论》,讨论其中关于身体的解剖学观念是如何被接受的。
在这些以时间顺序串联起来的个案研究中,讨论的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却区别颇大的问题,第一是中国人的身体如何被与这些病理的图像相联系起来;第二则是这些视觉的经验如何改造了中国人对自身身体的理解。
韩国英在《论天花》( “De la Petite Vérole”)中,声称他想要确定天花的起源地以及中国种痘的方式是否有效,但文章结论却将天花与中国国民性联系起来。当伯驾展览林官的画作时,是试图在美国获得在中国建立医院的资金支持。但这种展示逐渐将中国人的身体在美国观众面前转化成一种病态身体的代表。照相技术进一步将中国病理的身体放到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医学共同体中,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各地的医生之间形成的交流的共同体,照相技术显然促进了这种交流,韩依薇认为这种技术促进了一种转变,即从一种记传性和描述性的模式到一种理性的转喻式的模式,即中国的疾病样本代表了中华帝国。创造出了一种病理学上的“他者”,建构出一种中国的种族特征,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本质性特质。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是如何在纠结之中接受这种移植的身体观以及其对中国身体的病理性描述的。韩依薇分析了在王吉民、武连德的《中国医史》如何接受了韩国英的天花中国起源论和中国种痘术无效论和鲁迅诗歌是如何接受了解剖学的身体观念。但正如郭彦龙所指出的,这种对应是一种历史情境上的对应,而并非两者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艺术史研究》第1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2页。要在韩国英与《中国医史》之间、《全体新书》与鲁迅之间建立起联系,还有很多的历史缺环。
韩依薇的研究展示了视觉在殖民化身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揭示出视觉在西方现代性身体诞生的故事的另一侧面,即视觉如何将“他者”的身体变为患病的身体,而在这些地方的知识精英中输入新的“现代”的身体图像。在这一研究中,韩依薇显然跟随了之前所提及的Barbara Duden的见解,视觉与现代性的造成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视觉的现代性亦会随着现代帝国海外扩张和殖民化的过程,塑造其他地域的身体现代性。视觉的现代性是否就此区分了中国历史上的感觉世界,其他的感觉对现在之前与之后的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其载体或表达方式又是什么样的?
三、心与物游:身体感、情感与物相联系的研究取向
在现代社会之前,关于身体的图像资料很少的情况之下,巫鸿和蒋人和所编辑的论文集中展示了中国历史中对身体的种种图像再现的形式,见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iang eds.,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言语仍然是理解身体感觉的基础。只是,如何理解言语,本身就是个问题。费侠莉曾将自己比喻为维特根斯坦,而将栗山茂久比喻为庄子,是因为当她在尝试区分言语的层次以突破文本和身体之间的谜障时,栗山茂久却在他的著作中,展示出一种“惊异”。让他惊奇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身体,在不同文化中却有如此类似却又不同的表达方式。③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于是栗山茂久把关注的重点从不同的感觉类型,转移到言辞。在他对日本的“肩凝”、中国的“虚”和西方社会的“紧张”概念研究中,逐渐将作为身体经验范畴的“身体感”放到中心的位置,通过一种比较的路径检视感知身体的方式。③在他与北泽一利合编的论文集中,他们强调身体观随着科学知识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时,身体感与文化相互联系而更为稳定。栗山茂久、北澤一利编著:《近代日本の身体感觉》,东京:青弓社,2004年,第11~12页。也就是说,他将Barbara Duden探索现代与传统区别的“身体感”概念,转化为区别并理解文化差异的工具,在他的眼中,与身体感相关的话语在一个文化群体中延续,界定着他们与“他者”的边界。
这种比较式的文化史路径,却并不如他将身体史的研究重点转向身体表达方式的影响深远。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和梅道芬(Ulrike Middendorf)编辑的《从肌肤到心灵——传统中国文化中情感和身体感的感知》一书,Paolo Santangelo ed., in Cooperation with Ulrike Middendorf, From Skin to Heart: Perceptions of Emotions and Bodily Sens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收录的论文都来自2004年3月在威尼斯卡佛卡力大学(Università CaFoscari di Venezia)召开的“南亚和东亚文化中身体感和情感的感知”国际研讨会。史华罗在此书的导论《身体感与情感的双向网络》( “Introduction: The Bidirectional Network of Bodily Sensations and Emotions”)中讨论了书的主旨:身体感觉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并经常与记忆和情感相联系,甚至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因此身体感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讨论的议题。此书试图强调在中国文化中身体与情感如何相互连接和转化的过程。他强调,书的作者们受到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和话语分析的影响,将其对身体和心智的分析聚焦于语言之上。因为只有通过语言,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是某种感觉或者是某种情感,语言是将感觉和情感之间的概念相联系,并具体化的途径。该书借由这样的理念,希望开启汉学研究新的路径。这一路径显然透着栗山茂久的影子。史华罗开始发表关于身体与语言的研究,也可始自栗山茂久的邀请,Paolo Santangelo, “The Language of Body as Repulsive/ Seductive Language: The Case of the Literati in Late Imperial China,”Kuriyama Shigehisa 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History of Bodily Experience, pp. 55~100.
史华罗是欧洲中国学中情感史研究的倡导人之一,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新儒家思想中对情感的表达及其思想史意义,Paolo Santangelo, Emozioni e desideri in Cina:la riflessione neoconfuciana dalla metà del XIV alla metà del XIX secolo, Bari: Laterza, 1992. Idem, Gelosia nella Cina imperiale attraverso la letteratura dal XV al XIX secolo, Palermo: Novecento, 1996. Idem, Le passioni nella Cina imperiale, Venezia: Marsilio, 1997. Idem, Lamore in Cina: attraverso alcune opere letterarie negli ultimi secoli dellImpero, Napoli: Liguori, 1999. Paolo Santangelo ed., Love, Hatred, and Other Passions: Questions and Themes on Emotion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他在那普勒斯意大利东方研究大学建立了一个分析中国文学和非文学文本材料的工作小组,旨在收集研究散集在明清两代众多史料中有关情感和心态的描述,身体感成为其情感研究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当他将情感历史的研究与身体感搭界时,他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的语言中,存在情感和身体感表达混同的现象,对此进行分析,可以为理解文化和社会提供了一个观察点。当然史华罗的这一转向并非完全来自中国学的身体史问题意识的影响,也有感觉文化史家Constance Classen等学者著作的影响。Constance Classen, Worlds of Sense: Exploring the Senses in History and Across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93.在这个论文集中,关注情感和身体感的研究者,采取了三种相互关联的路径。第一种,是关注文学以及其他文献中对情感的论述或表达,比如“气”“伤”“皮肤滥淫”“意淫”,这些语言如何在身体感和情感之间游走,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意涵。第二种,则关注文学和其他作品中,如何描述情感和身体感,进而塑造人物,甚至是文化的建构。方秀洁(Grace S. Fong)则提供了第三种路径,即身体如何成为创作的语境,又成为书写的对象。她指出疾病是明清女性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女性在罹患疾病时或疾病痊愈后都经常书写疾病,疾病的经历甚至成为写作的前奏。作者指出这种女性使用身体的疾病感受来表达情感的写作,说明疾病的主题和其多样化的再现模式,能够为女性建构一个可选择的空间,同时其与中华帝国晚期文人文化中对私人和个人再现的转向有密切的关系。Grace S. Fong , “A Feminine Condition? Womens Poetry on Ill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131~150.
在余舜德主编的《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一书中将身体感与另一种主题相联系,即物质的世界。他在代前言《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里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从其在云南西北部的藏区做田野工作过程中,由于身体经验(包括清洁感、舒适感)所面临的挫败感切入主题,指出身体的感受包括意涵和感觉、文化与本性,既非纯粹的身体感受,亦非单纯的认知。这种感觉的表达往往在身体与物质环境的互动中凸现出来。此书尝试关心在身体与物之间密切的互动中,文化如何在扮演斡旋角色的同时,亦受体物入微的过程改变,并成为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动力。作者在文中回顾了感官研究到身体感概念的学术史变化,认为感觉人类学尚未受到人类学主流肯定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试图比较不同社会使用五种感官的比例,或者强调某一种感官在当地社会扮演的角色,这种研究方法难以解释文化中真实生活的层面。因此他尝试使用栗山茂久所使用的“身体感”一词,将其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Categories)”,强调身体经验是多种感官的运作、融合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身心的结合。他还试图进一步讨论,在文化环境中塑造的“有经验能力”的身体,如何感知周遭的世界及他人行动的意义,并具有使用身体感行动的能力。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这个项目可以溯源到李亦园先生主持的“文化、气与传统医学”研究计划,课题中将“气”作为身体感觉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此课题结束之后,部分参与者延续“气”的课题逐渐注意到阴、阳、冷、热、虚和实等类似的项目,乃至洁净、肮脏、舒适、卫生等身体感觉的相关议题,《体物入微》是其近年研究成果的集结,尝试探讨人与物之间密切互动的关系如何影响文化对这个世界的建构,强调“是体物入微的过程形成身体感项目组成的感知方式与内涵(而非概念)再现内在与外在的真实”。在此之前,他们研究的成果已经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比如《思与言》第44卷第1期(2006年)是“身体研究”专号包括颜学诚的《“身体研究”专辑前言》、余舜德的《物与身体感的历史:一个研究取向之探索》、龚卓军的《身体感与时间性:以梅洛庞蒂解读伯格森为线索》、钟蔚文和陈百龄等人的《从信息处理典范到体会之知:专家研究典范的变迁》、蔡璧名的《身外之身:〈黄庭内景经〉注中的两种真身图像》和丁亮的《〈老子〉文本中的身体观》等论文。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65期(2006年)“物与身体感”专号。包括余舜德、颜学诚的《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专号”导言》、张珣的《馨香祷祝:香气的仪式力量》、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以中国侗人的社会生活为例》、余舜德的《市场、价值建构与普洱茶交易中的陈韵》、颜学诚的《什么是好茶?茶叶比赛的人类学研究》和郭奇正的《卫生、城市现代基础设施与商品化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上海里弄住宅的社会形构》。在这本论文集中,从身体感和体物入微的方向,参与的研究者希望从三个方向加以讨论。
首先,文化中的成员需要知道文化中的知识,从而能够成为社会成员。即文化能够对社会成员的身体感觉造成多大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身体感觉划归认同和排斥异者。因此,对社会成员身体感的观察需要以文化边界为切入点。其次,身体感虽与文化建构有密切的关联,但也与生活的物质环境互动密切。再次,身体接受的讯息在身体感网络中直接呈现为外在概念。在此层面上,需要特别重视表达身体感的各种概念。
史华罗和余舜德重视身体感的语言表达,显然是认为,以语言表达为中介可以将身体与其他研究题目联系起来。同时,描述身体感的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可能展示出多种身体感官的互动关系。两位学者都不再单独研究,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多学科的对话群体。在这两本群体完成的著作中,以对语言的关注为基础,将身体感与其他的研究议题进行了连接。如果将两本书对读,可见身体感及其语言表达被放置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之间,即社会和文化及其物质形式对人的塑造,以及人对社会和文化的调适和表达。
四、言说与触觉的回归
当关注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大多研究者,转向关注语言中对身体感觉的表达,强调整体的“身体感”,而非单个的感觉类型时,许小丽(Elisabeth Hsu)则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她指出,如果对尸体的视觉探查是近代欧洲解剖学发展的中心因素的话,那么对活体的触觉探寻是中国古代医学出现时最重要的感觉因素。Elisabeth Hsu, “Tactility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in Context, 18-1, 2005, pp.7-34.这种将触觉作为中国医学、乃至身体文化的“特质”,并非是新论,这种“惊奇”,在17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叙述中就已经出现,而栗山茂久的研究,也展示出在“西方医学的源头”——希腊罗马医学中也有类似对于“脉搏”的探索,但其表达形式和历史发展却与中国的脉诊呈现了不同的方向。但是,许小丽不是要重复17世纪以来的论述,她试图强调触觉在中国医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她贡献给《体物入微》的《脉,视觉到听觉再到触觉诊查:运用“身体感”对汉代早期医学手稿的新解读》一文中,她讨论战国末期和汉代早期与脉学相关的三种出土文献,即张家山汉简《脉书》、马王堆帛书《脉法》和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指出张家山汉简《脉书》中提到的“相脉”似乎基本上是依赖于视觉的观察,但是对于此段文字中“视”的解释是否能将视觉与医学诊断联系起来,仍需斟酌。直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保存的淳于意的诊籍中,才将脉与内脏联系起来,“切脉”成为一种创新的诊脉方式,即通过触觉来感知“气”,这一变化使得气成为诊断和医学理论的重要概念。
在许小丽的新书中,她承认了自身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情结,1986年她刚刚进入中国研究这一领域,在阅读李约瑟的著作时,发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到了20年后,她依然觉得困惑:“脉”的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诊脉之后用来表达触碰脉的感觉的术语又意味着什么?从战国晚期到汉代,气和身体的概念又意味着什么?病因的理论是怎样的系统,诊断是否一定要确认疾病的原因?带着这些疑问,她翻译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关于淳于意记载的全文,并对前十个医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Elisabeth Hsu, Pulse Diagnosis in Early Chinese Medicine: the Telling Tou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当她将研究主题回归到单个的身体感觉类别时,她并未遗忘语言的意义,只是她并不止追寻语言可译性(Translatability)的理论,而是将其变成了一种实践。她强调感觉人类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其证明了感觉不只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在追问关于脉、气和病因理论的语言表达之前,先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段记载本身的文本问题。《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录淳于意在几乎遭遇“刑狱之灾”之后,在面对汉代皇帝的询问时,讲述其治疗病患的经历与诊病过程。许小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文体与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联系,但她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所差异,即《封诊式》是假设性的案件,而淳于意的诊籍则是对过去的事件的叙述并涉及历史人物。在淳于意的叙述中,他的治疗判断都是准确的,并能治好病人,这些案例显然被选择过,以来彰显其医术。同时每个医案也呈现出类似的叙述模式,包括对疾病名称的叙述、诊脉的所得以及造成疾病原因的分析。在详细地分析了这十个医案之后,许小丽希望能进一步讨论前面提出的问题,淳于意在诊脉时感受到了什么?他如何将自己的触觉经验用言语表述并与他人交流?他使用的这些术语是否与其生活经验相关?这些术语所指的准确意思并不可知的情况下,是否能建立起一种感觉性的联系?这些术语是否有一些共同的重复性的特征?
许小丽指出,淳于意通过关于气的语言来描述他在诊脉时的触觉,也就是说,气并非仅仅是一种实体、一种概念,同时也是一种表达身体感觉的语言载体。同时,通过与早期脉学文献的比较,许小丽认为淳于意在选择其描述诊脉时关于脉动的词汇,体现出他是一个尝试调和不同学说的人。同时,通过与生物医学关于征候和病因关系的比较,许小丽认为,与其说淳于意通过脉诊建立起的一种关于诊断的叙述,不如说他建立的是一种关于预后的叙述,也就是并非每一种医学都需要找到造成疾病的确切原因,才能治愈患者。
在许小丽之后,中国古代医学史中对触觉的关注不再局限于脉诊。黃薇湘(Margaret Wee-Siang Ng)讨论接生时的触觉描述,同时好奇女医在接生时的身体感觉是如何传递给她们的学生的?Margaret Wee-Siang Ng, “Healing Hands: A Study of Tactile Touch in Medical Writings in Song and Ming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anel on“Making Senses of the Chinese Textual Tradition Problems of Experience, Language and Knowledge” of AAS-ICAS Joint Conference, March 31th-April 3rd, 2011, Honolulu, Hawai i.针灸、伤科、骨科、按摩等等医疗实践中的触觉体验对知识研究意味着什么,都还有待探索。
五、余论:走向日常的言语与身体
当把Barbara Duden的问题与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的身体联系起来,身体的现代性与追寻过去人们对身体感知的问题,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如果我们假设,身体的现代性是一个在全世界“扩张”的过程,那么被它遮蔽的不同地域的身体世界,是否都以知觉为基础?在他们自身的历史中,不同的感觉是否有权力代谢或交替的过程?在这种身体的现代性在不同的地域扩展时,视觉是否都扮演了“优先性”的角色?视觉与现代身体的故事,是只有一种叙事,还是其中也充满了各种意外的叙述。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当我们尝试理解过去不同地域的身体感觉时,不仅仅是“古今”的差别,却也是不同地域文化表达方式的呈现。
于是,一个比较身体史的问题逐渐变成了一个“语言”的问题。正如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一书的开端所引用的“罗生门”式的故事,不同的语言承载着多元的文化意义,讲述着身体的不同的故事,同时再建构着身体的感觉。
但当我们把研究的对象落回到“具体”的人之上时,身体的观念与感觉之间是否可以截然分开?强制将所谓身体感与文化相联系,所谓的“身体感”范畴可能只是空洞的言辞,而文化研究也落入到了“还原论”的囹圄之中。近来,Joy Parr尝试找寻沟通社会身体与感觉化身体的概念空间。Joy Parr, “Notes for a More Sensuous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anada: The Timely, the Tacit and the Material Body,”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2-4, 2001, pp.720~745.同时,身体观、身体感和身体的行为实践之间是否能截然分开,也成为疑问。Mark Smith强调,感觉的历史其研究传统从社会史中受益匪浅,在语言转向之后感觉的历史应该更多向社会的向度回归。Mark Smith, “Making Sense of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7-1, 2003, pp.165~186. Idem, “Producing Sense, Consuming Sense, Making Sense: Perils and Prospects for Sensory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0-4, 2007, pp.841~858.正如,在Byron Good对哈佛医学院学生如何被训练以适应临床医学的需要的研究中,他强调一种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科学范式是当代美国医学知识和教育的中心,医学生通过观看、书写和讲话的训练,学会如何将其病人建构为医学的对象。Byron Good, “How Medicine Constructs its Objects,” Byron Good, Medicine,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知识和言语会重新塑造身体,并通过知识的再生产与规训,重新塑造身体的行为和感觉方式。如何在被语言再现的观念、感觉和社会行为之间找到一个讲述的平台,成为重要的问题。
“日常”成为了近来研究者共同选择的一个概念,余舜德和他的同仁们将与“身体感”对话的概念从“物质文化”发展到了“日常生活”,强调:“这类日常生活之身体感受的例子可谓无所不在,或因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琐碎,只有在跨文化的比较或生活环境出现显著变动时,我们方会发现这些感知项目是否得到满足,或我们是否具有辨认、判断它们所传递的讯息之能力,实密切影响着我们能否悠游、生存于这个世界。”余舜德:《〈“日常生活的身体感”专号〉导言》,《考古人类学刊》2011年第74期。在他们的论述中,日常生活成为身体感塑造、形成进而造成文化差异的运作场域,同时也成为一个不断重新“生产”身体感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创造着身体文化的持久性,同时也产生着种种差异。同时,对身体感的文化探索,也成为将“日常生活性”(Everydayness)具体化的过程。延续之前的研究路径,他们依然特别重视文化中表达身体感的观念概念或言辞,比如“虚”“威仪”“烦”“舒适”“洁净”“现代感”。当人类学学者们从Pierre Bourdieu, Henri Lefebvre,Michel de Certeau,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和Margaret Lock处获得灵感时,历史学家也在自身的学术脉络中更加重视“日常生活”的意义。无论是德国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学派,还是Peter Stearns的倡导,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本来都是作为反思“结构化”或者“社会科学化”的社会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文化史的推进过程中,日常生活性因其与实践的密切关系,亦成为反思文化史的重要路径。在Alf Lüdtke的研究中,experience本就是重要的概念,他研究纳粹时期的工人,试图在宏大的政治经济形势之下剥离出群体经验的塑形过程,及其与日常世界之关联。Alf Lüdtke, “What Happened to the ‘Fiery Red Glow? Workers Experiences and German Fascism”, Alf Lüdtke ed., William Templer trans.,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98~251.Peter Stearns则从一开始,就将身体感觉(特别以嗅觉为例)作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对象。Peter Stearns,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 Whys and Hows”, Peter Stearns ed., A Day in the Life: Studying Daily Life through Histor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6, pp.1~18.同时日常生活史亦试图反思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简单化叙述。在这些论述之中,现代性不再是社会性和观念性的变革,同时也是在特定时空之下经验和身体感觉的塑造。简美玲对苗族村寨烦闷(Rat)的讨论,就是通过反思其与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单调与无聊状态的差异,强调烦闷并只是现代化造成的,同时也是“是以有经验能力的身体,所编织的网络来面对个人安身立命的群体与世界。”简美玲:《烦闷、日常与黔东南高地村寨Hmub人的游方》,《考古人类学刊》第74期。
因此,“日常生活性”(Everydayness)或者“社会的回归”提供了另一种相反的路径。之前的研究只展示社会和文化塑造身体的一面,身体仅被视为文化表达的载体。身体与文化的互动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正如Emily Thompson的研究揭示了身体感觉及对其的观念探讨,可以重塑人们生活和实践的空间,揭示出身体感实在化的一条路径。她承袭Richard Leppert试图打通视觉和听觉之间的联系的路径,通过声音对音乐的再现,讨论身体的社会意义及其欲望被激起与规训的过程。Richard Leppert, The Sight of Sound: Mus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她的研究展示出对声音的探索和控制如何塑造了建筑的空间乃至城市的空间。Emily Thompson,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 MIT Press, 2004.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运作及其造成的文化表达,究竟是身体感实在化的一种中介,还是其本身就是身体感实在化的一部分,是值得一再追问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将身体和语言的互动转化为理解行动者的关键性切入点。我们也许不应忘记Alain Corbin的教诲,即感觉史通过对表象和情感的追寻,寻找社会行为背后的意义。这种努力也将长时段或者地区的历史重新落回到具体和确实的文化和社会场景中,也将确实和谨慎重新放回到历史解释之中。Alain Corbin,“Intervention au Colloque de New York Universit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5-2, 2002, pp.114~115.在Alain Corbin获得2000年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aise)颁发的贝古尔大奖(Grand prix Gobert)后,纽约大学的法国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French Studies at NYU)其研究组织了一场专门的研讨会,本文是Alain Corbin在会议最后对这些讨论进行的回应。对文中引述的观点,同卷Sima Godfrey的文章有详细的阐述,见Sima Godfrey, “Alain Corbin: Making Sense of French History,” pp.381~398. 在这里,身体感不再是区分传统与现代性、或者不同文化认识的概念工具,而是找回历史解释中的多样和具体的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