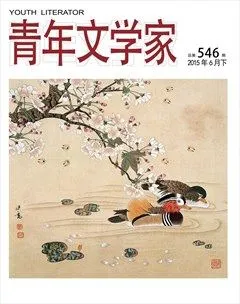卡夫卡《变形记》之多维解读
2015-05-09孙雅洁
孙雅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8-0-02
卡夫卡《变形记》一文,经翻译仅仅三万余字,却还原出了一个真切的世界。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内心独白给我们以启发,或许只有当人不再站立在人类中间时,才能真正认识到何为人。下面试图从六个层面谈谈阅读了本书之后的感想。
首先是人类中心思想。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便以自己的劳动不断改变着这个客观世界。从最初的游牧、畜牧到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建成与发展,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地膨胀,以至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我们之所以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已经与自然本身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人类社会建成之前,地球本就分布着各种植物、动物,各自区分又分享着领地。而人类将自己存在的空间定为一种绝对的界限,凡是在此界限之内的都是只属于人的世界。故而在发现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虫之后将其隔离,或称囚禁在自己的房间之内,在最后更是想要把他驱逐出他自己的家。因为建筑——这种人类文明的产物,只适宜于人类居住,并不属于除了人之外的其它生物。除了对于空间的占有,人类中心思想还体现在对自身智慧水平感到的绝对优越性。人们自然地认为人类是具有高智慧的生物,而将其它生物当做低能、没有思考力的,继而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可以将别的生物玩弄于股掌之内。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也描述了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他的父母、妹妹不同他讲话,认为他不具有理解力。而事实上,此时的格里高尔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他能够明白家人所谈论的话,为他们的处境担心着;十分照顾家人的感受,将自己隐藏起来;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依旧醉心于妹妹的小提琴声,而那些房客却早已不耐烦……这让我联想到《庄子》中的一段:“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虽然格里高尔的智力和理解力不排除是因为他曾经是人,但是正因为此他才有机会去代甲虫说话,就如同庄子一样,让别的处于失语状态的生物拥有了发言权。
第二是人际之间亲情的淡漠。无论是在中国或外国的传统家庭中,父亲更倾向于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可能源于男性性格中天生带有的控制欲,无论是面对妻子或是自己的子女以至于外人,從内心深处都不喜欢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因而在亲情表达上往往会有些冷漠或不如母亲那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或许因为自己亲自孕育了子女,母亲对于孩子的关心和割舍不下往往更强烈。但是母亲的爱依旧超越不了某些的界限,母亲对于孩子的爱建立在符合或不太偏离于自己正常接受范度之内。对于一些畸形或有这样那样缺陷的孩子,母亲虽是不忍,但是与其他孩子相比所给予的爱也是有差别的。而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更是可亲可疏。若是说得直白一点,一个人的价值在于被需要,而他所得到的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过是对在他身上索取的东西的一种回报。一旦这种被需要不复存在了,那么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也会逐渐走向破裂,这个人其实也就“死”了。在最初的时期,格里高尔拼命地努力工作以偿还父母欠下的债务,还努力攒钱让喜爱小提琴、梦想着能够进入音乐学院的妹妹得偿所愿。可是一旦他变成了甲虫,他的父亲对他又推又搡、毫无耐心,不留情地用苹果砸他;他的母亲鼓足勇气想要来看看他却几次被他的外表所吓到;他善解人意的妹妹最开始还十分贴心地照顾他,最后却任他住在落满尘土的屋子里、承受饥饿以至于身体干瘪,甚至宣布要把他赶出去……这种种最终将格里高尔逼上了绝路,而讽刺的是,格里高尔之死对于他的家庭似乎是一种解脱。在他死的那天,他的家人们坐上电车去郊外放松,他出落得愈发美丽的妹妹的婚事才是一家人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不如说是失去利用价值的格里高尔,他是被边缘化、被遗弃的人,死亡是他唯一的出路。
第三是合理存在与不合理存在的问题。所谓害虫与益虫之分,不过是人类强加给昆虫的。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合理。凡是自然界孕育出来的事物,对于自然本身来说都是平等的。在自然视野中,没有善与恶、有用与有害的区分。在《变形记》中,人们将甲虫定义为,即使不是有害的也是无益、丑陋,应该被驱逐的。人类习惯性地凭借着自身的好恶去判定一个生物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在人类的生存空间之中。因而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只能将自己躲避在阴暗的沙发之下,用床单将自己完全地遮住。即使这样,也无法改变他被驱逐的命运。试想一下,如果格里高尔变成的是一只小猫或者小狗之类,是否他的命运会有所不同。人们常说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实际上不免是一句空话。这里的动物是经过人选择、人类认为合理的存在,并不包括老鼠、甲虫、蜘蛛这一类。人们可以允许猫、狗、小白兔、鹦鹉等生存在自己的空间之内,却对于蟑螂、苍蝇之类唯恐除之不尽、避之不及。对于植物亦是如此,人们在花园里种上名贵的郁金香,在田地里布满金色麦浪,却吝啬于给不知名的小草一席之地——尽管这原本可能就是属于他们的土地。在人类给自己圈定的范围内,天然地给万物划定了是否应该存在在这里的界限。而这个界限虽是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却对生物个体带着毁灭性,而这种不公平依旧决定着、主宰着弱势生物的命运。凡是人所不喜的,便都是不应在此空间存在的。人占据了自然,便拥有了决定存在合理性的权力。对于没有可利用性的或长得丑陋的,便毫不留情地驱赶、扑杀。或许人类自身应该思考,是否如此具有侵略性的自己才是最不合理的存在。
第四是对美与丑的判定。人是感性与理性相互作用着的物种,对于美与丑的判定更多的是凭借自身的直观感受。美是无法被定义的,但是通常美与丑的区分在于能否让人的内心产生愉悦的感受。从原始人开始,人类就拥有着向美的倾向,她们已经会用兽骨或是兽牙做成项链等美化自己。这种向美的特性让美的人更容易受到青睐,从而生存繁衍下去。而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却是被认为丑陋得难以忍受,即使他的父母也无法正视于他。显然大多数人面对甲虫,而且是放大了数十倍的甲虫是难以拥有愉悦的体验的。而这种美与丑的决定权,只在于人类。殊不知,对于甲虫,或是其它物种来说,格里高尔的外表也许正是他们所欣赏、羡慕的。当然,也会有人说美与丑不仅仅在于表象,更在于内心。但所谓心灵美,或许只是人虚伪性的一种折射。对于一个外貌不佳的人,人们内心反感着他的外表,却因为权力者所推行的社会价值观念而将其树立为楷模,以对心灵美的夸赞来掩饰内心的嫌恶。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人们为他的行为而赞叹,为他的死亡而惋惜。但是这只是一种局外人的姿态,若是设想自己是那个美丽动人而又青春的艾丝美拉达,真的愿意委身于那个又老又丑的卡西莫多吗?以美德来掩饰、标榜自己或许是恻隐之心,或许只是一张人皮面具。其实对美的欣赏和追求是人的本能,是人感性认识的直观产物。这种体验是一种向前的选择性,也是人类向着更优质方向发展的保证。“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性在人这里同样适用,而人就是自己的刽子手。显然,无论格里高尔保持着多么美好的内心品质,他也终究不免沦为美与丑的牺牲品,他也是被“人”杀死的“人”。
第五是暴力与冷暴力倾向。对他人、对自然采取暴力或冷暴力手段,是人惯用的排异伎俩。弱势的“人”和自然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之中,他们被扼住了喉管,在强力之下苦苦挣扎。《尚书·舜典》中所书,“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种天下大同,以音乐感化万物的理想社会也确实仅仅存在于人的理想之中。而且人的矛盾性与可笑,也在于总希望自己被高阶群体温柔宽待,对自己之下的往往随意践踏。优越感赋予了他们行使暴力的权力,也使他们成为了施暴的对象。在格里高尔做旅行推销员的时候,他被老板肆意地剥削劳动价值,甚至那个“既无骨气又愚蠢不堪”的老板心腹都可以责难他,这是他身为人时所承受的暴力。而在他变成甲虫之后这种情况则更为糟糕:他的父亲丝毫不顾忌亲情,粗暴地对待他,砸苹果以至于陷进他的身体、听任苹果与他的伤口一道腐烂。与暴力相比,冷暴力或许更能摧残人心。格里高尔被区别于正常人的世界之外,同那些没用的杂物一起被弃置在落满尘土的房间里。他被冷落、失去交流的权利,他发出的呐喊与辩白成为可厌的噪音,最终自甘于永远的沉寂。其实不仅仅是他,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物,都處于不自觉的施暴与受暴之中,以施暴来平衡受暴,倒也是一种有趣的和谐。以他的父亲为例,父亲从安逸的晚年生活中走出来,不得不去给银行做杂役。从父亲的照片和家常举止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有很强自尊心和优越感的人,却不得不去承受银行职员的眼色。而回到家,他把这种怒气、怨气全都施加给努力想要讨得自己欢心的格里高尔。与其说这是一种不公平,倒不如说这恰恰是一种变态的公平。
第六是人的脆弱性。人对于其他生物的排异行为,归根结底,更多的是源于人天性中所带有的恐惧感和畏惧感。虽然自莎士比亚,人类早已宣称自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是这种自我膨胀并不能改变人类自身具有脆弱性的事实。人也不过是自然中的一粒粟谷而已,自然自带着让人感到敬畏的力量。格里高尔的家人将变成甲虫的他囚禁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想要把他驱赶出去,正是人自我防御机制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把蛾子、蜘蛛、蛇之类驱逐出自己的生活范围,更多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让人感到害怕。人对于顺从于自己的生物,如牛羊、猫狗、鸡鸭,往往怀抱着极大的宽容性。因为这些生物,人类能够掌握他们的控制权,自然也就不易产生畏惧感。而事实上,面对大多数的自然生物,人都处于一种深深的无力之中。对于这种不可掌控感,人类只能凭借自身体型或工具上的优势,强行将他们驱逐出去,而这种过激的反应更多的不过是自身恐惧的外现。除了对不可控因素的害怕,人的脆弱还在于其社会性。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时时刻刻希望自己身处于社会这个群体之中,不会被异化对待。一个特立独行,与普适性社会标准相对立的人是无法继续在社会中存活下去的,只能被孤立、被放逐,最终走向灭亡。格里高尔其实是一个背离了社会标准的人,为社会认定的“正常人”所不容。格里高尔自己也明白了这一点,他为了不让家人难堪,将自己躲藏在沙发下面,远离临街的窗户。他听任自己一天天地干瘪下去,最终在家人的遗弃中孤独地死去。究竟是疯子疯了,傻子傻了,还是整个世界疯了、傻了;是世界遗弃了“我”,还是“我”遗弃了这个世界?
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解读并不局限在这些方面,格里高尔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的独特视角。格里高尔实际上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正是因为这种被边缘化,才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