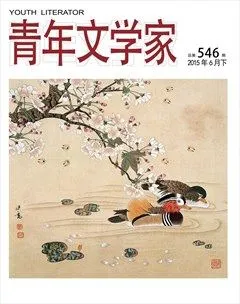顺承与反抗
2015-05-09陈向普
摘 要: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是女性存在的核心,在韦尔蒂的小说中孝顺的女儿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本文通过对比《乐观者的女儿》和《六月演奏会》中的两对母女,特别是在做孝顺的女儿和做自己之间做着艰难选择的女儿们,反映她们选择做孝顺女儿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关键词:《乐观者的女儿》;女性主义;韦尔蒂
作者简介:陈向普(1975.11-),女,大连外国语大学,河南洛阳人,应用英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8-0-02
《乐观者的女儿》是韦尔蒂获得普利策奖的长篇小说,作品充满了丰富的女性主义色彩。她以看似平淡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南方家庭的内部矛盾。故事的很大部分都是女儿劳雷尔对于自己父母的回忆。其中最让读者感到震撼的当数第三部分结尾处对于过去漫长的回忆。在母亲病重时,劳雷尔和父亲一样,毫无能力把母亲从病痛中解救出来,更不能击退死神的逼进。家庭,朋友甚至牧师都不能给母亲贝基以安慰,最后贝基在绝望中死去。在去世前,母亲对着劳雷尔说出了那段最震惊的话,“你本可以挽救你的母亲,但你却只是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我为你感到绝望 ”。对于聪颖,敏感的劳雷尔,贝基临死之言肯定深深地伤到了她。这个部分暗示了很多女性选择做孝顺女儿所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劳雷尔。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母女关系以及强大的女性传统从一代传到下一代都是很难界定的。然而,在韦尔蒂的小说中,期待使得很多女儿在接受女性传统方面显得尤其困难。当然和谐快乐的母女关系也是存在的,但是贝基和劳雷尔的关系却不是如此。我们无从知道贝基的观点,因为在小说开始的十年前她就去世了。邻居,朋友,她的丈夫和女儿的记忆再现了贝基的一生。在小说开始,麦凯尔瓦法官向医生描述他的眼疾时提到了自己的妻子。他是在修剪妻子的玫瑰時眼睛被刺伤的。他补充到,“贝基肯定会说我活该”。法官的假设反映出记忆中妻子典型的反应。
父亲总是会溺爱独生女儿,所以法官在女儿婚礼上的大肆铺张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是二战的困难时期,劳雷尔的婚礼上还是有香槟和从新奥尔良请来的黑人乐队。在妻子的眼中,法官的行为“完全是铺张浪费,幼稚”。当回忆道这一段时,劳雷尔,就像个孝顺的女儿,完全站在妈妈的立场上。然而她的两句话却值得推敲,一句是直接的宣告,“妈妈是迷信的”,完整的意思在接下来的假设句中完全体现出来,“妈妈或许是认为过度张扬自己的幸福是不幸的”。如果是这样,贝基让所有的幸福瞬间都显得很可疑。上帝会惩罚看起来过于幸福的人;过度沉浸在快乐中也会使幸福变味。如果劳雷尔关于母亲的迷信的说法属实,那么早在劳雷尔的婚礼上母亲的表现就为这个幸福的时刻施下了最咒语,暗示着后来这种迷信的应验:劳雷尔和菲利普的婚姻幸福美满,然而菲利普的死亡结束了这种幸福。纵观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劳雷尔对于自己童年的回忆在贝基作为年轻女性的回忆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年轻时的贝基很独立,比自己的哥哥们都勇敢。随着她年轻时故事的展开,读者发现很少有女性能够和贝基相比。卡罗尔吉利根在中说过,“敏感于被人的需求并承担起照顾别人的责任使得女性能够注意到不同自己的其他的声音,在做决定时也会考虑到别人的观点”。而梅·萨藤曾经说过,“妈妈们很温柔,毫无疑问,我们身体里母性的部分能够给予这种温柔,而我们身体中孩子的部分渴望感受到这种温柔”。不管是梅·萨藤还是卡罗尔吉利根,她们关于女性,关于母亲的观点到了今天也不过时。但是如果这个标准套在独立,勇敢,坚韧的贝基身上,那种母亲应有的温柔,敏感如果不是完全缺失的,至少也是次要的。
对于一个不敏感,更不温柔的,甚至在临死还要诅咒自己女儿的贝基来说,劳雷尔是孝顺的。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劳雷尔的记忆重现,她开始重新审视父母,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缺陷,同时也重新审视作为孝顺女儿的角色。自始至终劳雷尔生成父母是相爱的。但在最后,贝基不仅否认了女儿,也否认了丈夫。丈夫承诺将死的贝基他会带她回老家,对于这些无用的承诺,贝基喊道,“骗子,骗子”。在一家人执手相对无言后,贝基朝着劳雷尔说出了最后的诅咒,因为女儿没能够完全认同和参与自己作为将死之人的绝望和痛苦。韦尔蒂大部分小说中的女儿都是母亲孝顺的女儿,至少在母亲去世前。父母有时要求过多,就像小说中的贝基的朋友把法官的再婚归罪于劳雷尔;认为女儿们就应该呆在家里照顾父母,而不是跑到芝加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在《金苹果》,特别是《六月演奏会》和《漫游者》中,读者又看到了孝顺女儿,维吉的身影。《乐观者的女儿》和《漫游者》极为相似。两部作品都关于于一个亲人的故去;两个故事都聚焦于葬礼,在葬礼上聚在一起的邻居们说起逝者时的夸张言语让孝顺的女儿困惑不已,不知该不该说出与他们观点相反的实情;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故事都有强势的母亲和孝顺的女儿。故事中母亲凯蒂和贝基有明显的区别。贝基大学毕业,嫁于法官,住在城里;而凯蒂住在城郊,嫁于农夫,靠卖花草和冰激凌为生。尽管两部作品相隔22年,但却有着共同的主题:强势的母亲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女儿就应该成为她们期望的那样。
在《六月演奏会》中,女儿维吉开始时并不是个孝顺的女儿。她是钢琴老师的得以门生,并有一段甜蜜的恋情;甚至成为了钢琴师。然后她离开了家乡去了孟菲斯。读者不知道在那里她呆了多久,做了什么。只是在她17岁时她回来了,母亲迎接她的是,“你回来的刚刚好,该挤奶了”然后就解开帽子,扔在他俩之间的地上,盯着她的女儿。如果维吉有伤心,难过或者绝望的故事要倾诉,分享,她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如果她希望趴在妈妈的怀里痛哭一场,她也没有能够这样做。如果她衣锦还乡,没有人祝贺欢呼。实际上,痛苦是母亲的特权,但是母亲不是为了女儿哭泣,而是为了丈夫和儿子。叙事者说,“在她的房子里,除了她没有人可以哭,只有她可以,为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因为他们都离开了”。凯蒂和为维吉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着,直到凯蒂死亡的晚上和她葬礼的那天。这时的凯蒂再也不能种花和水果到路边去卖了。因为中风,她只是整天坐在那里,等待着维吉下班回家。最后当维吉回来时,我们看到这样的对话:
凯蒂:看看太阳都到哪里了……
维吉:我看到了,妈妈
维吉到家晚了,在她还没来得急换下高跟鞋和上班装时,凯蒂已经开始列举她的任务了,维吉什么也没说,把念叨着“我已经自己呆了一天了”的凯蒂哄金了屋子。凯蒂在一个星期天去世的,或许有个四十几岁的孝顺女儿对于凯蒂来说不只是个福气。但是母亲的去世并没有终结维吉的角色。第二天维吉被要求观看母亲的身体,当她拒绝时,人们竟说“你真不配有这样好的妈妈”。像劳雷尔一样,维吉也不再做孝顺的女儿,而是开始做自己。她的决定来得很自然,没有准备,没有预兆。有人问,“你要留在这吗,维吉”她回答,“明早就离开”。
在美国南方,更多的时候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不得不照顾家庭。在刻画凯蒂和维吉时,韦尔蒂承认女儿们被母亲们的要求和期望死死地禁锢住。女儿们或许在母亲们活着的时候无法原谅她们,但当母亲去世时,女儿们才能够真正离开家,开始自己的人生。所以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要想不再是个孝顺的女儿,成为独立的个体,母亲必须死去。如果说在母亲们活着时,女儿们是她们不断地要求的受害者,那么去世后的母亲成了受害者。去世使得母亲把自己的女儿从一切日常的繁琐中解放了出来。
对于韦尔蒂作品的女性解读可以发现韦尔蒂的焦点在于对母亲的态度,在于女儿要寻觅不同于母亲的独立的生活。她们不想变成她们母亲那样的人,通过离开家乡到北方接受教育,她们俨然已经成为了完全不一样的独立的人。
母亲的去世重新定位了女儿的角色。她们的生命是她们自己的,她们的角色不再是在母亲的家里打理家务的孝顺的女儿们。女儿顺承母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反抗母亲也不是总是如此明显的。维吉和劳雷尔离开了他们母亲的家,甚至是母亲的城市。反抗母亲是孝顺女儿想要独立,想要成为自己的必要的第一步。孝顺女儿的故事对很多先是认同母亲后来反抗母亲的女性来说并不陌生,正如有评论者所说,“我想只有当你的父母都去世时,你才成为你自己。说起来很残忍,但却是事实”,而更恐怖的是对于女儿们来说这尤其是事实。
参考文献:
[1]Eudora Welty,The Optimists Daugh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