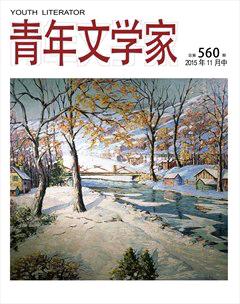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雪国》中男权中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2015-05-09黎宏博
摘 要: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一系列作品中对日本女性之美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作家在《雪国》中塑造的女性驹子,更成为了世界文坛中的经典形象。本文试图从男权中心视角这一角度,分析这一女性形象获得成功的原因。作者在文中对驹子的赞美,无不是透过男性视角来对女性的观察,迎合了男性的审美期待,反映了女性在日本社会中的低下地位。
关键词:男权中心;女性;欣赏;审美期待
作者简介:黎宏博(1985-),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2-0-01
《雪国》讲述了无所事事的富二代岛村三次来到雪国,与艺妓驹子交往的爱情故事。驹子身世悲惨,15岁被卖到东京做女招待,被赎身后,恩主又染病去世。与师傅之子行男订婚后,未婚夫又身染重病。为未婚夫治病,驹子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在风月场上强颜欢笑,内心无比痛苦。虽然如此努力,却仍未能挽回行男病死的结局。驹子对岛村一往情深,希望每年能够与之相聚,却在岛村眼里视为徒劳,终于被岛村厌倦抛弃。
一、对驹子的赞美
在以往对《雪国》的先行研究中,无不对驹子这一形象大加欣赏与赞美。具体内容归纳如下:
1.牺牲精神
例:驹子为未婚夫筹钱治病,不惜沦为艺妓,强忍苦痛卖笑。
2.不对等的爱情
例:“多悲伤啊!”“你了解我的心情吗?”“唯有女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去爱一个人啊。”
3.徒劳之美
例:“驹子恪守婚约也罢,甚至卖身让他疗养也罢,这一切不是徒劳又是什么呢?”;“岛村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唉,这个女人在迷恋着我呢。这又是多么可悲啊。”
4.洁净
例:“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她过于洁净了”。
二、驹子被赞美,被欣赏的原因
1.牺牲精神
驹子身世之悲惨本已令人同情,又为给未婚夫筹钱治病做出巨大牺牲。作者对其牺牲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但在歌颂的背后,无意识地透露出作者站在男权中心视角上对女性道德的期待。驹子只是与行男有婚约,就必须牺牲自己最美丽的年华,甚至要通过沦为艺妓这样一种极端的途径来挽救行男,随着道德的光辉升至极致,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亦丧失殆尽,自身完全淪为男性的附庸,生命的意义完全寄托在男性身上,而这一点正是作者所热情歌颂的。同时,既迎合了广大读者的道德审美需求,又使男性读者男权中心观念及被服务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2.不对等的爱情
驹子在岛村有家室的情况下,明知自己与岛村的爱情没有结果,岛村终将抛弃自己而去,却仍像飞蛾扑火般不管不顾,热烈地爱着对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是一种不要求对方的、单方面的“无偿之爱”。作者通过将二人的爱情不对等化,将爱情中女性的地位置于了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而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中,男性正是通过强化女性在总体上低于男性的自我评价,来导致女性自卑感的产生,从而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丽特在《性的政治》中,将此描述为“性的政治”的策略,即男性试图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女性地位的贬低,来明确两性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作者在小说中对二人关系的这一设置,无疑起到了这一作用,巩固了男权中心社会,同时也迎合了男性读者的阅读期待。
3.徒劳之美
驹子虽身世可怜,却苦练琴艺,学习文学,这些努力在岛村看来全然无用。而驹子对岛村的深恋也毫无任何结果,努力赚钱为行男治病也未能挽回行男的生命。徒劳的努力换来了驹子的悲剧命运。在这里,作者仍然是以男权中心视角出发来创作,将女性定位在弱势的地位,赋予女性以艰难的生存状态,使其无论如都无法挣脱悲剧命运。而岛村的冷漠、无谓,更强化了男性地位,凸显出女性的悲剧色彩。
4.洁净
小说中几次强调了驹子的洁净,不论是身体的洁净还是日常生活中。而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身体洁净的描写通常被上升到精神层面,要承担道德的重负,暗示着女性心灵的纯洁,如《红楼梦》中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其对女性洁净的赞美,实则隐喻着男权社会对妇女道德的要求,背后隐含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心理,而这种占有欲又是排他的,从贾宝玉的另一句话中即可看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在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赤裸裸地由“纯洁”转化为“贞洁”。而川端通过岛村对驹子的观察来赞美其洁净,同样隐喻着驹子对岛村爱情的纯真、无私,进一步满足了男权主义心理对女性的心理期待。与此相对,岛村在已有家室的情况下来到雪国寻花问柳,却没有在道德层面受到批判,而是被作者有意无意淡化,两性地位之不平等更加凸显。
三、结论
《雪国》的作者在作品中以高度的热情对女性美和女性的高尚给予了欣赏和赞美,并对女性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与此同时,在赞美与同情的背后,可以窥见另一种“叙事话语”,即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宣扬或固守,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对男权中心及男尊女卑的认同,从而站在男权中心视角下,依照男性的审美观对女性进行要求、审视。而作者对消费者的脉搏把握地也十分精准,迎合了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的阅读期待,为他们塑造了一个符合男性心理的完美女性形象,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享有权、裁判权、占有欲、自由感和优越感,使读者在这一阅读的狂欢中得到了男权心理的满足,从而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