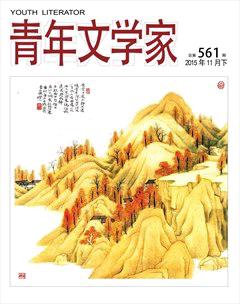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看民族志研究的发展
2015-05-09刘亚玲
刘亚玲
摘 要:民族志研究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规范,现已广泛运用于众多学科。民族志主要强调要深入田野,与当地人一起生活,通过观察和互动体验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并将其揭示出来。因此研究者与作为被研究者的“他者”成为了民族志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因素。随着民族志研究经历了各个思潮、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研究者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互动也经历了演变,后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客观存在的、被研究的对象,而是与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共同建构意义世界。本文试图简要叙述民族志的概念,其5个时期的主要认识论及这对重要概念的演变等,了解民族志研究的概貌。
关键词:民族志研究;意义世界;研究者;他者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3--02
一、民族志研究的定义
民族志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早期民族志研究发源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其他地区残存的“原始文化”所产生的兴趣。通过对一些原始部落进行调查,他们发现那些被西方社会人文比较“落后”的民族实际上是人类进化链中的一个环节”[1]”。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其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化为方法与文体意义为一体的学术规范。
民族志的权威地位是由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确立起来的。马林诺夫斯基将科学实证精神贯彻于自己的田野工作中,尝试将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标准化。通过与特洛布里恩群岛岛民长达两年多的亲密接触,获得了“土著人”生活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整理土著人的生活资料,进而撰写关于他们的民族志。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者将他们的发现与先验的理论取向整合起来,以个人经验和科学权威为基础的学科合法性由此确立起来。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在现代主义背景下仍在占据着人类学中心位置,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
二、认识论观点下民族志发展的五个时期
目前民族志研究者对其历史分期暂时没有统一的划分,丹曾和林肯大致将之分为五个时期:传统期(1900-1950),现代主义期(1950-1970),领域模糊期(1970-1986),表征危机期(1986-1990),后现代主义期(1990至今)[2]。
传统期时的主导思想是实证主义。受到当时自然科学及盛行的量化研究的影响,研究者们认为应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个时候的民族志研究者讲述的故事通常带有几个特征:客观性,认为自己看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固定性,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永远不会变;永恒性,相信自己的作品永垂不朽;殖民性,以一种帝国主义的眼光从上至下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陈向明,2000)。
第二个时期是现代主义期,被认为是质性研究的黄金期。主导思潮是后实证主义,认为只有不断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把研究的结果进行证伪,才可能逐渐接近客观真理。第三个时期是领域模糊期。格尔茨指出,多元的、解释性的开放的角度已经代替过去人文社会学科里那种功能主义的、实证的、行为主义的探究方式。应以文化呈现及意义解释为出发点,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描述,对其象征符号进行意义解释。
接下来是表征危机期,研究者感到了语言表述中存在的危机,开始对语言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等知识论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们在这一时期已经完成了对传统人类学经典的彻底摧毁,曾经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效度”、“信度”、“客观性”等问题重新变成了问题”[3]。
最后一个时期是后现代主义时期。民族志研究出现更加多元的局面,注重不同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方法也更兼收并蓄。
三、研究者与“他者”关系演变
在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和他者是一对重要的概念。通过对这一对概念演变的阐释,也可揭露出民族志视角在各个时期的变化。为何选用“他者”而不使用“被研究者”,也是民族志方法论演变的结果。辩证地看,在民族志最重要的田野调查中,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根本上并不单是一个写作问题,还是研究者在田野中如何询问、探索、倾听、观察和体验研究对象的生活和关注点。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研究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和科学仪器,直接观察到“客观”、“真实”的“事实”。主动的研究者可以对被动的被研究者进行观察,从而获得有关知识。这种观点基本遵从的是实证主义的思路,认为主体和客体是可以分离的,只有可以感觉到的才是真实存在的,研究者只要按照严格的观察程序就可获得可观、真实地被研究者信息。
从象征互动主义的理论角度来看,个人的行为是人际互动的结果(Blumer,1969)。人类的知识产生于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过程中,理解只有通过人际的互动才可能呈现出来。因此,研究者必须要与“被研究者”进行互动才能获得对方的意义建构。
“存在主义社会学认为若要理解他人,则应和他人一起生活,亲身感受、接触、倾听和观看以理解他人的生活背景、生活事件和对此的观点。理解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在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对成为客体的自己的体验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4]。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经历被视为人类学家的专业标志。民族志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进行田野调查和记录田野笔记。从一方面看,研究者在田野调查时所处的立场源自他对生活的看法,其之前的经历、视角、理论基础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并促使他采取这种而不是另一种模式去感知、思考和探索。
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者在撰写田野笔记时一个常见的问题是,研究者不能始终保持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对民族志研究者来说,理论并不是简单的等待分析者通过社会事实逐一检验。分析中的每个过程就包括了理论和数据间的不断交流和反思,理论已经内化于数据中。因此,他们认为,研究者在建立田野事件和分析观点的联系之时,就已经创造了理论,而不是发现了理论。
因此,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不是客观、真实地存在于那里,等待研究者发现和揭示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共情等一起建构了意义世界,二者在研究者中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被研究者”是文化客位的视角,而“他者”则更多的是文化主位的观点。“他者”参与研究,通过与研究者互动也塑造了研究者的世界和身份。因此,现代的民族志研究更倾向于用“他者”而不是被研究者以澄清传统上人们对后者的偏见,以指称那些与研究者一起构建了研究意义的人们。
四、小结
民族志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人类学历史上的第一个实际性繁荣期。与英国泰勒式的被称为摇椅人类学的范式和方法论不同,现代的人类学及民族志研究更加注重研究者深入田野,记录田野笔记,与被研究文化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描述并阐释他们的生活事件、看待问题的视角等,揭示当地人的意义世界。同时研究者自身也不可能从研究中隐去,抹杀自己的先验,而要合理利用自身的前见,是自身的生活经历、理论视角更好地为研究服务。
注释:
[1]陈向明,质性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同上.
[3]同上.
[4]陈向明,质性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Blommaert Jan, Dong Jie,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 beginners guide[M], Tilburg University.
[2]DENZIN Norman K., LINCOLN Yvonna S..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 The Sage Publications, 1998.
[3]陈向明,质性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罗伯特·埃莫森,雷切尔·弗雷兹,琳达·肖著,符裕,何珉译. 如何做田野笔记[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罗素,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册)[M]. 商务印书馆,2013.
[6]张连海,从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演进转向与对垒[J]. 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