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老北京的“你”
2015-05-05崔亚珏
崔亚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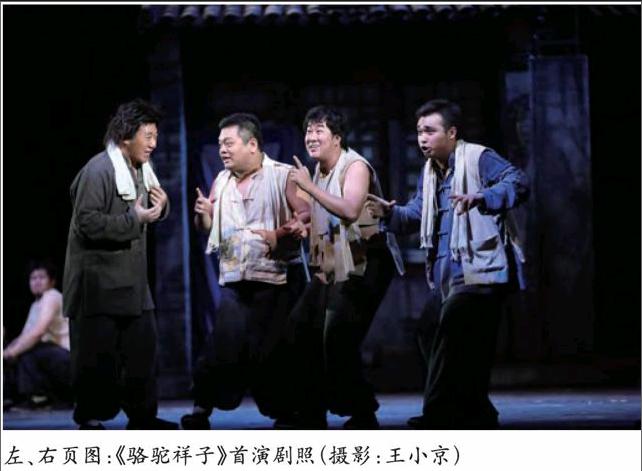

2014年6月25日,国家大剧院歌剧厅上演原创歌剧《骆驼祥子》,之前在微博、微信圈流传甚广的“急赤白脸地”的演唱提示,也终于让观众找到了它的出处所在。《骆驼祥子》虽然曾以众多的艺术形式进行改编,但与西方歌剧艺术的“碰撞”还是第一次。曾经。老舍先生以具有京腔京昧、幽默通俗的艺术语言和简洁有力的现实主义笔法塑造了祥子、虎妞等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艺术形象典型。也深刻地反映了老北京的市民生活与城市风貌,而在今日它的世界首演过后,也依然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回味。
不同于以往的民族歌剧,《骆驼祥子》以西方歌剧经典的形式的美学概念和美学标准为依据,发挥歌剧抒情性、戏剧性、交响性的特长,启用气势恢宏的西洋管弦乐队、美声歌唱演员及气势恢宏的合唱团。同时也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大三弦和唢呐等民族乐器,使作品在宏大的外在形式之下有了细腻的流露。其中的单弦曲调贯穿祥子这一角色始终,从自然音到半音化再到无调性,成为祥子命运一步步走向悲剧的“主导动机”。
虎妞勾引祥子的场景中,人物的复杂情感、忐忑与纠结在不同的层次中推进,极具表现力。而在虎妞之死的段落中,音乐以巨大的弧形表现了虎妞由虚弱难产的低沉无力。到后来对生命的呼唤、对祥子的留恋的大幅高潮,充满了“大歌剧”般的张力。在全剧中作曲家郭文景采用自己喜爱与惯用的创作手法,调动了各式各样的音乐语言来丰富人物的塑造。如在小福子圣咏般的咏叹调中引入了民歌《小白菜》的旋律,而在第七场的幕间合唱曲《北京城》当中,也引入了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的音调。唢呐的旋律在全剧中多次出现。成亲的“喜事”和送葬的丧事,都以唢呐作为引子。苍凉的音色让连喜事都让人觉得压抑与窒息,残酷与优美的并立在戏剧性的表现之余也直接预示了虎妞与祥子婚姻的悲剧结局。在全剧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中。也显现着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种方式使人观剧时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能够更加直接地超然于舞台现实情境而直达内心——当虎妞欢天喜地地唱道“我嫁了我喜欢的丈夫”的同时,祥子却感叹自己“娶了讨厌的母老虎”:当两人婚后闲逛庙会时,虎妞说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祥子却说:“我有力气,我可以拉车,我讨厌这样的生活。”两人的婚姻错位和生活的矛盾深刻而显著,比起最后凄惨的结局更具有悲剧色彩。
老舍先生的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丰厚文学底蕴为歌剧的创作与舞台呈现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在虎妞难产而死这一整个故事的悲剧顶点更是通过音乐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当言语不足以表达情感之时,是音乐使我们听到了她内心的复杂情绪与呼唤。她以独白式的口吻,让我们看到了她在诱骗祥子,假装怀孕等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来自内心深处对于爱情的向往,让人看到了这个“女汉子”也有着和其他女子一样的细腻而平凡的心愿。而通过虎妞这段咏叹调所唱的:“我爱你,请你原谅我的坏脾气,请原谅我逼你成亲欺骗你……我走后,天凉你要记得加衣……”那个泼辣的虎妞不见了。她的悔愧无力、复杂思绪和对于生命的留恋在她生命的最后时间里集中爆发,演员对于歌唱力度的控制与情感的掌控,使人对虎妞产生无限的怜悯与同情之余,也联想到另一位来自文学作品当中的经典女性形象——卡门,这两个“辣”女子都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她们自己眼中的爱情,而这爱情不仅没有给她们带来幸福,反而让她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们身上都具有对比极为强烈的戏剧性,现实与憧憬的极大反差让虎妞的音乐艺术形象呈现也完美地契合了西方歌剧中“爱、死、美”的欣赏诉求。而最后,祥子虽然没有死。但他已然成为游走的亡魂,“生”对于祥子来说是比死更残酷的状态,这对于观众而言是巨大的情感冲击与震撼。
我们常听到“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样一句话,我想,其“高”在于,它可以让人在现实的超脱之下对过往有回忆,对未来有憧憬。马勒曾说:“我的音乐是留给五十年后的。”而经典的故事与素材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在空间上则更具有超越性。78年前老舍先生留给我们的经典跨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它的意义就如威尔第歌剧《奥赛罗》、《麦克白》之于莎翁原作,其中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是当代人对于经典想象空间的扩展,成为我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以国际语言与本土特色对于歌剧艺术的坚守和延续。未来的中国歌剧艺术,只有继续以歌剧的通用语汇来与世界进行交流,才能够找到更多的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而在审美方面,要脱离对于单纯的听觉或视觉感官刺激的追求,才能通过艺术描摹人的情感、困惑与思考,通过音乐呈现来反思自己、展现自身的独特思考。除《骆驼祥子》之外,近年来如《燕子之歌》、《红河谷》等原创歌剧对于中国音乐语言国际化也正做出积极的尝试,展现出的艺术效果以超越语言表达的穿透力直抵人心。
有人说:“如今的时代社交环境空前丰富,文化选择也空前多样,那么我们还需要走进剧场欣赏歌剧吗?”而《骆驼祥子》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嗟叹不足而咏歌之”,歌剧是歌与声、词汇与想象融合的最高形式,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灵魂语言,在思想和情感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其他艺术形式无出其右。著名的指挥家丹尼尔-奥伦认为歌剧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不同的角色同时运用各自的特性音调歌唱,同时表现爱与恨、欢欣与痛苦,既能让全然不同的情感并存,又能达成高度和谐”。在歌剧演出现场,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家的咏唱,舞台布景进行视觉与听觉的联动,平面人物立体化的转换,让人无意识地生成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情感寄托。歌剧人物的爱恨与情仇、无奈与彷徨都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曾经或正在经受的心灵体验,当这些体验“无处安放”之时,歌剧便会“代替”我们这些“努力而认真活着的人们”去释放。
演出落幕后的北京城华灯璀璨,在阑珊之处,氤氲着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与情怀。回味起歌剧中出现的四合院、白塔、大碗茶、“兔儿爷”、京韵大鼓等“北京记忆”,这部歌剧让原作当中的人物与这些符号进行了跨时空的汇聚,为我们铺开了一幅城市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