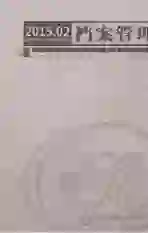战争与档案工作
2015-04-23潘未梅
潘未梅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档案工作,简要讨论了战争中档案工作的开展;此外,本文展示了如何从战争与档案工作的关系分析档案学的基本问题;另外,本文简略讨论了档案工作发展中与历史研究和辅政两者之间关系。
关键词:战争; 档案;加拿大;档案工作
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艾利·维索(Elie Wiesel)
(镌刻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入口处)
近年来,西方档案界对战争与档案的关注度逐渐提升,如,美国档案学者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x)分析了档案和战争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包括问责、档案的纪念品属性以及纪念品的档案属性、墓地,档案与战争、战争中的科技与档案;[1]希瑟·苏卡(Heather Soyka) 和艾略特·维尔切克(Eliot Wilczek)探讨了记录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挑战;[2]布鲁斯·蒙戈马利(Bruce P. Montgomery)研究了伊拉克战争中的伊拉克犹太档案的归还和归属权问题。[3]与西方档案界相比,我国档案界在对战争和档案的学术研究上成果较少。
本文将探讨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档案工作,尤其是加拿大远征军档案的收集。一方面希望可以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另一方面希望可以推动档案与战争和其他大型事件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将按照以下顺序展开:第一部分将概括“一战”爆发前加拿大档案工作的发展状况,以为后文提供背景;第二部分将介绍“一战”期间的加拿大档案工作;第三部分将讨论“一战”中加拿大档案工作为我们提出的若干问题。
1 “一战”爆发前的加拿大档案工作
“一战”爆发前,加拿大的档案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4]其显著特点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历史界,对建立国家档案馆的倡导和游说。[9]随着对政府文件管理需求的增加,档案工作开始由对历史档案的收集逐渐转向对政府文件的管理和系统接收。这一过程意味着加拿大档案工作由依附于历史学成长为关注档案本质的独立学科。
1842年独立之后,加拿大政府面临的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加拿大的国家认同感。这不仅意味着独立于英国和法国的独立意识,也意味着打破不同省、种族、宗教、阶层等之间的壁垒以形成国家意识。[9]这一需求带动了叙写加拿大历史的潮流,如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所言,对国家身份建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政治前身的身份;拥有国家历史和共同的记忆;共同经历所带来的共同荣誉与耻辱,喜悦和悔恨”。[5]与此同时,加拿大的历史学也在经历研究方法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历史界开始由依靠传言、文学史料等转向青睐更加真实可靠的档案原件。[9]
然而,在独立之前,加拿大没有自己的档案工作,管理加拿大所生成的文件分散于其宗主国和管理者个人手里。于是,历史学家倡议查找和复印英国和法国档案机构所保存的有关加拿大的档案,联络曾经管理过加拿大的政府官员以收集其个人档案。[9]这一背景也为加拿大的“总体档案(Total Archives)”概念奠定了实践基础。
除了收集档案外,此时加拿大档案界在政府文件管理上也有了一定的进展。1912年,加拿大颁布了第一部公共档案馆法案(Public Archives Act)。尽管该法案在对政府文件收集和整理的权力划分上有些模糊,并且也没有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对文件保存和销毁的责任,但总体而言其扩大了国家档案馆对政府文件管理的权限。[6]随后的调查揭露了政府机关对文件管理的忽视和文件管理的恶劣状况,尽管调查委员会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如政府文件管理机制和规范,但这些都随着“一战”的爆发被搁浅了。
2 “一战”期间的加拿大档案工作
对“一战”中加拿大的档案工作起推动作用的是马克思·艾特肯(Max Aitken)和阿瑟·道蒂(Arthur Doughty)。这一部分的内容也将围绕他们的贡献展开。
2.1 马克思·艾特肯。1879年出生于加拿大,马克思·艾特肯年轻时就已经在商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在1910年去了英国,此后活跃于加拿大和英国政界,在战时成为两国之间的重要协调者。1914年“一战”爆发后,马克思·艾特肯从英国返回加拿大;利用以前的政治关系[包括当时的首相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民兵和国防部长山姆·修斯(Sam Hughes)],和自己曾经从事新闻行业的背景,他在1915年以中校入伍,主要负责加拿大海外远征军的文件,尤其是对伤亡的汇报。1915年3月加拿大第一师奔赴法国的时候,马克思·艾特肯扩大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并戏称自己为“加拿大目击者”(Canadian Eye-Witness)。到后期他的职责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收集和保存战争文件,主动生成文件记录战争,利用战争文件宣传加拿大远征军。[7]以下将对这三个方面分别介绍。
2.1.1 收集和保存战争文件。在加拿大第一师奔赴法国的时候,马克思·艾特肯随军队去了战场,他穿梭于战壕之间,定期撰写报告向罗伯特·博登和山姆·修斯汇报军队的表现,并通过媒体向加拿大介绍前方的战况。为了保管他在此过程中所生成的文件,1916年1月,马克思·艾特肯建立了加拿大战时文件办公室[Canadian War Records Office(CWRO)]。
英国军队规定,每支部队都应保存准确的文件、日记以促进战后历史的书写。作为大英帝国的军队,加拿大远征军也受该规定约束,并需将文件移交至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战时文件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加拿大有了自己的战争文件管理机构,因而,成立之后便要求英国国家档案馆将加拿大远征军的文件归还。此后,作为加拿大的官方文件办公室,战时文件办公室收集与加拿大远征军相关的所有文件,包括每支部队的成立过程、训练、所获得的荣誉、报告、地图、命令、个人日记等。战时文件办公室定期向各部队发文督促以保证文件的移交。
从战士的个人日记到司令官的战术和战况总结,每份日记和文件都为了解和认识战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从不同角度反映战争,因此,战时文件办公室在收集文件时也会有意识地收集不同群体的文件。
除了对接收的文件进行基本管理之外,如分类、归档和编目,战时文件办公室还对文件的“质量”进行审查和控制,如字迹能否辨认,是否有信息缺失,地图和附件是否齐全等。马克思·艾特肯指出:“这些(质量)审查的目的在于避免未来无法更正的信息遗漏和缺陷,所以应在这些当事人对事件记忆犹新的时候指出他们叙述中的弱点并要求改正。”[8]为此,1917年2月,马克思·艾特肯专门写信给加拿大集团军(Canadian Corps)司令,要求能够在战争日记的质量控制方面得到协助。随后,战时文件办公室定期向各部队下发文件,指出日记的缺陷和问题,改正的办法,以及其他评价和建议;还专门派职员到前线指导文件的撰写以保证部队的表现能够生动呈现,战争的细节能够被真实记录。[7]
2.1.2 主动生成文件记录战争。除了收集和接收文件之外,马克思·艾特肯还大胆运用高科技来记录战争。1916年4月,加拿大第一位官方摄影师被战时文件办公室获批任命;其在“一战”期间拍摄了4500多张战争照片。[7]尽管很多照片为摆拍,[10]但对于当时后方的加拿大人民以及今天的研究者,这些照片为他们了解前线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与此同时,1916年,F.O. Bovill中尉被任命为战地电影摄影技师,直到战争结束共拍摄了40000英尺的电影。[7]除了照片与电影之外,在战时文件办公室的支持下,加拿大创作了1000多幅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7]
2.1.3 利用战争文件宣传加拿大远征军。战时文件办公室所收集的文件极大地促进了对加拿大远征军的宣传。大批战争题材的历史书籍、杂志、画报、电影等被出版,多场展览被举办。这些活动筹集的资金又反过来进一步支持文件收集活动。加拿大宣传活动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人觉得“加拿大在管理战争”。[10]确实,尽管加拿大军队的骄人战绩是其被誉为大英帝国的“突击集团军”的基础,但马克思·艾特肯所领导的宣传工作对其形象的塑造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2 阿瑟·道蒂及其战争档案工作。作为当时国家档案馆馆长(Dominion Archivist),阿瑟·道蒂在战前极大地促进了加拿大档案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发展。[9]尽管在战争档案的收集上,阿瑟·道蒂要比马克思·艾特肯略微逊色,但其档案学的背景也使其贡献了更专业的观点。1915年12月,阿瑟·道蒂向首相申请去海外收集与加拿大部队相关的公共和私人文件。在参观了战时文件办公室之后,阿瑟·道蒂对马克思·艾特肯和他所领导的战争档案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马克思·艾特肯也许诺战后将所有的战争文件移交至加拿大国家档案馆。
但阿瑟·道蒂认为战争档案不应局限于前线部队所生成的文件,也应包括加拿大各级政府在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所生成的文件,因而回到加拿大以后便向首相申请对战争文件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但随后的调查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对军事机密的担心,对调查者权限的质疑,担忧自己的部队在被审查等。[7]尽管阿瑟·道蒂希望该调查能够继续下去,但他此时已经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对战争纪念品的收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作为一个专业的档案工作者,阿瑟·道蒂表达了他对于档案来源的顾虑,而且他认为个人和组织在活动中生成的文件要比活动后专门生成的文件价值高。
战争结束后,战时文件办公室本准备将收集的海外战争档案移交至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但因国家档案馆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接收和保存这些档案,这些档案被移交至了加拿大民兵和国防部(Department of Militia and Defence)。因为战后反战情绪的高涨和财政的紧缩,这些档案直到1962年才正式移交至加拿大国家档案馆。[7]
3. 若干问题
3.1 档案工作者在战争中的角色。马克思·艾特肯在战争档案收集方面的做法给我们提出的最直接的问题是档案工作者在战争中,以及更广泛的大事件中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该扮演怎样一种角色。
现代战争具有突发性、短暂性、破坏性、分散性、高科技性等特点。这意味着:第一,需要具有政策、指导方针等保护现有档案免受战争的破坏;第二,需要具有政策、指导方针等保证档案工作者及早介入对战争所产生文件的收集。第二点所遇到的挑战更大,尤其是,如何保证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收集上的权威;如何保证档案工作得到前线官兵的有效重视;如何收集新型文件,如社交媒体上产生的文件;如何保证所收集的文件得到有效的管理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战争档案有效保存的基础。
此外,档案工作者也应重视与媒体的关系。作为一个善于利用媒体的人,马克思·艾特肯对媒体的利用不仅直接宣传了加拿大军队,也间接地证明了战争档案工作的价值,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然而,马克思·艾特肯的有些做法值得深思。以希拉里·詹金逊为代表的经典档案学者认为,档案是公平的(impartiality)、真实的(authenticity)、自然的(naturalness)、有历史联系的(interrelationship)、 独特的(uniqueness)。[11]以这些属性为参考标准,马克思·艾特肯的一些工作是与档案的属性相悖的。比如如何看待他主动生成文件来记录战争,如何看待他为了控制日记质量来介入和指导官兵写日记等。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罗伯特·麦金托什(Robert McIntosh)认为马克思·艾特肯的活动证明,档案工作者在文件生成过程中不是毫无参与,也不仅仅是证据的捍卫者,相反,其在文件从生成到最终销毁或者永久保存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主动参与和影响。[7]让用户知晓档案工作者对其所看到档案的影响是以汤姆·奈斯密斯(Tom Nesmith)为代表的档案学者的学术主张之一。
3.2 档案与历史研究和辅政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的现代档案工作发展过程相似,加拿大档案工作是在不断平衡与历史研究和辅政两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前进的。历史研究对现代档案工作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其所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最直接的莫过于谢伦伯格所提出的文件双重价值论。辅政一直是隐含于档案学中的一个部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档案是统治者为了有效管理国家所生成的,也因此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如,占卜的甲骨通常存放于宗庙中。对辅政的研究能够使档案工作者认识档案的生成和本质,因而与档案学的本质更加贴近。[12]我国档案学者也认识到了档案与历史研究和辅政之间的双重关系,如覃兆刿教授提出的档案双元价值观:以“旧档无用”所代表的档案“工具价值观”和近代的“信息价值观”,其中后者是档案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延续。[13]这种观点固然与信息时代的特征相吻合,也有利于档案工作价值的推广,然而,考虑到历史学对档案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谨慎把握这一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Cox, Richard. Archives, war, and memory: Building a framework [J]. Library & Archival Security, 2012, 25(1): 21-57.
[2]Soyka, Heather, and Eliot Wilczek. Document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s [J]. American Archivist, 2014, 77(1): 175-200.
[3] Montgomery BP. Rescue or return: The fate of the Iraqi Jewish arch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013, 20(2): 175-200.
[4] 山东大学谭必勇副教授的文章对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建立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具体参见:谭必勇. 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1872-1936)[J]. 外国档案, 2014, (2): 06-19.
[5]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M]. (London, 1910) p.360.
[6] Rose, Kathryn. The Long Reach of War: Canadian Records 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Archives [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12.
[7] McIntosh, Robert. The great war, archives, and modern memory [J]. Archivaria, (46): 1-31
[8] 转引自:The great war, archives, and modern memory [J]. Archivaria, (46): 1-31
[9] Wilson, Ian E. "A Noble Dream": 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J]. Archivaria, 1982, (15): 16-35.
[10] Cook, Tim. Documenting War and Forging Reputations: Sir Max Aitken and the Canadian War Records Offi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J]. War in History, 2003, 10 (3): 265-295.
[11] Duranti, Luciana. The concept of appraisal and archival theory [J]. American Archivist, 1994, 57(2): 328-344.
[12] Duranti, L. Archival science [G], Kent, A. (ed.), Encyclopa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arcel Dekker, INC., New York, 1996: 1-19.
[13] 覃兆刿. 从一元价值观到双元价值观——近代档案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影响[J]. 档案学研究,2003, (2): 10-14.
(摘自《外国档案》电子期刊 作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信息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