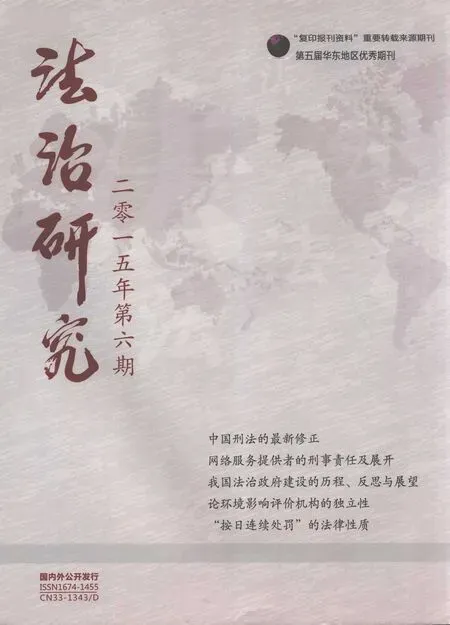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法的反思与建言——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修订
2015-04-17胡学相尹晓闻
胡学相 尹晓闻
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该罪的立法意义在于捍卫司法裁判的法律适用权威,提高公民乃至政府对法律的忠诚和尊重意识,塑造和巩固国家法治化理念,维护国家法治秩序。由于该条规定是延续了79刑法的立法理念,而且语言叙述过于简单,对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够明确,法定刑的设置不尽合理。因此,2015年全国人大常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提高了法定刑的幅度,并将单位纳入犯罪主体,适应了社会变迁和法律规范协调统一的需要。但限于本罪刑法规范的定型化观念,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九)》对本罪的规定还是过于抽象和笼统,致使本罪在司法适用中仍然会遇到新的问题。因此,为了更好打击抗拒履行法院裁判文书行为的力度,维护司法的权威,提高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仍有必要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变迁
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早在1810年《法国刑法典》就将暴力抗拒法律或者政府命令、法院传(拘)票或判决书的行为规定为抗拒政府之罪。其后,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也将抗拒法院裁判性质的行为规定为该类犯罪。①赵秉志:《刑法各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
我国1979年刑法并没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而是将拒绝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归属为妨害公务罪范畴。1979《刑法》第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1997年刑法修订时,立法机关将该类性质的犯罪从妨害公务罪中单列出来,并对其罪状、法定刑等进行了修订,成为现行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为更好地认定和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1998年4月2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判决和裁定、有执行能力等概念的含义,界定了犯罪情节,并对犯罪主体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扩充解释,认为除了负有执行义务的自然人以外,还将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列入刑罚的处罚对象。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对象作了立法解释,明确了犯罪客观方面的具体内容。②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规定:“刑法第313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立法解释还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具体分为五种不同情况。200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施行的《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进一步落实了立法解释中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各种情形。除此之外,《通知》再次重申了《司法解释》对犯罪主体的规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抗拒执行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36条规定将刑法第313条修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刑法修正案(九)》系对该罪犯罪主体和法定刑的修订向科学立法方面推进的一步。但是,还是有更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二、犯罪主体的扩充适应了社会变迁和法律规范之间协调统一的需要
首先,《刑法修正案(九)》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从自然人主体扩展到单位主体,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调整需求,符合该罪的立法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单位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社会的活动将日益频繁,单位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将日益增多。单位成为债务履行义务人的情形也非常普遍,而且涉诉标的额往往较大,逃避执行的能力更强,容易与其他利益部门相互勾结在一起共同抗法。根据一项关于“执行难”的调查,某基层法院2007年至2009年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1062件,该法院未执结的270件案件中被执行人是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有133件,占未执结案件总数的49.25%。③微山县人民法院:《对基层法院“执行难”的调查》,http://www.docin.com/p-607455338.html,2015年8月23日访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为了本单位或者职工个人的利益,公然组织本单位职工对抗法院的执行行为比比皆是,如围堵殴打执行工作人员,砸毁警车,冲击法院等。④李祖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证研究》,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3期。单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见,与自然人犯罪相比,单位抗拒执行判决、裁定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将单位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与社会形势发展与单位抗拒执行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维护了法院的司法权威与公信力。而且,由于刑法设立本罪的目的是要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义务履行人进行法律制裁,而义务履行人除了公民等自然人外,当然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单位就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种。可见,制裁单位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也是符合本罪的立法目的的。
其次,《刑法修正案(九)》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实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之间的协调统一。《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有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行为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行《行政诉讼法》第65条和2014年全国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48条都规定: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含《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处罚对象来看,只要是单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就可以直接追究主管人员(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可见两部法律的立法原意与刑法中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是一致的。《刑法修正案(九)》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扩展到单位主体不仅实现了法律规范之间的统一,而且为解决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中存在的执行困难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刑法保障。
最后,《刑法修正案(九)》对于犯罪主体的扩大与《刑法修正案(八)》中的相关规定相统一。《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276条进行了修改,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刑法》第276条之一第2款明确规定:“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如果单位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可能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该单位因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拒绝支付劳动报酬被诉至法院,并经司法审判作出裁判,要求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仍然拒绝支付,则根据现行《刑法》第313条的规定,该单位不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从而摆脱了刑事责任。刑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统一导致了犯罪认定和刑事责任追究的困境。《刑法修正案(九)》将单位列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能很好地解决这两类犯罪刑法规范之间的逻辑上不统一的问题。
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界定
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客体,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认识分歧较大。有的学者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审判制度;⑤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也有学者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人民法院的正常活动秩序;⑥谢望原:《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页。有人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的裁判活动的权威性;⑦刘宪权:《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页。还有人认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执行判决、裁定的正常活动。⑧齐文远:《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9;苏惠渔:《刑法学》 (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0页。另外有学者不使用犯罪客体的概念,而以刑法法益取而代之,认为本罪所侵害的法益不是私法上的债权而是国家利益。⑨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由于刑法是一种以规范形式表现价值的产物,犯罪客体是刑法规范定义犯罪的一种模式规格的预先设定,没有刑法规范就不可能有犯罪客体。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关系角度定义犯罪客体,还是从法益角度来理解犯罪客体,犯罪客体应当是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产物,而非事实本身。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所有‘犯罪客体’要涉及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生产力、社会秩序或者法益,都是刑事立法的价值评价根据的体现,他们无法直接转化为规范内容。”⑩杨兴培:《犯罪客体—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所以,犯罪客体应当是一种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应当由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因为“利益可以反映与表现各种社会关系,用利益可以说明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目标,用社会关系可以揭示犯罪的实质,犯罪是通过侵害利益来损害社会关系的。”⑪胡学相:《犯罪客体新论》,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具体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说,这种社会利益既不是具体的审判制度,也不仅仅是司法机关执行判决、裁定的正常活动。因为,审判制度和审判活动都只是事实本身,而非价值评价的结果。至于将法院的活动秩序,或者裁判活动的权威性,或者国家利益作为本罪的犯罪客体确实是基于价值判断的视角,但却显得过于笼统和抽象。
笔者认为,在确定具体犯罪的客体时,不能局限于对该犯罪归属的同类客体的阐释,而应该明确该犯罪的具体客体。基于对犯罪客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分析,就不能只将刑法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秩序”这一同类客体确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客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除了侵害国家司法审判活动的秩序之外,还必然侵害了判决、裁定确定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侵犯了国家审判活动秩序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学术界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歧意见较大的还是本罪犯罪对象的确定。依据《刑法》第313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是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但是,由于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种类很多,而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学术界对本罪犯罪对象的认识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所指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己经生效的裁判。至于哪些判决、裁定已经生效,应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予以确定。⑫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35页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将该罪的犯罪对象从判决、裁定扩充到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的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因此,有人认为应当对本罪犯罪对象作广义的理解:它应当是指人民法院就有关具体案件的实体或程序问题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具有执行内容的一切裁处决定,根据法院判决裁定的最终表现形式不同,可将其分为如下六类:判决、裁定、法院调解、决定、通知、命令。⑬同注①,第615~625页。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的行为是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答复》(2000年12月24日)指出:“刑法第313条规定的‘判决、裁定’,不包括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对于行为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调解书的行为,不能依照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于是,又有人提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从判决、裁定扩展到包括调解书等各种司法文书有违法律制定的目的,认为“以不符合人们一般语言习惯的方式将‘判决、裁定’的适用范围任意扩大,则其含义就不能被人们所了解。这既起不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也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难以具有预测可能性,照此处罚当事人当然显失公平。”⑭吴占英:《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载《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的扩充解释无疑是正确的。首先,《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以及《公证法》已经赋予了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的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的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与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具有执行意义上的同等效力。其次,自2010年最高法制定《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来,各级法院调解案件在全部案件中占有很大比例。例如,2010年各级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5.29%。⑮2011年3月1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如果把抗拒执行法院的生效调解书的行为排除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外,将导致众多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基于对《刑法》第3条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希望摒弃79刑法确定的“比照”、“类推”制度,认为调解书不属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范围。而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与刑法具有同等效力的立法解释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裁定扩展到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正是符合了“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第313条规定的完善。这样,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答复》既没有存在的根据,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四、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罪状表述的商榷
《刑法》第313条及《刑法修正案(九)》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罪状表述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笔者认为,尽管在罪状表述理解上的困难不大,但从刑法语言严谨、规范角度来分析,上述表述是值得商榷的。
1.罪状表述使用“执行”,容易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从词源上看,“执行”一词含义有三:一是坚守节操;二是承办、经办;三是当今通义,有实施、实行之义。《辞海》对“执行”的解释有两种含义:一是实施、实行。二是依法定程序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行政处罚决定等付诸实施。《辞海》将“执行”概括为依法定程序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行政处罚决定等付诸实施,应当是指负有实施义务的有关机构(司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实施的行为,而不是指判决、裁定或行政处罚决定等确定的义务人履行法律文书义务的行为。因为,一般情况下,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人并不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履行义务,而负有义务的有关机构实施法律文书则必须受“法定程序”的限定。可见,诉讼法意义上的“执行”正是这种含义。在诉讼法上,“执行”是指司法机关执行工作人员履行和实施法律文书的职务行为,而对履行法律文书内容的直接义务人的行为通常称为“履行”。由此可见,“执行”与“履行”的语义是对应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权利义务及不同法律关系层面上来理解的。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有能力履行判决、裁定义务的人,不可能是实施、承办执行判决、裁定的执行人(司法机关)。这从《刑法修正案(四)》规定的“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可以得到证实。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表述义务人履行法律文书时几乎都使用“履行”而不用“执行”。如《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章“执行措施”中对被执行人执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全部使用“履行”一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可见,《刑法》第313条用“执行”一词表述罪状,混淆了不同的主体及其行为性质,容易使人产生理解上的偏差,用词不恰当。在笔者看来,将“执行”改为“履行”更为妥当。
2.罪状表述中使用“拒不”双重否定容易导致语义反向。从字义上分析,“拒”、“不”两字都是否定词,语义都指“不、拒绝”的意思。“拒不”并列使用,尽管人们可能普遍理解其含义,但从语义逻辑学和刑法语言规范确定性角度来看,“拒不”的表述方式并不是很严谨。“拒”是“拒绝”,是否定,“不”也是否定,双重否定蕴含着肯定的意义。也就是说“拒不”的意思反向为肯定和同意的意思。进而可能推断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语义实为“同意执行判决、裁定”。故上述罪状用语失当,应当加以修正。笔者认为,应将“拒不”改为“拒绝”以避免双重否定导致的语义反向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也存在“拒绝”表述罪状的情形,如《刑法》第311条“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中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五、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适用
日本学者木村龟二认为:“刑法在法律上具有明确规定无价值行为应受刑罚处罚的机能,预先规定出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可对一定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这就是刑法的评价机能。”⑯[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页。然而,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还应当遵循“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即利用刑法规范进行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如果对于同一个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做数次刑法上的评价,则无异于扩张了行为罪责,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正如有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所说:“对于同一个犯罪行为,不得重复地多次加以处罚,这即是刑事实体法上的一罪一罚原则。为实践这一个实体法上的原则,在刑事程序法必须有相对应的配合原则,这即是一事不再理原则,认为对于同一个被告的同一个犯罪事实,不得重复开启另一个刑事程序,予以重新审判。”⑰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台北林山田发行2006年版,第258页。国内甚至有学者认为,禁止重复评价不仅体现在量刑上,而且还贯穿于定罪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禁止定罪中的重复评价甚至较之禁止量刑中的重复评价更为重要。⑱陈兴良:《禁止重复评价研究》,载《法学论丛》第1993年第6期。
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言,如果行为人因拒不执行民事、行政裁判而构成本罪,人民法院对行为人执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裁判时,行为人仍然拒不履行,法院是否可以再次认定其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现行《刑法》、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九)》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有观点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权威,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仍然可以再次以本罪对其进行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当。因为,一方面,刑法设置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法旨意在于打击恶意逃避债务行为引发的“执法难”问题。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执行难”主要是指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难”。从有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犯罪对象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来看,尤其是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规定的构成本罪“情节严重”的五种犯罪情节来看,基本上都指向民事或行政裁判、支付令、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另一方面,行为人再次拒不履行的判决、裁定是基于其先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行为符合了犯罪构成要件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属于刑事裁判。行为人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刑事裁判的抗拒是不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因为,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来看,只有对判决、裁判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才可能构成本罪。而人民法院对犯罪人作出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裁判往往是要求犯罪人履行刑法上的义务,即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表现为犯罪行为人接受刑罚的制裁。根据《刑法》第313条和《刑法修正案(九)》第36条规定,犯罪行为人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可能接受的刑罚是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刑。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和刑罚执行体制下,几乎不存在犯罪行为人抗拒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刑制裁的可能。即使真有犯罪行为人抗拒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刑的执行,并要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也不再是依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定罪量刑,而应当依照破坏监管秩序罪、脱逃罪、越狱罪等来定罪量刑。如果人民法院对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作出的是单处罚金的刑事裁判,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人抗拒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事裁判要求其缴纳罚金的义务也不可能再次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首先,刑事裁判中的罚金刑不同于民事、行政裁判中自愿履行的赔偿金或补偿金,是一种较严厉的刑罚方法,具有其他民事或行政制裁措施不可比拟的刑罚强制力。我国现行《刑法》第53条和《刑法修正案(九)》第3条均规定了罚金刑执行的方式:“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其次,行为人的再次拒绝履行人民法院对其作出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事裁判确定的义务(要求其履行缴纳罚金)的行为与第一次拒绝履行人民法院裁判的行为侵犯的是同一犯罪客体,即国家审判活动秩序和司法权威,并且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拒绝履行的行为。因此,从犯罪形态上分析,行为人的多次拒绝履行人民法院裁判的行为是基于概括的故意和侵害同一法益的数个同性质的行为,且触犯了同一罪名,即使构成犯罪,也应当属于连续犯,在刑法评价上“仍有必要将其视为单一”。⑲柯耀程:《变动中的刑法思想》,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80~381页。根据“禁止重复性评价”刑法原则和“一事不再理”的刑事诉讼法原则,就不能再次对该行为人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最后,即使人民法院在对犯罪行为人执行刑事裁判的罚金刑时遭到抗拒必须追究刑事责任时,完全可以依照《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而不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定罪量刑。
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法定刑的合理性问题
司法裁判确定的义务能够得到履行是实现法律效力和维护司法权威的最终保障。法律和司法活动应有的各种价值必须依靠司法判决和裁定被履行来实现。《刑法》第313条的规定事实上形成了司法制度以及法治的最终保障性规范。如果法院的判决、裁定得不到实施和履行,司法制度的公正、效率就无从可谈,公民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也难以树立。“执行是诉讼的最后阶段,是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保证,是国家法律得以具体贯彻和执行的保障。”⑳胡夏冰:《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研究综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在我们看来,看似“不起眼”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却是维护实现法律强制性和司法的权威性以及实现整个法治的最终保障。因此,很多国家都将此类犯罪归入“重罪”。如《意大利刑法典》将侵犯司法裁决的权威犯罪列入“重罪分则”。《喀麦隆刑法典》将抵抗法律实施的行为定为“抵抗罪”,也属于重罪范畴。《喀麦隆刑法典》第157条规定轻微抵抗法律实施罪的法定刑是“3个月以上4年以下的监禁。”㉑于志刚、赵书鸿译:《喀麦隆刑法典》,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而我国97年修订的《刑法》第313条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设置的法定刑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足以表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一种轻罪。《刑法修正案(九)》在充分考虑犯罪情节的基础上修改该罪的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与97年《刑法》第313条规定该罪法定刑设置相比有了较大改善。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法定刑配置仍然有失科学性。
一是与类似犯罪设置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刑法修正案(四)》公布以后,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类似或相关联的犯罪的法定刑都高于本罪。例如《刑法》第399条规定的“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尽管这两种犯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性质不太相同,前者是渎职罪,后者是妨害司法罪。但两者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都导致司法判决、裁定不能被执行,最终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况且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作为过失犯罪,其法定刑一般来说理应低于作为故意犯罪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比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的大。
二是容易导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较重情节下法定刑适用的落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法定刑为“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刑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表面上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属于侵犯财产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属于妨害司法罪,两罪法定刑不具有可比性。但当两罪发生转换时,将可能导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规定的较重情节下法定刑适用的落空。因为,行为人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下,将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行为人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且该判决或裁定内容是要求行为人履行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只有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下,才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尽管两罪对犯罪情节的表述语言不同,但司法实践往往将“造成严重后果”与“情节严重”视为同一层次的犯罪情节,“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明显重于“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情节,因为“情节特别严重”也可能包括“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因此,根据两罪的刑罚设置,如果行为人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并且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下,为了得到较轻的刑罚处罚,会千方百计将案件引入司法裁决,致力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向“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转换,从而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节严重”而非“情节特别严重”下的法定刑,即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这样犯罪行为人就轻而易举地规避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较重情节法定刑的适用,减轻了其刑事责任,其结果必将令人匪夷所思。
综上所述,现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九)》应当改变97刑法中对于本罪确立的立法思路,充分认识拒绝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罚功能和价值,仔细分析刑罚设置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对《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罪状和法定刑进行修订。可以参考《刑法》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各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在综合平衡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的法定刑基础上适当提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刑幅度,以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此外,由于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单处罚金刑,行为人抗拒履行客观上仍然可能符合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再次定罪处罚将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因此,建议取消本罪单处罚金刑的刑罚设置。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刑法》第313条修改为: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履行而拒绝履行,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