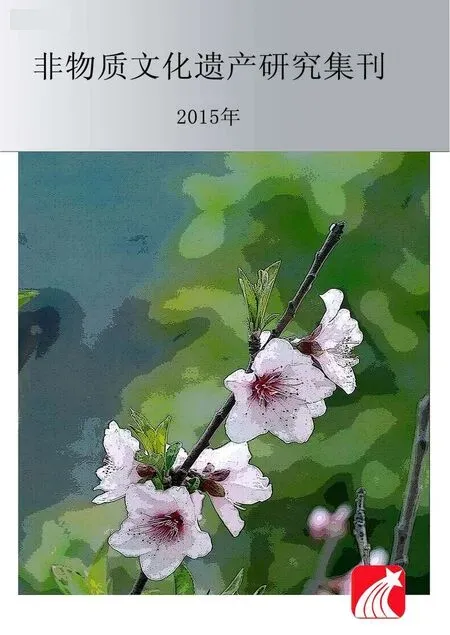人格化载体的培养与美学精神的传递①
——浅析昆曲传承的核心内容
2015-04-17胡斌
胡 斌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人格化载体的培养与美学精神的传递①
——浅析昆曲传承的核心内容
胡 斌②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艺术,其传承内容从表象上看首先是这门“场上艺术”的“人”和“戏”。为了实现“人戏合一”的传承目的,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才作为演员培养对象,并按照行当的归属进行唱念传习和形体教学。在昆曲表演艺术的传承实践之中,昆曲表演人才的培养和昆曲剧目的继承是一个相互依存、共生共长的过程,两者共同构成昆曲艺术人格化的载体。事实上,昆曲在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凝练出一套精确、严谨、系统的舞台表演美学,昆曲传承除了技艺层面“唱、念、做、打”的表象内容之外,还包括昆曲表演艺术内在的美学精神,而这恰恰是昆曲艺术的精华所在。因此,从本质上说,“人戏合一”与“美学精神”,才真正共同构成了昆曲传承的两方面核心内容。
昆曲传承 人格化载体 美学精神
昆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首先是一门舞台表演艺术,而构成“场上艺术”主体的是“人”和“戏”,这两者在这一文化形态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因此,从表象上看,昆曲传承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人,即演员的培养;二是戏,即剧目的继承。事实上,这两部分的传承内容是交织共生、协同发展的。当成熟的演员在舞台上搬演经典剧目之时,人和戏两者合为一体,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昆曲传承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作为文化形态的昆曲,自然而然承载着它自身独有的美学精神。故而从昆曲传承活动的深层次来看,历朝历代的昆曲传承实践之中,始终有意无意地也包含了昆曲古典美学精神的传递。“人戏合一”与“美学精神”,一表一里,形具神生,共同构成了昆曲传承的核心内容。
一、人格化载体的培养
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过程都是以人的智能及其表现形式为主体来实现的。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和培养新的传承者。作为昆曲艺术来讲,其保护和培养的核心对象就是人——演员。简单地说,昆曲艺术长远的发展,根本上依赖于一代又一代可以演好昆曲剧目的好演员。
演员作为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表演者的通称,在昆曲艺术中,则指运用昆曲表演艺术,把传奇剧本的文学人物形象创造成为舞台人物形象的表演者。演员是创作者,角色是作品,那么演员是怎样成为创造的角色的呢?简而言之,是用自己的身体、声音和感情作为工具和材料进行创作的,所以说演员的艺术是三位一体的艺术。昆曲乃至所有的表演艺术,归根结底的体现者都是演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昆曲演员,塑造出成功的角色,必须在三位融为一体之前进行不断的训练。所以,昆曲传承实践是一个以培育优秀演员为目的的过程,也就是昆曲艺术人格化载体培养的过程。那么,什么样的昆曲演员称得上优秀呢?一个优秀的昆曲演员需要通过哪些方面的训练?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
(一)选材与行当
“选材”就是挑选合适的人才进行演员训练,并且最终要达到一定的训练目标。历史上,曾有很多关于演员培养目标的论述:早在元代,胡祗遹就曾对演员提出“九美”的要求,不但包括了形体素质、风度气质和生活修养,而且还分别提出了念白、歌唱、表情、节奏掌握等方面的要求;到了明代,戏曲理论家们对于演员表演的研究比元代更加深入,观点准确、独到。潘之恒在他的《鸾啸小品》卷二《仙度》一文中,称赞杨姬“其度若仙”,如此描述道:
人之以技自负者,其才、慧、致三者,每不能兼。有才而无慧,其才不灵。有慧而无致,其慧不颖。颖之能立见,自古罕矣!①[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仙度》。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潘氏此说颇具见地,他认为一个好演员的艺术素质应该包括“才、慧、致”等三方面的内容。“才”是才华,“慧”是智慧,“致”是风致,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潘之恒所提出的高要求,是一个演员通过专业训练和舞台实践之后所能达到的境界,也是检验昆曲人才培养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演员若要达到这样的表演境界,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他(或她)必须是一个“可造之材”。清代戏曲家李渔,本人集编剧、导演和家班主人三重身份于一身,因而他自然而然肩负着训练和培养演员的任务。在昆曲传承领域,他是行家能手,真知灼见良多,在其著中就有关于“取材”的详细论述:
取材维何?优人所谓“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气长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娇婉而气足者,正旦、贴旦之料也,稍次则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带质朴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壮而略近噍杀者,大净之料也。至于丑与副净,则不论喉音,只取性情之活泼,口齿之便捷而已……①[清]李渔:《闲情偶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李渔认为,取材就是给演员安排一个合适的行当,不同的演员,各有长短优劣,比如说,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来选择行当就是很科学的一种方法。行当的区分,是培养演员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昆曲传习的重要内容,按照行当去教学,是培养昆曲人才最为基本的一个原则。
行当主要是指戏曲演员的分工,根据角色的不同类型予以划分。昆曲诞生之初,行当基本沿袭了南戏的旧制,分生、旦、外、贴、丑、净、末七色;到了晚明,王骥德在《曲律》中提及的角色家门有十一色;清乾隆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录了“江湖十二色”。到了近现代,昆曲与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不断交流新的角色分工,在生、旦、净、末、丑五大类基础上派生出二十多个家门细流,主要有:大官生、小官生、巾生、穷生、雉尾生、老旦、正旦、作旦、四旦、五旦、六旦、大面、白面、邋遢白面、老生、副末、老外、小丑、副丑、杂。其中的大面、老生、官生、正旦,最能体现一个班社的艺术水准,这四个行当也俗称“四庭柱”。另外,历代艺人也有将昆曲十个基本家门合为“十大庭柱”,即净、官生、巾生、老生、副末、正旦、五旦、六旦、副丑、小丑。对于昆曲传承来说,演员学艺,总是要先划定行当,才可以选择教师和学习内容,如果学艺中途因主客观原因要更换行当,也就代表着很可能要更换教师和学习内容。一个出色的昆曲演员,必然能在所从事的行当里有一定的造诣,必然能演绎好性格、年龄、身份、地位、气质相对接近的一类角色,这也是昆曲教学以行当为基础的优势。
生、旦、净、丑,不但作为四个门类、四大支柱构成昆曲的行当体制,而且各行当都创造了许多各自的看家戏,这些戏的出现,标志着某一行当发展的成熟。在长期的演出、流传过程中,广大昆曲爱好者将演出剧目与俗称熟语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大批“俗称剧目”。比如,小生有“风花雪月”“琴棋书画”“书见惊”“三醉”和“三访”等;旦角有“衣西翡蝴”“一门九娘”“三母戏”和“三刺”等;净角有“七红八黑”等;老生有“三法场”“三赋”“三扁担”等;丑角有“五毒戏”和“油葫芦”等。这些剧目涵盖了昆曲艺术的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行当,显示出昆曲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家底。“传字辈”①关于“传字辈”的统称,不同材料中的标示不同,有“传”字辈,有“传字辈”,也有不加双引号的情况。本文统一使用“传字辈”这一用法。丑角演员王传淞就曾经这样描述:
在我们昆曲副丑行当中,打基础的戏很多,有不少是规定的必修课,譬如“五毒戏”。老先生教戏时,先挂起一幅立轴,上面有钟馗驱“五毒”的内容,让我们看看清楚五种传说中有毒的生物。所谓“五毒”,是从民间传说中来的,相传是蜈蚣、壁虎、蛤蟆、蜘蛛和蛇。但是有几种其实是无毒的,如壁虎、蜘蛛和蛤蟆,因为生得形状可怕,所以也受了冤枉,千百年来成为“五毒”的象征。②王传淞:《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昆丑的看家戏“五毒戏”,即《下山》《问探》《游街》《羊肚》《盗甲》,这五出戏唱做繁重,文武俱全,通过剧中丑角的特殊表演,形象地模拟蛤蟆、壁虎、蜈蚣、游蛇、蜘蛛五种有毒动物的形态。从昆曲传承角度来看,类似这些本行当“肉头戏”的学习,能够为刚刚定位归行的青年学员打下扎实的学艺基础,能够迅速地帮助学员掌握本行当的表演特点,举一反三,事半功倍,掌握用本行当的艺术语汇去创造角色。事实上,这是昆曲培养演员的一个传统,也是培养青年演员行之有效的途径和内在规律,即采用学习剧目的方式来饰演人物、把握人物、塑造人物,并同时兼顾学习和传承本行当的技艺。
(二)唱念传习
戏曲艺术包含唱、念、做、打四个部分的技艺层面,唱和念是属于演员“三位一体”的表演中的声音部分。“昆曲唱曲念白在实践中的重大成就,是在于引入并消化了我国历史悠久的四声音韵学说。传统音韵学中的四声(指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种调类)、五音(指喉音、舌音、牙音、齿音、唇音五种以发声器官部位命名的字音)、四呼(指开口、齐齿、合口、撮唇四种发声口形)诸说被转化为追求昆曲‘字正腔圆’‘传情达意’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法。”①顾聆森:“唱念音韵”词条。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页。
这些基本技法,就是长期的昆曲传承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教学方法,对于规范和提高演员的唱功和念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开始涌现出不少与唱曲相关的专业论著。如沈宠绥的《度曲须知》,全书共三十六章,着重解说了南北曲的演唱方法和技巧,为演员的唱法训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至清中叶,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在昆曲演唱的字音、口法、腔法、声情处理等方面,更做了科学且深入浅出的论述,较《度曲须知》有所发展。此书的问世,对于纠正演员学唱中的毛病,熟练地掌握口法技巧,甚至如何到位准确地传递感情,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李渔的《闲情偶寄》“声容部”也有关于“正音”的论述:
正音维何?察其所生之地,禁为乡土之言,使归《中原音韵》之正者是已……正音改字,切忌务多。聪明者每日不过十余字,资质钝者渐减。每正一字,必令于寻常说话之中,尽皆变易,不定在读曲念白时。若止在曲中正字,他处听其自然,则但于眼于依从,非久复成故物,盖借词曲以变声音,非假声音以善词曲也。①[清]李渔:《闲情偶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正音”主要是从昆曲演唱需要出发,强调遵循《中原音韵》,尊苏州吴音为正音。在昆曲传承过程中,“正音”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即一个演员“唱”和“念”的基本功。在《闲情偶寄》“演习部”中,李渔还专门详细介绍了如何习曲,从“解明曲意”“调熟字音”“字忌模糊”“曲严分合”“锣鼓忌杂”“吹合宜低”等方面进行了专门分析。李渔家班的台柱演员乔复生本是山西平阳人,王再来是甘肃兰州人,都不是苏州人氏,但经过李渔的正音训练后,规范了口语,掌握了标准的昆曲发音,演出时获得一致认可。
清代王德晖、徐沅澂合著的《顾误录》,更是详细论述了唱曲的基本要领,合称为“度曲八法”,分别是审题、叫板、出字、做腔、收韵、换板、散板、擞声。另外,他们还总结了“度曲十病”,即方音、犯韵、截字、破句、误收、不收、烂腔、包音、尖团不分、阴阳含混。这些习曲的经验之谈,都是艺术家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对于后世的昆曲传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形体训练
唱和念是昆曲表演中的声音部分,而做和打就是属于形体的部分,同样需要经过规范的系统训练。除了“取材”和“正音”,李渔也对昆曲演员的“习态”做了独到的论述:
态自天生,非关学力,前论声容,已备悉其事矣。而此复言习态,抑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说闺中,此言场上。闺中之态,全出自然。场上之态,不得不由勉强,虽由勉强,却又类乎自然,此演习之功之不可少也。生有生态,旦有旦态,外末有外末之态,净丑有净丑之态,此理人人皆晓;又与男优相同,可置弗论,但论女优之态而已。男优妆旦,势必加以扭捏,不扭捏不足以肖妇人;女优妆旦,妙在自然,切忌造作,一经造作,又类男优矣……①[清]李渔:《闲情偶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习态”,是对演员身段规范的要求。李渔关于“自然”的论述以及男旦和女旦表演尺度的掌握,对于今天的表演艺术依然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整体看来,李渔对于演员的教育,始终是以演员为中心,这种教育理念是科学的,他所列出的表演要求和标准,在今天的教学和演出实践中依然在沿用。
李渔之后,黄幡绰的戏曲表演专著《梨园原》(原名《明心鉴》)对戏曲的形体训练做了更为细致的理论概括,主要有“辨八形”“分四状”“眼为引”“头微晃”“步宜稳”“手为势”“镜中影”和“无虚日”。比如说“辨八形”,就是指舞台上人物的表情、形体动作的表现。所列的“贵”“富”“贫”“贱”“痴”“疯”“病”“醉”八种人物的状态,联系起“面容”“眼神”“身段”“步伐”,各有不同,相互配合,统一地融入表演中,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剧情再做不同的细致处理。和《顾误录》一样,《梨园原》也提出了十种不合要求的表演和演唱的“艺病”,即“曲踵”“白火”“错字”“讹音”“口齿浮”“强项”“扛肩”“腰硬”“大步”“面目板”。
用今天戏曲的行话来说,形体训练的内容就是表演程式和表演技巧,如腰、腿、台步、圆场、山膀、云手、水袖、扇子、翎子、把子以及硬毯各种觔斗、软毯各种摔扑技巧等,统称为基本功,也就是“唱、念、做、打”四功中的“做”和“打”。这些表演程式和表演技巧,应对每一个不同的行当,又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因此,不同行当的表演人才,其训练的方法和内容,自然也大不一样。
总而言之,昆曲的表演,是一种集合多元素、多功能,融会贯通、有机综合的表演形式。它结束了以唱为主的表演形式,取而代之的是载歌载舞的舞台语汇,用这样音乐化、舞蹈化的言语和形体来塑造人物形象,抒发角色感情,是昆曲最为鲜明的艺术特征。
除了演员之外,剧目也是昆曲传承的核心内容。没有剧目,演员无戏可演,没有演员,剧目无所依存。培养昆曲演员的过程,一方面是昆曲表演艺术传承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昆曲剧目继承的过程,这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昆曲艺术人格化的载体。
据《中国昆剧大辞典》词条分类,“剧目戏码”一项共有三个分目,二百九十七个条目,分别是“传统剧目”“新编新排剧目”“存目备考”。“传统剧目”包括“昆唱杂剧”十七种、“南曲戏文”九种、“明清传奇”二百二十部(包括“俗创剧目”八十七部)。根据1996年出版的《上海昆曲志》一书比较系统的统计,上述剧目,由于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传字辈”艺人那一代保存下来并且还能上演的传统折子戏仅剩五百四十出。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到一半左右。
二、美学精神的传递
昆曲美学揭示的是如何按照美的规律从事昆曲表演艺术的创作,反映昆曲表演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数百年来,昆曲经过历代文学家、音乐家以及表演者案头和场上的多方实践,凝练出一套精确、严谨、系统的舞台表演美学,结合文学、音乐、舞蹈、表演等各种艺术形式,以写意、抽象、抒情、诗化为主要特色,发展成一种丰富成熟而又婉转优雅的戏曲样式。因此,昆曲传承,除了技艺层面“唱、念、做、打”的外在传承,还包括昆曲表演艺术内在的美学精神,而这恰恰是昆曲艺术的精华所在,也是昆曲传承实践中必须承载的另一方面核心内容。
(一)情 真
中国古代诗歌,讲求“言志”,“志”既可是载道之志,也可是言情之志;舞蹈艺术讲求“情动于中形于外”,强调外部动作必须是内部主观感情的体现。戏曲虽然较诗歌和舞蹈等艺术样式产生期晚,但是它融诗歌、舞蹈等艺术为一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抒情”的艺术特色。
和元杂剧相比,昆曲因为大量的文人士大夫参与创作,因此更注重写情,剧本体制和歌舞化的表演都更加利于演员去抒发人物感情。潘之恒在《情痴》一文中说:“古称优孟、优施能写人之貌,尚能动主;而况以情写情,有不合文人之思致者哉!”潘氏认为,昆曲表演,要求演员以自身之情去体验角色之情,在生活的积累中去寻找情感依据,方能塑造出动人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以《牡丹亭》为例:
盖余十年前见此记,辄口传之,有情人无不歔欷欲绝,恍然自失。又见丹阳太乙生家童子演柳生者,宛有痴态,赏其为解。而最难得者,解杜丽娘之情人也。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之无足怪也。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惟其情真,而幻、荡将何所不至矣。①[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情痴》。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3页。
潘氏认为演员必须是有情之人,对饰演的角色有浓厚的感情和如痴似醉的追求,才能捕捉到角色的感觉,获得其中的情感体验,甚至必须达到“情痴”的忘我之境,方能够全然入戏,淋漓尽致地表现角色之情。杜丽娘“以梦为真”,“情痴而幻”,“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②[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汤显祖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杜丽娘之情,且真且幻,因此,他认为最难得的是“解杜丽娘之情”的演员,“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之无足怪也”。
所谓的“情真”,并不是指演员自身的真实情感,而是指要求演员把角色之情信以为真,准确、深刻地捕捉到角色之情,并转化为自己的感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培养昆曲演员的过程中,要求演员学会“体验”,没有深刻的“体验”,就不会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也是昆曲表演艺术的必然要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如此写道: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③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王氏的论述,不仅仅是指诗词的创作,对于包括昆曲表演艺术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艺术,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一个出色的昆曲演员,除了“唱、念、做、打”技艺层面的精湛,也需要他(她)“入乎其内”,深知其意,体验角色的情感,分析人物的性格,方能使角色立体生动起来。而“情”这一字,恰恰就是昆曲演员达到“入乎其内”最佳的、唯一的途径。在潘氏的另一篇文章《与杨超超评剧五则》①[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与杨超超评剧五则》。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页。中,他还提出了昆曲表演需要掌握的五个方面,详解如下:
(1)“度”:一是指演员适度的舞台感觉,即“分寸感”;二是指人物的气度,又分“度人”(角色感觉)与“自度”(自我感觉)。
(2)“思”:指情思,即主观思想和精神。情感自心中自然流出,动作有内在的充分根据,要求演员表演达到“字字皆出于思”。
(3)“步”:指形体动作,即舞台上的台步和身段,要“合规矩,应节奏”,并且要给人以美的表演和造型。
(4)“呼”:是一个角色对另一角色的思念或情感投射,故“呼发于思”,同时也是演唱之前的情绪酝酿。
(5)“叹”:是念白中的“叹声”,既要“缓辞劲节”,又要“其韵悠然,若怨若诉”,如此能起到“警场”的效果。
这五方面对昆曲演员的要求,不仅仅是“唱、念、做、打”的简单拼凑,也不仅仅是有了情感体验就可以完美传达的,而是需要技艺层面和情感层面相互联系、相互融合,寓情于技,以技传情。
提倡昆曲表演要“情真”,是明清两代戏曲理论家普遍的观点。那么如何做到“情真”?用汤显祖的话说,首要的前提就是“择良师妙侣,博解其词,而通领其意”②[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汤氏之后,李渔在《闲情偶寄》“演习部”中对于“解明曲意”的阐述,其实也是要求演员通过透彻地了解故事情节,以求把握人物的内心情感: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俱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有终日唱此曲,终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此所谓无情之曲。与蒙童背书,同一勉强而非自然者也。虽腔板极正,喉舌齿牙极清,终是第二、第三等词曲,非登峰造极之技也。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师讲明曲义。唱时以精神贯串其中,务求酷肖。①[清]李渔:《闲情偶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李渔的意思是,昆曲演员除了把曲子唱好以外,还要对曲情词义进行反复思考和领会,准确把握曲子的内在意义和思想感情。如果对原作者的意志、情感、格调等产生了误解和歪曲,所唱之曲只能是“死音”而非“活曲”。李渔之后,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也着重指出:
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宜讲,而得曲之情为尤重。盖声者众曲之所尽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独异,不但生旦丑净,口气各殊,凡忠义奸邪,风流鄙俗,悲欢思慕,事各不同,使词虽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则邪正不分,悲喜无别,即声音绝妙,而与曲词相背,不但不能动人,反令听者索然无味矣!②[清]徐大椿:《乐府传声》之“曲情”。
曲情根据曲词的含义而生,每一支曲有其独有的情感内涵,各不相同,因此演员必须准确把握每一支曲的曲情。仅仅是发声和唱字,而无法唱意和抒情,便是毫无意义的“无情之曲”,所演之戏也成了无生命的戏,表演的“情深”境界自然无从谈起。当然,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因为,演员不仅要能使自己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种理解透过其表演让观众感觉到它,从而形成剧作家-演员-观众之间的共鸣作用。
昆曲的美学,是抽象、写意、诗化、抒情,而“情”是其中的灵魂。昆曲表演艺术“以情写情”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纳入程式规范的情感体验,是演员感情节奏和音乐歌舞节奏的一种共鸣,更是这门艺术传统追求的途径和规律。对于昆曲传承来说,这是最高级的一门课程,对于初学者是很难实现的一个境界,更不是借助方法和技巧可以达到的,只能由名家和艺师向学员灌输“情”的理念,有赖于演员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的自我教育。
(二)传 神
形与神,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基本概念,任何艺术都离不开形象,戏曲表演艺术也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离开了对艺术形象的描绘和塑造就无法存在。先秦时代的荀况说“形具而神生”①[战国]荀子:《荀子·天论篇》。,认为“神”源于形,依赖于形。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中论及了神的独特意义:“以神为主,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南朝宋画家宗炳云在《明佛论》中说:“今神妙形粗,相与为用,以妙缘粗,则知以虚缘有矣。”其意是指以神为虚为无,而以形为实为有,追求形神与为用,且以神为精而以形为粗。《庄子》亦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事物的外表形貌,可以感知而言传,而其精神的微妙却只能意会,需要以审美思维体悟它。“无形则难以通神,无神则形无生气。形神相与为用,也就是有无相生,虚实相缘,艺术作品中形似与神似的相依相济。”②叶长海:《中国艺术虚实论》,《戏剧艺术》2001年第6期。
这些哲学意义上的形神观,后来逐渐被引入其他艺术门类。东晋画家顾恺之首先提出了“传神写照”的说法,《世说新语·巧艺》记述: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①[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
“阿堵”即“眼睛”,顾恺之认为绘画传神处不在“四体”而在眼睛,目能传情。到了宋代,“传神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以苏轼为代表。他在论画之时,将此观点引入了戏曲表演美学之中:
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误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②[宋]苏轼:《传神记》,《苏东坡集》续集卷十二。
“优孟衣冠”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著名典故,苏轼提到这个故事,意在论证戏曲表演艺术在形成之初就包含了传神的美学因素。在尚未有人提出这个命题之前,传神已经作为一种美学追求融入了戏曲的表演。
明代以前,对于戏曲表演的论述很少,较多的只是记载演员的活动经历,不涉及表演的研究。只有胡祗遹的“九美说”,提到了对表演传神的追求,第八项“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而忘倦”,便是这个意思。他要求演员深刻理解剧本中人物的情感依据和行为逻辑,通过传神的表演去吸引观众,让观众感受深切,“如在目前”。
明代昆曲演出兴盛之后,关于表演艺术的评价和研究也随之增多起来,并且作曲家们对表演美学不断提出独到的见解。潘之恒提出的“度、思、步、呼、叹”五个方面的表演技巧,其中,就有关于传神的命题。另外,他在《神合》一文中写道:
神何以观也?盖由剧而进于观也,合于化矣!然则剧之合也有次乎?曰:有。技先声,技先神,神之合也,剧斯进已。……所谓以神求者,以神告,不在声音笑貌之间。今垂老,乃以神遇。然神之所诣,亦有二途:以摹古者远志,以写生者近情。要之,知远者降而之近,知近者溯而之远。非神不能合也。①[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神合》。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所谓“神合”,是指演员表演时使用的程式技巧和内在精神气质的融合,表演的形式和内容达到和谐统一,渐臻化境。潘氏认为,“神”绝不只停留在“音容笑貌”上,而是蕴含在人物外在形态中的内在生命气质,如何抓住这内在的生命气质呢?两个方法,即“以摹古者远志,以写生者近情”,意思是说,塑造古人重在把握精神志趣,演绎今人重在体验内在真情。
潘之恒观剧数十年,经验丰富,见解深刻,他还提出了“以技观”,以“中节合度”观,“以神求”等层次不同的欣赏要求。“以神求”是观众对演员表演提出的要求,强调戏曲表演不只是要有“技”,还要有“神”,两者“合而化矣”。演员在台上如果出现“形离”和“神沮”的情形,就无法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表演的失败。
对于昆曲传承来说,最初是以“赋形”为基础的,而根本任务应该是“传神”。“传神”作为“赋形”的最高要求,是昆曲传承的终极目标。对于昆曲表演艺术来讲,“传神”是核心和灵魂,有了“传神”的内在要求,“赋形”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在实际的传承过程中,“赋形”和“传神”,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当一个学艺者的技艺达到一定程度时,两者能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① 本文是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社科规划立项课题“江南地区昆曲传承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4JDJN01Z)、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浙江昆曲教育模式研究”(项目编号:Y201328466)及浙江师范大学人文社科一般研究项目“陈与郊杂剧研究”(项目编号:SKYB201136)的阶段性成果。
② 胡斌(1982- ),男,浙江缙云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戏剧戏曲学),研究方向:中国戏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