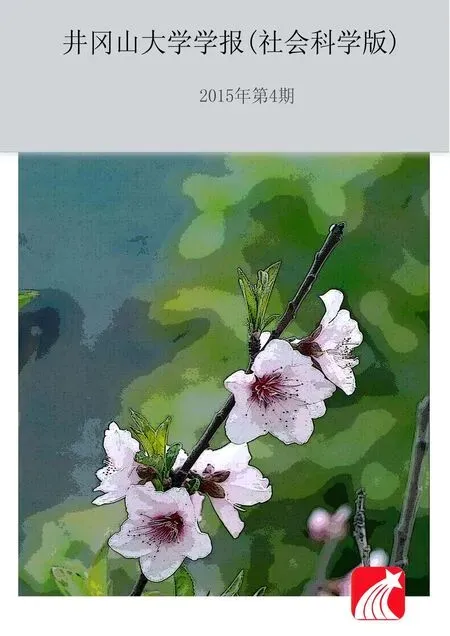试论庾信《哀江南赋》的承传接受
2015-04-15何世剑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何世剑(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试论庾信《哀江南赋》的承传接受
何世剑
(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庾信是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其 《哀江南赋》乃赋中之名篇,传诵千古。后世接受庾信 《哀江南赋》的历史进程可概括为三个时期:1、北周至宋代,为 《哀江南赋》接受的奠基期, 《哀江南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其接受表现主要有:阅读、赏析、笺注、评骘等;2、元代至清代,为 《哀江南赋》接受的升格期,它激发了天下士子在知识分子立场与身份、民族矛盾及社会冲突等诸多方面的升格思考;3、近现代以来,为 《哀江南赋》接受的深化期,承传庾信的 《哀江南赋》成为了一种文化自觉和“集体无意识”的接受行为。
庾信;《哀江南赋》;承传接受;史纲
庾信是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在南北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演进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诗文创作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广泛的影响,研究他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庾信所撰《哀江南赋》,乃赋之名篇,有“赋史”之称。由于其语言悲美、结构宏伟、使事用典妥贴,更由于其浸蕴着深深的 “乡关之思”、“身世之悲”、“故国之哀”,“缅王室、述祖德、叙时事、寄哀情”等质性,引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品赏、笺注、评点、拟写等接受兴趣,特别是在社会矛盾激化、民族问题上升、地域冲突明显之际,庾信的《哀江南赋》经常会跃入文人的观照视野,成为审视的对象和考察的重心[1](P56)。后人接受《哀江南赋》,实则“借庾信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吐出的都是对家国的思念与热爱的滚烫气息。《哀江南赋》成为赋之经典,根源于此。本文主要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夷夏之辨”及“忠君爱国”理念的影响下人们接受庾信《哀江南赋》的进程、表现,把握《哀江南赋》接受潮的成因、性质,梳理其内在衍化、拓展、流变、转承的逻辑。
一、北周至宋代:《哀江南赋》承传接受的奠基期
在北周至宋代这一历史时期中,庾信的《哀江南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其接受表现主要有:阅读、赏析、笺注、评骘等,它为人们所肯定,是这一阶段的接受主流。许多人认识到它所具有的深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刻的反思批评意识及强烈的“乡关之思”,认为它代表了庾信后期的主要写作心态,反映了庾信高超的写作技艺。这一阶段对庾信《哀江南赋》的认识和接受,确立了此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后世对它的接受基调、接受表现。
北周文风贞刚,人们对庾信诗文却普遍持“好赏摹仿”态度,这从庾信与北周皇室宗亲的大量诗赋酬唱中可见一斑。如史书中明确提到赵王宇文招“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北周滕王宇文逌在庾信在世之时,为之出资编订集子并撰序,可谓是第一个有功于庾信《哀江南赋》接受之人。宇文逌比庾信年小许多,但他们成了忘年之交。庾信在北朝生活贫困时,得到了宇文逌的大力接济和帮助。庾信集中有《谢滕王赉巾启》、《谢滕王赉马启》、《谢滕王赉猪启》三篇,是庾信在接受了滕王宇文逌的惠赠后写的感谢信,看得出两人交情甚密。当时北周王公大臣好学、崇尚 “南风”,对庾信诗赋有较好的接受“期待视野”,普遍存有“求新尚异”的文化心理。宇文逌序言末征引宇文护评价庾信“南人羁士,至孝天然”之语,见出他肯定庾信思念故国的行为。
隋代盛行“革文华”之风,对庾信诗文的接受持谨慎保守态度,限制了《哀江南赋》的较好流传。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高扬圣人之学、儒家之学,以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对抗文学的审美性,高标文章思想内容而贬斥写作技巧。庾信作为“宫体诗”、“徐庾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其文章无疑是李谔批判的对象。“初,属文为庾信体”的晋王杨广,为了不让诗文创作影响和改变他在高祖心目中的良好印象,甚或是有意迎合父王新变文风的政治举措,抛弃了“庾信体”。“隋末大儒”王通在《文中子·事君篇》中说:“文士之行可见……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2](P106)王通常以继承孔子衣钵自居。他之所以批评庾信,认为庾信是夸人,乃在于庾信不符合他理想中的“君子”标准。当然,在这一社会文化语境中也因为有识之士对廋信的《哀江南赋》做了一些“笺注”等基础性工作,从而奠定了它在唐以后的接受基础。如废太子杨勇曾令魏澹注《庾信集》。《隋书·魏澹传》说:“及高祖受禅,(澹)出为行台礼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聘陈主使。还除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遇之,屡加优锡,令注《庾信集》,复撰《笑苑》、《词林集》,世称其博物。”[3](P950)魏澹注《庾信集》今已不存。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从《通志·艺文略》中见到郑樵著录《哀江南赋》注有“魏彦渊”一家,认为魏彦渊“即魏澹也”,并推断“此盖所注《庾信集》中之一卷,经唐人析出,偶存于宋秘阁者”。魏澹是第一个为《庾信集》作注之人,开创了“笺注”这一接受庾信诗文的方式。据宋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唐人、杂纪下”所载,此注至南宋末即散佚,今已不存。
有唐一代,整体上对庾信诗文保持一种开放的学习态度。鉴赏方面,如苏颋、蒋乂等人自小皆能熟练背诵《哀江南赋》、《枯树赋》,有“神童”之美誉。在创作方面,唐人充分吸收了庾信诗赋的养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唐诗加以发展。“初唐四杰”、李白、杜甫、李商隐等许多大诗人都受庾信诗文沾溉,一定程度上为《哀江南赋》的传播接受起到了助推作用。杨慎《升庵诗话》指出:“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唐人绝句,皆仿效之。”[4](P206)葛晓音先生也指出:“从初盛唐到中晚唐的诗歌名篇中,到处都可发现庾信影响的痕迹。”[5](P245)初唐史家令狐德棻等在撰写《周书·庾信传》时,全文载录了《哀江南赋》,指出:“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6](P498)首次拈出“乡关之思”来评骘庾信入北后的创作心态和思想情感。总体上讲,初唐史家对庾信行为有所回护,对庾信诗赋较为褒扬,奠定了其后历朝接受的基调——肯定庾信及《哀江南赋》为主流。《崇文总目》卷五载:“《哀江南赋》一卷,王道珪注;《哀江南赋》一卷,张廷秀注”[7](P276);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八》曰:“开府仪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又《略集》三卷:庾信《哀江南赋》一卷,唐 张廷芳注;又一卷,崔令钦注;又一卷,魏彦渊注”[7];《宋史·艺文志七》曰:“《庾信集》二十卷,又《哀江南赋》一卷”[7](P277)。从以上书目及史书所载可知,在武则天到唐玄宗执政时期,掀起了一阵笺注《哀江南赋》的热潮,出现了王道珪、张庭芳、崔令钦三家注,此三注至南宋时期还在流传,后散佚,今已不存。依据现今能见之唐李峤撰、张庭芳注、胡志昂编《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8]中引用的庾信诗3处,与今本对照均无误,见出张庭芳对庾信作品较为熟悉,其笺注庾信《哀江南赋》一文的行为应该确已发生。中唐时期,杜甫对庾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9](P896)“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10](P1499)还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说:“哀伤同庾信”。可见杜甫对庾信亦多有接受,他既继承了庾信诗歌的清新,也非常喜欢庾信的老成文风,并对此加以摹仿。逮至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等沉溺于对内心感伤的吟咏,“哀同庾开府”,体味庾信的痛苦心情,达到情感的强烈共鸣。如李商隐《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有言:“何因携庾信,同去哭徐陵。”[11](P6200)何焯《义门读书记》指出:“义山五言出于庾开府”[12](P1243)。李商隐在用典、遣词造句、意象、主题、比兴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庾信有着明显的因袭。整个唐代,贬抑庾信人格及《哀江南赋》文学成就者不多,仅崔途等少数几人,一般均承认庾信后期有较为强烈的“乡关之思”。
北宋时期对庾信诗赋的接受可以用 “推许陶杜,毛疵庾徐”来概括。欧阳修等撰修《新唐书》时,直接揭示和阐发了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庾信为中国诗歌的律化奠定了基础。黄庭坚高度赞许庾信对写诗艺术的刻意追求,说:“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13](P105)但他也指出:“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14](P216),认为前人对杜甫和庾信句法上的紧密关系言过其实。秦观称许“徐、庾长于藻丽”,认可了庾信组织文字的能力;张戒说:“子美诗奄有古今……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在子美不足道耳。 ”[15](P307)他认为杜甫诗接受了徐、庾的经验,但高于“徐庾体”;又说:“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15](P315)张戒站在儒家诗教的立场,对徐、庾等人执着于吟咏内心情性,在文字组织上费工夫的行为甚为不满,而主张像陶渊明、杜甫一样落笔天成,内容雅正,自然无邪。《哀江南赋》及庾信的另一篇赋《愁赋》,成为此期体认庾信后期心态的代表之作。批评之声渐次多了起来,如王禹偁《和自咏》:“庾信悲哀休作赋”;胡宿 《上两浙均输徐学士》:“江山满目,多庾信之悲哀。”等等。当然,理解庾信苦衷、同情庾信哀愁的人占多数。宋臣外放为官、羁旅边关或漂泊异乡时,经常会想起命运不济的庾信,与之进行一次又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感慨身世时运。如刘挚《金陵》:“吟毫千百年间事,剩写江南庾信哀。”欧阳修《上胥学士(偃)启》:“庾以流离而多感”;张耒《归马》:“思归庾信正多愁”;晁以道《秋》:“故知庾信多清泪”;刘一止《曾宏父将赴官都城示诗次韵自述并赠其行》:“庾信多哀思,年来方解愁。”庾信“老更成”的乡关之思作品抚慰了普遍带有“老”“愁”心态的宋人。李步嘉先生《〈哀江南赋〉旧注发微》一文曾引“宋晁迥《法藏碎金录》卷六记刘安国好诵《哀江南赋》”事,再结合晏殊《类要》、曾慥《类说》中有“《哀江南赋》注”,推断“宋人在读《哀江南赋》后曾作过不少笺注是可以推知的”[16](P62-63)。 特别是南宋时期,庾信《哀江南赋》尤其流行。南宋周文璞《诵〈哀江南赋〉》一诗有言:“……惟吾爱好词,细碎穷注笺。中间多佚事,他书亦不传。极欲补阙漏,今方长弃捐。重效嘈囋声,庶几与周旋。”从周氏“重效嘈囋声,庶几与周旋”句见出,宋时庾信的《哀江南赋》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多重”阐释力的文本了。
宋金元之际,对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达到高峰,我们可以通过“使金(辽、元)宋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考察。使臣们将庾信作为一个参照,在“庾信”行为及《哀江南赋》的对待性向度上,由于礼法观、价值观等不同,在价值判断、行为选择方面有着两类相反的接受表现。一类汲养于儒家忠君爱国宗法礼仪制度之中,凭借自我的价值理性、高迈的人格精神超越了生死规约,没有追步庾信,而是矢志不渝,奏响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音;另一类则在情与礼(情与理)的斗争、仕与隐的抉择、生与死的矛盾之中终于没有坚守,选择了前者,和庾信一样在沉沦中获得了新生。从社会的演进和大中华文化的发展来讲,他们也为时代的前进作出了贡献。前者,可以坚持操守而终获遣归的洪皓、朱弁、张邵为代表;后者,可以文虚中、吴激、高士谈等为代表。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前者,他们也很少批评庾信,而是在拜读庾信的诗赋时,一起思念家乡、故国,升华哀情愁绪。如洪皓《次韵学士重阳雪中见招不赴》:“哀哉庾信江南赋,闷读频移玉座春。”[17](P19175)时间上的流逝感、地域上的偏离感、文化上的落寞感、行动上的耻辱感、心态上的悲愤感等曾影响到庾信诗文写作变化的因子都漂移到他们身上,一一书写为哀怨诗词。在使金士人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庾信所曾经使用过的“乡关”、“南冠”、“南望”、“胡尘”等词汇及江南风物意象。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可以看作是几百年之后庾信“乡关之思”作品的“异代同响”。
二、元代至清代:《哀江南赋》承传接受的升格期
元代至清代,《哀江南赋》引起了文人士大夫对之笺注、吟咏、评骘、仿作之兴趣,它经常走入反观历史、寻求心理寄托和行动坐标的天下士人阅读视野,在他们胸中激起了阵阵涟漪,激发了天下士子在知识分子身份、民族矛盾及社会冲突等诸多方面的升格思考。
元代笺注庾信《哀江南赋》者仅王防御一人,方万里悼挽王防御有言:“温饱逍遥八十余,稗官原是汉虞初。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哀江南赋笺成传,从此韦编锁蠧鱼。”[18]王防御笺注《哀江南赋》本,现已不存,不过透过方万里的挽诗,我们能感受到王防御笺《哀江南赋》用力甚勤,博览群书以向深处发掘贯通。元人对于庾信其人及 《哀江南赋》,受到了民族情绪的干扰,整体上评价不高,如元方回《恠梦十首》之三:“肯顾江淹恨,焉知庾信愁。”宁顾江淹之恨,不愿体味庾信之愁;吴莱《送俞观光学正赴调京师》:“佐朝肉藿岂异谋,庾信诗赋但雕锼。”评之以“雕锼”,完全否定庾信诗赋创作成就。元祝尧撰《古赋辩体》,也认为“用事亦未如徐庾之堆垛”。偶有如赵文者,“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综观整个元代,因蒙古族统治中原,带着“仇视异族”心理的汉人,很少能原谅庾信“叛族背国”的变节行为,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哀江南赋》,读出来都是变味的感觉。
明代,总体来讲,庾信的《哀江南赋》颇受肯定和敬重,常为学人所思感、诵读,除王世贞外,对之持贬抑态度者鲜有几人。首先,明人编纂、整理和刊刻了庾信的文集,《哀江南赋》得到了较好的校勘、辩误和修订,庾信文集的出版方便了世人对《哀江南赋》的接受。现存的明本《庾信集》大致有七种,分别是:汪士贤校《汉魏诸名家集·庾开府集》(《汉魏六朝诸家文集·庾开府集》);屠隆评点《徐庾集·庾子山集》;张燮 《七十二家集·庾开府集》;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庾开府集》;阎光世《文选遗集·庾子山集》;黄澍、叶绍泰选《汉魏别解·庾子山集》;叶绍泰编《增定汉魏六朝别解·庾子山集》。这些庾信文集刊刻之后,许多藏书家将之收藏。如明王道明藏编 《笠泽堂书目》,列有:“《庾子山集》四册;庾信……《庾子山集》四册,国朝屠隆评。”可知王氏收有《庾子山集》两部,其中之一为屠隆评本。在清康熙年间,屠隆评《徐庾集》广受欢迎。吴兆宜等撰《庾开府集笺注》、倪璠撰《庾子山集注》均选用屠隆《徐庾集》作为底本进行笺注、发微。而清初兴起笺注《哀江南赋》热,诸家选用的也当是屠隆评点本。有些庾信文集前有序文,对庾信及《哀江南赋》有评议。如张溥《庾信集题词》说:“周滕王逌序《庾开府集》云:‘子山妙擅文词,尤工诗赋。诔潘安而碑蔡邕,箴扬雄而书阮籍也。’称重至矣!庾氏家世南阳,声誉独步。子山父子出入禁闼,为梁文人。雀航之战,倒徒先奔,违才易务,任非其器。后羁长安,臣于宇文,陈帝通好请还,终留不遣。虽周宗好士,滕赵赏音,筑宫虚馆,交齐布素,而南冠西河,旅人发叹,乡关之思,仅寄于《哀江南》一赋,其视徐孝穆得返旧都,奚啻李都尉之望苏属国哉!子山在梁,每一文出,京都传诵。初使北方,人颇轻之,读《枯树赋》始知敬重,盛名易地,橘枳改观,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几及。文与孝穆敌体,辞生于情,气余于彩,乃其独优,令狐撰史,诋为‘滛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19]从此《题辞》可见,张溥非常钦慕庾信的才华,同情庾信入北后的悲苦遭际和思乡心态,给予了庾信非常高的综合评价。他肯定了庾信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对初唐文风的影响,对于令狐德棻在史书中对庾信的诋毁,给予了严厉地反驳。此外,明人“以诗言志”,表达了对庾信《哀江南赋》的认识。如明徐有贞撰《题西游遗稿后》说:“生平岂解荷雕戈,羁旅时还操尺牍。思深庾子哀江南,愁甚杜老歌同谷。”(《武功集》卷三)生逢乱世,羁旅途中,蓦思庾信,想到他漂泊异域,终身未归,不仅对他的那份痛苦的思乡之情产生共鸣,情不自禁地拿起了“尺牍”,写下了对他的理解。主张为诗“上溯六朝”的杨慎,更是将庾信抬升到很高的位置加以论评。他接受了庾信的“缘情绮靡”诗学观,主张诗歌“吟咏情性”,无所依傍。杨慎被贬谪云南几十年,最后死于寓所。在云南时期,作为一个流寓天涯的游子,杨慎追法庾信,写作了许多“乡关之思”的作品。杨慎与其妻子黄娥的诗文往来,写下的许多至情至性“思乡诗”,成为明代此类题材中的珍品。明谢榛“撰有《哀江南》诗八首”(《四溟集》卷三),同题继作。当然,在那一片“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复古声中,亦有诗家对庾信其人其文颇有微词,如王世贞说:“庾开府事实严重,而寡深致。所赋《枯树》、《哀江南》仅如郗方回奴,小有意耳,不知何以贵重若是。”(《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矛盾、民族冲突激烈,对庾信的《哀江南赋》接受达到高潮。此期,《哀江南赋》既是志士仁人的精神食粮,批判敌人、高歌猛进的号角;又是失节忘义者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成为他们回首往昔,自我忏悔的心灵变奏曲。失节忘义者如钱谦益、吴梅村的诗文中,常常出现“庾信”意象。他们引之为知己,表达其愧悔心态和故国之思。
整个清代,由于是外族(满族)主政中原,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固守汉族正统观念的民族主义者对于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争端不休,意见纷纭,有走极端的表现——“爱之者欲其生,恶之者欲其死”。前者认为庾信“乡关之思”是怀念故国,体现了其高尚的忠君爱国情操,如傅山、王夫之等;后者则反感和厌恶庾信,由人及文,认为这是庾信对自我的一种辩护,企图掩盖、开脱其“失节”之罪责,无耻之行,罪不可恕,全祖望可为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推行高压的“文化专制”政策,制造血腥恐怖。在这一百三十三年时间里,《庾子山集》及《哀江南赋》并没有成为禁毁文本,注释、仿作《哀江南赋》的行为时常有之,而鉴赏和批评《哀江南赋》的举动也没有遭到干涉。《哀江南赋》在此期被广为诵读,走进了清初文人的记忆深处。申屠青松先生指出:“寄托故国之思、创作借鉴、迷恋考据,是当时文人热衷注释《哀江南赋》的基本原因。”[20](P41)此论甚确,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分析。笺注者可以胡渭、王洄、王婿、归庄、陆繁弨、徐炯、徐树榖[21]、吴兆宜、倪璠等为代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庾开府集》指出:“近代胡渭始为作注,而未及成帙。兆宜采辑其说,复与昆山徐树榖等补缀成编,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见之书,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捃摭残文,补苴求合,势不能尽详所出。如注《哀江南赋》‘经邦佐汉’一事,引
《史记索隐》误本,以园公为姓‘庾’,以四皓为汉相,殊不免附会牵合。后钱塘倪璠别为笺注,而此本遂不甚行。然其经营创始之功,终不可没。与倪注并录存之,亦言杜诗者不尽废千家注意也。 ”[22](P3838)《提要》虽然在论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得失之时较为苛刻,指正了吴氏笺注时犯的一些错误,但也认为“其经营创始之功,终不可没。”倪璠《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注释详细该博,“比核史传,实较吴本为详。《哀江南赋》一篇,引据时事,尤为典核。”倪璠将庾信所写作的《哀江南赋》提升到“赋史”的高度进行认识和阐说。倪璠 《庾子山集注》曰:“《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赋记梁朝之兴亡治乱及己世之飘飖播迁,古有 ‘诗史’,此可谓‘赋史’矣!嵇叔夜《琴赋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音声,则以悲哀为主。”[23](P98)总之,倪璠在注释时,一方面通过它去体认庾信由南入北、身仕二朝的那种复杂的曲折的文化心态,去感受庾信当时的那种痛苦经历、悲哀心路;另一方面借庾信所创作的这一文本,切入当时那个波折动荡、硝烟弥漫、鼓角争鸣的年代,感受当时南朝宫廷内部勾心斗角、朝廷上下尔虞我诈的一幕幕丑陋的图景,随着庾信的笔触慢慢延伸认识的视角。倪璠注本之所以在清代影响甚大,被认为是注释“庾信集”的权威。文集选编者亦奉庾信《哀江南赋》为圭臬,对之作了细读品赏。如杨绳武编有《文章鼻祖》六卷,选诗文十四篇,以庾信《哀江南赋》为压卷之作。他指出:“子山此赋,事备家国,义兼诗史。……盖其体则古诗之流,而其义则兼乎史矣”;又说:“子山此赋,其原出于《离骚》,其流极于少陵之《新乐府》。”[24]还有人在评点其它文学作品时,征引《哀江南赋》名句,挖掘和阐扬其中所蕴藏之“义理”。据毛国瑶先生所发现的靖藏本《红楼梦》,其中第十八回有“畸笏叟”引庾信《哀江南赋序》语所作之墨笔眉批,说:“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大族之败,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25](P195)“畸笏叟”肯定了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对梁朝灭亡的反思与批判,揭示了“盛极必衰”的哲理。余英时先生针对畸笏叟此评语,指出:“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25](P255)之后,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再论“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也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26](P195)。总之,受民族矛盾激化和社会冲突升级的影响,此一历史时期中出现了诵读、研习、笺注、征引、阐释、评骘《哀江南赋》,化用其中经典意象,仿作同题材文章等诸多现象,激发了天下士子在知识分子立场与身份、民族矛盾及社会冲突等诸多方面的升格思考,它标志着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进入了升格期。
三、近现代以来:《哀江南赋》承传接受的深化期
如果说元明清时期的《哀江南赋》接受主要寄寓了汉族文人深深的“故国之哀”、“乡关之思”,那么近现代以来的《哀江南赋》接受,则具有了深化的表现、内涵和意义。承传庾信的《哀江南赋》成为了一种文化自觉,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接受行动,标志着《哀江南赋》接受走向深化发展。
第一,庾信《哀江南赋》在此期已经内化于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灵,成为他们自觉反抗民族侵略、封建统治和追求和平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文化批判武器。
在清代向近代转型之时,爆发了许多社会矛盾,矛盾的激化一方面主要表现为社会动乱和民族战争,如农民起义战争,也有中外之战争(如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可以视为转型之余波;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新旧党争与宫廷政变,如“百日维新”,乃至后来的袁世凯、张勋复辟等。这些社会变革,作为诗赋写作之主题,都曾通过摹仿庾信《哀江南赋》之旧形式得到表达。金应麟在鸦片战争时,“每退朝过宣武门,往往就余城根寓庐谈海上事,相对嗟叹”。他辞官归故里时,路过镇江,看到了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侵略后的镇江景象,悲慨于人民抗英斗争未得到支持而失败,愤然写下了一篇《哀江南赋》,来控诉帝国强盗的残暴罪行,揭露清政府统治的腐败无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时,王闿运撰写了《哀江南赋》并自注,目的在纪洪杨之乱,形式上刻意模仿庾信《哀江南赋》,用韵上标明“用庾子山旧韵”,其中有不少典故也援引自庾信。姜书阁的《骈文史论》指出:“《哀江南赋》,即不仅从形式上仿庾信原作,甚至用韵以追步庾赋,就是明证。”[26](P532)章炳麟虽然对庾信评价很低,说:“自屈宋以致鲍谢,赋道既极。至于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愈远。世多慕《小园》、《哀江南》辈,若以上拟《登楼》、《闲居》、《秋兴》、《芜城》之列,其靡已甚”,但面对帝国列强的侵略,他也追步庾信,创作有《哀韩赋》、《哀山东赋》等,前文哀悼韩国(朝鲜)的覆亡来警示国人当自强,后者抒发了对德国、日本侵略者抢占山东青岛等的悲愤,凛然正气、爱国情怀盈贯全篇。
另外,生活在动乱年代的李详、高步瀛等先生,面对清初《哀江南赋》笺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迎难而上的求索精神。他们秉持“求真务实”的研究理念,将庾信的《哀江南赋》笺注推向了又一个高度。李详先生的《〈哀江南赋〉集注》,注前有他作于“宣统辛亥三月”之序。在序中,李详首先征引何焯之说,对庾信《哀江南赋》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加以综评,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指出:“子山《哀江南赋》,体放《西征》(本何义门说),近摹《郊居》,遒文巨制,取精用宏,衣被词人,殆逾千载。令狐《周书》,载之本传,风流好尚,诚所服膺。亦如班氏之传马扬,非文不显,固有例也。”[28](P325)其次,他考索梳理了庾信《哀江南赋》的笺注历程,为前代之注不传而惋惜,又为清以来之笺注冗杂、未审、残阙而伤怀。他说:“《新唐书·艺文志》有张庭芳注一卷,崔令钦注一卷。《宋史·艺文志》庭芳之外,又有王道珪注一卷,惜皆不传。国朝昆山徐树榖兄弟据五家之说,辑为此注一卷,刊行于世。嗣有吴江吴氏、钱塘倪氏,统注全集,蔚然可观。顾徐吴两家,先后并出,公然相袭,又其隐括群书,初无义例,倪则兼袭徐吴,益以冗长。凡有未审,诸家之注,俱付阙如。”[28](P325)再次,他简要地叙说了自己的《哀江南赋》笺注经历,并对其“笺注”体例作了说明。他说:“余三十年来,味此书,每有所获。近乃综取诸家之说,仍其姓氏,加以考证。篇卷纪年,补入夹注,以避窜易。 ”[28](P325)最后,他交待了笺注《哀江南赋》的目的和感受,指出:“既以揽彼精英,遂欲公诸同好。写定如左,庶几有快炙背美芹子者,一取赏也”[28](P325)。高步瀛先生《〈哀江南赋〉笺》作于民国二十三年,晚出于李详之注。其笺分别刊载于 《师大月刊》1934年第14期、1935年第18期、1936年第26期,他在其 “笺”正文前撰有 “前言”。第一,高先生解释了重新笺注《哀江南赋》的原因,即 “幼喜读 《哀江南赋》,而苦无善注”。[29](P103)后来看了清人之注, 感觉“谬误亦多”,“颇不满意”[29](P103),深以为恨。其直接促因是“得李氏详注”,“然仅有赋序注,以下未刊,数年来多方求之,亦不可得”[29](P104),故他“草笺此编,授诸生”[29](P104)。第二,高先生对其笺注所采选文本进行了说明,他说: “窃尝拟取庾集吴倪二注,存其是者,订其谬误,补其疏漏,别成一编”[29](P104)。看其笺注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出吴 (包括吴笺注文中征引的张尚瑗、王洄等人之注,高氏有转引说明)、倪注外,他还采撷了李详等人之注。与清代以来的《哀江南赋》笺注相比较,高步瀛先生之笺有承继,亦有新创。许逸民先生校点《庾子山集注·哀江南赋》之中有些注文当受到了李、高二位先生的启发。相比于清初归庄、陆繁弨等人借笺注《哀江南赋》来表达其“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哀悼江南沦陷异族之手”,李详、高步瀛先生更多的是像胡渭、阎若璩一样,走“经世致用”之“实学”路线。当然,身处乱世的他们潜心治学,选择《哀江南赋》文本进行笺注,也应该是有“寄托”的。他们不只是从骈文的角度欣赏《哀江南赋》的形式美,而且注重发掘《哀江南赋》中的哀怨精神、家国思念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两位先生人品、学问都值得称道。如高步瀛先生在日寇侵占北平时,闭门称疾,不与敌人合作。临终之时犹吟陆游《示儿》诗以明志,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赤忱热心”。李先生是骈文好手,高先生是古文大家,但他们对于“汉魏六朝”之学都研究颇深,尤其是在《文选》学方面建树甚多。他们笺注《哀江南赋》,还出于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对庾信诗赋的赞赏,如高氏《汉魏六朝诗选》、《汉魏六朝文选》选庾信诗文较多,超出庾信同时代之人。总之,庾信《哀江南赋》这旧瓶子,经常被新派、旧派文人用来装入时代、社会所酿制的新的辛辣之酒,奉献给世人品尝,催生下一颗颗滚烫的、悲伤苦涩的泪珠,其中写满了对中华民族的深情,对祖国大地的爱,甚至还有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人道主义”风范;写出了对涂炭生灵命运的悲哀,和对世界安定和平、自主自立的向往。
第二,在动乱飘摇的年代中,庾信的《哀江南赋》被许多家庭(很大程度上是“书香世家”)列入家学的“必读书目”,成为了后世家小启蒙、教育之读本,学习、创作之典范。这样的家庭甚多,如陈宝箴家庭、曾国藩家庭、钱钟书家庭、汤一介家庭,等等。就其对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表现来讲,主要有二:一为着眼于传承其中的“辞章”,可以曾国藩家庭为代表;一为立足于传承其中之“义理”,可以汤一介家庭为代表。
曾国藩对于庾信的诗赋作品还是非常欣赏的,他不仅仿作有《哀江南赋》,练习书法以《枯树赋》为帖自励,而且在向子弟传授“为学之方”时,着重指出:“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后宜将《文选》最惬意者熟读,以能背诵为断。如《两都赋》《西征赋》《芜城赋》及《九辩》《解嘲》之类,皆宜熟读。《选》后之文,如《与杨遵彦书》(徐)、《哀江南赋》(庾)亦宜熟读。”[30](P37)(《曾子家书》)强调子弟们须熟读《哀江南赋》,以能背诵为要。
相比于曾国藩主要从诗文技巧、辞章典实上对《哀江南赋》加以强调,以提高写作水平,汤用彤先生家庭在乱世中倡导背诵庾信《哀江南赋》,则显然“寄托更深”、“立意更远”。汤一介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向他人提起过父亲要求他背诵 《哀江南赋》这一往事。他说:“(父亲)见我爱读诗词,有一次从 《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找出他常读的《哀江南赋》给我读,这是他唯一一次单独叫我读的东西。 《哀江南赋》是南朝庾信写的,讲的是丧国之痛。还有 《桃花扇》中的 《哀江南》也是父亲常吟诵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正值国难,我父亲常吟诵这两首,表现了他的伤时忧国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之深。而我父亲又深受我祖父的影响……。”[31](P4)《哀江南赋》中的“家族”观刺激着汤用彤先生,他秉持其父所说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理念,视之为“家训”来教育子孙。
综上可见,从历时的角度讲,受不同历史时期“夷夏之辨”及“忠君爱国”理念的影响,后世接受庾信《哀江南赋》的进程颇不平稳。以《哀江南赋》接受潮的成因、性质、表现为基准,把握其内在衍化、拓展、流变、转承逻辑,将接受所达到的高峰作为分野标志,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北周至宋代,为《哀江南赋》接受的奠基期,庾信的《哀江南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其接受表现主要有:阅读、赏析、笺注、评骘等;元代至清代,为《哀江南赋》接受的升格期,它激发了天下士子在知识分子立场与身份、民族矛盾及社会冲突等诸多方面的升格思考,在明清之际,随着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又一次达到高峰;近现代以来,为《哀江南赋》接受的深化期,承传庾信的《哀江南赋》成为了一种文化自觉和“集体无意识”的接受行为。
[1]何世剑.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表征及内涵[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1,(7).
[2][隋]王通.中说:卷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3][唐]魏徵.隋书:卷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张葆全,周满江.历代诗话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5]葛晓音.八代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舒宝璋选注.庾信选集[M].洛阳:中州书画社,1983.
[8][唐]李峤.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全唐诗:卷五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14]贾文昭.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卷上[M].合肥:安徽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室,1982.
[15]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6]李步嘉.《哀江南赋》旧注发微[J].江汉论坛,2003,(8).
[17]傅璇琮.全宋诗:卷170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M].四库全书本.
[19]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十一(上)[M].四库全书本.
[20]申屠青松.清初《哀江南赋》注本考论[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1]徐炯,徐树榖.哀江南赋注[M].续修四库全书本.
[2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3][清]倪璠.庾子山集注[M].许逸民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24]杨绳武.文章鼻祖[M].四库全书存目补编本.
[25]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
[26]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7]姜书阁.骈文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8]李详.李审言文集:上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29]高步瀛.《哀江南赋》笺[J].师大月刊,1934,(14).
[30][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4册[M].上海:世界书局,1936.
[31]汤一介.中华民族需“反本开新”——汤一介教授访谈录(二)[J].中国评论,2004,(5).
Yu Xin's Ai Jiang Nan Fu:Inheritance and Reception
HE Shi-jian
(School of Art&Desig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i Jiang Nan Fu (A Verse on Lamenting Southern Bank of Changjiang River)is a historyhonored masterpiece of Yu Xin,literary master of Six Dynasties.The inheritance and reception history of Ai Jiang Nan Fu consists of three period.The first is from Northern Zhou Kingdom to Song Dynasty,a stage of reception beginning in which more and more scholars read,appreciated,annotated and commented the work. The second is from Yuan Dynasty to Qing Dynasty,a stage of reception rising,in which intelligentsia are stimulated to think about their identity and standpoint,national contradicts and social conflicts.The third is modern times,a stage of deepening reception,in which scholars receive the work wit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Yu Xin;Ai Jiang Nan Fu;inheritance and reception;history brief
I207.224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4.015
1674-8107(2015)04-0096-08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
2015-03-2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赋学批评理论的承传接受研究”(项目编号:12CZW015);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庾信诗赋承传接受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43)。
何世剑(1979-),男,江西萍乡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论与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