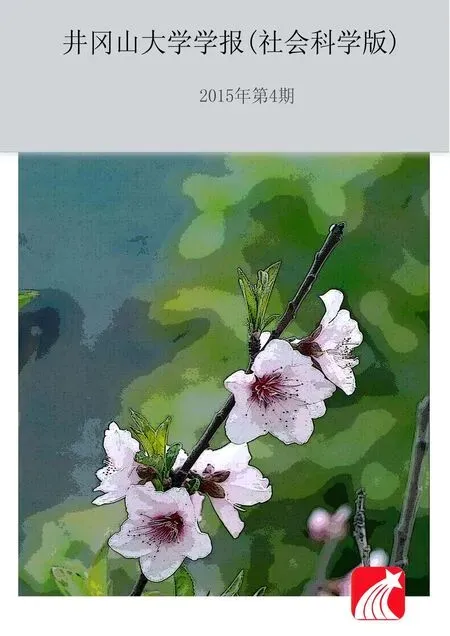广松涉“新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2015-04-15朱荣英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朱荣英(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广松涉“新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朱荣英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广松涉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加以融合,借助西方哲学平台试图为之提供一种不同于原苏联解释框架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视界。他的以实践第一性和关系存在论所界定的马克思人学思想,以 “物象化论”对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分析,以 “事的世界观”对 “物的世界观”的超越等等,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对我国当代哲学深入研究实践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理性启示。
广松涉;“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当代意义
一、广松涉“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旨趣
广松涉是日本著名的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他以浓郁的东方文化色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加以融合,借助西方哲学平台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种不同于原苏联解释框架的新理解模式,“差异性地构筑起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层面”。[2](P103-107)他一开始就要求“回到马克思”并试图恢复马克思原初视界的实践指向,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神圣般的金科玉律和包医百病的“莫里逊丸”来对待,而是以独特的探索性目光和现实性视界,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历史追踪以及问题把握,他也反对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原典文本的逻辑深处或者驻足于历史文献的纯粹考证上进行所谓理论诠释,而是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的最新需要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高度上,力主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新阶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超越了近代思想体系的地平线,无论是“科学主义的客观主义”抑或“人文主义的主观主义”,都不能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相提并论,实践唯物主义内在超越了近代哲学地平上的这两种极端形态。然而,吊诡的是,在前苏联哲学那里,曾经被马克思哲学扬弃了的近代哲学的东西,却被武断地置于马克思哲学的名下,将之做了退行性的理解不说,而且还将它统一的体系割裂开来,弄成了二元性的东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本是一个“唯”,现在却弄成了“二唯”。在前苏联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大夏的基石,作为第一哲学,它在自然观中的运用而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在历史观中运用而产生了唯物史观。广松涉认为这样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动态历史原像,实际上是前苏联教条中最顽固的内容。除此之外,前苏联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关注人类主体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哲学就是实现了 “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人道主义学说,这种人道主义就是人类的普遍的类本质。广松涉主张不论这些观点是 “有意的歪曲”抑或是 “无意的误解”,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解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中的不少人,也正是藉此而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腐朽的思想体系,并试图藉此攻击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当代要想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不是去创立什么新形态、新体系、新模式,而是首先要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从古今中西的历史大视野出发,恢复马克思主义原初的地平线,从学理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动态发展的历史真迹,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以往我们用教科书模式去反注经典文本的做法,实际上不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尊严,恰恰相反,而是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与形象。要想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与实践功能,就必须采取实践诠释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释义的初始情形与理论原貌。换言之,必须从解决当代问题入手,以融入实践为验证标准,以引领社会革新为旗帜,以重现原典思想的当代意义为准绳,任何教条化、绝对化、僵化的做法,都与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及其批判精神相背离。
正如有的学者指认的那样,广松涉通过对马克思的实践观、异化观及海德格尔存在论等有益成果的批判性分析,试图揭示日常意识的虚假构成机制及其理论局限,运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对之做出物象化的解释,以人类实践的历史性、文化性构造来说明实践第一性的关系构造,同时指出了日常意识物象化的认识局限性。[3](P55-60)但是他却没有能够指出造成这种虚假的物象化的实际根源,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物质性基础。更严重的还在于,他忽视了这样一种基本事实,那就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人们的物质性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日常观念,而不是相反。仅仅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造成物象化的意识,而不去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种批判事实上是一种隔靴搔痒。换言之,在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面临什么样的理性张力与思想困惑,他的物象化论的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广松涉认为,自己的“物象化论的构图”,既是“理解马克思后期思想的重要钥匙”,也是构想“社会哲学、文化哲学方法论的基础”[4](P1),立足于物象化论(关于“关系主义的存在事态”理论)去考察问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与基本方法。应该说,这种自我肯认还是比较实际与客观的。因为广松涉以物象化作为本体论与方法论,对马克思实践哲学进行了独具日本特色的理解,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系列重要概念与观点,如人的实践性本质、关系性存在的历史内容、历史与人的活动的一致性、“物的世界观”与“事的世界观”的区别、物象化与异化劳动等等内容,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也具有多方面的理性启示。而广松涉以“关系存在论”和“实践第一性”原则进行阐释,旨在论证他的“事的世界观”对“物的世界观”的合理扬弃,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对旧唯物主义特别是前苏联教科书框架的有力批判,也是对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和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弘扬,当然也与我国哲学界多年来一致倡导的实践唯物主义路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契合性。[5](P9-13)虽然对马克思哲学许多问题的理解还存在重大差异乃至本质区别,但是他毕竟以一种卓异的风格重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不可超越性,因而对科学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实践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广松涉从“关系存在论”出发重新诠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广松涉与阿尔都塞一样,都主张马克思主义人学并不是什么抽象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导致自然科学精神的内在断裂,更不是什么“人学实体论”、“主体唯物主义”或者“人学唯物主义”,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 “实践关系存在论”。但是,在广松涉看来,虽然阿尔都塞开始从现实的人入手去论证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类本质,这的确与马克思实践人学具有内在相通之处,并以之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人学灵光划清了界限,但他仍然充满了令人费解的成分,仍然保留了“隐性的黑格尔神学构架”[4](P18)。因为他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分析,先验地预设了人的异化与复归的神秘过程,即从“人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到“被异化的非本真存在”再到“扬弃异化而复归人的本真存在”的过程。与之不同,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来分析历史的,揭示了人和人的社会生活的实践性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对世界的实践把握,表现出人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对象性活动中处于一种主体性地位,彰显了自己的主体性特征与能力,意味着作为主体性的人在面对外部物质世界时,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在对象性活动中主动地选择客体,主动地决定运用何种中介手段和怎样运用这种手段,主动地决定对客体的改造方式与评价方法。人的主体性使得外部对象作为客体按照人作为主体所确定的方式与人发生关系,同时也使得人作为主体按照同样的方式与客体发生关系,使得他们作为整体的因素按照人的目的与需要协同地发挥整体功能,从而形成现实的、具体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构系统(“关系的规定态”)。[6](P243)作为主体的人的目的与需要,决定着人与物发生关系的方式与方法,制约着价值生成与实现过程的结构与特性。正是这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使物为人而存在、使人为人而存在、使自己为自己而存在,实践成为人特殊的存在方式,成为理解和把握人及人的社会生活本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对人所作的这种实践性分析,既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有重大差别,也与施蒂纳之流的人本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马克思扬弃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实体性人本主义的哲学框架,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关系存在论。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实践关系存在论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视界,是马克思一生中所开创的最伟大的哲学变革之一,它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说与感性的人本学,也超越了唯心主义的观念实体论与精神现象学。[7](P22-31)旧唯物主义的唯实体至上、以客体吞没主体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唯客体主义”、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它与唯心主义所宣扬的唯灵论、唯理论,在实质上完全等同、毫无二致。它们都不足以表征马克思实践关系存在论的根本点,不足以揭示马克思实践第一性的思想路线及其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
广松涉通过强调实践第一性,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与能力,根本改变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目的,把实践之上的人的历史活动作为自己哲学把握的唯一对象,这样,以实践取代了物质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范畴。但是,这种实践第一性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的第一性,而是功能性的第一性,是承认物质本体之当然基础上的第一性。马克思将实践提升到本体地位加以把握,与唯物主义物质本体思想并不矛盾,恰恰是内在统一的。实践本体是一种关系本体,它承载着参与实践活动的各种物质性要素,默默地将物质本体包含在自己的前提中,这样既与客体本体论、主体本体论区别开来,又以决定性的胜利姿态超越了心物二元论及主客二分方式。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真谛就在于从实体本体论向关系本体论的转变,以实践关系的存在论新范式凸显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地平。正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了历史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历史的高度一致,实践关系成为马克思哲学最高意义上的逻辑本体,凡是旧哲学将人理解为实体的地方,马克思都将它重新理解为关系性的存在。任何实体都不能离开关系而存在,都只能存在于特定的关系中。任何事物都是属人的,都是为人而存在的,而都是以物的关系所掩盖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质实体首先是以与生存实践的关联相适应的表相而呈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也就是实践关系中的历史的生活世界,即所谓在世界历史关系中的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客体的物质性与实践的主体性,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存在关系性的本体的‘主体际性’”[4](P11)。实践说到底是一种关系,是人与自然双向对象化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关系,是自然对人的生成与人对自然的生成的关系性活动,是交互主体性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人学就是基于实践关系的社会存在论,实践关系规定着人作为人的最高本质,实践第一性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人学的最高原则。广松涉分析了世界是怎样通过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而呈现为一种主体性的关系态的 (一种关系性的社会存在),而人的这种主体性的关系存在,又怎样被日常意识虚幻地表述为一种物象化关系并反过来支配人的活动的,进而,又透过物象化关系的构图及其扩展来如何揭示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本质与发展规律的。通过这种分析,显现了马克思哲学所描述的人的世界,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关系性存在,这种存在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赋予各种特定意义的,世界对人的生成与人对世界的生成,都是在交互主体性的活动中完成的。实践所造就的这种“关系意义态”,是一种“事的世界”(实践的事实或者“用在的自然”),不能仅仅视作主观的关系或者客观的关系,而是主客体交互作用中而生成的物象化关系、为我而在的关系,是人的实践而非别的什么,才赋予世界以社会性的存在形式与意义的。实践是理解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相分离又相统一的唯一根据。
三、广松涉以“物象化论”对马克思异化劳动论进行的批判分析
广松涉论证人的实践关系性存在论的根本旨趣,在于弘扬他的“物象化论的构图”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从早年不成熟的劳动异化理论走向晚年的科学的物象化论,后者是天才的马克思给人类做出的突出贡献。在马克思新的物象化论中,抛弃了各种先验的逻辑假设——实体论、观念论等等,把实践第一性确立为一种根本性的“新人学原则”,把人理解为基于实践的关系性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历史的本体,不再是唯客体主义的物质实体或者唯灵主义的观念实体,而是人的主体际性的共同活动所构成的实践关系性的主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与历史,不过是这种实践关系的物化,即社会关系的物相形态。在他那里,“物化概念被规定为以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实体与事物的属性来表象人与人的关系”。[4](P12)实际上,这是人们在通常条件下从直接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物相错认即“物象化”。对于一定的社会存在,物化并不是所谓的人的本真存在的异化,而首先是一种具有深刻必然性的普遍有效的事态,人们就是对这一社会方式存在着物象化式的错认。
马克思不仅仅批判性地阐明了经济现象中的物象化问题,而且对历史领域、社会政治领域的物象化以及道德制度、群众运动等等的物象化问题,都做出了科学的分析,物象化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容与普遍特征。[8](P7-14)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物象化进行过定义式的论述,但在其晚期的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用法: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以物与物的关系或者是以物所具备的性质、自立的物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事态。不难看出,这样的事态被物象化一词所称呼着。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事态,就是物象化现象。这种现象,马克思在早年是以异化理论来论证的,而在晚期著作中是以物象化理论来替代的。在与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早期构图中,已经蕴含了晚期物象化构图的主要内容,异化论与物象化论并非毫无关联的,而是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后者正是在对前者进行辨证扬弃的基础上而成立的。
广松涉物象化理论的基本内容是:1.关系的物象化是这样一种事态: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以外观相异的、物质的关系之形式出现,就会错认为一种物象化事态。关系的物象化,并不是指有关系的事物像字面意义上那样生成转化为物象的存在体,物象化的这个“化”,不是直接呈现的,而是反思得来的。在日常生活中,以物的关系、物性、形态的形式出现的事物,经过理性的反思,我们认识到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其实是被物的关系掩饰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折射映现、虚假现象,这种物象化是我们在日常意识中共同构造的事态。2.物象化是人们的理性经过反思而主观构图的结果,它不是本体的实体存在,也不是自然的存在物,而只是人们思维中对它的想象类比,完全是一种主观构境的结果。在思维中人们对物象化构造的“关系规定态”,并非真的存在这种事态,相反,以客观的、对象的形式存在的物象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并非原本就客观存在,而是一种虚构。3.物象化是思维建构的东西,这种虚构并非蓄意妄想,而是以一定的实际存在的关系态作为存在根据的。虽然不是真实的图像而只是一种虚假现象,但是,它对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物象化不仅仅现存地被感知,而且是作为现存的物象而存在的,它反过来又控制人们的实际行动。不管它如何被认定,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物象最终是客观地、对象地现存的物象,这个物象直接地制约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4.人与人关系的物象化存在,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尽管是以客观的、对象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往往具有那种特异的存在性质,事实上,往往鲜为人知、不易察觉。因为,它附带着自然物的形式,自然存在及其属性往往会被各种文化的、社会的形式遮蔽它的物象化。就这样,人与人的实践的主体际关系被物象化为关系存在态,即所谓的文化的、社会的形象,通常在为感性的自然的现实所担负并存在的同时,如果将其自身的存在性质加以规定的话,呈现出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形象。这种特异的存在性质即自然的关系,却被社会、文化的形式物象化了,这种物象化构图还往往被赋予理想的性质。其实,它恰恰忽视了“物象化的内在机制”及马克思物象化理论的根本旨趣。
马克思并不是将超感性的东西宣布为形而上学就草草完事了,而刻意要指出的是:以那样的形象客观地、对象性地存在的特异物象,实际上不过是一定的主体际的诸关系的折射映现,并且阐明了这个神秘的物象之秘密,带有拜物教的特征。广松涉的物象化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马克思所说的物化,绝不是什么关系本体的外在化物相,亦非什么主观的虚假形象。在马克思看来,物化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4](P13),即对自然的占有和对象化,这是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根本不需也无法消除。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在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外在性的物化,即历史主体颠倒地表现为客体、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遮蔽着并且受这种异己的力量支配。这种历史性的物化就是异化,马克思要消除的就是这种异化并藉此来证明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性与暂时性。对于前一种物化,马克思却要加以肯定,而不是要将之视作外在的物象化;对于后一种,马克思强调要诉诸于颠覆性的社会革命来完成,而不是进行什么物象化的意念革新。正是在这一点上,广松涉却陷入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唯心论泥潭,且越来越偏离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本真轨迹”。[9](P17-20)
四、广松涉以“事的世界观”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当代表述
上文中谈及的两个重要概念即“事态”和“物象化的内在机制”,都与广松涉的哲学理论——“事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换言之,“事的世界观”是其他两大理论的哲学基础。广松涉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事的世界观”:在认识论的视角中,它意味着对传统主客体二元结构模式的超越,并以四肢构造的理论模式去替代它,从而实现了认识论历史上的一场革命变革。在本体论的视界中,它意味着对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主义、理性至上主义的超越,并以关系的基始性、根基性、始源性替代了客体的基始性、根基性、始源性,以关系本体论——实践关系存在论替代了物质本体论,完成了本体论领域的一场重大革新;在逻辑的层面上,它意味着汲取了后现代主义之“与同一性开战”的先锋理念,与同一性、一元性、本质性、直接性为基础的假定相对立,而以差异性、延异性、异己性、疏离性的根源性范畴取而代之,强调本体论上构成要素的复合型与关联性,以相互作用范式取代单一因果决定范式。在其《存在与意义》一书中,他认为“事的世界观”是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哲学,它抨击的是传统的日常性观念及其在理论反思中占居统治地位的“物的世界象”[4](P14)。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这种“物的世界象”理论,它把诸多种类的直观中的“物”视作构成全部世界的基础,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或者几种原初的物质形态,将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物,直接认定为世界统一的基础或者本质,把握世界必须且只能从客体入手进行纯粹外在化的描述。显然,这是一种实体主义的、唯客体主义的世界观,它认为有没有存在以及有什么样的存在,与人的内心观念无缘,与主体特征及其活动亦无缘,只能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进行纯粹外在性的描述。将外部世界仅仅作为感性直观的对象(物相图景)来解释,以感性的实在性来认定唯物主义的基础,以现实性的感性存在物作为整个世界统一的始基。对于这种感性对象性存在,“根据这一世界观的统觉,首先可以直认存在着独立存在的存在体(实体),这些实体具备着诸种性质,并且相互地关系着。此处形成这种描象,具有性质的实体初始性地存在,实体间第二性地结成关系。——实体观历来有许多种类,质料—实体论、形相—实体论、原子—实体论等、此外,还有一元论和多元论。 ”[10](P1)广松涉认为,只有扬弃唯客体主义抽象的哲学路线,而从主体关系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人及其世界的真实关系与本质,才能“确立一种新的关系主义的‘事的世界观’”[4](P15)。
广松涉承认自己的“事的世界观”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或者说,他实现了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向马克思实践关系存在论的一种归属。在他看来,任何“事”都是关系中的事,即都是“关系性的事”,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此在去在”,即在一定时间内的世界中存在的事态。这种关系性的事态,不是当下“在场”或者“上手”的实体性的物相,而是在特定关系中因“此在”积极的“在”而开展出的事件或者事情,广松涉将之称作“用在”,事实上就是“实践之存在”。整体的世界就是因人的实践活动而开拓出的事实,对事实、感性及对象必须做实践性的理解,才能解释世界的真正本质。可见,他所说的“事的世界观”不是别的什么理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科学实践观;他所说的“关系性的事”,就是实践性的存在或者实践事实。因为惟有实践才是连接主客体关系的中介与基础,属于人的任何事实,都只能是在实践关系中并作为它的结果而存在的事实。实践是人与世界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整个世界都是在实践中对于人的合目的合规律的不断生成。若远离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要么如唯心论者把世界看成是能动性的精神的展现,要么如旧唯物论者将世界理解成与人无缘的 “绝对的自然”,这两种理解都不是对马克思的正确理解。广松涉认为,“事”是一种“用在的自然”即实践事实,而非“自然而在的自然”,纯粹外在性的自然是 “无”,“无”不是不存在而是对人来说没有实际意义。事态世界不是直观的“视象”、感性事实,而是存在本身在物象化后所生成的事实——关系性的事情。关系性存在是第一性的,关系是初始性的存在,而实体则是第二性的东西,是被关系物象化后而生成的虚假形象。广松涉以物象化方法所推崇的由“物的世界观”到“事的世界观”的转变,从实体主义向关系主义的根本转向,得到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广泛支持。无论马赫、海森堡的理论抑或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现都表明,实体主义本体论早就陷入自我崩溃、自我否定的泥潭,而关系主义存在论则日益成为主流趋势,关系性存在成为人们考察问题的“基始平台”。[11](P63-66)关系初始性这种存在论,常人不易直观,而直观到的恰恰是关系被物象化的虚假形象,结果人们往往将物象化中的关系错认为“物”。物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错认的视象,马克思哲学就是探讨关系如何被物象化为物的。
马克思认为,物象化不是某种纯粹的客体变化,而是一定的关系事态转化为对于人来说的“为我性的物象”——以物象的形式而存在(物为人而存在),这并非仅仅是认知的事态,而是实践性的事态,是被交互主体性实践活动介入其中而文明化了的自然事实,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建构出来的人化的、属人的事实。对于这种建构,广松涉又以四肢存在结构论做了进一步说明。“四肢结构”是广松涉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于理解他的实践关系存在论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世界始终是以现象的二肢、观念的二肢构成的四肢存在结构,一切事物均处在四肢基座的实践建构之中,这是“事的世界观”的源发依据。显然,广松涉以这种怪异的词句和字眼来表征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建构与发展,实际上很牵强,所以,他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只是“新”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他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当代表述,只是激活了马克思哲学怪异的另类视像。
[1][日]参坂真.现代的思想状况和马克思[J].前卫,1983,(1).
[2]张一兵.广松涉: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9).
[3]杨思基.日常意识的分析与扬弃——评广松涉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理解[J].湖湘论坛,2010,(6).
[4][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彭曦,庄倩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任平.广松涉“事的世界观”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河北学刊,2007,(5).
[6]肖前,等.实践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7]张一兵.广松涉:物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像》解读[J].哲学研究,2008,(4).
[8]王南是.广松涉对马克思理论物象化论阐释及其扩展[J].学术研究,2007,(6).
[9]孟飞.广松涉的“物象化”论简评[J].中南大学学报,2012,(2).
[10][日]广松涉.存在与意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邓习议.实体主义批判——广松涉哲学视域中的西方哲学[J].河北学刊,2009,(1).
A Brief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Justice Logic
LU H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The shift of western doctrines of political justice from prescriptive political legitimacy to prescriptive-procedural political legitimacy is in fact aimed to solve the self-limit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operation.Such an evolution of logic shows how socio-political justice may lead to substantial justice through procedural justice in a time out of ethical politics.Though such a procedural justice to certain extent guarantees the justice of power in operation process,it is,in the Marxist perspective,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prescriptive one.In one word,both of them started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presumption of human nature based o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division,which is a product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 modern binary paradox.
political justice;prescriptivism;prescriptive-proceduralism;political legitimacy
B15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4.008
1674-8107(2015)04-0054-06
(责任编辑:韩 曦)
2014-05-24
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境遇及其实践超越——以广松涉为例”(项目编号:52YH:2014-01)。
朱荣英(1963-),男,河南尉氏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