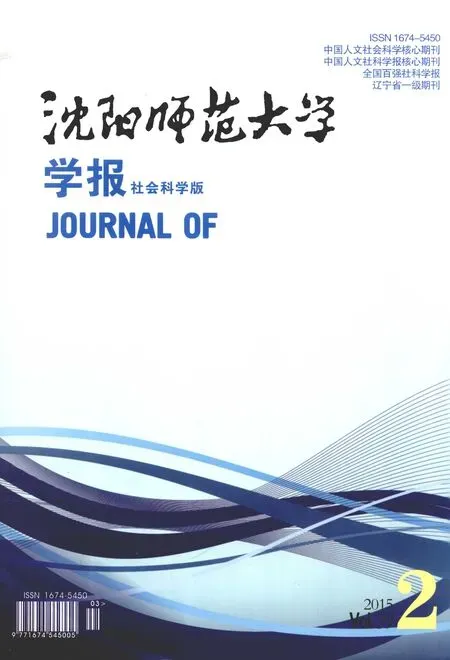生活政治视域下的《共产党宣言》解析
2015-04-11刘力红
刘力红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生活政治视域下的《共产党宣言》解析
刘力红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内蕴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生活政治的微观视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了呼之欲出的契机。因为使“一切东西都烟消云散”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现代人似曾相识;从挑战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存在的合理性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无奈与生机中,现代人仿佛可以听到某种源自自我生命深处的哀叹与抗争;至于对未来的生活方式的愿景,则又何尝不是承载着现代人深深的渴望?因此,在现代性所代表的宏大叙事遭到批判和解构的现代社会,《共产党宣言》仍然能够以其丰富的内涵发出自己精彩的回声。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发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内蕴于《共产党宣言》中的生活维度来解读它,比仅仅从社会政治的维度来思考它,显然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内蕴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中的生活政治的微观视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了呼之欲出的契机。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从来都不缺乏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关注对象的微观视角,只是受制于既有历史条件,内蕴于马克思哲学之中的微观视角被他的社会政治这一宏观视角所遮蔽了[1]。然而,离开了对本来内涵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的微观视角的理论潜能的挖掘,很容易将马克思解读为抽象的教条,一如传统的教科书解读模式所做的那样,在日常生活问题日益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的现代社会,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在现代社会,要想全面呈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深刻的理论洞察和实践力量,必须立足于内蕴于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微观视角,从生活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一、作为“资本逻辑”基础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由于马克思总是立足于人与生活环境的辩证关系来把握人,认为人总是具体的环境中的以特定的方式生活的具体的人,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这些具体的人是指处于阶级斗争条件下的具体的人。因此,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具体个人所处的阶级状况,正是其具体的生活方式的集中表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伴随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及其产生、发展、灭亡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及决定其存在的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以价值增殖为目标,具有利己主义的性质;同时,又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一方面,它用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守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以至于,封建的所有制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还立足于他的唯物史观具体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同时指出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产生过程。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具体说,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世界市场的开辟及与之相关的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巨大发展,反过来,这些发展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成就,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简言之,现代大工业与由其产生的现代交往之间的辩证运动构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基本内涵,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是现代大工业和现代交往辩证运动的产物。
进而,马克思通过具体分析资产阶级的存在方式,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内在活力和发展状态。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275这本身也我是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从中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活力。马歇尔·鲍曼正是在此意义上“把《共产党宣言》看作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宣言的原型”[3]115。
马克思认为,正是依赖于这种生命活力,资产阶级成为真正的创造者,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遍地开花。他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到全球各地落户、创业,建立联系,开拓了世界市场,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卷入其中,使世界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相互往来和彼此依靠。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此外,资产阶级还通过迅速改进的生产工具和便利的交通,把一切野蛮的民族都卷到资产阶级的文明中来,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及所谓的文明制度,变成资产者。这样,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生活方式。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生命活力归根到底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所释放出来的活力,是一种受制于物的增殖和占有这一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因而,它终究会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陷入混乱,丧失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由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灭亡的必然性。他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使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有制关系,现在不能再支配自己所创造的社会了。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社会文明过渡,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然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只能使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存在受到威胁。因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无非是通过消灭大量生产力,夺取新的市场,更彻底地利用旧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其结果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这样,资本阶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活力终将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窒息。
由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虽然无法在自身之内解决人类文明的困境,却创造了解决人类文明困境的物质因素,因此,只有以此为基础,完成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的转变,才能使人类文明摆脱困境。资本逻辑的困境只有被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取向的人本逻辑所取代,人类文明才有新的希望。其中,无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正是解决人类文明困境的动力因素。
二、挑战“资本逻辑”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由于内蕴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的价值目标是价值增殖,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独立化而成为不受具体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制约的资产阶级社会,一旦以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的内涵、以发展为特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再能够支配自己所创造的社会,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自身的发展的源头活水的资产阶级社会必然走向尽头,无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正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因素。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被动存在的、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他指出,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此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亦即,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受制于资本的逻辑,因此失去了自身与工人的生命需求之间的统一性,工人不能期望通过这种活动,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的同时,确证自身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处于这种生活方式中的工人的生命尊严受到了挑战。
进而,马克思分析了内蕴于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内涵和改变世界的生命活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并不是被动地屈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是组织成为阶级和政党进行反抗,在不断受到工人自相竞争的内部矛盾的破坏中不断重新产生、强大;在包括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在内的旧社会内在的诸多冲突中不断发展自身,使自己不断壮大。作为现代大工业的产物的无产者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他自身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没有什么东西必须加以保护,因而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当然,无产者一无所有的特点,也决定了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
可以说,生存需求和意义需求同时被否定,完全丧失了其人之为人的生命尊严的无产阶级除非起来反抗,否则没有出路可言。然而,无产阶级除非对在客观上由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其实是作为其自身的反抗的客观条件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否则就会陷入盲目性。为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成为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做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资本的形成和增殖是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又依赖于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资本生存的条件。雇佣劳动的存在条件是工人的自相竞争。因此,只要工人用彼此之间的革命团结代替他们之间由于竞争所造成的分散的状态,就可以消除雇佣劳动存在的基础,进而使资本乃至资产阶级丧失生存的条件。而资产阶级在有意无意中造成的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则使工人具备了通过联合而达到革命团结的条件。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使以工人之间自相竞争为存在条件的雇佣劳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了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产阶级及与之相应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本条件。这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就被挖掉了,它产生了自身的掘墓人。
换言之,被动的处于资本逻辑之中的无产阶级,要想摆脱这种被动状态,就必须挖掉资本逻辑赖以存在的根基—雇佣劳动制,而雇佣劳动制存在的基础又是工人之间的竞争,所以,只有通过联合而非工人之间为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展开的残酷的竞争,才可能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这一客观基础,而消灭资本逻辑及由这种逻辑所决定的基本生活方式的源头活水,才能实现人类生活方式的实质性的变更。
在现代社会,仍然遭受着现代性之苦,在很大程度也不得不承受着资本逻辑统治之苦的现代人,如何才能根本上摆脱这种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僵化的整体性之痛,可以说仍是现代人所关心的问题。那种企图通过全面抛弃现代性、整体性的努力已经被现代人的意义危机所否定,建立在个我孤独奋斗基础上的种种后现代的思考,被证明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安身立命之感。马克思对超越资本逻辑的深刻洞见仍能为人们最终超越现代性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工人之间为了争取生存必需品而进行的竞争仍是现代人的宿命(当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如许多西方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这种仍然受制于资本逻辑的生活方式通过消费主义这种新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新形式并不能掩盖它受制于物质生存之需的实质。)那么,通过联合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仍不失是现代人最终摆脱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所在。当然,在现代社会,人们未必通过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完成这种联合,也不仅仅是因为生存困境而联合,或许,深层的意义危机也可能成为激发人们从事自觉的社会性联合的契机所在。现代的教育的发展和信息联系的发达,为这种联合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建构
由于人类的超越性需求所决定,我们从来都不会也不应该被动地屈从于某种外在必然性的宿命。对自然必然性的抗争,人类创造了工业文明;同样,对盲目的社会历史必然性的挑战,则呼唤着一种在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式的诞生。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正是一种内蕴于社会历史规律中的新的文明样式的愿景,它承载着人类有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想,但又不失现实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首先指出了共产主义的共同生活方式不是建立在世界改革家所发现的思想、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共产党人的原理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而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它是阶级斗争这一现实关系的产物,其最近目标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即建立无产者之间的现实联系,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反,人们的意识、思想则随着他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思想的历史仅仅证明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共产主义革命在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实现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又同传统观念实现最彻底的决裂。
进而,马克思通过反驳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责备,论证了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建构的合理性和目标。当然,这种合理性不是来源于人类的精神,而是来源于现实的关系。其中,在物质领域,针对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马克思首先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即要废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关系,而不是废除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占有关系。因为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因此,共产主义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仅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而只是消灭这种占有所反映的工人的可怜境况——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显然,以消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为前提和特点的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合理的。在精神领域,针对资产阶级把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认为消灭教育,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要消灭的仅是一种把人训练成机器的教育,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归根到底,共产主义反对一种维护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的教育,而不是消灭一切教育,其精神领域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呈现。概言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所要反对的只是资本阶级的私有制及建立在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把人训练成为机器的教育,反对受制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认为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灭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才能建立更加合理的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
最后,马克思通过对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合理性的分析,指出了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特点。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活的劳动只是增殖的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过去支配现在,活动着的个人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只有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因此,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和自由,消灭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买卖自由。代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样,工人的生活就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仅仅作为人们的生存手段而存在的状态转变成为目的本身,现在支配过去。马克思预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当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的性质。在未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未来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动态和谐的存在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每个人通过自身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历史规律并非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变革之中的铁的必然性,而是通过人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得以实现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表现为通过辩证理性主导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二者之间矛盾解决的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摆脱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盲目必然性的统治,开始通过自觉的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来满足每个人的整体性的生命需求,并为这种整体性的生命需求的满足创造了客观条件。共产主义不同于人类既往文明形态的根本之处在于,在那里,在微观政治的社会生活层面,具体的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身整体性的生命需求的满足认同为自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证的客观基础,因此能够自觉地尊重和利用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并通过这种自觉的生活方式确证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现实[J].中国社会科学,2011(3):40-5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责任编辑李菁】
A11
A
1674-5450(2015)02-0046-04
2014-11-21
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基地课题(ZTS201309)
刘力红,女,辽宁瓦房店人,沈阳师范大学讲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