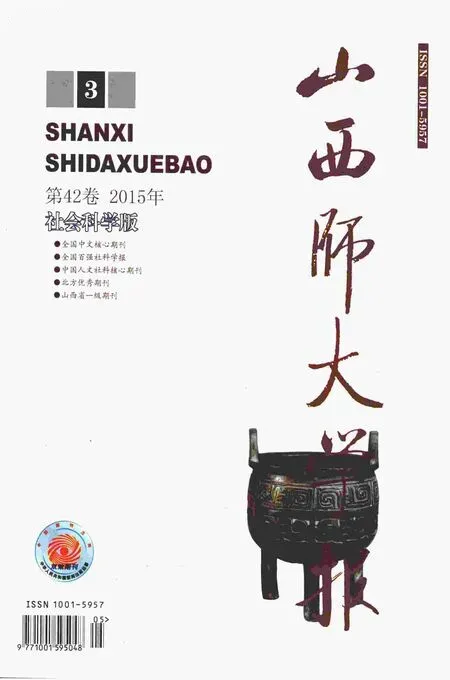闲谈结构、个人笔调、杂糅语言
----论语派小品文的文体创新路径
2015-04-10俞王毛
俞 王 毛
(南昌师范学院 中文系, 南昌 330032)
1930年代,论语派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期刊为依托,大力提倡言志文学,并以之对抗传统载道文学,矫正“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1]296。在言志文学理想的烛照下,论语派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散文类型——幽默性灵小品文。此种小品文题材广泛、风格幽默、形式自由,既不同于传统散文,也不同于同时代的左翼杂文和京派散文,表现出高度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
对于论语派在散文文体建设上的贡献,前人已有较多研究,如庄钟庆对论语派幽默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解读[2]。杨剑龙对论语派小品文幽默风格和闲适笔调的分析[3],等等。不过,总体上看,目前对论语派小品文文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论者主要关注小品文的思想和风格特征,对于其形式特征则有所忽略。事实上,形式改造是论语派小品文文体创新的主要路径和着力点,通过对闲谈结构、个人笔调、杂糅语言的强调和运用,论语派更新了文体观念,“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4]394,为散文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以闲谈结构促进体裁解放
在悠长的中国散文传统里,最初并无多少体裁上的限制,先秦、两汉散文往往结构自由、文气贯注,唐宋以后,散文结构逐渐凝定,清代占主流地位的桐城派散文深受八股文的影响,法度森严,固守着起承转合等结构格套。文学革命中,桐城文章成为批判的靶子,但是胡适、陈独秀等人反对的主要是桐城文章的仿古主义,对其结构上的弊病则缺少关注。真正将散文结构作为一个独立命题提出来的是论语派作家。在《文章无法》一文中,林语堂论述了散文的体裁和结构问题,他指出,文章并无一定的体裁,体裁是根据思想和个性千变万化的,所谓“起、承、转、伏”等正统文章作法并非文学创造之要领。[1]408为了推翻散文结构的陈规、打破散文体裁的束缚,他提倡学习西方随笔的闲谈体结构方式,在行文中“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1]480。陈炼青也撰文指出,小品文写作是自由的,它不像论文似的玩着法宝,不必讲究“文章之组织和前后的次序”[5]。刘半农则以自己的创作经验说明闲谈体的创作方法:“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日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6]在他们的提倡和示范下,闲谈体小品文的写作蔚然成风。
论语派作家几乎都是闲谈体的好手,他们所创作的说理、抒情、叙事、记游等类型的散文多是不讲结构、不讲章法的闲谈体。如林语堂的《女“论语”》就是一篇谈笑从容、妙语如珠的文章。此文从古时“妇言”说起,谈到自己的男女平等观念,谈到女性善用直觉的思维特征,谈到女性的谈话特征,最后列举三段与不同女性之间的对话以佐证自己的看法。全文东拉西扯、枝蔓丛生,却始终围绕女性谈话特征组织材料,时时信马由缰,而又收纵有度,给人一种挥洒自如的感觉。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论语派也多以闲谈笔法结构材料。论语派作家不欣赏传统传记按人物的姓名、字号、籍贯、生活史的顺序记写人物的套路,或是现代名人录的罗列人物头衔、著述的履历式写法[7],他们更愿意以轻松幽默的笔调闲谈传主的日常琐事,如此不但为传主作传神写照,也使作者自己的个性表露无遗。简又文的《我的朋友林语堂》就是这样一篇不循格套而风采自见的传记。文章从林语堂宗教信仰的改变谈起,逐渐将笔触伸入其家庭生活、读书写作、爱国情怀,所写的多是家常事件,如林语堂给孩子们买零食、陪孩子游戏、与朋友开玩笑的情形,传主的理性精神、温雅品性、亲和作风、家国深情却如闻如见,由于作者是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来记写朋友,在传达出传主个性的同时,作者本人善戏谑、重友情的神情风度也跳荡在字里行间。论语派闲谈体最大的特征就是自由,围炉谈天般的亲切氛围,真诚无伪的谈吐方式,庄谐并出的行文风格,若断若连的文章结构,在在显示了闲谈体的自由品性。阅读这类小品文,犹如听一位热爱生活的智者轻松自然地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不知所起也不知所终,却能给人带来智慧的启迪和审美的愉悦。
论语派之提倡闲谈体小品文,是将西方的学理文和中国的“大品文章”作为反面参照的。闲谈体对于学理文的反叛在于其反体裁性。在林语堂看来,“文本无一定的体裁”,学理文却固守某种体裁,“不敢越雷池一步”。相比之下,小品文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体裁的限制,小品文作者“认读者为‘亲热的’(famili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既然是朋辈闲谈,写作态度大可随便,这样写出的文章自然意态横生,趣味盎然,“不论所谈何物,皆自有其吸人之媚态”。闲谈体对于载道文的反叛在于其个人性。林语堂将闲谈体与大品文的区别看成“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区别:“言志文系主观的,个人的,所言系个人思感;载道文系客观的,非个人的,所述系‘天经地义’”,大品文章因禁忌甚多,蹈常袭故,谈不出大道理来,小品文行文自由,场面上也许不如大品文好看,其入人处反深。[1]480—483闲谈体小品文既不同于学理文的严谨枯燥,又不同于载道文的循规蹈矩,其随意自适的结构形式恰与“言志”的内容相得益彰。此种小品文的成功客观上起到了冲击散文陈旧格套、解放散文体裁的作用。
二、以个人笔调改变板滞文风
在提倡闲谈结构的同时,论语派作家还提倡个人笔调,希望以之改变传统散文的教训口吻和板滞文风。在传统社会,不少作家秉持载道文学观,认为散文必须代天宣教、代圣贤立言,他们的文章立意大都庄严堂皇,充满教训意味,行文则起伏分明,板重艰涩。新文学兴起之后,古文的载道观念受到批判,但新文学家关注的主要是散文内容的变革,至于形式方面的更新,除了以白话代文言这一点外,结构、笔调等要素很少涉及。事实上,不少新文学家以民众导师自居,“开口‘天下’,闭口‘国家’,时时板起青年导师铁青的面孔,处处不忘领导世界新潮流”[8]49,因而他们的散文同样表现出训诫色彩和庄严气象,创作主体的真实性情被刻意掩藏,散文也因此少了个性的鲜活。林语堂在上世纪20年代即已注意到现代散文的这种弊端,曾提倡以幽默笔调来改变“板面孔”文学一本正经的写法[1]531—535,只是当时应者寥寥,效果不大。论语派形成之后,林语堂再次提倡笔调的改革,力图以个人笔调改造散文观念,改变板滞文风。他的提议得到了论语派其他成员的支持,他们立足于流派期刊,彼此声应气求,终于使个人笔调小品文的写作形成规模。
在《论小品文笔调》、《小品文之遗绪》、《说自我》等文中,林语堂一再解释个人笔调的含义,分析个人笔调的表现,鼓励作家将其应用到小品文写作中去。林语堂指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又叫闲适笔调(familiar style),是西人对小品文笔调的称谓,其要旨在于表现个性与真情,“一人行文肯用一‘我’字,个人笔调即随之俱来,即大喜大怒,私见衷情,爱憎好恶,皆可呈笔墨中矣。至‘以自我为中心’乃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亦整个现代文学与狭义的古典文学之大区别”[9]。他将个人笔调看成笔调上的解放,认为这种解放与白话取代文言而达到的文字上的解放有同样意义。[1]482由此个人笔调说得到了众多同派作家的响应。简又文对林语堂的个人笔调说评价极高,将其与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相提并论:“他主张用轻松的个人的笔调来写出个人心里的真思想,真感觉,这确是文学界的大解放。多年前胡适之等提倡白话文是文学革命之先锋,那是改革文学的工具,性灵文学是改革文学的实质和精神,是要把人们的灵魂放在文字的躯壳中,使其成为生活的、真实的文学,就这一点而论,我以为林语堂在文学革命的功劳实在不少。”[7]与此同时,陈炼青、林疑今、郁达夫等流派成员也从理论上对个人笔调说加以丰富和补充。陈炼青《论个人笔调的小品文》(《人间世》第20期)肯定了个人笔调的价值;林疑今翻译了英国作家亚历山大·史密斯《小品文作法论》(《人间世》第2、4期),该文以蒙田和培根散文为例详细阐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品文创作方法;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林语堂所提出的个人笔调的文体表示赞同,他指出:“文体当然是个人的;即使所写的是社会及他人的事情,只教是通过作者的一番翻译介绍说明或写出之后,作者的个性当然要渗入到作品里去的。”[10]7
除了理论上的认同和呼应,大部分论语派作家在创作中也很注意个人笔调的运用,他们的文章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征,如周作人之冲淡、林语堂之洒脱、姚颖之幽默、冯和仪之爽直、俞平伯之古雅、郁达夫之清俊、老舍之温和、老向之素朴……都是个人笔调说的形象诠释。下面对周作人、姚颖之文略作分析,以见论语派个人笔调之一斑。
周作人被称作文体家,他的散文中,既有类似于古人笔记的《苦茶庵小文》,也有极像西方闲谈体的《厂甸》,还有大量读书随笔如《风雨谈》系列文章,以及书信、序跋等。他总是能够将热望、喜悦、愤怒、痛苦诸种感情纳入轻松、谐趣的言说中,文章淡而有味,癯而实腴。如他的《怀东京》(《宇宙风》第25期)一文,是对他视为第二故乡的东京的追忆,作者细数日本的服装、饮食、建筑中的近情合理之处及日本文学与音乐的悲剧美感,文中流淌着对自己六年日本生活的追怀,对日本衣食住诸方面的热爱,对日本文艺的欣赏,也夹杂着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愤恨。这些感受本极强烈,但以叙述、议论、引用代替直接的感情抒发,有了文字上的这种缓冲,强烈的褒贬与爱憎也就变得平静内敛,文章由此获得澹然之味和闲适之趣。
姚颖《京话》从体裁上来看属于地方通信,如林语堂所说,其时“地方通信写成文学在中国尚少见”[11],而姚颖不仅将《京话》写成文学作品,且使其成为《论语》的品牌,其秘诀就在于个人笔调。姚颖擅长幽默,他曾对《京话》写法作过如下说明:“写时虽未经再三考虑,但大体有个范围,即是以政治社会为背景,以幽默语气为笔调,以‘皆大欢喜’为原则,即不得已而讽刺,亦以‘伤皮不伤肉’为最大限度。”[12]以幽默笔调写时事为《论语》所提倡,《京话》实现了论语派的这种文学理想。《京话》所写多为严峻的政治、社会问题,由于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和幽默笔调,往往能够化板重为轻松,取得涉笔成趣的艺术效果。《论语》第18期之《京话》就是这样的例子,文章在报道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赴陕西为迁都作准备的消息之后,对此种行为作了一番评论:“这不特是朱柏庐所说‘宜未雨而绸缪’、‘无临渴而掘井’的普通意义,恐怕还含有长期抵抗的意味在内罢。说明白些,就是‘小子,你再凶,我就算让了老家,然而我还有行宫及别墅呢!’”如此三言两语就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怯懦无能,嘲讽了不抵抗主义的虚弱本质,幽默笔调的表现力确实令人拍案叫绝。
论语派小品文的个人笔调充满个性色彩和自由精神,其对个人笔调的提倡为散文文体的更新带来了有益的启示,诚如论者所指出的,个人笔调小品文“为五四以来追求个性发展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新品种”,“这种新的散文文体,无论在当时为纠正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中出现的文体缺点计,还是为以后的新文学散文创作的繁荣计,都是具有创意性的”[13]。
三、以杂糅语言打破语言藩篱
讨论论语派小品文的结构和笔调,无法绕开作为其物质外壳的语言问题。与闲谈结构和个人笔调的个性化色彩相呼应,论语派小品文在语言的选择和运用上也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精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语言已经完成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但由于当时占主流的是工具论文学观,作家在文学语言资源的择取上仍受到许多清规戒律的束缚。五四时期,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论述中,语言主要是作为启蒙的工具在起作用。胡适认为,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现代白话和古代白话则是活的语言,是构成“文学的国语”的基本材料,在写作中应以白话代替文言。在19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中,工具论语言观更是占了主导地位。作为大众语的重要推行者,瞿秋白否定了现代白话文的现实意义,认为大众语绝对不能用文言和书面白话,只能采用百姓的口头语言和民间俗语。[14]859—860胡适、瞿秋白等人所看重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审美功能,其着眼点是在读者方面。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他们就在语言的通俗化上下功夫,而他们的做法又矫枉过正,于是语言的禁忌愈来愈多,这些禁忌在文言、书面白话、口语之间竖起了坚固的藩篱,文学语言所能摄取的资源愈来愈少。尽管工具论语言观从来不曾完全实现过,但是语言建设上的这种闭关自守的做法毕竟不利于现代文学语言的生长。
论语派的语言观与工具论者的语言观针锋相对。在论语派作家看来,语言作为文学的形式要素,其功用首先就在于表现自我,只要适合于传情达意,用什么语言都不成问题,使用或不用某种语言的理由不在于该种语言之“是非”而在于“能否”。周作人就曾指出:“我们写文章是想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力量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15]193林语堂也指出:“夫语者何,心声也,心上忽然想起,笔下照样写出。”[1]412他们秉持这种以表现为目的的语言观,在语言资源的摄取上就显得十分通达。周作人曾于1922年提出兼容并包的语言观:“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16]773这种攫取古今中外的语言资源并将其加以融合的思路为加强白话文的审美意蕴创造了条件。后来,他将这种思路具体表述为“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与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16]779—780。林语堂以“雅健”为小品文语言的标准,认为“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17]227。为此他提倡俗话和语录体。林语堂所说俗话就是普通劳动者的语言,他认为俗话足以达意传情,是真正白话,引车卖浆者流是所有白话作家的老师,“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18]203。林语堂之语录体主要指类似于宋人语录的文白夹杂的语言,公安派小品文字是其代表。在他看来,语录体文字信口而出,轻便清新,“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1]413,极富表现力。林语堂既提倡俗话,又提倡语录体,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在他看来,俗话是今人白话,语录体是古人白话,二者有着简练传神、达意畅适的共同点,不妨随意撷取,“熔炼锻合”,创造出一种简洁、清新、“又美丽又灵健的文字”,以实现语言“真正的解放”[1]511—514。老舍的语言观同样十分开放,他重视现代白话,同时主张批判地继承文言,因为“语言是一代传给一代的东西,不能一笔勾销,从新另造”[19]70,对西方语言技巧他也多所借鉴,“在文法上,有时候也不由得写出一二略为欧化的句子来”[20]726。由此不难看出,多数论语派作家都取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他们的小品文语言杂取文白,融合中西,句式长短随意,语气轻松幽默,总体上呈现出率真自然、清新简练的风格,又因作者个性和好尚的不同而拥有各自的特色。
论语派作家中,不少人善于将文言和白话调和在一起,他们的小品文字通脱老成,极富风致,如周作人的读书笔记,林语堂的论说文,郁达夫的日记和游记,俞平伯的《秋荔亭随笔》,如愚的《也是斋随笔》,简又文的《东南风》和《西北风》等;也有不少人善于将俗话、口语、欧化语融会贯通,他们的语言爽朗亲切、俗白精准,如老舍、丰子恺、何容、老向、冯和仪等人的叙事抒情小品文。而且这些作家大都不止一副笔墨,如简又文,他的《东南风》充满古雅之趣,《我的朋友林语堂》则俗白亲切;又如林语堂,尽管积极提倡语录体,他的多数文字还是以欧化作底的,由于他语言功底的深厚,能够使欧化语与古文妙合无痕,从而瞒过不少读者的眼睛。
丁晓原指出,“主体对于作为工具的语言的选择,体现着他对语言功能的认知,还体现着他对语言与对象之间特殊关系的理解”[21]。论语派以语言为主体意识的载体和自我表现的方式,通过对各种语言资源的灵活运用与合理调适,突破了狭隘的工具论语言观的束缚,打破了文言、白话、俗语、欧化语之间的藩篱,创造了高度个性化的、富有表现力的杂糅语言。杂糅语言既增添了小品文的韵致,也促进了现代散文语言的发展,同时,有了这种个性化的、灵活多变的语言,论语派对闲谈结构和个人笔调的追求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综上所述,闲谈结构、个人笔调与杂糅语言一起构成了言志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通过选择闲谈结构、个人笔调、杂糅语言,论语派实现了小品文文体的创新。这种新型散文的成功,更新了散文文体观念,打破了长期以来阻碍散文发展的种种有形无形的束缚,使散文写作成为充满自由精神的艺术创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论语派小品文的提倡和实践都是依托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期刊进行的,这些期刊由于个性鲜明、经营得法,在读书市场上十分畅销。林语堂等人利用自己的出版优势,反复申说,不断示范,幽默性灵小品文的创作遂成潮流,论语派的文体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这对于提升散文的艺术品位、推进散文的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1] 万平近.林语堂选集(上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2] 庄钟庆.论语派与幽默文学[J].新文学史料,1989,(3).
[3] 杨剑龙.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陈炼青.论个人笔调的小品文[J].人间世,1935,(20).
[6] 刘半农.《半农杂文》自序[J].人间世,1934,(5).
[7] 简又文.我的朋友林语堂[J].逸经,1936,(11).
[8] 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9] 语堂.说自我[J].人间世,1934,(7).
[10] 赵家璧,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1] 语堂.关于京话[J].宇宙风,1936,(22).
[12] 姚颖.京话序[J].宇宙风,1936,(22).
[13] 沈永宝.论林语堂笔调改革的主张[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14] 瞿秋白文集:中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15] 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本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6] 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夜读的境界[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7]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
[18]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
[19] 老舍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0] 老舍全集: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1] 丁晓原.语言三维视角下的中国散文现代转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