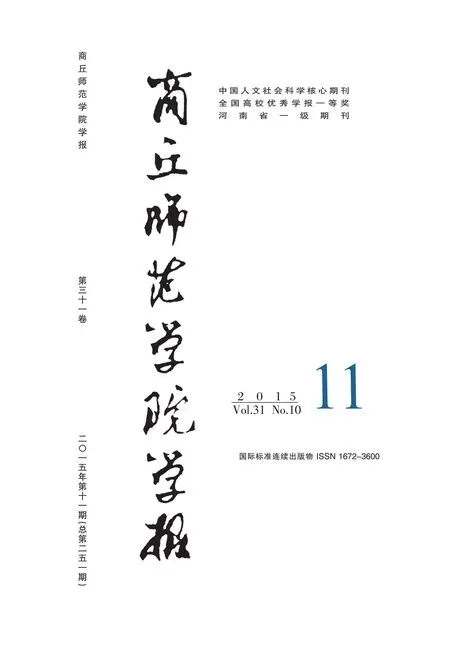严复政治学思想新论
2015-04-10王秋
王 秋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严复政治学思想新论
王 秋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严复从天演论出发论及政治学,认为以亚里士多德和卢梭为代表的政治学理论在国家类型划分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上存在重大问题。他从国家演化动力的角度将国家分为基于保护共同利益的真正国家、基于同种同祖的宗法国家、基于同宗教信奉的宗教国家三种。他认为“自由”或“专制”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程度,真正国家的政治治理并非取决于多数人的自由或是少数人的专制,而是在于是否有基于公理与民意的根本法律。
严复;政治学;天演;内籀
《政治讲义》一书反映了严复对政治学的系统思想。本文从方法论选择、国家分类及其旨趣、自由观念的正名、对专制政治之新的解释及其与宪政的关系等方面论析严复政治学思想的新意所在。
一、从历史术、天演术、比较术论政治学的变革
严复认为,中西传统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奠基在对天之理解之上,天在上,地在下,由此而论及人之尊卑贵贱,而日心说则打破这种天地之上下观念,进而抽空了以此论尊卑贵贱的世界观基础,导致“三百数十年之间,欧之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1]1241。在严复看来,导致近代政治变革的理论动因,就是联系十分紧密的天演论、历史方法和内籀方法。
在论及政治学与历史关系时,严复指出:“盖二学,本相互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1]1243严复援引西方成语之本意并非仅仅意在强调历史学与政治学之紧密关联,而是要由此推论历史方法在政治学近代转型中的重要价值。他认为,传统政治学是从心学或自然公理谈论政治问题,而从历史研究政治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新形态。
从历史学科的发展看,严复认为,历史学科不断发展,近代随着专门史的不断分化和独立,最终普通史演化成政治科学,并且从历史学演化而出的政治学能够见到政治演变之因果关系,而这是历史的可贵之处。他说:“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1]1243由此,严复认为,历史方法在内籀术(归纳法)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对历史、政治演进的因果关系的探究,近代政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因为对历史方法和内籀之术的运用。
严复强调了历史方法、天演方法、内籀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历史方法是占据基础地位的,此种论述方式之下,严复实现了对中国历史方法的重新激活,驳斥了流行于20世纪初期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一些见解,对当时中国人流行的政治观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推演出自己最具政治演变公例的结论。
二、从国家类型的新划分到政治新公例的推演
严复认为,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首要对象,而对国家进行分类,则是辨别异同、获取政治规律的基本途径。因此,严复在推出自己的政治规律理解之前,按照历史方法的要求,先对前人诸如亚里士多德、卢梭等人的国家分类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按照天演论的观念,对国家进行新的分类,由此阐发自己对政治演变之公例的新观念。
亚里士多德按照掌握着国家治理权力的多寡,将国家分为独治、贤政和民主三种类型。在严复看来,这种方式与古希腊的“壤地极小”的“市府国家”的现实相适应,而与近代的地域更为广阔、组织更为复杂的“邦域国家”不相适应。卢梭亦存在此种问题,故而导致其民约论的政治思想似是而非。
严复从“天演涂术”讲求政治,认为在天演程度较低的阶段,天的要素(宗法或宗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要素,至天演程度较高,则人为要素(主要是共同利益的维护)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性作用更为明显。按照推动国家演进主导要素的差别,严复将国家分为基于保护共同利益的真正国家、基于同种同祖的宗法国家和基于同信奉宗教的神权国家三种。这种划分克服了亚里士多德三分法不适用于邦域国家的弊端,并且将国家演进的动力要素和国家演进程度的高低有机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解释政治问题时更有普遍效力。此外,严复还着重分析了“惟以压力”结合的第四种国家形式。他认为,此种国家以强力“并兼”主导政治运行,是国家演进的无机体状态,因此,程度更低,为非自然演进之国家,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严复在此表达了对高度专制的政治统治的批评,并指明其必然被取代的命运。
在此基础上,严复还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声:“是故除非一统无外,欲为存国,必期富强,而徒以宗法、宗教系民者,其为轻、重之间,往往为富强之大梗。于是不得不尽去拘虚,沛然变为军国之制,而文明国家以兴。证以东西历史,此说殆不可易也。”[1]1265他认为,必须改变中国以宗法和宗教管理国家的传统形式,向追求富强、维系共同利益的“军国之制”发展。这种政治改革之关键在于“参用民权”,而“参用民权”之程度决定了政治的“自由”和“专制”程度。因此,严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和“专制”两大政治概念进行了正名和学理辨析,并由此确立了自己对政治问题的独特理解。
三、从对“自由”的正名到对“专制”政治形式的辨析
严复认为,民权自由的程度和政治专制的程度是紧密相关的,对于自然演进的国家而言,民权的自由度或者专制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国家现实政治的需要。
在严复看来,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惟个人之所欲为”,而政治作为管理之术,是要“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因此自由与政治是相矛盾的,如何使二者相互调剂,是“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之问题也”[1]1279。
严复认为,那种强调自由根源于种族的观念是错误的,征诸历史,他认为普鲁士从种族上来说是条顿种族,从宗教信仰来说,是路德改宗的新教。但是,普鲁士在18世纪的政治体制则是专制体制,与同为条顿民族和路德新教的英国、美国的政制有所差异。通过对自由概念进行正名和征诸历史的方式,严复认为“民权自由”之多寡要看是否符合国家政治治理的现实需要——国家面临的外患程度。如果政治治理违反了这种需要,就会有亡国的危险。
严复指出:“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虽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为用,而生变例,亦自有之。”[1]1292严复对“民权自由”利弊的分析,是按照天演程度和历史演进的原则进行的,指出了“民权自由”多寡与国家面临外患程度的紧密关系。这一论述有其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列强殖民程度不断加深的历史条件之下,因此,严复认为此时中国的宪政改革要以实现富强以维系社会的共同利益为首要目标,而不能将民权自由作为宪政改革的中心,“自由或不自由的评判标准在于政令简省就是自由。而次政令必须建立在立宪的议会制度上,让人民的意愿得以表达,并且根据法典节制的权力,不使其滥用权力”[2]219。
在论述了“自由”之于政治治理的利弊关系之后,严复进一步对“专制”的国家形式进行了辨析,并且指明了“专制”的国家形式所具有的现实性。他认为,“专制”的现实合法性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获得论证:一是征诸历史,二是政治学说的比较辨别。
通过征诸历史,严复指出专制的政治体制虽然并非国家的长治久安之本,但却往往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他说:“往者吾论自由,终乃揭言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今言专制,又云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但须知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势会合、未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当时,则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1]1305-1306在严复看来,专制体制是政治体制发展的过渡性环节,并且民主政治的实施程度与民众的素质密切相关。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而言,民智、民德、民力都亟待提高,因此,他认为政府应当在教育、宗教文化乃至政治权利方面加强管理,而不是抽象片面地实行自由和自治。严复对西方的民主自治理论虽然有所向往,并且高度肯定将自治程度作为衡量政治治理程度的标准,但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严复则强调较高程度的自制和全方面的代表制度只适用于民智程度较高、地域较为狭小、人口数量也较少的国家。而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地域和人口状况,都不宜实行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的“代表制度”。因此,他认为从民约论生发的代表制度和自治管理固然有其重大意义和价值,但不宜过度美化,并且对其所能达到的政治效果也不宜过高估量。
在严复看来,专制政治无论是得益于天命论的合法性庇佑,还是得益于宗教的合法性庇佑,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取得民众支持,根本上是取决于民心所向。通过对专制国家形式的论述,严复强调了政治管理只有符合天理、符合民意,才是专制国家形式得以长期存在的真实基础。民权之“自由”程度或国家之“专制”程度都取决于国家所面临的外患程度,以及政治治理合乎科学和民意的程度。
严复从万物自然演化的观念出发,通过诉诸历史经验和比较归纳方法,对国家类型进行重新划定,并在此基础上对自由观念和专制政治制度进行了不同于西方政治学和当时中国流行的政治观念的解读,反映了严复在政治公例寻求上的新探索,以及对中国政治变革的理论回应,其思想依然具有值得深思和探索之处。
[1] 王栻.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刘桂生,林启珍,王宪明.严复思想新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李安胜】
2015-08-30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研究”(编号:GBB1213030)。
王秋(1979—),男,黑龙江双鸭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K25
A
1672-3600(2015)11-004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