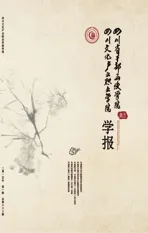“玩”与“拙”的艺术——从孩童到大师
2015-04-10白泓果,巫大军
【摘 要】当代绘画的艺术观念与形式愈发多元化,艺术家开始对传统绘画进行重新认识与探索,逐渐解放固有的艺术观念与绘画技法,尝试艺术的多种可能性,追求感性表现和真性情的自我表达。我们看到,少儿美术教育中常常以“玩”为创作活动的过程,形成以现当代艺术大师 “拙”为结果的形式倾向。通过分析高考美术教育过程与结果的艺术本质背离性,以及国内外艺术家、艺术活动与“童趣”的“拙”与“玩”的关联性,以“拙”与“玩”作为一种方式的当代艺术表达进行初步探讨。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784(2015)01-91-4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简介:白泓果(1994—),男,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在读本科生;巫大军(1969—),男,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在绘画创作与美术教育过程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充满童真的儿童艺术上,寻求一种天性的回归。儿童的天性里充满了热情与好奇,他们自然而然以自己单纯的眼光和活跃的思维来观察、理解世界。由于他们常常不受“科学”、“理性”的绘画理论与技法的限制,就能自由自信地表现自己的画面,所以绘画作品中充满原初状态的简单与淳朴。正是这种最纯粹、最率真的自然流露,触及到了艺术的本质。 [1]通过玩耍中建立绘画图示与世界的关系,形成“大师”般的洒脱之气,稚拙可爱。因此,在现代绘画艺术作品中,涌现出许多带有拙朴化和童趣化的艺术作品,“拙朴”和“童趣”成为现代绘画的重要美学因素。两者相互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拙朴是一种简率而自然的美,有大方、恬淡、浑厚的特点,体现了大美的境界;童趣是一种天真的美学因素,造型夸张、用色大胆、敢于表现、富有灵性,重视表达认识世界的感受,体现充分想象力与个性,进而有别于高考美术“生产线”的“撞脸”。
一、“玩”与“拙”是少儿美术教育常态
常常有人说: “小孩天生是艺术家。”的确,绘画是儿童的天性,是儿童思维自由活动的重要表达。艺术活动常常是感性的,儿童时期正是感性的自由想象力最丰富的时期,绘画对于儿童来说就是展现自由的艺术天性,不具备也不需要明确的功利性、目的性。因此,少儿美术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培养正确的自由感知力,去除条条框框的成人标准,有利于培养和挖掘儿童的艺术天性,丰富儿童的想象力、增强儿童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反之则会扼杀儿童的艺术天性。
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准确地再现与重复,而是心灵的表达与自然的结合。所以,儿童绘画艺术最佳的状态应是保持其所特有的童真性。绘画对于儿童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玩,是儿童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艺术天性,也是最纯朴的艺术表现形式,自由想象式的“玩”。儿童往往会用一些简单散漫的点或者线来象征自己心里的事物,但这些点和线条无不表现着一个稚嫩生命对未知世界美好的憧憬和情感。 [2]儿童的绘画过程应该是由他自身主导的、有趣的、精彩的游戏,这种游戏往往被家长看成贪玩好耍,如果以成年人的片面标准来评判和约束,儿童的自由天性发挥不仅仅大打折扣,还会扼杀其多元智能。所以,应当鼓励儿童学会在绘画中玩耍,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且获得快乐,而不是强迫他们画一个具象的物体。
在此,应当反对儿童进行素描、临摹等所谓的基础训练,反对灌输画得像的写实“美术基础”。很多小孩喜欢描摹和临摹小画册或卡通画里面的人物,无可厚非。但小学、儿童美术班的临摹课程意味着设置标准,标准则是儿童画大忌,这种教育方式实则是对孩子揠苗助长。一个成年人艺术爱好者,去临摹、研究大师的作品是一种理性的方法。一个小孩,一开始就去临摹别人的画法,那就完了。儿童的接受能力非常强,如果认为临摹得像原作就是画画的全部,就会失去与生俱来的个性特质。所以不要让儿童临摹别人的画,不要过早去学习别人的技法,更不要去模仿别人的风格。并且提倡自由化的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画由心生,心随天性,鼓励孩子长期坚持涂涂画画,发现孩子的倾向性与可能性,自然会形成独特的风格。目的性、标准化很可能会使孩子成为匠人,而自由的绘画创作才更能使孩子成为有思想的艺术家。
二、高考美术教育与“玩”“拙”相悖
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老观念的影响,到21世纪的今天,上大学仍然是学生和家长关注的头等大事。成绩平平加上艺术招生规模化,文化课分数要求降低,在客观上给很多文化成绩较弱的学生带来了考入理想大学的希望,致使美术高考成为升学的一种捷径。参加美术高考的学生首先进行美术专业基础的培训,然后参加美术专业考试,最后参加全国文化高考,生产线早已近乎一条龙。但这是一条与“拙”、“玩”无功利性、目的性结果背道而驰之路。
美术高考招生机制三十年未变,考试的方式主要是把对象的造型画准,所谓写实的准确、生动作为考察的重要标准。每年全国有几十万计的美术考生,面对如此大的市场,各种大大小小的美术高考培训机构的培训方式、目的性明确,纯粹是训练考生的应试能力和技巧,与艺术本身并无多少关系。据查,美术高考培训班的课程设置都是以省考和各大艺术院校专业考试内容为主要培训方向,个别培训班还针对某些学校的设计专业开设命题设计的训练。在这样的情况下,培训班的教师让学生在大量的美术高考辅导书籍中临摹复制,并且训练考生用记忆的方法去画,将一幅画背下来应付考试,甚至帮考生调配好色彩考试会考到的静物的不同部位的颜色。这种培训方式直接导致了考生对兴趣爱好、综合素质以及文化理论的忽视,在无以复加的重复中磨掉了本从儿童时代延续而来的天真。
众多美术考生并非真正热爱美术,往往是因为与日俱增的升学压力和较差的文化成绩,从而将美术作为升学的临时道桥,很多考生通常是在专业考试前几个月才开始参加美术培训。最短的时间集中强化培训,上名牌大学的专业分录取线,更是成了评判美术高考培训班优劣的一种行业内的标准。他们认为只要考试时画得像、效果“强”就可以得高分。学生在这种重复强化中没有了对艺术的热情和自己独特的想法,即使顺利升学,也是在学艺之路上艰难踟蹰着。
罗丹曾说:“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发现。”美术学生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独特的观察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独特的自由创造力。而目前的美术高考制度和机械化的教学模式只会让考生在形体上作亦步亦趋的摹写和无休止的重复磨练,把艺术基础训练降低为匠人式庸碌的手艺活,原本绘画的乐趣几乎荡然无存。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来说,不仅违背了心理认知和生理发育的基本规律,并且有可能丧失其绘画天性和绘画兴趣,阻碍美术学生未来的艺术创造性发展。当代国内鲜有艺术巨匠,从某些方面应归咎于我国长期以来高考美术教育的误区、目的性引导。
三、“拙”与“玩”的艺术史
由此看来,溯本清源的时候到了。纵观美术史,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古典写实绘画不再一统天下,特别是照相术的发明,绘画的观念与形态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等众多现代绘画新兴流派的艺术家们均表现出对“童趣”的关注,并且在艺术创作中使用“童趣化”的表现手法。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追求,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从儿童那里重新获得天真、纯朴和清新的内在品质。
在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中,梵高、克利、米罗、毕加索、夏加尔、德库宁、卢梭等大师们更是强烈地追求单纯拙朴的绘画风格,不再拘泥于简单、客观地描摹自然世界,而是渴望心灵的释放以及达到简单纯真的艺术境界。这个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艺术轮回,毕加索曾说过:“我曾经能像拉斐尔那样作画,但我却花了毕生的时间去学会像儿童那样作画。”这里所说的“像儿童那样作画”,其实是推崇儿童无目的、无意识的绘画状态,在艺术过程中回归艺术天性。艺术大师克利也十分推崇儿童的作画状态:“儿童的神秘世界令人向往,是人们苦心放弃其他一切而想要追求的理想天地。”马蒂斯甚至认为:“毕生都应当善于用儿童的眼睛观看世界,因为丧失这种视觉能力,对于画家来说也就意味着丧失一切独创性,即丧失表达的个性。” [3]不少艺术家都收藏儿童艺术作品和画册,而且研究儿童艺术作品。艺术家们不仅在儿童绘画中受到启发,并且吸收和模仿儿童艺术作品的特征,继而融汇出独特的绘画语言。国画大师齐白石晚年作品无处不体现着稚拙生动,那富有童趣的题材、简约的构图和简练的造型如同儿童绘画一样,质朴而无拘束,充满了一颗纯真的童心。
当代艺术“玩”的过程、“拙”的结果也与儿童绘画表现出很多惊人的相似,作品呈现与自由散发的儿童绘画是如此相似,甚至于很难区别。中国当代艺术家刘野就是一位童趣盎然的实践者,他以率真的卡通图像描绘着新时代的童话,画面饱含童趣意味,但在画面背后隐藏比儿童画更多的信息。他经常使用画中画的手法,与典型的个人结合。圆圆的小孩大头和Dickbruna的小兔子、蒙德里安的方块、马格里特的超现实主义帽子或者范·艾克的古典主义圣母一起出现在画面中。他与中国当代艺术潮流若即若离,坚守着“传统美学”和人性真善美的本质表达,他创作出一幅幅令人回味的作品,包含着对人性的推崇和对生活的热爱。另一位是著名的被称为最值钱的美国当代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他三十年来创造了大量的具有不锈钢、塑料、玻璃质感的各种玩具般的装置与绘画形象,在艺术视角与情感表达上更接近于儿童绘画表现出的魅力与活力。他直接利用、复制日用品,创造可爱、精致的卡通形象,形成充满想象力的大众图象组合,给观众带来一个又一个新的视觉冲击。昆斯声称自己的作品并不包含什么艺术史隐藏的意义,看上去就是一些简单艳俗的小玩意儿。这些都不仅在形式上吸收了儿童天性使然的特点,儿童作品表现的是儿童天然的朴素与纯真,艺术家的作品却是艺术升华后的朴素与纯真,让观众都进入一种天真、单纯的氛围里。当然,艺术家的艺术追求是一种超越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创造,具有本我境界的“童趣”式的玩着;“朴”不是简单幼稚,“真”也不是简单的视觉真实。“艺术大师们为攀爬艺术境界的高度,培养自身的才情与学养,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从不懈殆,才造就一身功夫。” [4]它绝不是从集训强化的“生产线”而来。“童趣化”的当代艺术形态也在玩世、卡通、艳俗、行为、装置艺术领域层出不穷、开花结果,虽然有些缺少沉淀的艺术作品昙花一现,但是艺术史里正在发生且不可回避的艺术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对人性的回归与时代烙印,“玩”是艺术家的本性与童年纯真的结合,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这种“真”、“拙”、“朴”的境界本应就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存在状态,它关乎艺术的本质。
四、结语
人类艺术的活力一直都体现着儿童绘画的心理和表达,“玩”是天性与基础,“拙”是形态与表征,“真”是结果与本质。儿童以自由、朴实的手法表达主观的想象和情感,其绘画作品呈现出稚拙的、天真、开放的趣味与特质,它自然而然地回归到艺术的本质上。当代艺术中的童趣风格是艺术家内在心理本质的特殊表现。“童趣化”并非仅仅是在形式上对儿童艺术语言的模仿和挪用,作为一种表象,它体现了艺术家对真的向往及表达,通过艺术创作释放并升华情感。我们看到“玩”是儿童的天性,创造是艺术的本质活动,由此去反观我们的美术教育与美术创作,塑造“真”的艺术,我们可以“玩”,因此而“拙”,没有急功近利,这样或许会走得更远,这是一个值得努力探索的课题与方向。
【责任编辑:闫现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