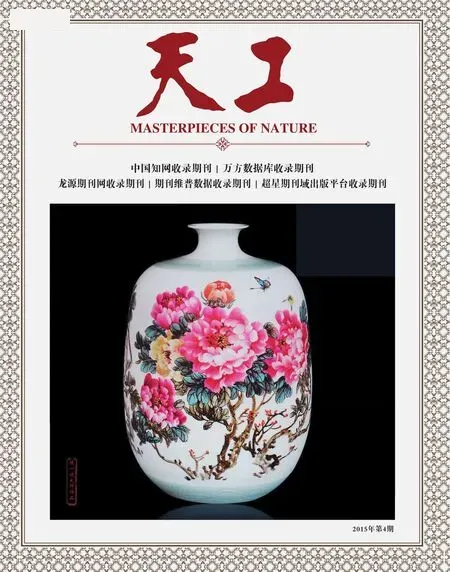维纳斯的诞生:对曲线的一次静观
2015-04-10文匡宇
文 匡 宇
维纳斯的诞生:对曲线的一次静观
文 匡 宇
在艺术作品的形式因之中,作为线条出现的曲线意味着情绪、神性、先验性以及意义的发生。在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中,从画作的构图、人物造型以及深层意义主题等方面,曲线都扮演着决定性的意义。对这一作品的阐释,力图敞开的是蕴含于该作品之中的,并导致这一作品以如此这般形态出场的意义生成机制。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美第奇家族;曲线 ;直线
一、曲线
曲线具有一种隐约的忧伤:风在空中拂过的痕迹,那优雅转向的鸟雀;离人互别时的心绪波动,列车驶出站台即将行进在蜿蜒的铁轨;爱或恨、笑或哭、拥抱或漠然、生或死,在这些节点的瞬间,滑落的饱满泪珠,甚或在皮肤和骨骼的自然走向所勾勒出的渠道上随物赋形而淌下的泪流。
曲线就是一种隐约的忧伤。直线是人类的想象,而曲线才是上帝的作品。平面几何学中的关于点线面的公理,终究是属人的,建基在身体器官、空间感与意识的基础之上。而在宇宙——上帝的造物中是找不到一条纯粹直线的,正如我们找不到上帝一样。不过,这种寻找本身,只是一种实证的顽疾罢了。因为,恰恰对于纯粹直线的构思本身,以及对于纯粹直线的不可实证——在这一悖论中,上帝显身。

《Creation-Adam创造亚当》(米开朗基罗)

《Creation-Adam创造亚当(局部)》(米开朗基罗)
在米开朗基罗的笔下,上帝的面容并非威严。那白发白须具有云的晕和韵,而神情带着令人诧异的伤感。因为,我们可以从神的额头上已经簇成的两条皱纹曲线中察觉出造人瞬间神之波动。他是否已经预见到这一造物对他的离弃?而那勉强伸出曲线手指的被造物,睡眼朦胧,并不急切——他是否隐约在蒙昧中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对于他和他的肋骨而言,将是永恒的重负?
二、翡冷翠·1482
但是这一重负总需要稍微卸下一些。在人呻吟、流汗、劳作、生产、嫉妒、谋杀、背叛、受难之间隙,美作为这人间的不可能之可能,于是也作为瞬间与永恒在矛盾和悖论中的和谐闪现,安慰着人,迷惑着人。正如此,美的显现本身,却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欣慰与忧伤。
关于美的这一品质,无人能及波提切利对它的悠然心会。
在美蒂奇家伟大的洛伦佐推荐下,波提切利离开翡冷翠,去罗马为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工作,并充当调和翡冷翠和罗马之间关系的外交角色。在为教皇绘制严肃的圣经场面的工作中,画家缺少自由和安逸,更何况身负政治任务。于是,当他返回翡冷翠时,很快就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群中找回了之前的惬意与轻松。波提切利再一次接受洛伦佐的堂兄洛伦佐·迪·皮尔弗朗西斯科·德·美蒂奇的委托,创作了《维纳斯的诞生》。之前的委托,就是朱利亚诺瓦·德·美蒂奇委托创作的《春》。
那时,是在1482年的翡冷翠——这个城市的名字(Florence)来源于花(flora)。而此刻,这朵文艺复兴的娇花,正握于伟大的洛伦佐这个文艺复兴王子的掌心。洛伦佐有一位朋友和秘书,名叫波利齐亚诺的诗人,他曾写下诗篇:
她航行在白色波涛的海面上,
一个超过人类面貌的年轻的贞女,
被强壮的西风之神吹送着朝向海岸,
过程型激励理论试图说明人们面对激励措施,选择以何种行为方式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弗罗姆于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人们预计某一行为能带来有吸引力结果的时候,个人才会采取特定的行动。且激励程度由效价和期望值决定,即激励程度=效价×期望值。
在蓝天下,在她出生的贝壳里。
波利齐亚诺的这几行诗句,给予了波提切利以灵感。画中那个站在扇贝壳上的女子——从一出生就如此并永远如此的美神与爱神,其面容再一次被波提切利塑造成西蒙娜塔·维斯帕奇的肖像——在此之前,她已经出现在《春》之中。而这个少女,正是委托人和朱利亚诺的挚爱,她17岁时死于肺痨。所以,使得波提切利万古流芳的这两幅画作,其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安慰那苟活于人间的爱人而已。
三、维纳斯的诞生:她之所在与曲线的动因
在《维纳斯的诞生》中,严格的说,不是维纳斯而是那纯白、米黄和粉红的贝壳居于平面的垂直中心线上,贝壳向上衍射出的弧线以及向下蔓延开的细密弧线,饱满充实如同六月清晨阳光的晕圈。而这线条的金色基点,恰好位于作为维纳斯支撑点的左脚踵之下。这种构图,是对中世纪圣母圣子或者诸多圣人造像的颠倒。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光晕总是出现在这些人物的头顶上方,以此来暗示神之荣耀。而现在,1482年的翡冷翠,波提切利却将光晕置于一个异教神祗的脚下——而这个神的名声可不像她的容貌一样纯洁无暇。在这样的倒置设计当中,画家既完美地将波利齐亚诺的诗句加以形象化的顷刻呈现,同时也将如许信息传递:那荣耀神的金色光芒,此时此刻,正构成寄予着人间爱恋和纯美之化身的立足——而这并非神之荣耀,而这荣耀是为了一个立于其上的更高目标。这一目标,就是爱与美。

《春》(波提切利)

《维纳斯的诞生》(波提切利)
在这一目标的顶端,在这一张典型翡冷翠古典美女的鹅蛋面孔之上,我们再次目睹了金色——女神灿烂的金发。于是,在上与下的金色之呼应中,一具羞涩的纯白女体在轻柔中,漂越过绿色的大海,向我们航来。然而,更直观的是,女神的体态却是倾斜的——这一女体明显呈现出向左侧的重心偏移。这一偏移,使得女神的身躯如同一枚拥有完美曲线的娇嫩百合花瓣。这枚花瓣,恰由于这微微的弧度与偏移,就正好将其重心置于整个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之上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枚花瓣的倾斜?或者说,是什么造成了她的身体在这一瞬间所呈现出来的向左受力的态势?难道是女“神”本身在诞生之际天然的羞怯与矜持?难道是作为“女”神本身天生的娇弱、无力,或者所谓的波提切利式的“妩媚”?
这枚花瓣饱含羞惭、乏力和妩媚的弧度和曲线,表达了爱的二元:情感和贞洁,而其起因来自于女神右侧(画面左侧)。在那里,象征着性爱的强壮西风神(男性神)鼓吹出风儿阵阵;在他怀中,花之神如同缠绵的水蛇一样,将他牢牢抱紧——随着她而来的,是在风中洋洋洒洒飘忽不定的朵朵粉色玫瑰花。
由于风神的吹动,造成了整个画面一系列曲线、弧度以及姿态动作的后果:首先是由于受到风力,所以维纳斯体态的向左偏移;然后是维纳斯头部的金发被风吹动而向左侧高高飘起;接下来,为了让长长的金发不至于漫天飞舞,于是羞怯的维纳斯用左手将长发发端控制并将其遮掩私处;画面右侧匆匆走来代表贞洁的时序女神霍拉,她携带着点缀着各色花朵的金色长袍,正努力将其覆盖在初诞生的女神身上,然而,风却将这一努力在这个顷刻化为徒劳——长袍极其醒目地被鼓动起来,飘扬起来,越出了霍拉的头顶、高过了时序和春天的限度,如同一面终将属于维纳斯的金色旗帜,将维纳斯头部的那抹金发的线条无限延展。

《维纳斯的诞生(局部,水平直线)》(波提切利)
因为有作为动力的风,所以整个画面上部获得了一种连绵不绝的曲线之连续节奏。而这条横贯不绝的线条看不见。于是,这条真实存在但却超出人的视觉之外的线条,将画面构图中所包含的以维纳斯为中心的四人-三元组合勾连一气。
这并非局部的美,而是在一个连贯的而且可能的象征系统中,将诸多单独的不和谐或旁逸斜出进行协调。而恰是通过对造成连绵曲线的那看不见力量的表现,波提切利完成了这样的事业:当神以其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点燃人的灵感和爱欲,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由神所燃起的灵感和爱欲中寻找神;如有可能,对那神秘之力的描摹则是对人最好的奖赏。
四、忧伤
对维纳斯静观,或者对这一作品的凝视,会使人陷入一种摆脱了欲望的幻觉。你会觉得,是的,事情当时就是这样;毫无疑问,这就是美本身。这种感觉,会促使人去关注:女神的诞生,诞生于何处?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波提切利在这幅作品中所描绘的一切被我们认之为理所当然?
女神的诞生地,这是一片宁静的无名海湾,人迹罕至。在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片海湾的风貌,海面的远景风平浪静,海面的中景和近景由于已经涉及人物和行动,所以逐渐波光潋滟。而曲折的海岸则渐次退入远景的海平面。海天一色的海平面,作为一条看得见的平直线条,与前景(画面平面上方)的那条看不见的风之线条构成了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从形式上说,这条看得见的直线,对于画面而言起到了背景构造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就平面而言,这条直线正好位于维纳斯的肚脐(人体重心)的水平线上。但是,从二元对立的意义角度而言,这条直线的分量远远低于那条看不见的曲线。一方面,这条直线的完结点,从画面平面观之,恰好位于维纳斯的左手肘,它并未贯穿整个画面;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水平线条,仅仅是可视可感的有限天地之边界,这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而那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之轨迹,在精神的意义尺度和画面构型价值尺度上远远高于这一有限天地。
然而,这些相对平直的线条,却与女神本身构成了一种情绪和意义上的紧张。尤其是中景处连续凸起的海岸,如同一个个带有威胁性的锐利尖刀,指向着刚刚诞生的女神。这一威胁性的因素,造成了情绪上的隐隐波动:一方面,是女体的轻柔、婉转、眼波流动、柔情似水;另一方面,是天地的平宁、淡漠、无知无觉、永恒故我。
美诞生于何处?就诞生在这样的所在。在一个不被人所知晓也拒绝人抵达的平静海湾,绝世之纯美在这一顷刻,缓缓诞生。带着淡淡的忧伤,带着对爱与美自身走向人间所即将遭遇到的命运之预感,她缓缓行来。在曲线之中。
[1][美] 保罗·斯特拉森(Paul Strathern).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马泳波,聂文静,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3][英]玛利.波提切利画传.张春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朱双.西方绘画大师:波提切利.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匡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长期文学理论、西方思想史和艺术理论等研究。
J05
A
2095-7556(2015)04-009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