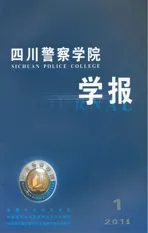对我国民事案件真实保障的历史分析
2015-04-09杜若英
杜若英
(北京大学 北京 102206)
对我国民事案件真实保障的历史分析
杜若英
(北京大学 北京 102206)
如果要保障民事纠纷得到正当的解决,一国民事诉讼就需要建立一套保障案件真实的制度。对此,我国民事诉讼也不例外。从我国民事诉讼法历史沿革的角度看,苏俄和民国时期的案件真实保障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改革应当面对这两者的影响,注意两者的区别,避免两者的混用,并结合我国民事权利实现特点,构建一套可以确保当事人权利实现稳定的案件真实保障制度。
民事案件;案件真实;证明标准;辩论原则;证明责任;推定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对同一案件事实提出相反的证据,法院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77条关于证明力的一般原则对证明力进行判断,也可以依据第64条规定的法官职业道德、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还可以依据第73条规定的案件情况进行判断[1],这样的立法规定所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果上述三个条文分别得出了证明力大小不同的结果,我国法院究竟应该适用哪一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实际上,对这一难题的回答,则直接取决于以下问题,即我国以何种案件真实作为保障案件真实的目标?此外,对于需要发现真实的案件,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以下简称民诉法)第7条,我国法院有权不受原审判决拘束根据法律和查明的事实对案件进行判断[2]。那么,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在什么范围内可依据《民诉法》第7条主动调查案件事实,当事人又在什么范围内可依据《民诉法》第7条启动法院对事实的调查?也就是说,在我国,法院与当事人应如何负责案件真实的保障?最后,如果争议事实陷入不清,我国法院在依据《民诉法》第64条第1款让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时,仍需要解释当事人是否因客观原因未能提出证据[3]。而且,即使在当事人双方均不申请鉴定而导致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我国法院仍得以《民诉法》第64条第2款主动调查证据,解决事实不清的问题[4]。这样的做法不仅产生疑问,即争议事实陷入不清,究竟是当事人的风险承担,还是法院未尽调查事实义务?或问,我国应如何处理案件真实无法发现的情形?上述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应如何保障民事案件的真实?
为了阐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必须首先面对两种民诉理论和制度对我国民诉法的影响,即苏俄和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之所以要面对两者有以下原因:第一,苏俄模式曾是我国民诉法构建所借鉴的对象之一,时至今日,我国民事诉讼法依然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5]。第二,民国民事诉讼通过台湾地区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亦产生着重大影响[6]。第三,我国民事诉讼在构建完备的民事案件真实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如不将两者加以区分或者混用两者,会导致我国民诉缺乏可预见性。第四,苏俄和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都需要通过案件真实的保障确保当事人民事权利实现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两种民诉都需要解决相同的问题,具有可比性。
本文以1923年通过的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张文蕴译版)和1930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颁布的《民事诉讼法》(郭卫勘校版)为基础[7],首先尝试阐明苏俄和民国时期案件真实的保障目标,其次对那时保障案件真实的权责分配问题进行阐述和比较,再次对两者如何处理案件真实无法发现的情形进行阐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最后指出我国在上述三方面应予完善的必要和途径。
二、苏俄与民国案件真实的保障目标
(一)苏俄与民国案件真实保障目标的内容。
面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纠纷,无论是苏俄还是民国都要面对真实与权利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在此,尤为重要的问题是,法官适用民事法律的基础是什么?在苏俄学界看来,只有法官核查每一个要件事实是否已经齐备并且真实的基础上,才可以适用法律解决民事权利纠纷[8]。这种认识来自于辩证唯物主义[9]。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苏俄学界权威的观点认为虽然法院对案件真实的调查并不像在自然科学中的发现真实一样,但是,只要法院的确认是穷尽现有条件的结果,或所确认的案件真实无法被怀疑,法院就已满足了社会对法院判决的信任,从而保障了案件真实的客观和绝对,协调了法院判决与真实之间的关系[10]。苏俄学者进一步认为如果法院和审判员向着事实的本质、特性不断探索,是一定可以完成这种全面负责任务的[11]。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苏俄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追求案件真实上是无区别的[12]。
面对同样的问题,民国民诉学者认为国家干预民事的利益争议需要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符合法律事实,并由法官判断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否真实[13]。民国学者曾言:“盖证明者系当事人提出证据使法院可以确信其主张之事实为真正之行为”[14]。“民事诉讼上之证据……仅可如历史上之证据使得依普通之经验主观信为真实而已。”法官需“强固”地确信事实已经显明的,被称为证明;法官只需“薄弱”地确信事实已经显明的被称为释明[15]。证明与释明虽然用词不同,但并非实质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可见,民国学者认为,对于事实的认定只是一种法官主观上可以信赖的真实。正是在信赖的意义上,法官的心证才有强弱之分。
(二)苏俄与民国案件真实保障目标的形成。
案件真实形成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种是依据法定条文判断案件证明是否成功,这种方法被称为法定证明或者形式证明;另一种方法是依据法官对个案的判断确定案件证明是否成功,这种方法也被称为自由心证或者内心确信。无论是苏俄还是民国都采取自由心证的方式形成案件真实,也就是将确定案件真实的权力赋予法官,让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中自己决定案件的真实,即所谓形成心证[16]。虽然两者在与法定证明比较时具有此相同点,但是两者对如何形成心证的回答却是皆然不同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证明方法与证明标准。所谓证明方法问题,就是指法官凭借什么方法确定证明成功?所谓证明标准问题,即法官何时可以确定证明成功?
针对方法问题,苏俄学者认为,为了保障法官对案件毫无错误的认定,法官需要利用真正的科学方法,才能获得确信[17]。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会对诉讼中的证明产生全面帮助的作用[18]。例如,法官可以利用如X光技术、光谱分析、指纹鉴定等最新科学技术,查证案件真实[19]。另外,对于苏俄学者来说凡是能够调查案件真实的手段都是证明方法,因此,虽然当事人陈述和物证未被苏俄民诉法规定,但是两者也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20]。面对相同的问题,在民国学者看来,法官可以依据自身的感知在每一个案件中发现可以信赖的真实,并以说理的方式论证自己信赖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理由[21]。在审理中,必须采用法定的证明方法对案件真实进行认定。
针对标准问题,苏俄学者认为,如果法官亲自使用正确的方法得到能与客观事实相符的结论,则可以认定证明成功。或者说,“苏维埃的审判员在调查和判断证据的过程中应当遵守唯一证据的标准——即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人们意识中一种反映形式的内心确信——行事”[22]。同样是证明标准问题,民国学者认为,一般社会生活经验中相互信任的标准就是法官形成强固确信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民国学者非常强调以经验法则(也称经验定则,即各领域恒定的经验)作为法官判断证明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那时的学者曾言:“惟法院于事实之真伪,虽有判断之自由,然非漫无标准,即其判断必依经验法则而为之。”[23]法官不必以数理推理至无相反的可能存在才可信任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三)两种案件真实保障目标的比较。
由上可以发现,苏俄与民国的两种理论认识存在如下区别:第一,在以何种真实作为法官确认案件的目标方面,苏俄重视案件真实的客观性,而民国重视案件真实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案件事实在苏俄被认为是真实的时候,苏俄的法官要保障社会中的任何人能够无怀疑地认为案件事实是真实的。但是,同一案件事实在民国被认为是真实的时候,即使存在关于案件事实真伪的怀疑,只要法官能回应这些怀疑且阐述信任的理由,那么,法官就可以信赖当事人的主张是真实的。第二,在如何形成所保障的目标方面,苏俄的法官采用科学式认知方法自由地采用证据,在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相符时,认定证明成功。民国法官仅能使用法定证据以符合个人逻辑规则、经验法则和自然规律的认知方法,在法官对当事人的主张全面信赖时,认定证明成功。
三、苏俄与民国案件真实保障的权责分配
(一)苏俄对案件真实保障的权责分配。
基于前述关于案件真实客观性的认识,苏俄民诉法要求诉讼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应穷尽一切手段调查案件真实。起诉的目的就在于启动法院能动的审判活动[24]。案件真实是正确裁判的前提,发现案件真实是诉讼机关的任务。《苏俄民诉法》第5条第1句规定:“法院应尽一切方法查明诉讼当事人的真实权利及相互关系,不受已提出之释明及资料的限制;而以讯问当事人的方法,究明为解决案件的真实情况,并用证据认证之;对于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劳动者,应为积极之协助以达到保护其权利及法益之目的,并使其不因不明法律,文化落后或者类似之情况而蒙受损害。”同时,根据同法第118条第2句和第3句,对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法院可以无条件地依职权收集证据,并要求当事人补充证明不充分的证据。另外,苏俄的检察机关同样负有发现真实的义务,其可以监督案件的审判结果[25]。
与此相适应,苏俄民诉法也要求当事人各方要积极主动地参与案件真实的调查。除当事人要协助法院发现案件的真实之外,还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当事人自己要积极发现案件的真实,这一点《苏俄民诉法》第118条第1句明确要求,当事人就自己提出的请求原因和答辩基础负证明义务。其次,当事人要对案件过程中的一切问题说明意见和理由。这三方面内容在苏俄模式下,被称为辩论原则,当事人只有在这三方面都积极主动地参与,才是与客观真实发现相调和的辩论原则[26]。
(二)民国对案件真实保障的权责分配。
对于由谁负责案件真实这一问题,民国民诉法认为应由当事人负责,即当事人负责主张事实、提出证据,其主张可以限制法院的职权调查。这样的原则被称为辩论主义,其基础在于民法上私法自治原则。在民法中,当事人有处分自己权利的自由,所以在民诉中,当事人也应当对自己权利的争议及所依据的事实有处分的自由。享有这份自由的另一面,则意味着当事人自己负责,即对实体权利的主张和对该主张所依据的事实负责。在此前提下,当事人可向法院主张事实并声明证明方法由法院调查,法官必要时依职权调查证据[27]。另外,法院只在特定情形下不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限,例如在案件涉及公益时,法院自己调查本案事实,并可不待当事人声明即依职权调查证据[28]。不过,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结果要给予当事人对此结果进行陈述的机会,从而可以与民国民诉中采用的辩论主义原则相协调[29]。
(三)对两种权责分配基本原则的比较。
在对案件真实发现的权责分配方面,苏俄与民国有以下不同:在苏俄,法院、检察机关都负有发现案件真实的义务,有权监督民事案件,同时,当事人也负有发现真实和协助法院调查事实的义务;在民国,当事人并无协助法院发现真实的义务,法院除特定情形外无需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而且也不存在检察机关对确定判决进行监督的制度。由此可以总结:苏俄民诉,以案件真实的客观性为核心,构建了一套以法院依职权调查和以当事人对所有问题主动辩论相结合的权责混合式案件真实保障原则。在苏俄,当事人辩论和法院依职权调查之间并无主次之分,当事人和法院都要在案件真实发现过程中保持积极性,而民国民诉,以案件真实的主观性为核心,构建了一套以当事人负责主张事实、提出证据为主与以法院职权调查权为辅的权责分层式案件真实保障原则。在民国,辩论主义和职权探知有主次之分,一方面以保障当事人的主动性为原则,另一方面,在法院保持被动性的前提下,保障法院有限的主动性。
四、苏俄与民国对案件真实无法发现的保障
前述基本原则从由谁确保证明成功的角度对案件真实进行了保障,证明责任问题和推定则从如何承受证明失败的角度对案件真实进行保障。无论是苏俄还是民国都无法否认案件事实不清的存在[30]。针对这种情形,证明责任制度为法院提供了一种在事实不清时进行判决的方法,而推定则会通过改变证明对象的范围,影响证明责任的适用。一国推定制度的范围越宽,案件真实需要证明的范围就越窄,证明责任适用的范围也就越窄。
(一)苏俄与民国的证明责任制度。
以现在的观点看,在苏俄,并没有客观证明责任的理论,因为,在苏俄,证明责任并不是一种风险的负担,而是一种义务的承担。苏俄学者认为,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必须证明其主张的义务[31]。而这种义务的分配规则分为三步:第一,当事人首先要在起诉时提出证据。《苏俄民诉法》第76条要求原告在起诉状中载明证据[32]。同样,被告也要就反驳起诉的事实提供证明[33]。第二,法院也要承担证明责任[34]。法院不能因为一方当事人没有证明案件真实就驳回其诉讼请求[35]。在当事人穷尽证明方法又不足以发现案件真实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36]。第三,只有当包括法院在内的所有诉讼主体都无法查明事实的时候,才让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主张失败的后果,让反驳权利主张的当事人承担反驳失败的后果,而且这种证明责任是可以在证明过程中多次转移的,而判断是否转移的确立是由法院根据审理情况决定的[37]。
在民国民诉中,证明责任是一种诉讼风险,其作用为,克服事实不清情况下法院必须作出判决的难题。而且,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以实体法的规定为内容,诉讼法中只有形式上的分配规则[38]。也就是说,以谁从事实主张成立中获利,谁承担举证风险为原则,也就是客观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39]。这种证明责任不会因为主张与反驳的变化而变化。
通过关于证明责任问题的比较,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苏俄,证明责任并非风险负担而是义务承担,只有在客观上无法发现案件真实,法院才能让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而且这种风险的承担会根据证明过程的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换,简言之,苏俄民诉保障事实不清的客观性。与苏俄不同,民国证明责任并不因主张与反驳发生转换,事实不清的出现也不以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为条件,如果事实不清,法院只需根据已经确定的证明风险分配规则对民事权利争议进行判决即可。也就是说,民国民诉保障的是事实不清的可预见性。
(二)苏俄与民国的推定制度。
如果要全面考察证明对象,可以从两个角度,一方面,可以从需要证明的角度看,另一方面可以从不需要证明的角度看,也就是免证的事实。推定制度作为免证的事实与证明责任问题关系密切。一旦案件事实被推定,无论证明责任作为一种义务还是一种风险,都会得以减轻。
由于对案件真实客观性的要求,推定在苏俄民诉法中的内容如下:苏俄的法律推定不包括法律拟制(不可推翻的推定)。因为法律拟制只能保障形式真实,无法保证客观真实。苏俄民诉不允许不可推翻的推定,任何推定应都是可以推翻的[40]。因此,推定只有在与客观真实保持一致时才被作为免证事实。与此相反,在民国民诉中,法律拟制(不可推翻的推定)可以作为免证的事实。例如,即使胎儿尚未出生,为了保护其利益,也视为出生[41]。
之所以存在上述区别的原因在于:在苏俄,推定的设置只是为了法院审判的便利,因为,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推定就视为客观真实,法院不必再调查案件真实,从而减轻法院负担的案件真实调查义务。但是,只要推定阻碍客观真实,换言之,只要被推定的事实有相反的证据,推定就不会被承认。而民国推定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以可预见的方式缓解当事人证明困难。该制度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不可推翻的推定,避免当事人因证明困难而无法实现权利,同时,因为这种推定是法定的,所以可以进一步保障一种可预见的证明责任制度。
五、对我国案件真实保障的评析
(一)我国案件真实的保障目标。
建国之初,我国效法苏俄,以“实事求是”“全面、客观”为标尺,刑诉与民诉的证明标准也是一致的[42]。不过,目前关于案件真实的理论已经发生变化。有权威观点认为通过立法确定的法律真实标准,不影响对客观真实标准的追求[43]。也就是说,客观真实有三方面含义:“首先,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必须以案件事实为基础,而不可主观臆断;其次,在终极的意义上,承认案件事实是可以认识的,诉讼制度应以发现案件事实为基本目标;最后,在具体诉讼过程中,遵循法定诉讼程序得出的符合法定证明标准的事实,应当作为法官裁判的基础事实”[44]。按照此学说,客观真实在学术界已经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是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一种终极目标。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学术界关于案件真实标准的理论发展总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摒弃客观真实说;其二,采纳法律真实说;其三,区别对待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对后者采用较低的证明标准”[45]。同学界一样,司法实务界中权威的观点认为,诉讼活动应当以客观真实作为审理案件的最高目标,但是,民事诉讼只能以依法审核的证据所确认的案件事实为民事裁判的基础。该观点还认为,民事诉讼中不可能每一个事实都与客观真实一样,民事法官必须及时做出裁决[46]。
根据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案件真实的客观性已不是我国民诉保障案件真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我国案件真实保障的建构也并非以案件真实的主体性为目的。因为,正如学者已经批评的一样[47],我国学界所称的法律真实并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回答,而只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回答,即只要遵守法律规定进行认定的事实即是真实的,也就是我国理论界并没有对案件真实的性质做出实质上的回应。司法实务界以《证据规定》第73条中采取的高度盖然性为标准认定案件事实,这也意味着我国法院只需比较证明力大小,不必再以案件是否为真作为标准认定案件事实。然而,在我国,证明力大小的比较实际上又是难以预见的,根据司法实务界权威的观点,我国法官要从两方面判断证据证明力,法官既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判断证据证明力,也要依据职业道德、逻辑规则和个人经验判断证据证明力[48]。不过,如何处理同时使用这两方面原则所产生的冲突问题,却并没有规定和说明。因此,我国证明力的判断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法定证明与自由心证的混用模式,这样的缺陷破坏了案件真实的主体性标准,因为,其他形成心证的法定规则可以直接影响法官心证的形成,例如,法官可以直接根据《证据规则》第77条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判断,无须根据自己的确信判断证据证明力。
上述表明,尽管我国对案件真实的理论有所发展,但是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对保障案件真实的基础和目标作出选择。对此,本文认为,就基础而言,我国立法者首先要以保障法官对个案真实的确信为原则,以法定证明力判断规则为例外,也就是说要对《证据规定》第64条作出原则与例外的区别对待,从而使心证形成体系化。这样的做法可以使我国法官有独立认定案件真实的权力,奠定保障案件真实的基础,避免形式证明的弊端。在此基础上,就保障的目标而言,我国立法者应根据民事权利的特点以保障法官发现案件真实主体性为原则,以保障案件真实客观性为例外,也就是说,对权利可以处分的民事案件,我国立法者要对法官附判决理由的个人确信进行保障,对权利不可以处分的民事案件,则要保障法官对个案真实的认知可以经受以下标准的检验,即社会中不特定人对同案可获得相同认知的标准。如此,可以使案件真实的保障程度与当事人权利实现相适应,既符合当事人实现个人利益的需要,也符合我国对国家、社会和第三人利益保障的需要。上述理论具体到证明标准方面,本文认为,对待权利可以处分的民事案件,法官应在对案件真实产生全面确信时,认定案件真实;对待权利无法处分的民事案件,法官在确信案件符合客观实际时,认定案件真实。也就是说,我国应重新考虑《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规定,因为高度盖然性,意味着法官可以在不确信案件真实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法官规避案件真实的发现义务,不利于我国对案件真实的保障。
(二)我国案件真实保障的权责分配。
建国之初,“就地调查、及时调查”“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当时的审判方法。随后,我国民诉法第7条、第12条、第14条的规定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存在说明我国民诉法仍然处于以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共同承担发现案件真实的基本架构中。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审判方式开始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方向转型,在此背景下,通过《证据规定》第15条和第17条,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然而,在法院限制自己发现真实作用的同时,《证据规定》第3条却要求当事人在法官的指导下“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提出证据。在基本架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我国法院在是否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的权限方面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民诉法》的规定为法院适用提供了以下的可能性:对于同一类事实,我国法院既可以适用《证据规定》第15条不予调查案件事实;也可适用《民诉法》第7条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而且,最差的可能是,我国法院还可以在自已不予调查案件事实的同时,依据《证据规定》第3条要求当事人承担发现真实的义务。这种变化,很可能导致,我国对案件真实的保障从当事人、审判机关共同对案件真实起到积极作用变为形式上共同发现案件真实,实质上仅有当事人一方对发现案件真实起积极作用的案件真实保障模式。因为,目前,在共同发现案件真实的保障模式的前提下,当事人不仅无法再依靠起诉启动整个法院的调查权,而且,当事人还必须自己完成案件真实的发现。另外,通过司法解释所进行的改变不仅会加重当事人发现案件真实的负担,而且也会破坏审判程序的稳定性,损害当事人对审判程序的信任。其原因有二:第一,目前规定的不可预见性无法保障我国每一个当事人都能够在审判中获得可预见的权责分配;第二,在共同发现案件真实的原则下,法院在审判程序中积极作用的缺失也使得审判监督程序被频繁启动,从而会导致我国法院的既判力和诉讼安定性长期处于不稳定。
上述不足说明,我国仍然需要在法院与当事人权责分配问题上作出进一步完善。对此,本文认为,为了能够使我国在当事人与审判机关之间有一个稳定而公平的权责分配,我国应当区分情况对当事人与审判机的权责进行分配:对于需要保障案件真实主体性的情形,应采取以权责分层的案件真实保障原则,因为,这样可以在发挥当事人争取自身权利积极性的同时,尊重当事人处分自己权利的自由。但是,对于需要保障案件真实客观性的情形,则应采取权责混合的案件真实保障原则,因为,此时对案件真实的发现不仅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也是保护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基础,法院承担案件真实的发现义务,可以避免当事人因维护自己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
(三)对我国案件真实无法发现的保障。
对于证明责任,我国《民诉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在我国《民诉法》立法之初,该条规定是在保障案件真实客观性的前提下提出的,因此,可以推断我国民诉法设立之初所称的证明责任和当下所称的客观证明责任在实质上是不同的。不过,2001年,我国最高法院以该条过于原则不具操作性为由,通过《证据规定》第2条将其解释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也称为客观证明责任)[49]。实际上,这条解释是直接将适合于案件真实主体性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嫁接在了以案件真实客观性为前提的证明义务分配制度上。这种做法使得我国证明责任问题,成为一种风险负担与义务承担的混用。因为,我国民诉法规定中的该条自1991年起并未变化,这样规定的含义本意上是一种义务分配,即当事人负证明义务,且法院在当事人无法负证明义务时,负证明义务,在本质上,应属当事人和法院共同负担一种客观不能的证明风险。然而,我国最高院直接借鉴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将该条予以细化,实际上是用一种形式上的风险分配规则替代了义务分配规则,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事实不清,法院可以不再调查或者审查导致事实不清的实质原因是否为客观不能,这种做法使得我国人民法院所负的保障事实不清风险的客观性义务处于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相互推诿,本文认为,仍然要区分情形处理我国的证明责任问题,将证明责任问题的风险分配与义务承担相互区分。具体而言,对于需要保障案件事实客观性的情形,则法院不得因当事人证明不足而经行裁判,而应在穷尽所有条件下,判断案件事实是否能被发现,也就是说,此时,法院应保障只有在客观不能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承担事实不清的风险。对于需要保障案件真实主观性的情形,应当以客观证明责任的适用为原则,通过形式上可确定的证明风险分配规则,使当事人可以预见事实不清的风险,避免因为权责混同,打击当事人追求自身权利的积极性。
根据我国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推定制度仍未规定在其中。《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我国所有的推定都限定为可以被反证推翻的推定,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保障案件真实的客观性,但是这也意味着法律拟制(不可推翻的推定)不应当存在。这种规定在保障案件真实客观性方面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却会使我国证明责任问题雪上加霜,因为,根据《民诉法》第65条规定,已经分配好的证明责任可能随着审理而发生改变,而当事人按照之前的分配规则做出的努力就会被浪费,从而打击当事人追求自身权利的积极性。
为了使我国推定制度与证明责任制度相互协调,对于需要保障案件真实主体性的案件,我国立法者应当引入不可以推翻的推定,从而为客观证明责任提供基本的可预见性保障。然而,对于需要保障案件真实客观性的案件,则可以保留现行的规定,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类案件中证明责任并非风险负担,在当事人和法院发现真实的主动性都有所保障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推定保障法院审判的便利,通过反证的提出保障案件真实的发现。
六、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苏俄和民国时期保障案件真实的理论、原则与制度,可以发现:苏俄以保障案件真实的客观性为目标,采取案件事实与客观实际相适应的证明标准,以自由的证明方法科学式地确信案件真实,同时,以权责混合的方式保障法院与当事人共同发现案件真实的积极性,并使法院与当事人共负证明义务,禁止不可推翻的推定,确保案件真实无法发现只能产生于客观不能的原因。民国以保障案件真实的主体性为目标,以法院对当事人主张的全面信赖为证明标准,以严格的证明方法合理地确信案件真实,同时,以权责分层的方式保障当事人发现案件真实的积极性和自由,并采取确定的证明风险分配规则,允许适用不可推翻的推定作为实现权利的基础,以保障当事人发现真实的积极性与风险的可预见性。
为了能够在这两者基础上构建起一套可以确保当事人权利稳定实现的案件真实保障制度,本文认为,我国立法者应面对两者的影响,结合我国民事权利实现的特性,调整我国案件真实的保障结构。具体而言,在案件真实保障的目标方面,我国民诉法应根据民事权利是否可以处分,以保障案件真实的主体性为原则,以保障案件真实的客观性作为例外,特别是在心证形成过程中,对于可以自由处分的民事权利争议,法官应以全面确信案件真实为原则,对于不可自由处分的民事权利争议,法官应以信赖案件真实符合客观实际为原则。在案件真实保障的权责分配方面,对于需要保障案件真实主体性的案件,应采取权责分层的原则,对于需要保障案件真实客观性的案件,应采取权责混合的原则。在案件真实无法发现的保障方面,也应根据案件真实保障的目标,一方面,构建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并引入不可推翻的推定;另一方面,维持法院与当事人共同负担证明义务,同时保留现行的推定制度。
[1]浙江省宁波市中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甬商终字第1135号[Z];同案浙江高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商提字第81号[Z].
[2]湖北省高院判决书,(2013)鄂民二终字第00077号[Z].
[3]最高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428号[Z].北京市高院民事判决书,(2013)高民终字第3298号[Z].
[4]最高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842号[Z].
[5]张卫平.大陆地区民事诉讼的沿革、改革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正[A].汤德宗,王鹏翔.2006两岸四地法律发展(下册)[C].2007.肖建国.人大民事诉讼法学的特色与贡献[J],法学家,2010,(4):170.
[6]张卫平.大陆地区民事诉讼的沿革、改革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正[A].汤德宗,王鹏翔.2006两岸四地法律发展(下册)[C].2007.肖建国.人大民事诉讼法学的特色与贡献[J].法学家,2010(4):179-180.
[7]苏俄民事诉讼法[Z].张文蕴,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郭卫.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上海∶上海法学书局,1931.
[8]Die sow jetische Zivilprozessordnung und ihr Einflu?aufden sow jetzonalen Zivilprozess,Rechtsw issenschaftlichefolgeHerhausgegeben von der Rechtsabteilung des InstitutsBerlin 1955:119.
[9][苏]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M].王之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210.或者,德文翻译版,A·JW yschinski:Die innereüberzeugung und das sozialstische Rechtsbewu?tsein im sow jetischen Proze?.R ID 1952.Nummer5.
[10][苏]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M].王之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228.
[11]A·JW yschinski:Die innereüberzeugung und das sozialstische Rechtsbewu?tsein im sow jetischen Proze?.R ID 1952.Nummer5:12-13.
[12]Diesow jetische Zivilprozessordnungund ihr Einflu?aufden sow jetzonalen Zivilprozess,Rechtsw issenschaftlichefolge Herhausgegeben von der Rechtsabteilung des InstitutsBerlin 1955.:123.
[13]邵 锋.改订中国民事诉讼法论[M].北平∶北平朝阳学院,1936:194-195.
[14]施 霖.民事诉讼法通义[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行,1946:215.
[15]石志泉.民事诉讼法释义[M].北平∶好望书店,1937:390.
[16][苏]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M].王之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189.
[17]Diesow jetische Zivilprozessordnungund ihrEinflu aufden sow jetzonalen Zivilprozess,Rechtsw issenschaftlichefolge Herhausgegeben von der Rechtsabteilung des InstitutsBerlin 1955:123.
[18]A·JW yschinski:Die innereüberzeugung und das sozialstische Rechtsbewu?tsein im sow jetischen Proze?.RID 1952.Nummer5:6.
[19][苏]C·H·阿布拉莫夫.苏维埃民事诉讼(上)[M].中国人民大学审判法教研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 280.
[20][苏]C·H·阿布拉莫夫.苏维埃民事诉讼(上)[M].中国人民大学审判法教研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 235.
[21]郭 卫.民事诉讼法释义(上册)[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318.
[22][苏]C·H·阿布拉莫夫.苏维埃民事诉讼(上)[M].中国人民大学审判法教研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 250.
[23]余 觉.民事诉讼法实用(上)[M],重庆∶大东书局,1946:465.
[24]Diesow jetische Zivilprozessordnungund ihrEinflu aufden sow jetzonalen Zivilprozess,Rechtsw issenschaftlichefolge Herhausgegeben von der Rechtsabteilung des InstitutsBerlin 1955:118-119.
[25]苏俄民事诉讼法第118、254条.苏俄民事诉讼法[Z].张文蕴,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41、75.
[26][苏]A·多勃罗沃利斯基,[匈]Д.涅瓦伊.社会主义国家——经互会成员国民事诉讼-书序篇[J].刘家辉,译,民事诉讼参考资料,1980:46-48.
[27]郭 卫.民事诉讼法释义(上册)[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289,民国民诉法第282条、第331条.
[28]民国民诉法第541条.郭卫.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上海∶上海法学书局,1931:122.
[29]郭 卫.民事诉讼法释义(下册)[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377.
[30][苏]C·H·阿布拉莫夫.苏维埃民事诉讼(上)[M].中国人民大学审判法教研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 246,民国民诉法第265条.
[31]Abramov,Sovetskij Grashdanskij Prozess Gosjurisdat Moskau 1953,S190德 文 翻 译 于Die sow jetische Zivilprozessordnung und ihr Einflu?auf den sow jetzonalen Zivilprozess,Rechtsw issenschaftlichefolge Herhausgegeben von der Rechtsabteilung des InstitutsBerlin 1955,S121脚注232.
[32]苏俄民事诉讼法第76条.苏俄民事诉讼法[Z].张文蕴,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29.
[33]Judelson,K.S“Problema Dokasywanijaw Sovetskom Grashdanskom Prozess”Gosjurisdat Moskau 1951:274,德文翻译于Die sow jetische Zivilprozessordnung und ihr Einflu?aufden sow jetzonalen Zivilprozess,Rechtsw issenschaftlichefolge Herhausgegeben von der Rechtsabteilung des InstitutsBerlin 1955,S122.
[34][苏]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M].王之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277.
[35]Judelson. Die sozialistische Rechtsprechung in Zivilsachen und das Problem der Beweisfürung, Reschtsw issenschaftlicher Informationsdienst.1954.:103.
[36]Die sow jetische Zivilprozessordnung und ihr Einflu? auf den sow jetzonalen Zivilprozess,Rechtsw issenschaftlichefolge Herhausgegeben von der Rechtsabteilung des InstitutsBerlin 1955:122.
[37][苏]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M].王之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260-276.
[38]民国民诉法第265条.郭卫.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Z].上海∶上海法学书局,1931:60.
[39]郭 卫.民事诉讼法释义(上册)[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318.
[40][苏]C·H·阿布拉莫夫.苏维埃民事诉讼(上)[M].中国人民大学审判法教研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 233.
[41]民国时期民法第7条,郭 卫.民事诉讼法释义(下册)[M].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7.
[42]陈一云.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14.
[43]江 伟,吴泽勇.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J].中国法学,2002,(1).
[44]江 伟,吴泽勇.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J].中国法学,2002,(1):27.
[45]吴泽勇.中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J].清华法学,2013,(1):75.
[46]林文学.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典型案例裁判理由[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242
[47]吴泽勇.中国法上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J].清华法学,2013,(1):76.
[48]林文学.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典型案例裁判理由[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233-234.
[49]林文学.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典型案例裁判理由[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69、222.
The Historic Analysis on the Real Security in Civil Cases in China
DU Ruo-Ying
To guarantee the justifiable solution of the civil disputes,a system is needed to be set up in civil procedure law in a country to guarantee the truth of a case.China has no exception.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procedure law in China,the systems in Soviet Union and the system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directly or indirectly,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ours.At present,Chinese civil procedure law reform must confront to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wo,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confusions,and combining with the Chinese features,set up a series of systems to guarantee the civil rightof every party.
Truth of a Case;Evidence Standard;Principle of Debate;Evidence Responsibility; Presumption
DF7
:A
:1674-5612(2015)01-0081-10
(责任编辑:李宗侯)
2014-12-08
杜若英,北京大学法学院2011级博士生,柏林洪堡大学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此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对联合培养项目的奖学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