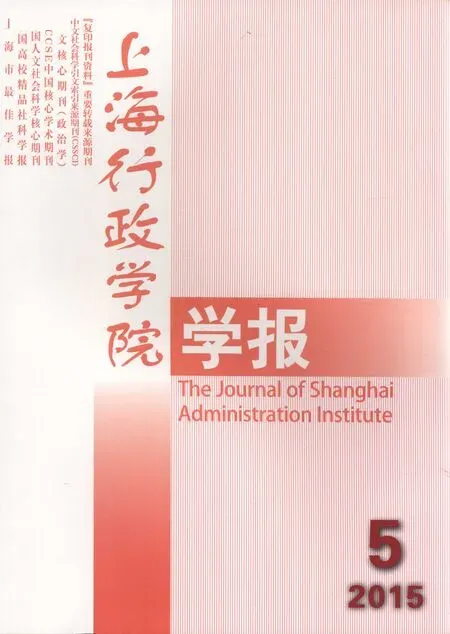中国经济增长特点和趋势若干问题的探讨
2015-04-09刘伟
刘伟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中国经济增长特点和趋势若干问题的探讨
刘伟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是高估还是低估了中国的实际水平?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无发展,总量扩张的同时有无结构升级?增长有无效率支撑?其三,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波动性有多大?怎样认识现阶段宏观调控的松紧幅度?其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潜在增长率是否出现下滑趋势?实际经济增长强劲势头还能持续多久?等等。这是本文所讨论的。
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结构升级;潜在增长率;发展方式
一、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有无低估或高估?
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达到了新的规模和水平,就GDP总量而言,到2014年末已逾63万亿人民币,按不变价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28倍左右,年均增长率为9.7%左右,折算成美元(汇率法)达到9.8万亿,占全球12.2%以上,成为仅次于美国(占全球23%,17万亿以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人均GDP水平而言,到2014年末达到4.7万元左右,按不变价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倍左右,年均增长8.5%左右,折算为美元(按汇率法)达到7500美元以上,属于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水平。
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就总量而言,是否高估了中国经济规模?在以GDP指标作为基本考核和激励指标的条件下,GDP数值往往可能存在虚报,特别是地方政府容易产生GDP冲动,所以也就出现了长期以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GDP数量及增长率与地方政府各自统计后的加总数及年均增长率不符,并且显著小于后者的状况。事实上,从与历次经济普查数据对照来看,通常的年度统计数据一般低于普查的数据,或者说,通
常的年度统计上总体上是少统计而不是多统计出了GDP,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统计核算上。我国的实业,包括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的统计核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较稳定的基础,第三产业的核算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先是试点(1985年以山西为例),尔后逐渐推开(1987年全国开始统计),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核算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转化,才逐渐建立起了对第三产业的核算统计指标,缺乏统计的历史基础。尤其是服务业的核算又有其复杂性:一是服务业的新业态不断出现,如新时期以来市场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市场性服务活动,信息革命推动的互联网服务等等,都是新的服务业态,其所形成的产值如何统计核算是需要不断研究的新问题;二是第三产业中的经济主体极其活跃,单位数量大、占比高并且变化迅速,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显示,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所有企业数中,第三产业的企业数占77.9%,其中小企业数量大,同时,在第一、第二产业中有营业执照的个体经营户中,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占全部数量的94.3%,这些数量大、个体规模小的服务业企业变化迅速,要及时反映和追踪其变化的情况,在统计核算上存在很大困难;三是宏观经济体制发生深刻的变化,使得一些以往在是非市场性的无偿服务或自我服务的活动,逐渐转变为市场性的有偿服务,并由政府行政手段提供的方式逐渐转向由市场交易的方式来组织其生产、分配和消费,如传统的城市住房分配机制向商品房机制的转变,部分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从单纯事业性服务向产业性服务的转变,等等。怎样把这种体制变化带来的服务活动性质的变化反映到统计核算中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第三产业产值统计长期存在被低估的倾向,在前期主要是由于一些按国际标准应纳入,但由于体制性原因而未纳入统计,现阶段则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业态和中小服务性企业急剧变化等原因,使得对服务业的统计核算相对滞后。对照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第一次经济普查(2004年)后所得出的GDP数据比年快报数据增长了16.8%(2.3万亿),其中93%是来自第三产业(2.13万亿);第二次普查(2008年)所得GDP数据比年快报核算数多出4.4%(1.3万亿),其中81%来自第三产业(1.1万亿);第三次普查(2013年)后GDP数据较年快报核算数多出3.4%,其中71.4%来自第三产业。可见在年统计核算中,GDP数据被低估了,并且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产值被低估,尽管被低估的程度在三次普查中逐渐降低。①
2.进行国际比较时如何折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10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显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2014年中国GDP估计值将达17.63万亿国际元,美国则为17.42万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在2014年4月IMF公布的数据中,这一超越要等到2019年才能实现,新的研究把中美两国在这一指标上的关系变化整整提前五年,因而得到广泛关注。
目前,国际上进行国家间国民收入比较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经常使用的指标有两个: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总收入(GNI)。汇率法是用美元来反映各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主要由世界银行公布。为减少因经济波动产生的短期影响,在将各个国家的GDP由本币转化为美元时,采用的是三年平均汇率。在运用数据时,总量比较往往直接使用GDP指标;而在反映人均国民收入时,为更好地体现“收入”的精神,则更多地使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GDP和GNI指标之间从构成内容上相差“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两个指标的实际数值尤其是人均数值之间的差别不大。购买力平价法是由世界各国参加的国际比较项目(ICP)在公布各国国民收入时使用的方法,通过各国提供的GDP及其构成以及相应的价格资料,力图以共同的购买力标准反映世界各国的经济总量。
理论上讲,购买力平价法就是要把各国每年生产(或支出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及其形成总量,都按照美国价格重新算一遍,由此得出按美国价格计算的各国GDP。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进行这样细致的操作,所以通常通过编制各类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指数,对支出法GDP的各个项目进行调整,最后汇总得出按照“国际元”(也称为PPP美元)计价的GDP。这项工作现在得到世界各国统计机构的广泛支持,并且取得很大进展。2014年6月,国际比较项目办公室公布了2011年轮次的ICP数据结果及世界主
要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按细分类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法GDP及其构成,大大推进了这项研究的进展。而IMF公布新的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的时间序列(至2019年),就是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推进的。其中,主要国家2013年以前的数据为实际数据,2014年以后的数据为分析预测数据。所以严格地说,还不能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2014年中国GDP超过美国,只能说IMF的研究预测认为有可能发生这种超越。真正能否超过,还要看实际GDP统计与核算的结果。
购买力平价法的基本思想是更好地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生活水平之间的比较,类似的商品(如西红柿),美国和中国的价格就可能有很大差别,如果按汇率来反映不同国家的家庭或个人在平均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由于价格水平上的差别,反映的结果实际上是有偏差的。用购买力平价标准度量的世界最大的15个经济体(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达70%以上)中,有8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法GDP与汇率法GDP比值大于1(按数值排序分别为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巴西、韩国),这说明这些国家的物价低于美国(排序越靠前物价总水平越低,印度的商品总体而言最便宜),而购买力平价法GDP与汇率法GDP比值小于1的国家有6个(按数值排序分别为意大利、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说明这些国家的物价总水平高于美国,加拿大物价最高(不是某一件商品,而是商品价格的一般水平或总水平),意大利相对便宜。在这些国家中,价格总水平高于美国的全部是发达国家,美国是这些发达国家中东西最便宜的;而低于美国的全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国家。从总体看,这一比值变化反映出来的特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收入水平反映)较高,其价格总水平与美国相比也就相对较高,反之就较低。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对价格总水平虽然有差别,如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之间有差别,但差别相对较小,在10%以内。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就很大,如印度是美国的3.6倍、中国是美国的1.7倍,这种价格总水平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化参与程度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参与国际化的程度越低,商品的市场交流程度也就越低,与世界一般价格水平的差别也就越大,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和汇率法GDP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如果用汇率法计算,印度的经济总量为世界第10位,规模不到日本的一半,但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则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为世界第三,规模为日本的1.45倍。但从国际地位看,无论从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度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印度都远远不如日本。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IMF按照ICP的新结果做出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展望,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GDP超过美国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说明在共同价格标准下,中国当年最终需求的规模可能超过美国,但还不能得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结论。从这一结果看到,一方面,这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取得的积极成果,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从综合实力看,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从国际经济活动参与度和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看,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存在差距,由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总量的提升并不足以抵消这种差距。
进一步对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总量进行对比,在即将进入21世纪以前的199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按照2010年的初步核算结果,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首次超过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独立国家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才完全确立。根据后来最终核算的结果,其实在2009年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而到了2013年和2014年,由于日本经济衰退、日元贬值以及中国经济仍然增长强劲等多方面原因,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左右,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中国的这一国际经济地位已经无可置疑。
从1999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超过日本,到2009年按汇率法计算的GDP超过日本,中国用了10年时间。但1999年日本按汇率法计算的GDP是中国的四倍,而2014年美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只有中国的1.68倍,假设中国保持年均10%左右按美元计算的年均名义增长率(年均经济增长率7%、汇
率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共同影响为5%),而美国保持4.2%的年均名义增长率(1999-2013年的年均名义增长率,包括实际增长和通货膨胀两方面影响),那么大约在2021年左右,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就有可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那时中国以人均国民收入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于美国,因此就发展潜力而言仍然大于美国,或者说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有可能高于美国,如果中国能持续健康发展,就有可能在很长一个时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独立国家经济体的地位。不过,IMF的预测并没有这么乐观,在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预测数据中,2019年美国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大约是22.1万亿美元(按照从2014年起,年均名义增长率为5%推算),中国为15.5万亿美元(按年均名义增长率为8.4%推算)。如果按照这一估计,中国大约在2030年左右赶上美国。但在1999-2013年期间,美国年均名义增长率只有4.17%,而中国则是15.83%,显然IMF在预测中存在对中国的低估和对美国的高估,这也证明IMF在用购买力平价法进行2014年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比较时并不是有意夸大中国而只是承认现实。但无论如何,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的经济总量必定会超过美国,只是这种赶超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当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加快经济增长赶超中国、美国,如印度就有这样的潜力。
一般而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家总体收入水平低,其市场物价总体水平相应也低,因而,运用货币购买力评价法时可能高估其购买力水平,从经济史比较看,通常会将其水平高估10年左右。②其实,尽管我国目前汇率仍属政府有管理的非市场汇率,但在其不断扩大的汇率浮动范围之内,按汇率法进行折算总体上是能较为客观地反映真实水平的,尤其是若考虑到一系列不受汇率等价格因素影响的经济结构指标,如产业结构高度,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降至目前30%略强)等指标,与当代世界水平进行比较,在经济总量上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到2020年实现预定比2010年GDP总量(按不变价格)翻一番目标,将接近100万亿,按2010年汇率水平折算,也只能大体赶上目前美国的水平(17万亿美元以上),届时也还只能是列世界第二位。在人均GDP水平上我国现在是上中等收入水平③(按汇率法折算人均大约7500美元左右),如果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较2010年翻一番目标,以人民币计将达到6.8万元以上,按2010年不变汇率折算,将达到12500多美元,跨越世界银行划定的当代高收入阶段的起点水平(12476美元)。若按汇率法计,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是典型的低收入贫困国,在199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折算为美元,首次达到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进入温饱阶段),在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首次跨越温饱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到2020年实现较2010年翻一番目标,则我国用10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④
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从GDP水平列世界第10位,占全球1.8%左右,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起超过日本),占全球12.2%以上,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水平还只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中国经济又正处于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期,这一时期,一方面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另一方面又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实现的后期,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因而,又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这种判断,是符合中国经济历史发展实际的。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无真正的经济发展?有无结构升级和效率支持?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增长的同时有无相应的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可以是单纯规模扩张和数量水平的提升,这种规模扩张和数量水平的提升可以在制度不变、技术不变、没有创新和效率改进的条件下,通过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形成产出规模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规模增长。因而,增长往往在短期便可明显体现。经济发展则不然,实现发展阶段性提升的关键是经济质态的改变,而经济质态的改变核心是经济结构高度的提升,经济结构高度的演进(排除脱离效率提升基础
的政府行政、政策性推动的结构升级所带来的“虚高度”)只能是效率提升的函数,而效率提升只能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因而,发展只能在长期累积中实现,创新是长期过程,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结构转变,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过程归结为结构转型的过程(如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理论等)。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是一客观事实,尽管对所达到的真实水平、所达到的程度判断尚有争议,然而,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无结构升级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发展,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本身具有客观性,这种结构的深刻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1)三大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历史阶段性变化,从1978年至2013年,在产值上,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从28.2%下降至9.4%,第二产业从47.9%下降为43.7%,第三产业从23.9%升至46.9%;在就业上,第一产业就业比从70.5%降至31.4%,第二产业从17.6%升至30.1%,第三产业则从11.3%上升至38.5%。可以说,从结构上显示了跨越贫困(当代低收入穷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72%左右)加快工业化的特征,自2013年起第三产业在产值、就业比重上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开始显示工业化后期的结构演进特征。(2)产业结构高度所反映的工业化实现程度获得了显著提高,以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作为划分标准,从工业化起点(换算到现阶段为人均国民收入706美元)到工业化完成(换算到目前为人均国民收入10584美元),把“劳动生产率”(有量纲的数值)标准化,以三大产业的产值比与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值的乘积作为衡量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高度水平值(H),中国工业化水平在1978年还未达到当时世界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起点水平(H值为负值-0.020),现阶段工业化实现程度与当代完成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已达70%左右(H值已近0.7)。尽管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均大于1,并且大都H值已超过10,美国、德国等已超过14,足见其后工业化水平和再工业化水平之高),但有着实质性进展。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即在经济结构高度上赶上当代完成工业化国家的总体水平(H值达到1)。现阶段,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5省市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H值已大于1),山东、浙江、福建、辽宁等4省也已接近实现工业化(H值接近1),工业化水平低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有的还不到50%,表现出我国结构演进的地区非均衡性。(3)经济结构演变呈加速态势,从1978年至1985年,结构高度提升较迟缓,总体上是处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准备阶段;从1986年至1998年,产业结构高度进入稳步上升期 (年均H值提高0.6个百分点);从1999-2004年进入加速期(年均H值上升4.7个百分点);从2005年以后,产业结构高度上升速度进一步加快(年均上升6.4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累积性发展效应的逐渐增加。⑤
争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方面:(1)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扩张所带来的增长效应与效率提升带来的增长效应何为主要?总体上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相比较,前者开始的确为主要但具有逐渐降低趋势,而后者则有逐渐提高的趋势,说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并非始终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扩大,同时也有逐渐提升的全要素效率的支持。这与克鲁格曼所批评的“东亚泡沫”是有所不同的,克鲁格曼认为,东亚部分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而不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因此不可持续。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东亚泡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进而引发了对中国高速增长中的要素效率是否提升,效率是否给予经济增长应有的支撑等问题的质疑。就中国的情况看,据测算,自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之前,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的特征(克鲁格曼对中国的分析,恰是根据90年代中期之前的数据),而1998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中要素效率提高所拉动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从长期趋势看,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具有不断提升的趋势,而要素量的投入所做出的贡献相对在下降。⑥因此,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是有效率提升的支持的,尽管这种支持并不十分充分,特别是在1998年之前的增长中,要素效率提升所做贡献更显不足,但之后逐渐有所改善,因而,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相应地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结构高度的提升只能是
效率提升的函数,尽管这种结构高度的提升仍显相对落后。
(2)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全要素效率提升中,为什么产业结构变迁效应逐渐下降,而产业内部的净技术进步效应相对持续上升?结构升级是效率提升,特别是全要素效率提升的结果,而结构升级本身又反过来影响全要素效率,全要素效率上升的动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产业间结构变迁推动,即要素从效率低的产业流入相对高的产业,从而提升要素效率,二是产业内部净技术进步推动,即产业内部的竞争推动技术进步。我国经济在进入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以往传统体制下产业结构严重扭曲,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结构性效率低,在大量的低效率产业行政性地配置了大量的资源,而在客观上技术和管理水平较高的产业中资源配置严重不足,整个产业结构呈现严重的脱离竞争性效率基础的“虚高度"。因此,以市场化为目标导向的改革一经启动,大量资源冲破行政束缚,迅速从非经济领域向经济领域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生活转变),从低效率的产业领域向相对高效率的产业领域转变 (从当时客观上技术和效率水平不高的片面强调的重工业领域向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及社会需求度相对更高的轻工业领域均衡),从而使得来自产业间结构变化形成的要素效率显著提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改革初期短缺经济状况仍然严重,市场对产品需求强盛,供给普遍不足,企业不愁销路,市场竞争压力不大,因而产业内企业间竞争并不激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压力尚不足,所以,产业内的净技术进步对于全要素效率的提升产生的贡献相对弱。但是随着产业间结构失衡逐渐缓解、短缺经济状态逐渐克服,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对要素效率的提升作用会逐渐相对减弱,而产业内部企业间竞争形成的技术进步对要素效率提升的作用程度会逐渐加强,特别是在需求疲软、市场萧条的情况下,产业内的企业间竞争必然进一步加剧,由此推动产业内技术进步加速并提升其对要素效率的作用程度;当某些产业内部竞争及技术进步速度明显强于其它产业时,在产业之间形成显著的效率差异及盈利水平的差异,便会进一步吸引其它产业领域的资本向相对更高效率的产业领域转移,进而又会在新的产业技术水平上提高产业间的结构变化对要素效率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产业内的企业间竞争形成的技术进步是结构升级的基础,是结构升级的量的积累过程;当产业内的进步形成产业间效率显著差异,甚至出现新的具有相对更高效率的新兴产业时,便能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产业结构高度提升,带动结构升级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产业间的结构变迁效应是结构升级的根本,尤其是对于处在体制转换中的非均衡增长的我国经济发展而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程度交替变化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当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甚至市场疲软时,当产业间要素效率差异逐渐缩小,或者说缺乏效率突出的产业拉动时,即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时,不能也不应当主要依靠增大投入量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强行投入拉动,不仅缺乏产业结构变迁所形成的全要素效率提升效应,而且必然导致低效率下的重复投资,加剧低质产能过剩,需要特别强调推动产业内的企业竞争,努力提高产业内技术进步的速度,主要依靠产业内部的净技术进步推动全要素效率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增长,淘汰落后产能,强化全要素效率提升中的净技术进步效应,并为培育新兴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基础。另一方面,当产业间要素效率明显存在差异,或不同产业由于其内部竞争形成的技术进步积累不同,而出现产业间新的效率差异时,要素的边际产出差距在新的产业间技术结构下重新拉大,就应当也需要加速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需要打破行政性垄断,推动资源的市场性自由流动,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在产业的技术创新形成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基础和可能的条件下,在体制上的制度创新尤为重要,以保证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有效地转变为现实。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中,特别是在1998年之后,要素效率对增长的贡献逐渐加大,但在要素效率提升过程中,产业间结构变迁效应带来的全要素效率提升程度逐渐下降,而产业内企业间竞争形成的净技术进步带来的要素效率提升程度逐渐提高,从积极意义讲,可以解释为在市场需求疲软,进而产能过剩严重,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进而出口受挫的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强,因而
加快改革以适应市场,相应地提高了产业内净技术进步的水平。从消极意义上讲,产业间结构变迁效应作用长期持续降低,说明产业结构实质性升级动力不足,结构升级和转变受阻,产业内部的企业间竞争虽然在加剧,但并未真正形成具有引领性的高效率的创新性产业,产业内的企业竞争更多地起着淘汰劣质和低效产能的作用,产业内的企业竞争及相应的技术进步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和量的积累,还未真正达到发生质变,即形成新一轮产业间结构升级的水平,这意味着,产业内去产能的竞争仍会长期存在并继续加剧,经济增长受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的困扰进一步加深,事实上,在结构升级受阻的条件下,市场性的投资需求是难以扩张的,行政性扩张即意味着加剧重复投资,恶化产能过剩矛盾。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有多大?怎样控制增长速度的上下限?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不仅速度高,而且相当稳定,30多年平均年GDP增长率在9.7%左右,实际年增长基本都在这一平均增长率领域上下波动,在正态分布的假定下,在95%的置信度下,未发生过增长速度偏离控制区域之外的情况,在固定资产、社会商品零售、GDP三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增长及波动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最高,其波动性也最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最低,但波动性次之,GDP增速次之,但波动性最低,因为GDP增长速度的波动是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消费)波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两者的波动并不同步,相互间具有抵销作用。根据中国的实际经济经验测算,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一个标准差(平均值反映的是随机变量的集中趋势,标准差则反映变量的离散程度)为3.5个百分点左右,那么,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9.7%左右的话,其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在113.2%和106.2%之间,在这一波动标准下,中国新时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波动下限6.2%的年份只有3个(1981年、1989年、1990年),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增长速度高于波动上限13.2%的年份有6个(1984年、1985年、1992年、1993年、1994年、2007年),没有发生长期严重的过热或过冷的波动。⑦
统计数据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客观实际,与之相联系的问题是,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通胀和下行双重风险,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采取防止“过热”的全面紧缩,财政与货币政策若“双紧”,虽然可能有利于抑制过热所引发的通胀,但会同时加剧经济“下行”的矛盾;同样,也不能采取抑制“过冷”的全面扩张,“双松”虽然有利于刺激增长缓解“下行”,但却会同时加剧通胀。因而松紧搭配便成为宏观政策的基本选择,即现阶段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在其松紧结合的程度上,需要根据双重风险相互严重程度的演变,不断进行调整。这种松紧力度的调整,关键是在宏观政策目标导向上确定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及下限的波动幅度,而确定的原则在于三方面: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二是国民经济本身具有的可能,三是需要联系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⑧所谓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包含十分复杂的因素,但其中重要的是就业目标的需要,即就业目标对经济增长率的要求,这可以视为下限;所谓国民经济本身具有的可能,包含的条件也是十分复杂,但其中重要的是国民经济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即通胀目标对经济增长率的要求,这可以视为上限;所谓联系国民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主要是指实现预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所需要的平均速度,这可以被视为上下波动的中间水准。
1.下限:就业目标的要求。首先需要估算劳动力供给。以我国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根据国际国内死亡率的数据估算以后各个年份的15-64岁之间每个年份死亡人数,估算结果表明2013年我国工作年龄人口(99735.5万人)和劳动力数量(77793.7万人)已达峰值,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实际上进入2012年我国劳动力数量就开始减少了(减少350万人),今后长期里劳动力总量进入逐渐减少阶段,因而总量上的就业压力尽管很大,但压力会逐渐减弱。
其次需要估算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即估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相应带来多少劳动力需求,特别是对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从2000年至2012年的数据看,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对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波动幅度较大,最低年份是160万人(2000年),最高是481万人(2004年),均值是315万人。⑨
总之,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总量逐渐减少的时期,总量上就业压力开始减轻,但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转移问题,需要创造足够的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如果按照近年平均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6.5%的经济增长率便可带来2000多万人的劳动力需求,而我们现阶段包括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内,城镇非农产业实际就业需求增长量在1000多万人,6.5%的经济增长率形成的就业需求量完全可以吸纳这部分新增就业量,并且还会多余出近1000万个就业岗位,这部分多余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可以通过对原有就业者的工资上涨消化掉。一国在一定时期的自然失业率究竟是多少,是一个始终存在争议的问题,虽有许多估算,但往往难以准确,而政策目标失业率则是根据各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国情择机决定。我国2015年政策目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以下(考虑到实际统计上的缺失,参考入户社会调查数据,实际情况往往会略高于登记失业率),预计全年城镇非农产业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会达到1100万人左右,6.5%的经济增长率形成的就业需求量在总量上(不考虑结构)可以充分吸纳,并且有多余的就业需求量转化为工资提升,从而实现原有劳动者工资上升,新增非农劳动者充分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略低于上年,保持在4.5%以下的状态。显然,6.5%的经济增长率作为下限,不仅能够满足就业目标的基本要求,而且也还处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GDP上下波动的下限正常范围之内(106.2% -113.2%)。⑩
2.上限:通货膨胀目标的要求。就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物价水平并不高,PPI(厂商出厂价)已经长时期呈现负值(连续40个月为负),CPI(消费品价格)近年来也只在3%上下波动,有些时候已降到2%以下(考虑到统计误差,通常认为若在2%以下便需考虑防止通缩)。但是,一方面,由于潜在的通胀风险并未有效地得到控制,因此对于治理通缩的政策选择需极为谨慎,因为构成通胀压力的三大因素依然存在,一是2008年后反危机政策以来刺激经济形成的大量货币存量(2014年底M2存量已过122万亿)会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的通胀作用;二是进入新常态阶段国民经济生产总成本上升的势头带来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仍有待缓解;三是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形成的外汇占款进一步刺激需求拉上的通胀,而国际收支再平衡进程仍较缓慢。因此,虽然实际物价水平不高,但由于潜在压力大,宏观政策目标仍不敢贸然放松,对通胀上升水平需要在政策目标上予以控制。根据近些年的经验,CPI上涨率在3%左右,不超过4%或更高,国民经济不会产生大的动荡(2009年CPI达到5.4%也并未见到大的动荡),假定以4%以下作为3%左右的波动上限,或者说CPI不超过4%的水平,我国现阶段GDP增速不超过8%,在其它条件无特殊变化的条件下,应当是较现实的。另一方面,考虑通胀目标,在经济存在下行和通胀的双重风险下,不仅需要考虑控制通胀上限目标,同时需要考虑控制通胀下限目标,也就是说,以国民经济可能承受的通胀压力作为确定经济增长率上限的重要因素时,现阶段,要根据双重风险相互间的关系及威胁程度的变化,要同时考虑防止通缩。比如,若通胀率显著低于上年并且持续走低,甚至较长时间处在2%以下,甚至1%以下,就很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的预期,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对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通缩”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寻找其形成的根本原因,特别需要区分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通缩”。⑪由于市场需求疲软导致的通缩,在价格上升水平下降的同时伴随着市场萧条和失业率的攀升,这类属于“恶性”;由于成本下降带动的通缩,在价格上升水平下降的同时伴随着企业竞争力提高进而就业机会增多,这类属于“良性”。我国现阶段物价水平的走低,既有市场需求疲软的作用,同时也有成本降低的作用,属于恶性与良性叠加的通缩现象,因而既需要关注,进而需要设定通胀下限,防止出现严重的通缩,又不需过度刺激,进而需要设定通胀上限,防止潜在的通胀急剧转化为现实的通胀。因此,若考虑控制通胀的上限目标,2015年我国政府确立的政策目标为3%左右,那么,
经济增长率不超过8%,在其它条件无特殊变化的条件下,是很可行的;同时,若考虑控制通胀本身的下限,即防止通缩(比如以不低于1%为下限),经济政策应考虑在物价水平进入下限状态时加大松紧搭配中的刺激力度,推动经济增长努力接近8%的上限目标,这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的力度调节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其实也对宏观调控方式变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⑫
3.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其中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要比2010年翻一番,年均GDP增长率需达到7.2%左右,在已过去的4年里平均增长率在8%以上(2011-2014年分别为:9.3%、7.7%、7.7%、7.4%),若时间表不变,到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今后6年平均6.8%左右即可,考虑到2020年同时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翻番目标的要求,⑬而在此期间尽管人口增长速度已开始放缓,但人口总量仍是正增长,所以同时实现总量和人均水平翻番目标,实际增速要略高于单纯总量翻番所要求的速度,若今后6年年均达到7%左右即可同时实现总量与人均收入倍增目标。
这样,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格局下便可在6.5%(下限)、7%(平均速度)、8%(上限)之间调整松紧调控的力度。
四、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否具有下滑趋势?实际经济增长强劲势头还能有多久?
尽管中国保持了36年之久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到底能够继续保持多久,并且还能以怎样的速度推进,始终是人们关注和质疑的命题。这需要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做出中长期分析,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人均GDP水平上所体现的发展阶段上看,已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自2010年起),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经济增长不能不同时面临来自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条件变化的“抽紧”。从需求侧来说,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很可能出现投资需求不足(有资本而无有效投资机会),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很可能出现消费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降低消费倾向),进而形成需求疲软的市场格局;从供给侧来说,国民经济生产总成本显著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价格、环境成本、技术进步的投入等等,若效率提升相对滞后,必然形成严重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同时严重降低企业的竞争力。这就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约束经济增长,首先是约束其增长速度。再加之,伴随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基数水平的上升,增长速度的提升必然也受到影响。因此,在未来中长期里中国经济增长会怎样?便成为重要的问题。
在中长期增长趋势中,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决定于潜在产出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其偏离波动程度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所以,重要的是判断未来中长期里我国潜在产出的增长率,通常运用的方法是“增长核算法”,据此,潜在的产出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及产出的资本弹性等。⑭因而需要估算未来(到2030年)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率、全要素效率的增长率以及资本产出弹性。从预测结果看,在2016年之前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体上在7.0%以上波动;从2017年起有可能降至7%以下,直到2020年之前能够保持在6%以上的水平;2021年后可能降至6%以下直到2025年,从2026年起将可能降到5%以下,直到2028年,之后到2030年可能在4%左右。⑮
GDP的实际增长率围绕GDP潜在增长率波动(当然,GDP潜在增长率本身也是处在一定波动范围之内的值),具体波动程度受市场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因素、国民生产总成本变化以及政策目标的调整等多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GDP潜在增长率的预测是基于以往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劳动增长、产出的资本弹性等变化趋势,对未来做出的判断,如果这些因素在未来长期中发生新的趋势性变化,潜在增长率本身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如果时间跨度不是很长,各种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因素难以发生新的有别于以往长期形成的趋势性变化,那么,基于以往趋势变化规律所做出的预测
会有较高的解释力。特别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之前,近年潜在增长率会在7%以上,2017年起有可能降至7%以下,但直到2020年仍会保持在6%以上,考虑到2020年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翻番目标要求及围绕这一目标的政策调控,很可能促使GDP实际增长率在2020年之前的时间里达到平均7%左右的水平;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复苏迟缓,特别是我国本身经济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内需疲软在短期里受结构性失衡的制约难以根本改变,到2020年之前实现更高的实际增长率(如8%左右)不仅难度极大,而且也无必要(无论是从就业目标还是通胀目标,还是从增长目标的实现来说均无必要)。之后直到2025年之前年均潜在增长率可能降至6%以下,2026年至2030年则可能进一步降至5%以下,相应地GDP实际增长率如无特殊的政策变化和市场变化,将会顺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相应变化。⑯
显然,从现阶段到203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及相应的实际增长率具有持续下滑的趋势,这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如果以世界增长的平均速度作为参照,或者即使以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的平均速度作为比较,直到2020年之前我国仍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平均7%左右),甚至到2025年之前仍属较强劲增长(5-6%),高于世界平均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自1978年至2014年保持了36年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年均9.7%左右),还可能有10年的较高持续增长期。
究其原因,重要的发展因素在于,一是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穿越期,距离实现工业化目标尚有距离,但已进入后期加速阶段(预计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深刻并且迅速变化的时期,突出特点在于伴随非农产业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高度提升,城市化加速并且不仅是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迅速提高,城市建设本身的资本投入不断扩张,而且城市化质量提高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规模巨大;⑰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内部区域间差异显著,在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地区间发展上的差异能够转化为发展的资源,为梯度推进经济保持更持久的高速增长创造发展条件。⑱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也会相应变化,如果大体上按照以往的趋势,并且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做出较为保守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中,第一产业降至7%以下,第二产业为42%左右,第三产业52%左右,到2030年,则分别为4.2%、36%左右、60%左右。⑲从经济史来看,这个结构高度与其他有代表性的国家历史相比,与其所达到的人均GDP水平时相应的结构基本相符 (如2030年中国的结构与历史上19个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达到人均GDP 15000美元时很接近)。从与其他预测比较看,与世界银行和IMF预测的结果也较接近,世界银行在《China 2030》的系列报告中预测到2030年中国第二产业占比为35%,第三产业为6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2016-202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7.4%、41%、51.6%;2021-2025年则分别为5.9%、38%、56.1%;2025-2030年分别为4.3%、34.6%、61.1%。⑳
当然,无论是总量增长还是结构提升,这里所做出的趋势分析都只能是基于经济发展历史趋势和对相关因素变化的种种可能做出的预测,要把这种可能性切实转变为现实,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尤其重要的是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只有真正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推动结构转变。事实上,中国现阶段出现的总量失衡,无论是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还是严峻的经济下行风险,深层次的原因都在于经济结构性失衡。就通胀而言,一方面存在需求拉上的压力,而需求拉上的压力首要的源于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国际收支长期收大于支的失衡,使得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由此形成的“外汇占款”成为流通中M2持续增加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存在成本推动的压力,而成本推动的压力根本原因在于投入产出的要素成本结构难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长向主要依靠效率拉动的转换迟缓。就经济下行而言,一方面投资需求疲软,其重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乏力,自主研发和创新力不足,无论是企业作为市场力量,还是各级政府作为对市场疲软的替代,其投资行为都受到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的严重束缚,特别是在产能过剩严重去劣质产能任务艰巨的条件下,缺乏结构升级空间而又扩大投资,只能是加剧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疲软,其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从宏
观初次分配看,劳动者(工资报酬)、政府(税赋)、企业(资本盈余)三者间劳动者收入长期增速相对最为迟缓,比重逐渐下降,使消费增速及所起的作用与经济增长要求越来越不适应,从微观上看,劳动者及相应的居民收入内部差距不断扩大,从而普遍降低消费倾向,使消费需求动力进一步被削弱。显然,要缓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总量失衡的“双重风险”,根本在于缓解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而结构性失衡的缓解依靠短期的总量政策是难以奏效的,须依靠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转变只能依靠创新驱动,创新首先需要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活力来自制度创新。就中国现阶段制度创新而言,最主要的,一方面是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在宏观和社会长期全面发展的导向上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特别是使政府权力建立在民主监督和制度的约束之下。否则,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严重失灵,资源配置权利过于集中于政府,而政府本身应履行的宏观调控和社会发展职能又难以有效实现,企业若想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不能通过市场公平竞争获得(市场失灵),必须寻求与政府谈判的机会(政府集权);同时,对集中的政府权利在法治上缺乏民主和制度约束,使之可能滥用,这就使得企业与政府之间可能存在普遍的“寻租”行为,从而既破坏公平又瓦解效率,政府权力不受约束,企业竞争不经市场,就不可能具有公平;资源配置不根据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而是根据寻租式的“腐败指数”,就不可能有效率。事实上,市场化和法治化的严重滞后,也是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且难以穿越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注释:
①刘伟,蔡志洲:《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3期。
②刘伟:《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③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标准,人均GDP水平超过12476美元为高收入国,目前约70个国家;在此之下但在4056美元以上为上中等收入国,目前约54个国家;在此之下但在1026美元以上为下中等收入国(温饱),目前大约也为54个国家;102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的穷国(贫困)。
④当代70个高收入国家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平均用12.4年,其中20个人口大国,实现这一阶段跨越平均用11.9年。
⑤H=∑Vit×LPit,Vit为第i产业第t时产值占GDP比重;LPit为第i产业第t时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之比 (直接计算的第i产业第t时的劳动生产率)。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式中:LPif为工业化完成时的第i产业劳动生产率,LPib为工业化起点上的第i产业的劳动生产率,LPit为第t时直接计算的第i产业劳动生产率,所得H值达到1为完成工业化,大于1为后工业化,小于1为未完成工业化。(参见:刘伟,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1)
⑥根据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式结构总效应(TSE)=,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投入产出表上的相关数据及统计年鉴数据,可以求解出我国结构变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具体测算方法和说明以及公式各项的含义,可参见: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又见:刘伟、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⑦具体测算方法参见:刘伟《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3月。本文补充了2003年后的数据重新做了估算。
⑧无论实际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奥肯定律,Okun's Law),还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讨论的基础都在于判断失业率,进而再讨论与实际增长率以及相应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并力图找出较为精确的数量联系,以确认增长的目标幅度,但实际上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更多地是源于各国实际经验。
⑨按照这一均值,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7%左右,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很多,但每年实际非农产业新增就业量并没有这么多,多出的就业需求量(岗位)或者被再就业人员工资涨幅部分吸收了,即加薪而未加人,或者是原退休人员退后未增加新人,即减人而未增岗,弥补了退休造成的空缺。
⑩具体数据估算和方法,参见:刘伟、苏剑《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载《中国银行业》,2014年第9期。
⑪关于“通缩”的含义是有不同理解的,有学者认为同时出现经济负增长和物价总水平负增长时,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缩,也有学
者认为,只要物价总水平出现负增长就可视为出现通缩,应当说,物价总水平负增长累积时期长,又会拖累经济也进入负增长,但可能经济正增长,物价负增长,这可视为出现了通缩现象,并非严格的通缩。
⑫刘伟:《新常态下“通缩”的预期及宏观政策选择》,《区域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
⑬所提的是居民收入翻一番,居民收入概念中包含分配因素,从生产角度而言,保证居民收入水平翻番的基础在于生产的人均GDP翻番,至于在分配上能否保证广大居民普遍公平分享增长的福利,不是“被平均”翻番,则是生产之后的分配问题。
⑭潜在的GDP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产出的资本弹性×资本增长率+(1-产出的资本弹性)×劳动力增长率
⑮具体测算各项参数的分析,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苏剑等):《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展望》。
⑯世界银行在《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中预测中国在2010-2015年实际年均增长率为8.6%、2016-2020年为7%、2021-2025年为5.9%、2026-2030年为5%;OECD预测中国在2011-2060年年均增长率在4%左右;美联储则预测中国在2013-2020年之前年均增长率在8.5%左右,到2030年会降到6%。国内学者林毅夫等(2003)预测2014-2024年为7.08%;张延群和娄峰(2009)预测2011-2015年为8.3%,2016-2020年为6.7%;奉敬云和陈甬等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8年后不断下降,2025年后进入低于10%状态,2030年后进入低于5%状态;王小鲁等(2009)则预测2011-2020年若改革成功,年均增长可达9%,否则,只有5.9%。我们在此的预测略偏保守些。
⑰刘伟、李连发:《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积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⑱刘伟:《区域经济结构演进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⑲具体预测方法和分析可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展望(2012-2030)》(苏剑等)。
⑳参见:"China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Society",The Wor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P88.又参见:"World economic outlook:a Survey by the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刘伟,蔡志洲.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3).
[2]刘伟.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
[3]刘伟,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1).
[4]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
[5]刘伟.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
[6]刘伟,苏剑.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J],中国银行业,2014,(9).
[7]刘伟.新常态下“通缩”的预期及宏观政策选择[J],区域经济评论,2015,(3).
[8]苏剑等.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展望[Z],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讨论稿,2013.
Discuss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
Liu Wei
Many issues have been rais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Firstly,"What is the level of the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and"Whether it is overestimated or underestimated?"Secondly,"Is the growth accompanied with development?""Is the growth accompanied with upgrade of structure?"Thirdly,"How fluctuant is the rapid and sustainable growth?"and"Is there potential slip-down for this trend?"Fourthly,"How long will this trend last?"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se issues.
Economy Growth;Economic Fluctuation;Structure Upgrade;Potential Growth Rate;Mode of Development
F124
A
1009-3176(2015)05-004-(12)
(责任编辑 陶柏康)
2015-6-20
刘 伟 男(1957-)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