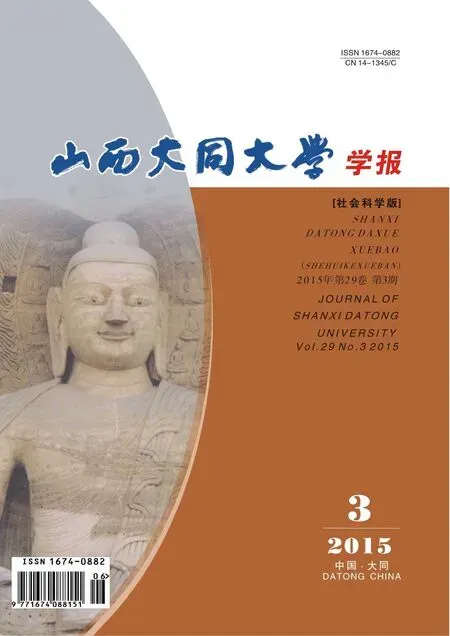从回译视角探究译者主体性
——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
2015-04-03王海丽
王海丽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长期以来,回译一直被认为是检测翻译效果的手段,然而,回译理论研究却被忽视多年。近年来,翻译研究视野日渐扩大,回译涉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在众多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大环境下,翻译领域迫切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来促进中英文作品间的有效互动,这时,回译不仅重归人们的视野,回译研究对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教学、以及翻译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回译研究
(一)回译的定义 回译的定义林林总总,较为全面的概括主要有以下三条:Shuttleworth&Cowie编写的《翻译学词典》中对back-translation的解释是:回译是译文译回原文的过程。[1]冯庆华等认为,回译也是一种翻译,是一种以译文为原文的翻译。[2]《中国翻译词典》认为,回译是指文字翻译过程中将译作再以原始翻译还原为原作,以此为手段检验译作语言文字的准确性。[3]结合以上三个版本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回译定义,回译就是将译文再一次译回原文,其功能和意义则取决于不同的回译用途。
(二)回译的用途 多位学者曾就回译的用途做出分类,方梦之将回译分为三种情形:检验性回译、研究性回译、机械性回译。[4]贺显斌层区分了三种回译:1.用作翻译策略的回译;2.译文质量检验和翻译教学手段的回译;3.作为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辅助工具的回译。[5]总体而言,回译可分为以下类型:作为翻译策略的回译、用于翻译教学的回译、用于语言研究的回译以及用于翻译研究的回译。
基于以上分类,回译可以应用于以下情形:首先,在翻译教学中,回译可以用来检测译文的质量,通过回译文与原文的对比,分析翻译过程中的得与失;其次是“引文”的翻译,即译文中有用原语书写的引文需要回归原文;第三种回译情形则涉及多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如原文为英语文本,译为日语,又由日语译为德语,此时,从德语译回英语的过程也属于回译的范畴,此类型多为原文已失传,需要汇总多种语言的译文得出最贴近原文的作品;第四种情形,目前应用得最为广泛,就是回译华裔作家的文学作品。当今许多华裔作家的英文原著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影响着英美文学及语言文化,此类作品的英译汉实为将英文表述的中国特色的文化、风俗等回译到汉语当中。鉴于回译的应用广泛,回译研究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对回译的研究并不能止步于方法与手段,在回译过程中,除了语言文字的作用,还有译者这个更重要的角色在不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二、译者主体性
毋庸置疑,翻译的客体是原文本,其决定译作内容,是不可撼动的客观因素。同时,翻译的主体是译者,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仅决定翻译的质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作。用回译方法检验翻译质量,首先要探明的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属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属性。[4]此定义突出了译者的本质属性为主体意识。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6]这一定义则强调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前提——尊重翻译对象及实现翻译目的。
简要地说,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从而体现出不同译者的独特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原文的制约、译入语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每一位译者没有差异,唯独自身因素的影响却造就了同一文本不尽相同的译文。译者的主体性是潜在的,受约束的,就译者主体性的应用程度而言,中国翻译史上有一人可谓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译作以弘扬中国文化、宣传中华文明为目的,在中外翻译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人便是国学大师辜鸿铭。辜鸿铭一生潜心将中国的儒学经典翻译成英文,较为突出的是他翻译的三部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和《大学》。古往今来,多位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辜鸿铭的译著,就辜鸿铭的生平轶事、著译与思想文化活动做出论述,[7]既往的论文著作对其旨在传播中华文化,消除西方人的误解进行肯定,对其在英译《论语》时采用的方法也有质疑。窥探这些质疑的渊源,不难发现所有的疑惑都指向了译者主体性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
三、译者主体性之于回译辜鸿铭英译版《论语》
纵观辜鸿铭的整部《论语》译著,在遵循原作思想前提下,辜氏译文的很多细节处理都体现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手段的抉择。以下文为例,通过对比此句的回译文与原文,辜鸿铭对整部《论语》英译可见一斑:
原文: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译文:An officer in a certain State asked Confucius,saying,“What is meant by the common saying'It is better to pry to the God of the Hearth than to the God of the House'?”“Not so,”replied Confucius,“a man who has sinned against God,——it is useless for him to pray anywhere at all.”
回译文:某国的官员问孔子,说:“俗话说,‘向灶神祷告比向房屋之神祷告要好’是什么意思?”“不是这样的,”孔子回答说,“如果一个人犯了背叛上帝之罪,无论他在哪里祷告都没用。”
(一)省略专有名词 省略专有名词是辜鸿铭英译《论语》的一个典型特点。《论语》书写方式为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其中多次出现孔子弟子的名字如子贡、子路、子产、子夏、子游等,其英文均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对于语篇中提及的历史人物,辜鸿铭大都采用省略的方法:如:“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peaking of an infamous emperor and tyrant of ancient times,remarked:‘His wickedness was, after all, not so bad as tradition reports’.”回译文:“孔子的一个学生,在谈到古代一个臭名昭著的帝王和暴君时说,毕竟,他的邪恶不像传说的那么糟。”翻译时,辜鸿铭将“纣”的名字略去,译为“an infamous emperor and tyrant of ancient times”——“古时一个臭名昭著的帝王与暴君”。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曾明确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译本引起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固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使其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其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以此为翻译目的,专有名词的作用就不甚重要了。一些专有名词的存在反而会影响读者阅读译文时的连续性,增加理解难度。因此,将专有名词省略,便于读者理解原文,更好地促进文化传播,实现译者初衷。
(二)将中国文化替换为基督教文化 例句中的“不媚奥,不媚灶,只媚天”,原文中“天”指代人间正义,这是孔子本人蔑视权贵,重天理讲良知的体现。辜鸿铭将“天”译为“God”(上帝)。将国人眼中至高无上的“天”译为上帝,是其对基督教文化认可的体现,也是在翻译时向西方文化的进一步靠拢。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以下的例句中,原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译为:“Confucius remarked, ‘At the service of the great Ti sacrifice[the 'Mass'in ancient China], I always make it a point to leave as soon as the pouring of the libation on the ground is over.’”回译文:“在伟大的褅祭仪式(古代中国的‘弥撒’上),我总会在将祭酒洒在地上一结束就刻意离开。”辜鸿铭将“褅”看做所有祭祀中最重要的一种,因其自身对“褅”的独特理解和解释。在他的所有言论与作品中,始终视儒学为中国的“国教”,而儒家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祭拜祖先”,褅则是祭拜祖先的最高仪式。他将之对应为“Mass”(弥撒——天主教中纪念耶稣基督的最高祭礼)。这两个概念皆属双语文化中最深刻的内涵,译者并未对“褅”这一异域词汇做出解释,而是直接列出“弥撒”,是其用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佐证。
辜鸿铭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学者曾经指出辜鸿铭保守主义的文化观是个人和社会的缩写,在辜鸿铭的作品中他的文化保守主义贯穿始终,从反东方主义、反话语霸权、儒教天下三方面指出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价值替代和统摄整个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发展,并借此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扩展力量。[8]然而,在辜鸿铭的《论语》译文中无论是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还是文化词汇,辜氏的处理都是在赤裸裸地消除中国文化的痕迹,作为一个保守的传统文化学者,在翻译如此重要的文化作品时用西方文化来省略和替换中国文化,便不难发现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痕迹。
译文质量无疑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译文从字词取舍、段落安排到整体布局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体现译者主体性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可见翻译时面临的种种选择还囿于译者的各种主观因素。上文提到的两方面,就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取舍,很多学者曾经提出了质疑。翻译目的不同,采用的翻译手段也不尽相同,对于专有名词以及文化信息是否应当省略,仁者见仁,在辜鸿铭眼中,译文能否被读者接受,中文经典能否和西方经典抗衡远比个别历史人物或某个文化术语要重要得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省略专有名词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将中国文化内容替换为基督教文化内容,可以看作一种创造性对等,是“具有一定艺术修养和目的语写作能力的译者,通过主观努力来实现的,通过这样的累积,译文才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9]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英文读者也渴望对中国文化有具体的了解,也有更多的中国历史人物被其所熟知,专有名词的去留则另当别论。判断译著的质量,评价译者的成与败,不能用固定的眼光和一成不变的标准,要在既定的时代背景、个人思想和生活状态下多方面多维度的考察。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发挥受到其读者定位、翻译目的、自身经历、双语能力、个人以及所出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读者定位及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内容,译者的经历和双语能力决定译文的质量,而译者个人及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则决定了译文传递的思想,因此,译者主体性从语言和思想这两个层面上对译文都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
四、结语
王宁先生曾指出,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拥有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翻译的一个方向。[10]如何更好地进行中译外?汉语中特有的文化信息和语言特色如何取舍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特色同时又为外语读者所接受?这都是每一位译者将会面临的棘手问题。译者主体性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翻译不仅是语码的转换,每部译作都会不同程度地体现译者主体性,译文才因此展现出不同的风姿,只有深刻剖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才有利于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实现原文与译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有效沟通。译者也可以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审视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翻译实践。
[1]Shuttleworth Mark&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15.
[2]冯庆华,李 美.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Z].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03.
[4]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97.
[5]贺显斌.回译的类型、特点与运用方法[J].中国科技翻译,2002(04):45-47.
[6]查建明,田 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19-24.
[7]刘中树.1978-2008年辜鸿铭研究述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11(第61期):79-85.
[8]刘治国.从后殖民理论角度浅析辜鸿铭的文化保守主义[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2007(09)116-118.
[9]郭建中.创造性翻译与创造性对等[J].中国翻译,2014(04)12.
[10]王 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