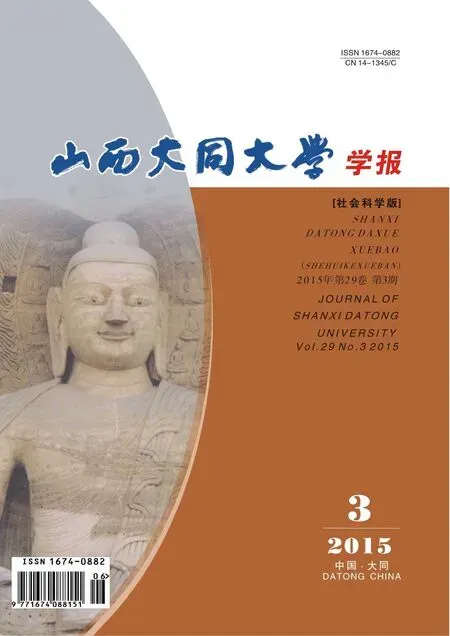西方性别气质发展研究综述
2015-04-03刘丹丹戴雪红
刘丹丹,戴雪红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开始就已经孕育着性别气质本质论的萌芽,认为理性、智慧、勇敢是男性气质的象征,感性、无知、柔弱是女性气质的化身,这二种气质是泾渭分明和相互对立的,而且男性气质优于女性气质,因此男性天生就比女性高贵和优越,由此造成了男女两性本质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的,使得女性在漫长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趋于屈从和附属地位。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性别气质偏见思想直到20世纪中期以来才逐渐被性别气质社会建构论所取代。社会性别气质建构论发展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的阶段,有力地挑战了传统性别气质本质论,为追求男女的平等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一、性别气质本质论(20世纪中期以前)
性别气质本质论把人的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或性别气质(gender)相等同,认为由于两性生理上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于是造成了男女性别气质的差异,男人具有男性气质,女人具有女性气质。性别气质是指以男女两性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为基础的,一整套固化的、强调两性对立的心理特点和行为举止。[1](P26)男性气质是指男性具有成就取向和关注完成任务的行动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女性气质是指女性具有同情心、令人亲切、对他人关心等亲和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1](P26)比如,男性拥有勇敢、理性、智慧等;女性富有感性、温和、亲切等。性别气质本质论是站在父权制的立场从维护男权文化的社会统治角度,把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性别不平等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并认为女性的低等地位归因于女性特殊的生理原因,女性天生就是男人的一部分并依附于男人。
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中,自柏拉图以来就已经开始强调男人与理性、优势、抽象、公共领域、统治支配相联系,女人则与感性、劣势、具体、私人领域、依附从属相联系,于是便将两性置于主与仆、优与劣、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由此使得两性关系变成了一种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等级关系。男性被置于积极主动占支配的地位,女性则处于一种消极被动受控制的地位。近现代西方哲学家诸如卢梭、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都秉承古希腊哲学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形成的性别偏见,把女性描述为依附并从属于男性,缺乏见识、智力平平,并把女性定位在家庭之中,把男性定位于公共领域之中,贬低女性价值,高扬男性价值,从而深化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统治。
20世纪以来性别本质主义理论思想主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用精神分析学对两性不同性别气质的产生做了详细阐述,认为两性性别气质不同主要由于“阳具崇拜”和“阉割情结”在起作用。弗洛伊德从男性中心论出发,认为男性才是真正完整而健全的人,女人跟男人相比由于没有阴茎所以是不完整的,不能与男人相媲美,作为女人总是要为此感到自卑的。于是在家庭中,女孩会自觉地倾向于认同温柔、和蔼可亲的母亲角色,这样才可以赢得男人的青睐。由于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使得男孩产生了恋母的情结,但是这样会面临父亲的“阉割”,于是男孩会主动屈服并向具有权威性的父亲看齐,并自觉接受其思想和行为规范,于是两性不同的性别气质在“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下逐步形成。弗洛伊德阐释的性别气质的形成主要是以男性的性别特征和男性话语权力为核心,女性则被边缘化,处于话语和权力的真空地带,后来女性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20世纪中期以前一直盛行的是以性别气质本质论为基础的性别角色论,着力塑造与两性生理性别相适应的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两性被置于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框架中,而且男性气质成为社会主导的气质,女性气质是作为男性气质的附属,男性气质总体上是优于女性气质的。性别气质本质论从生理性别出发界定性别气质,不免落入性别气质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中,忽视性别气质内部个体的差异性,片面地把性别气质范畴化,使男尊女卑的性别气质刻板印象不断地被强化,这是性别气质本质论的缺陷。西方哲学传统中秉承着自古希腊以来二元对立的男权制思维模式,带有强烈的性别本质主义色彩,由此形成男性处于统治地位,女性处于被压制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地位。因此,追求男女的平等必须打破并解构西方传统历史中秉承的男性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性别思维模式,正面肯定女性的价值与话语权,于是性别气质社会建构论便应运而生。
二、性别气质社会建构论
(一)性别气质建构论的萌芽阶段 20世纪中期——20世纪70年代属于性别气质建构论的萌芽阶段,开始挑战传统的性别本质论,性别气质建构论指出性别气质不是先天的,而是受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与习惯信仰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等影响所建构起来的,性别气质是不稳定的和可塑的,两性不同的性别气质主要是受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社会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气质也不同。这一点在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气质》中得到了印证。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挑战了传统人们对固化的性别气质认识,实际调研了相距100英里之内的三个原始部落,发现三个部落中男人和女人的性别气质迥然不同。美国思想家和人类学家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其著作《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中,也揭示了性别气质在历史文化中不断被塑造的特点,并倡导两性平等、和谐、合作的伙伴关系。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以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和格里尔的《女太监》、《完整的女人》为主要代表,这些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在传统以男性霸权为文化中心的社会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模式已经沦为男性统治女性的工具。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在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中写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P309)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和神话等方面分析了不同社会形态中女性的次等地位和与其相对应的女性气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作为“他者”(the other)地位的产生并不是由生理原因决定的,而是在社会中不断被塑造的结果。为性别气质社会建构论的萌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格里尔以“女太监”来比喻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精神阉割,批判了西方散文、诗歌、小说等文本中对女性气质的形塑,并在《完整的女人》一书中呼吁塑造具有健康完整人格的新女性。贝蒂·弗里丹《女性的神话》一书对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即女性的全部奥秘和价值主要是“相夫教子”,对女性最大的价值就是在家庭中做称职的家庭主妇的观点表示激烈的批判,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进行了批判,主张女性要走出家庭,充分发挥女性的聪明才智,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
(二)性别气质建构论的迅速发展时期 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属于性别气质建构论的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是性别气质建构论开始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女性主义研究主要致力于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解构和批判,探讨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对两性气质的塑造。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1970年发表的《性的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父权制”的概念并指出两性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父权制度下的政治统治关系,“这种统治比任何一种被迫隔离的方式更加牢固,比阶级的形式更加无情,更一致,而且毫无疑问也更长久”。[3](P31)米利特认为男性气质代表着权威与权力,主宰者整个社会并通过性别政治来统治和支配着女性。英国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女人等级》、《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等著作吸收了施特劳斯父权制起源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最初是源于父权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随着父权制社会结构的瓦解,把女性的附属地位归结于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并且受制于心理文化中代代传承的俄狄浦斯情结,于是主张从文化心理和制度层面消除女性的从属地位。安·奥克利(Ann Oakley)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社会》一书中对性别与社会性别作出明确区分,她写道:“‘生理性别’(Sex)指的是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差异:生殖器的明显不同以及与之相关的生育功能上的差异。但是,‘社会性别’(Gender)与文化相联系:指的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分类。”[4](P16)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为女性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为长期深陷性别本质主义泥淖无法自拔的女性主义研究带来了希望和曙光。以此为突破口,女性主义学者把研究焦点定位于性别气质的社会生成机制,探究社会制度对性别气质的规训与影响,女性主义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首次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新概念,认为两性气质是社会制度强加的产物,是通过文化、心理和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性别制度与社会经济政治相联系,但同时也有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之后,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女性主义者讨论的焦点,女性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考察社会性别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的性别理论。20世纪80年代,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琼·W·斯科特(Joan W.Scott)认为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5]((P145)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是由于社会权力关系决定的。这一时期,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性别气质的二元划分给男性和女性都带来了压迫。比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男性统治》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布尔迪厄认为,男性气质既给男性带来了特权,也给男性带来了紧张和压力“对男性价值的颂扬,其黑暗的对立面是由女性特征引起的恐惧和焦虑,男子气概,是在对女性且首先是在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6](P72)1987年康奈尔(Bob Conncll)在《男性气质》一书中也提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同时也造成男人内部的等价分化,把一些缺乏男性气质的男人归为次等的和低下的。由此可以看出性别气质的二分法不仅受到女性的批判,同时也给部分男性带来压迫,至此,性别气质的二分法逐步被质疑,也逐渐被性别气质的多元观所超越。
三、性别气质多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至今处于性别气质多元化发展时期。此时期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汲取了索绪尔的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等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开始反思话语权力对身体和性别气质的建构,倡导性别气质差异性、多元中心的性别气质和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寻求多元身份认同的女性主体话语权。性别多元观打破了从整体上笼统地把性别气质划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是深入到男性和女性群体内部,关注具体的个体的性别气质,发现个体内部的性别气质千殊百态,各不相同,而且性别气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女性主义者米歇尔·巴莱和特丽莎·德·劳里提斯(Teresa de Lauretis)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论角度来阐明性别气质的形成。女性主义者米歇尔·巴莱《意识形态与社会性别的生产》一文主要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阐述了意识形态是性别气质建构重要的场所,“社会性别之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历史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是意识形态与生产关系之内在联系的准确验证”。[7](P74)女性主义评论家特丽莎·德·劳里提斯在《社会性别机制》中提到性别气质是一种再现,而且是隶属于某个阶级的关系的再现,性别气质的再现表现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比如学校、媒体、家庭、教会和法庭等,她还指出:“作为一种得到制度化话语确认的、能够控制社会意义领域的理论,阿尔都塞的理论本身就能起到一种社会性别机制的功用”。[8](P207)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维蒂格(Monique Wittig)的观点也比较开放和激进,认为女性的心理乃至身体都是被社会所强加,她理想的新社会里所描绘的理想目标是社会中只有人的概念,而没有男人与女人的概念的区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一书,汲取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关于性别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主体的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旨在阐明语言、主体、性别和社会规则之间的密切关系。巴特勒不仅认为性别气质是在后天社会中不断塑造的,而且认为生理性别和性别气质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否认纯粹自然的生理性别的“白板”存在,生理性别也是被社会性别文化所侵蚀,浸透着社会性别规范的因子,她认为没有所谓的生理和社会性别之分,性别划分只是一种社会规则,主体的性别是社会法则塑造的,而且建立在统治阶级合法权力基础之上的,这种规则被不断的操演和引用,于是便书写出不同性别气质的主体,巴特勒认为性别是不断地重复操演的结果,“性别的内在本质,是通过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对身体进行性别的程式/风格化而稳固下来的。这样看来,它显示了我们自以为是自身的某种‘内在’特质,其实是我们期待并通过某些身体行为生产的;推到极致来说,它是一种自然化的行为举止的幻觉效果”。[9](序言9)随着时间的发展自我不断进行性别操演,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逐渐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而形成了所谓的关于性别的常识。因此,从性别操演理论角度来看,性别就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不存在真实与表象之别,所谓真实的性别气质不过是社会为了维护统治所制造的虚假的管控。
总而言之,社会建构论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本质主义的,批判了性别本质论调下贬低女性气质并且把女性置于从属和被压迫地位,主张消解以男性为主宰的性别本质主义理论,开始重新重视女性的价值、尊严和地位。在社会性别建构理论框架下多角度探究制度、权力、意识形态和话语对性别气质的建构,进而在此基础上解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提倡性别气质发展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力求摆脱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自由发展的束缚,为两性自由而平等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1]佟 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社,1999.
[4](英)Ann Oakley.Sex,Gender and Society Maurice Temple Smith Ltd.London,1972.
[5]谭兢嫦,信春鹰.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6](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 晖译.男性统治[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7](美)Judith Newton.Deborah Rosenfelt Feminist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M].Methuen,1985.
[8](美)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