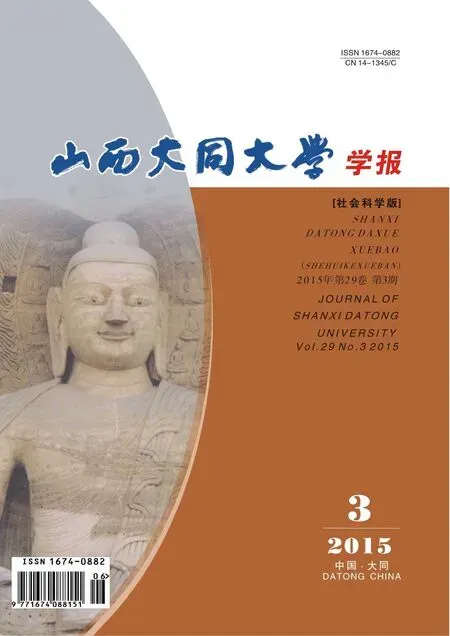外长城沿线山西边关古村镇民族民俗融合论析
——以大同得胜堡、落阵营和新平堡为例
2015-04-03卫才华
卫才华,张 鑫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边关村镇的实地调查中,我们无法回避“谁是本地人”这一问题。据新平堡一位村民介绍,他祖父是满族人,妻子是蒙古族人,四个儿子的妻子也都分属不同民族。虽然家庭成员是不同种族的混合,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汉族的观念和规范。①这个不同血统奇异混合的例子应和了“熔炉理论(The Melting Pot)”:边关古村镇的各民族群体都被整合进一个多元熔炉中,逐渐组成一个集蒙、满、汉、回等多民族于一体的全新社会,他们自身拥有的多样民俗文化也不断熔铸成一种全新的、融合性的民俗形态。[1]在磨合适应阶段,不同民族的民俗融合从独立发展到部分吸收,更多是单向的行为。到了双向融合阶段,不同的民俗主体开展双向互动,打造了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元熔炉,形成了边关古村镇交融互渗的民俗文化。这里的“双向互动”是一个关键词,民俗融合不是只靠一方的努力,不能只是一个民族民俗对另一个民族民俗文化的单线吸收,它需要双方的互动。在相互分享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群体真正达成了水乳交融的状态,扩大了“我群”的概念,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接受或履行对方的民俗模式,整合出一套同质的民俗规范,即“共有民俗知识”,主要包括优势互补的生产民俗、相互渗透的饮食民俗和兼容并包的信仰民俗这三种内容,通过熟练运用知识,不同族群的民众使自己尽快地适应新的民俗生活。本文以边关古村镇这一多民族杂居区为切入点,将丰富的典籍资料与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详实地分析这一区域不同民族在生产民俗、饮食民俗、信仰民俗三个层面的交融发展,展示此地民族民俗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地域特征与核心文化。
一、优势互补的生产民俗
地理条件的差异,或者说自然社会环境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不同族群不同的生计方式,主要分为渔猎采集业、畜牧业、林业和农业这四类。有些民族几乎专门依靠其中之一,还有些民族同时采用两类或两类以上的方式。同时采用两种基本生存方式的文化要占更大的优势,生活材料的选择更显多样。[2]这就使各民族生产方式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成为必要。生产方式又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民俗,“这类民俗伴随着物质生产的进行,多方面反映着人们的民俗观念,历史上对保证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3]不同的生产民俗“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民俗文化的博大和雄浑。[4]
元初,北方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忽必烈收复南宋、统一全国时,已经注意到使民安业的问题。蒙古族在本民族聚居区,“发展牧业生产,同时也以屯田等形式从事农业生产。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还使农业与牧业生产结合共同发展”。[5]可以说元代是我国古代蒙汉之间农牧业生产民俗互相交流、促进的黄金时代。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民族之间错居杂处空间格局的奠定,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生产方式上相互借鉴,逐渐形成了农牧结合的生产民俗,呈现出优势互补的特性:一方面,农业对牧业渗透,改变了游牧民族粗糙的农作方法,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另一方面,牧业也影响着农业,形成农区且耕且牧的生产民俗。
(一)从“漫撒籽”到精耕细作:农业渗透与游牧业的变化 少数民族发起战争最主要的目的是开放市场,通过与汉民交换,获取生活和生产资料,补充游牧经济的不足。正如林耀华所说:“畜牧生计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产品单一和不耐贮存。这就使得它对于农耕社会的贸易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6]所以,利用民族贸易市场的开放,游牧民族开始学习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漫撒籽”式的半农半牧的生产习俗,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形式。
游牧民族在边关古村镇定居之后,生活环境的变化局限了放牧经济的发展,为了生存,他们开始学习农业劳动。最初,南迁的少数民族还采用牧区“漫撒籽”式粗放型生产方式。从耕作业的情况来看,少数民族种植比较随意,“听其自生自长”。秋天收割庄稼也极为简单,只是把穗子割掉,忽视了处理庄稼叶、杆和茎等收尾工作。[7]建国之后,国家进行农村体制变革,土地收归国有,大队组织村民集体开垦和耕种村中空地,采用工分制分配劳动成果。在蒙汉民众共同耕种的过程中,蒙民学会了汉民精耕细作的农作法。上世纪60年代以后,蒙民又学会了轮作倒茬技术,对肥力水平不同的土地采用不同的轮作方式,如对肥力较低的土地会用“糜子—马铃薯—油料—大豆”轮换耕作;肥力较高的土地则是“小麦—蔬菜—玉米”交替种植。②同时开始利用犁杖、镰刀、锄头、簸箕等必不可少的农业工具,促进了耕作制度的改革。在访谈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类似的声音。
“我老家是丰镇的,据我‘大’说,我们家大约三十年代迁来的这儿 (得胜堡),刚开始,他可瞧不下这儿的人,他说汉人就会下死力气,能比他多收多少粮食,我们老家耕作是选一块地播种糜子,连种几年,这地就不行了,然后再找其他好地。这的人是‘闲种’,就是一块耕地分三区,一年耕种2/3,休闲1/3,像轮作。我们蒙人也确实懒,不爱动,就喜欢‘耍’,也不怎么除草、施肥,反正能出多少粮就出多少,听天由命。后来,生了我,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他着急了,就开始和当地人学,当地人也热心,觉得你勤快老实就教你,教选种子、农具、除草、施肥、束捆、脱谷等技术。”③
通过访谈,我们意识到,游牧民族南迁后,脱离了蒙古包,住进了四合院,甚至由几家或更多家形成圆形或方形的小村落,定居性不断加强。[8]但没有完全摆脱游牧民族的特性,他们“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9]重视牲畜,对庄稼种植态度较为随意。但在汉族人的影响下,农耕生产发生了很大改变,如种植作物种类、耕种农具、耕作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还学会了“打草技术”,真正从“漫撒籽”的生产方式转移到精耕细作的农业习俗。“打草”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牲畜过冬饲料不足的问题。[10]牧民南迁后,蒙民学会了汉人贮存干草的技术措施,将干草收割打包后堆放到宅院内墙壁四周,甚至还出售多余的干草。[11]大同落阵营村牲畜较多,有10多台打草机,每年每户打草的数量一般在1000斤左右,平均每户刈草12天,运干草5天。
(二)从“副业”到“主业”:牧业渗透与农区畜牧业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耕作制度一直强调单一的粮食种植,轻视畜牧业的发展。[12]也就是说,在古代农耕地区,“主业”专指种植业,相应的“副业”即畜牧业,主要针对草食性动物的饲养或放养。虽然历朝也重视马政,并在大同镇等地设立官办畜牧机构,如明代大同“设苑马寺,养以恩队军千余人”,但养马的目的仅为对付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的侵扰,并没有考虑配合补充当地农业发展。[13]对边关古村镇来说,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邻近的地缘优势使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并且相互影响。一方面,农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牧业提供各种工具和种子。另一方面,牧业也不断感染农业,而且从“副业”进化到与种植业并列的“主业”地位,形成边关农牧交汇区独特的生产民俗,主要表现为选择畜种、肥料循环再利用和放牧方法等习俗。
畜种选择习俗。为了提高牲畜的质量,必须选择优质的畜种。在蒙汉民族的杂居相处中,汉民学会了牧民选择畜种的方法,以“饲养”为主,主要经营牛、羊、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种类。牧民南迁定居汉地后,改变了以往“放牧”的生产方式,但游牧习性根深蒂固,以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牲畜仍是其主要财产,“人以孳畜多寡为富贫”。[14]他们传承着草原民族牲畜选择的方法。如相马经“相口齿止于三十二岁,异相者寿四十、五十”。[15]畜种选择技艺为农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技术支持,从传承的角度而言,这类技艺民俗又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以口耳相传的独特方式延续在民众的实践生产中。汉民除了接受学习牲畜选择方法之外,还学会了草原民族照顾孕期母畜的关键技法。他们认为“爱羔如爱女,日后得利益”,对待产后牲畜非常细致。在新平堡镇的农户家中,有的汉民家中母羊生产后不认小羊羔,就会学蒙人用低沉的声调念诵一段祈祝词:“台格,台格——台格,台格——”或是“奶羔,奶羔,奶——羔,奶羔——奶羔,奶羔,奶——羔,奶羔——”,希望母羊被驯服,哺育小羊羔。④
肥料循环利用。发展畜牧业既可以弥补种植业发展的单一性,又可以生产“农家肥”,并对肥料进行多层次、多途径的循环再利用。可将鲜牛粪稍加晒干,再混入马粪,就能加工出优质的有机肥料,应用到庄稼的施肥中,能种植出有益身体健康的绿色植物。“牲畜的粪便还可用于冬季取暖,它对空气污染少,烧尽剩下的灰烬仍然可以当作肥料撒到田地里。”[16]天镇县新平堡镇一户农民家中,全家饲养1头奶羊、18只鸡、2头猪和六亩地。主人利用闲置田地养羊喂鸡,用鸡粪调和猪料,用猪粪肥田,实际上在边关古村镇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无废弃物的生态系统。⑤在肥料处理的过程中,各种生物种群科学地衔接,巧妙地配合,互为依托,实现了农业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由上可知,围绕边关古村镇的杂居空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建立了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打造出农牧经济互补结合的生产范式。关于农业与牧业的相互补充,费孝通提出:“从本地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来看,‘农牧结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当时设想过的‘农牧结合’的办法是‘卖羊买牛’,发展奶牛业,种植玉米一类的作物,成熟后趁青贮窖,在草料缺乏时,喂饲牲畜或用以加强牲畜营养。这是一种为牧业服务的农业,不仅可以以农促牧,而且通过‘过腹回田’,又为农田提供了有机肥料,以牧促农,使农牧矛盾的恶性循环转变为农牧结合的良性循环”。[17]农牧结合本质上是把畜牧业和种植业置放在同等地位,并列成为“主业”,将“植物生产—动物生产—生态环境”紧密地连在一起,不仅注重对自然、社会和技术资源的利用,以及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而且通过农牧结合,利用“种—养”模式将粪便等“废弃物”有机结合到培肥改土的体系中,提高了土壤的肥力。这样,农业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资源都能得到综合利用,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促进、共生或相间无害的良性循环系统。[18]
二、相互渗透的饮食民俗
“饮食民俗是物质生活民俗内容之一,它主要指人们传统的饮食行为和习惯。具体包括饮食品种、饮食方式、饮食特性、饮食礼仪、饮食名称以及在加工、制作和食用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及其礼仪常规。”[19]边关古村镇居住的各民族由于生计方式的不同,日常食俗呈现出多样独特的形式。南湾村和丰镇市隆盛庄镇隆盛庄村的蒙古村民的饮食结构以肉食为主,新平堡、落阵营等汉族村落以米、面为主。但饮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借助战争、和亲、通贡和互市等形式,在传播流动过程中与其他邻近民族的食俗相互吸收、融化和调和,演绎出独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相互渗透的饮食文化。
少数民族南迁到山西北部,开始了与汉族漫长的杂居生活,逐渐形成了相近的饮食习惯。泰勒指出:“世界各地文化的一致性,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人的本性的普遍相似性,另一个是生活环境的普遍相似性。”[20]相似的食俗取决于少数民族和汉民族饮食民俗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生活在边关古村镇的蒙古族,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由牧转农,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农作物、蔬菜瓜果,畜养鸡鸭猪羊等家禽与牲畜,大幅度调整了传统的饮食结构,形成了包括肉食和汉族面食、蔬菜、猪肉等食物在内的饮食习俗。与游牧民族邻近居处的汉族,也接受了少数民族的习惯,开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一)“油煮糕、吃猪肉的蒙古族”:汉族影响的蒙古饮食文化 北方游牧民族最初居住在草木茂盛的地方,一直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畜养牛、羊、鹿等动物作为主要食物,形成了食肉习俗。少数民族南迁入汉地之后,他们依旧保持着嗜肉的习俗,日常饮食、节日庆典、祭祀礼仪等各种场合都要有肉食,还创制出蒸、炸、煮、烫等花样繁多的方法,烹饪出手扒肉、炸肉串、涮羊肉、烤全羊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随着蒙汉民族日常生产的密切协作,边关古村镇的少数民族群体开始重视农业发展,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除了肉类食物外,还接受了汉族的饮食习俗,逐渐成为“油煮糕、吃猪肉”的蒙古族。
边关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地汉族人的主食是油糕和莜面。“油煮糕”又称炸糕,是喜庆节日必不可少的传统食物,深受蒙古族村民的欢迎。“煎之油,谓之糕,称上馔。家有事以款宾客,以饷亲友,其但蒸食者曰‘黄糕’,并糠之,曰‘毛糕’。”[21]“油煮糕”用黍子面做成。黍子去皮后俗称“黄米”,然后可磨成黄米面。“油煮糕”做法比较复杂,包括“踩糕”、“素糕”等准备环节,最后要把做好的素糕揪成小剂子,用手略捏出皮,包上豆沙玫瑰馅或鸡蛋韭菜馅,捏成元宝状,之后上油锅炸,即“油煮糕”。炸糕一般是庆祝节日或生日的重要日子食用,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当地人的一日三餐几乎离不开素糕。
“我婆婆那辈来的这儿(新平堡),刚嫁过来吃那(素糕),咬不动,粘牙粘得厉害,也咽不下去,不喜欢吃,但没钱,没有那么多白面、白米,后来家天天吃,也就习惯了,家里都喜欢吃我做的,我这也算入乡随俗了。……甚至有人家家里办事、祭神,都叫我过去包糕,包红豆馅和韭菜鸡蛋馅。”②
在实地访谈中,不论是南湾村还是西马市村,村民说起油糕,顿时喜气洋洋。这种寓意“步步高升”的吉祥食物成为蒙古族日常食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拉近了不同民族间的距离。蒙古族共同体形成以后,主要以牛羊肉为主的蒙民在周围汉族村落的影响下,也开始饲养猪、鸡等动物。猪肉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日常饮食。《蒙古风俗追溯》一书载:“农业地区的蒙古族吃猪肉的日益增多,食用方法与满、汉族相似。近代以来,蒙古族地区养猪现象越来越普遍,猪肉基本己取代羊肉进入了人们的日常饮食”。[22]一到腊月,家家户户都会杀猪,做成扒肉条、肉丸子、烧猪头肉、制皮冻,还学会了腌肉。蒙古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其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猪肉、油糕为主,兼有蔬菜、莜面等,形成了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饮食风俗。
(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汉族人”:蒙族影响的汉族饮食文化 “不同民族的文化相接触,文化的传播一般是相互的、双向进行的,他们有选择地互相采纳对方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23]民俗融合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蒙古族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也是汉族胡化的过程。晋北汉族村落在影响蒙古族饮食习俗的同时,自身的传统饮食也在悄然变化,逐渐形成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边关食俗,《天镇县志》明确记载了明代大同镇守军的饮食情况,“野味榆生肉,盘飧蕨吐芽”。[24]
边地村民餐餐离不开酒和肉,酒肉成为日常生活和节日必不可缺的食物,酒肉习俗主要体现在年节、婚宴等重要场合,成为馈赠招待亲朋好友的必备佳品。解放以前,娶亲当天,早餐烩菜、油糕,中午宴席6个碗,即烧猪肉、清炖肉、浑炖肉、油炸豆腐、丸子、来回菜(茴子白杂以豆腐和肉)。串盘有四荤:鸡蛋、排骨、猪头肉、猪肝。初生婴儿的“洗礼”仪式上,摆宴席,用羊背子、羊后腿肉和炸糕招待客人。
“我们这儿都爱吃肉,中午饭可以不要菜,但必须有肉,最常见的是大烩菜,五花肉、油炸豆腐、土豆等,好吃实惠。每逢结婚生子,办席时,有条件的都得好肉好酒招待客人,什么猪肘子、烧鹅、烧鸡、鸭肉、扒肉条、肥肠,大众实惠的肉必须上,如果肉少了,客人得背后说你不地道。我们家老四结婚时,一桌20个热菜,18个肉菜。”⑥
蒙古人以酒成礼、以酒成事,日常餐饮和各种宴饮中都离不开酒,“家善酿,虽佣食午餐必先以酒”,几乎是家家酿酒,时时嗜饮。[25]“大碗喝酒”的豪气也传染了与之居处邻近的汉族民众。边关古村镇天气寒冷,风沙较大,村民最爱喝用高粱酿制成的“二锅头”(50°的浓香型烈酒),他们把酿好的酒放在皮囊中,“厚者饮数杯即酩酊矣”,能驱散冬日的严寒。[26]酒也出现在各种仪式上。据《天镇县志》记载:“中秋,会饮尽月乃止……冬至后生徒群聚饮博”。[27]解放初,各村村民如果订婚,至少准备两瓶白酒,瓶口塞以新鲜葱白,送往女家。女方收礼,于酒中放一小撮小麦,就此定亲。⑥豪饮还酿出了边关浓烈的酒文化,成为边关古村镇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元素,常以酒令、酒宴、酒礼等形式表达出来。以酒礼为例,当地特别讲究,从迎客到送客,从敬酒者到接受者都要有一套说辞,如果拒绝喝酒,或者宴席结束客人还没喝醉,就认为主人招待不周。
除了酒宴上豪饮之礼,受少数民族热情待客习气地感染,汉民也认同并接受了其豪爽好客的传统。应酬礼节不拘小节,对待宾客,不讲究所谓的揖逊谦让之礼。在宴席上,宾客坐于西北尊位,主人坐于东北,其他人各随宾客和主人两边就座,为客人捧上最有地方特色的酒肉等食物。《北虏风俗》详细记载了边关村民热情好客的习俗:“其在幕中,宾坐于西北隅,主坐于东北隅。宾之从者即列于西北之下,主之从者即列于东北之下,皆趺迦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饮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则酒肉之类……若候至日中,则食虽甚寡,亦必均分而无吝矣。孰意狠如狼、贪如羊者,乃能轸犹饥之念若此乎?”[28]
三、兼容并包的民族信仰
外长城沿线山西境内边关古村镇处于北方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圈的交汇带,不同的民族群体有着不同的民俗信仰。清朝大一统历史格局奠定之后,沿长城带交界空间内不同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似的生存环境和长期的互动最终促成不同民族由物质民俗的借鉴逐渐走向精神领域的认同。“所有的文化行为在本质上就是混杂的,是传播和同化的产物,换句话说,从来不存在什么‘本真类型’或‘纯粹体系’,因为人们总是在交换、改变、加工和组合他们的文化因素。”[29]具体表现在边关古村镇中,汉族信仰体系以其广大的包容性在历史上吸收不同的信仰文化并“修复”自身的信仰体系,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特征,使该地区形成“多元混杂”的宗教格局。“多元混杂”的宗教格局具体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多元信仰内容的共生并存,二是神灵共祀生活观念的普遍存在。
首先是多样化的宗教信仰和谐地生活在边关古村镇的空间体系内。它们各自发挥职能,互不干涉,形成互补。山西外长城沿线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两个角牛王爷,三只眼马王爷,红脸脸关公爷,背锅锅土地爷,肥肥胖胖是佛爷,瘦瘦干干孤和爷,红脸蛋灶神爷,疙瘩帽大仙爷,李世民真王爷,玉带束腰周仓爷,女婿名叫雨师爷,尖嘴嘴雷孤爷,下雨离不了龙王爷,老龙四儿火神爷,镇压鬼城煌爷,审鬼问案阎王爷,二鬼勾魂离不了土地爷。”⑦这支民谣形象地说明了当地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存、无所不包,既有佛教、道教、萨满教、喇嘛教等正教,也有奶奶、狐仙、黄仙等地方俗信。我们所调查的大同北部三个古村镇,从典籍文献记载和民众已知的庙宇共计41座。其中还有一些庙宇(如井神庙、五道庙等)为不完全统计数字。据民众解释,几乎是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五道庙,每口水井都供有井神庙,但在实际调查中,没有人能明确指出庙的具体位置,故影响庙宇的实际统计情况。按照神灵职司和功能来分,边关古村镇的信仰体系主要划分为三种:以孤魂、三星、四女、狐神为主的民间俗神信仰;以玉皇、真武、吕祖、观音为主的佛教和道教信仰;以药王、马王和牛王为主的行业神信仰等。⑧
其次是边关古村镇的民众奉行“神灵共祀”的信仰理念。边关古村镇是多元民族共同聚居、开展生产和生活的场所,在这个共同的空间内,“一种信仰同时由多个民族群体信奉,一个民族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侧重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两个方面交叉形成的结果是民族之间广泛的宗教共享”。[30]也就是说,不同族群的民众根据生活环境的变动不断修正和调试自身的信仰体系,吸纳和接受其他族群的信仰方式,形成了多元互渗的信仰格局,古村镇很多庙宇都是蒙汉人民共同修建的,如城隍庙、财神庙、奶奶庙、真武庙、泰骨庙和马王庙等。具体来说,“神灵共祀”主要体现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某一族群内的信徒转向信奉其他族群的神灵,另一种是某一族群的个体可信奉多个不同信仰体系的神灵。我们可通过田野调查中的两个具体案例来详细解读以上两种情况。
(一)“玉皇爷无所不能”:少数民族对汉族信仰的认同 如今,边关古村镇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他们不仅信奉释迦牟尼、宗喀巴 (喇嘛教)、白石和天神 (萨满教),而且信任阴阳先生与风水 (道教),还崇拜地方保护神 (奶奶、龙王、狐仙等)。在众多的信仰对象中,边关古村镇的少数民族群体尤其崇拜玉皇爷,玉皇阁随村可见。“道者,天帝总统六道,是谓天曹”。[31]“玉皇”是道家对天帝的尊称,是天界至高无上的总管,监管佛道两教以及各路鬼神。新平堡的玉皇阁,亦名镇边楼,位于该村十字大街的交点处,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最初是将领指挥作战的场所,既可登高望远,又可观察指挥,战争平息后,玉皇阁的军事色彩逐渐淡褪,成为保佑民众平安、祈求五谷丰登的空间。[32]《玉皇阁碑》详细记载了玉皇信仰和玉皇阁的设置情况:“迄嘉靖初,市民贸易,夜多寝其下,五鼓半宿,忽闻其上若多人喊应之声,如是者三,乃无由而火。佥异之,而谓神之归诸天也。……护国祚无疆兮,有道昌,虏酋来王。佑百姓永宁兮,五谷登,年期顺成。 碑刻中解释了玉皇阁功能的转移过程,从军事指挥台发展成为纯粹的精神信仰空间,围绕玉皇信仰和玉皇庙,边关少数民族群体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深化了对汉族信仰文化的认同。
在入村访谈中,一位蒙古族村民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个体如何接受玉皇信仰的过程。
“我们刚开始觉得汉族人太迷信,我们什么都不信,但是因为我小孩的事情我开始信了(玉皇爷)。我小孩小学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到医院都说要锯腿,可把我们吓坏了,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到当地的一个顶神的人,都说她身上是玉皇爷。去了后,她啥也没说,就给在黄表上写了点字,让给孩子擦腿,然后当月初一晚上八点多在村里十字路口,就玉皇阁下面烧掉,真可灵了,过了三天,我孩子腿就没事了。后来,我孩子考高中、考大学,我都去求玉皇爷赐护身符,玉皇爷一直保着我们全家平安,有钱。”②
就观念文化的改变来看,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将影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吉祥内容糅合进自己的生活,并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再次传播。个案中的少数民族个体从百无禁忌到“玉皇爷无所不能”,其实折射出了汉族信仰传播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轨迹,即“接触——契机——感染”。1.“接触”: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错杂居的生活状况为信仰的传播提供了碰触和了解的机会,在相互交往中,民众知晓了某种信仰在对方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2.“契机”:当俗民主体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时,通过科学手段也无法解释和处理,和他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人便会为他寻求解难的途径,这为他信奉某种神灵提供了一个契机。3.“感染”:当他的愿望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满足时,他开始惊异于神灵的灵验与伟大,并虔诚地接受这种信仰。之后他不断地向其他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神异事件,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一个传播媒介,在他的影响下,又一部分群众加入到信仰仪式中,其实是进入了新一轮的传播轨迹,使这一民俗信仰不断复现延续。长此以往,这种有规律的、复现式的扩散传播方式无限循环,就促进了信仰民俗的融合,也令不同民族对彼此精神层次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如果说民俗信仰的趋同过程总结出了不同民族信仰逐步趋同的规律,那么,不同民族组织和参与信仰仪式的行为就是在强化和巩固这一共同信仰。最典型的是当地送玉皇回天宫的活动仪式。当地人认为腊月二十是玉皇爷回天宫的日子,是日凌晨一两点开始,新平堡镇附近的村民就陆续来到玉皇阁举行活动,如保平堡、西马市、桦门堡、平远堡和兴和县的一些村民。整个仪式由三到五个顶神⑨的人主持,有时候会请阳高的鼓匠和丰镇的喇嘛教僧人来做法事,还要由本村集资从包头请专业的晋剧团,演出文戏、武戏和现代戏酬神,如《司马卯夜断三国》、《薛刚打朝》、《钟馗嫁妹》《呼延庆打擂》、《三姐下凡》等。⑩六点到八点之间,顶神的人会提前请本村手巧利索的妇女来做供品和素席,主要有菜馅油糕、凉菜和素羊杂。贡菜做好后,顶神的人“净手”,开始在玉皇阁上供。首先上三柱高香、三根香烟,并点燃黄裱,意喻告诉玉皇爷大家来给您送行。然后开始摆放贡菜、水果和糕点等,贡菜要放在专用的小碗中,碗旁要放新的红色筷子。上供结束后,民众按照来的先后顺序上香、磕头、许愿、请符。从八点开始,顶神的人开始请玉皇爷下界,附于自己身上,给信徒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这一过程持续到十二点,顶神的人组织人员在玉皇阁正下方的空地上放鞭炮,并点燃事先垒砌的一圈旺火,信众开始顺时针绕着旺火转九圈,心中不断默念“阿弥陀佛”,并开始许自己的心愿。至此,玉皇爷用完饭回天宫,活动基本结束。之后,民众回到顶神的人家中,吃素斋。⑪在腊月二十这一天,少数民族和当地汉人都严格遵循一些禁忌,为体现“上天有好生之德”,当地的蒙族禁止屠宰,不杀生,吃素;在家中和院中不悬挂内衣或堆积粪便等秽物。
拜祭玉皇的仪式仅有一天,却蕴含着深刻的内容。我们不能把玉皇信仰归属汉族或其他民族,因为通过玉皇信仰,不同民族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沟通和链接,正是玉皇信仰为不同族群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从仪式参与者的组成来看,蒙汉满等不同民族成员共同参与。从仪式的崇拜内容来看,内蒙丰镇请来的喇嘛僧人是黄教,村民祭拜的全能神玉皇爷是道教,民众口中不断念诵的“阿弥陀佛”是佛教用语,顶神的人本身可以视为是地方俗信的代言人。在玉皇爷回天宫的送行活动中,各项仪式“是对宗教观点的展示、形象化和实现。就是说,它不仅是他们信仰内容的模型,而且是为对信仰内容的信仰建立的模型。在这些模型的戏剧中,人们在塑造他们的信仰时,也就获得了他们的信仰。”[34]受汉族宗教信仰世俗化色彩的影响,少数民族更加重视现世生活,他们很少去内蒙古地区的“圣庙”,反而频繁出入汉族的佛道寺院和各种俗神庙宇。他们家中供奉的神位也是多教混合,有宗喀巴佛像和佛道仙君等,甚至有的家庭直接供奉汉族的一些传统民间信仰,如菩萨、佛祖、财神和保家神等。汉族在本民族多元信仰扩散的同时,也吸纳少数民族的信仰内容,庙会中经常会出现“汉人演剧,喇嘛跳神。娱乐而外,并为皮、毛、盐、碱、布、茶、牲畜之市集”的现象。[35]
(二)“各路神仙,为我所用”:多元民族信仰的和谐展示 民众对神灵的祈求几乎涵盖了人生的各种需要,从出生的祝福到死亡的安慰,从具体的职业护佑到宽泛的家国平安,从祈求战事顺利到希望战马健康,从天空到大地,从表彰榜样到高中科举,从心灵的镇静到物质的丰足,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36]各种需要为泛神崇拜提供了发展的温床。边关古村镇的村民既尊重佛道偶像,又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虔诚供奉狐仙、黄仙等地方俗神,此外,还专门立祠拜祭他们所尊敬的民族英雄,如三英祠中供奉了明朝驻守大同镇的郭琥、周尚文、麻禄三位大将,以此纪念他们的英烈事迹,从而激励后世子孙。
在边关古村镇的调查中,我们看到无论庙宇大小,都会供奉有香火和供品。一些简陋的小庙,甚至是几块砖搭起的小阁都享受人间香火。有的人家牲畜棚顶覆盖两块砖,就搭建出一个简易的信仰空间,旁边摆放供品和香烛,供奉“马王爷”,寓意保护家畜平安。有的家庭在厨房的锅灶旁虽然供奉灶王,但是没有实体的神像,只摆放一碗小米,里面插上三柱香,每月初一、十五上香、更换供品。由此可见,行走在晋北古村镇的内部场域,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供奉神灵,每一类事物都可能成为供奉对象。这样才能发挥各路神灵的神奇功能,从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当地民众认为神灵存在功能上的分工:观音法力无边,但对家禽家畜的瘟疫束手无策;马王爷保佑六畜兴旺,却管不到五谷丰登;奶奶添丁赐福,却帮不了升官发财。[37]因此,只有将各种神仙都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使“各路神仙,为我所用”,才能获得全方位的保护,尽可能趋吉避祸。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关于信仰多元化的说法。
“每位神职能不同,谁家求孩子去找‘奶奶’,谁家(孩子)想考大学去拜文殊(菩萨),谁家想当官发财去求‘老爷’,最大的神就是佛祖了,一般别人家主位都是佛祖。我家主要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所以我家佛堂主位是文殊,然后等挣钱吧,所以供了财神,不能和菩萨、佛祖一排,财神爷要坐西向东,肚里装18元钱和9根香,都是吉利的数字。在厨房供了灶王爷,都是初一、十五清晨上香、上供、敬黄裱。”⑫
边关古村镇还存在“见庙就进,见神就拜”的现象。落阵营村的一个整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非常虔诚,但她却在去佛观寺庙上香的途中,顺道拐进老爷庙、奶奶庙等道家神庙供奉香烛;还有村民家中的神龛上,主位为佛像,左右依次为财神和菩萨,还会有保家神的牌位,这种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通过对村民的访谈,我们得到了以下信息:
“你只要进了庙,就得见神就拜,每位神都分工不同,你不可能只求一位神,肯定是想让你家什么都好,身体好、工作好、孩子好,想要的太多了,所以,各路神仙都得拜,都不能得罪。……像我之前家中只供了佛祖,后来家里乱的不行,就是出了一些邪乎的事情,家里人老生病,孩子也不愿意学习,老人也去世了,就找人问了问,说是‘保家神’嫌我没供他,没有办法,人就是神管着了,只能都供起来。我家供的算少了,你去其他人家看看,还有供十几位神的呢!”⑬
访谈内容反映出边关古村镇“见庙就进,见神就拜”信仰现象的普遍,民众通过敬神和请神满足自身的三种目的:一是纯娱乐性的活动,如庙会、集会为天地神灵助兴等;二是庆祝新房落成、搬家动土、祈求五畜兴旺、孩子满月、老人祝寿、五谷丰登等生活事件;三是治疗久病不愈的病人和各种奇异怪事。民间信仰之所以如此普遍,源于民众期望生活圆满的心理活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很多常年吃斋念佛的信众却不得善终,他们开始意识到信奉单一神的不全面性:如果我只信奉一种神灵,会不会惹怒其他法力更高的神灵,遭到冷落和报复?如果我只信奉一种神灵,当我遇到该神无法解决的困难,其他神灵能否为我提供保护?答案是模糊的。而且对信徒来说,让他们完全放弃原来的信仰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是“神灵共祀”,寻求多重保护,这才是最佳措施。毕竟,“相对于神通广大的神灵佛祖,普通百姓实在太脆弱了,当他惹不起这些神灵的时候,只有把他们全供起来”。[38]多神崇拜的信仰现象就越来越普遍,并且给处于现实困境中的俗民群体带来了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寄托。于是百姓的各种行为都要求神问路,寻求庇佑,例如日常乔迁要和保家神打招呼,新房落成要告知土地爷,孩子满月要拜奶奶等。
由此可推断,边关古村镇信仰民俗是多种多样的,民众根本不去区分某种神灵到底归属何种宗教,也不去追求神圣的情感体验和精神的高尚升华,只是凭借自己的需要对神有所求,想求什么,就去拜和该内容相关的神灵。[39]在他们看来,神灵的所属系统和法力等级都不重要,关键是它们是否能满足民众的各种生活需求,从而达到祈福攘灾的目的。在落阵营村,家中老人过世,一般要同时请和尚和道士做法事,以超度死者亡灵。因此,村中常会见到道士、僧侣同时设道场对垒的现象。村民对佛教和道教同台诵经的现象,不会感到不伦不类,相反,他们会赞同这家子孙的孝顺,这也体现出一些民众对佛道等多重宗教信仰混搭情状的认同,不同民族的信仰文化基本上形成了兼容并包的特征。
四、结论
作为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或发生征战的过渡地区,以大同得胜堡、落阵营和新平堡为代表的外长城沿线山西境内边关古村镇,是在漫长历史岁月中不同民族交错杂剧,共同生活的重要区域。不同民族在此展开直接、充分和全面的族际互动,促进了彼此相互交往的频率,如此一来,民族间的共同性日益增多,差别性逐渐缩小,相似相融的民俗因子就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边关古村镇民族民俗的融合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单向到双向;由单一到全面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所涵盖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优势互补的生产民俗、相互渗透的饮食民俗和兼容并包的信仰民俗三个方面。本区域内部民族民俗的融合并非只是单纯的民俗事项的交融,更是不同民族之间情感的交流与价值观的互动,它不仅包括一些相对容易接受的民俗事象,诸如衣食住行等物质民俗、神话传说等口传文化,也涵盖了那些无形的观念性的民俗,如价值观、记忆、情感、主张和态度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产生了农耕与游牧交汇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核心文化价值,从而形成“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亲缘关系。
注释:
①被调查人:赵天宝,男,满族,1963年生,新平镇村民。访谈人:张鑫、卫才华、段友文。访谈时间:2014年1月28日中午。访谈地点:大同市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口。
②被调查人:聂爱枝,女,蒙古族,1952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南湾村村民。访谈人:张鑫、王慧、段友文、卫才华、杨晶。访谈时间:2013年8月3日下午。访谈地点:新平堡镇西马市村口。
③“大”是当地对父亲的称呼。被调查人:刘福,蒙古族,1940年生,得胜堡村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王慧。访谈时间:2012年8月6日。访谈地点:得胜堡村内南门边的空地。
④被调查人:许振清,男,汉族,1952年生,新平镇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王慧、卫才华、杨晶。访谈时间:2013年8月8日上午。访谈地点:新平堡镇628号院。
⑤被调查人:庞世田,男,汉族,1937年生,新平镇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王慧、卫才华、杨晶。访谈时间:2013年8月5日上午。访谈地点:新平堡镇023号院。
⑥被调查人:孙富村,男,蒙古族,1967年生,天镇县红土沟村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王慧、卫才华、杨晶。访谈时间:2013年8月8日下午。访谈地点:天镇县红土沟村178号院。
⑦爷字歌。大同民间歌谣集成[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孤和”地方俗语,是孤魂爷,主要职能是收管孤魂野鬼。
⑧根据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以及刘媛、陆阳。塞北、江南古村落对比研究——以新平堡和礼社为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76-78、《天镇县村镇简志》、光绪版《天镇县志》、1997版《天镇县志》、《大同县志》等资料整理村镇中重要的神灵体系。本文参考美国学者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27、351-358)中的分类标准,按照神灵的功能作用来划分。
⑨顶神,晋北古村镇非常独特的现象,据百姓介绍,这类人身上都附着一位或几位神仙,他们通过与神灵沟通,替民众解决各种难题,如升官发财、升学就业。我们通过观察村中一位顶神人的一系列行为,总结归纳出送玉皇回天宫的仪式。被调查人:董仙英,女,汉族,1968年生,天镇县新平堡村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卫才华、王慧。访谈时间:2014年1月20日中午。访谈地点:新平堡镇玉皇阁下。
⑩并不只是打鼓的,吹拉弹唱,当地人称为鼓匠。郭长岐、白凤兰:《移载塞外的晋剧之花——包头市晋剧团简史》,包头市文艺志史资料汇编(第一辑),1985年,第96、103页。
⑪被调查人:赵天宝,男,满族,1963年生,天镇县新平镇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卫才华、王慧。访谈时间:2014年1月28日中午。访谈地点:大同市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口。
⑫被调查人:吕金贵,1940年生,女,汉族,大同市大同县落阵营村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卫才华、王慧。访谈时间:2014年2月16日。访谈地点:落阵营村村口。
⑬被调查人:赵三,女,汉族,1946年生,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乡得胜堡村村民。访谈人:段友文、张鑫、王慧。访谈时间:2012年8月5日。访谈地点:得胜堡村小卖部前。
[1](美)戈 登著,马 戎译.在美国的同化:理论与现实[A].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美)凯西·F.奥特拜因(KeithF.Otterbein)著,章智源,张郭安译.比较文化分析——文化人类学概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张紫晨.中外民俗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4]欧 军.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比较[J].文科教学,1994(01):95.
[5]王 勇.西部生态治理及其本土性制度资源——立足甘青特有民族生态文化的初步探索[J].西北民族研究,2002(12):99.
[6]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7](清)徐 珂.清稗类抄(农商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蒙古地志[M].国书刊行会,昭和五十一年,第67-68页.
[9]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卷1·田赋,蒙古史文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1984.
[10]张 波.西北农牧史[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1]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12]马 克.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3](明)黄 瑜.双槐岁钞·卷第五·马政治,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
[14](元)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11)[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15](明)陆 容.菽园杂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闫萨日娜.一个蒙汉杂居村落的民俗融合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7]潘乃谷,马 戎.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8]武继承.试论农牧结合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大自然探索,1999(02):69.
[19]林继富.饮食民俗谫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24.
[20]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1]清光绪十六年(1890),洪如霖修,杨笃撰:天镇县志,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245页.
[22]呼和宝音.蒙古风俗追溯[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8.
[23]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4]洪如霖修,杨 笃撰.天镇县志,清光绪十六年(1890),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107页.
[25]洪如霖修,杨 笃撰.天镇县志,清光绪十六年(1890),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245页.
[26]晓 克.土默特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
[27]洪如霖修,杨笃撰.天镇县志,清光绪十六年(1890),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245页.
[28](明萧大亨.北虏风俗,引自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29](英)乔安娜·奥弗琳(Joanna.Flynn)等著,张亚辉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0]马 戎,周 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1]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2]天镇文史资料[J].1987(02):30.
[33]洪如霖修,杨 笃撰.天镇县志,成文出版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
[3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5](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著,刘明汉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 2 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36]刘 媛,陆 阳.塞北、江南古村落对比研究——以新平堡和礼社为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37]钟伯清.多元与和谐: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一个村落民间信仰的实证调查[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9):30-32.
[38]钟伯清.多元与和谐: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68.
[39]王守恩.论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J].世界宗教研究,2009(0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