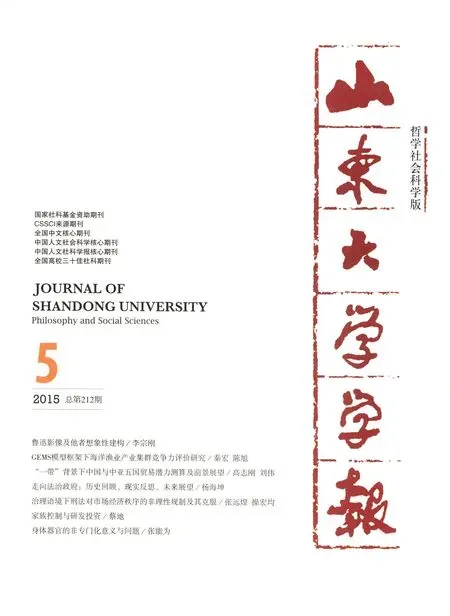论依法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
2015-04-03柳砚涛刘海霞
柳砚涛 刘海霞
论依法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
柳砚涛 刘海霞
依法行政之“法”不限于行政法,也包括其他部门法,这主要受制于各部门法在原则、理念等“求同”领域的相同性和相通性,以及行政事务的广泛性、法源共享、行政案件的复杂性等因素。其他部门法作为行政依据必须符合行政法无特别规定、蕴含一般法理、不为行政事务的本质或行政法理所排斥等基本条件。其在依法行政中的功能主要包括依据、依照、适用、参照、法理上的参考等。行政法应加紧构建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共享、共用、共建、互补、存异等关系形式。
依法行政;跨部门性;法依据;适用条件;关联机制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从审判依据角度明确了依法行政之“法”的规范载体,但并没有限定规范的“部门性”,由此产生下述疑问:依法行政之“法”是否具有跨部门性?在何种情形和条件下可以适用其他部门法?各该部门法在处理行政事务时的功能是依据、参照、引用抑或其他?
一、依法行政之“法”跨部门性的理由
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但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并非限于行政法,如外交行政机关处理外交或涉外行政事务依据的主要是国际法,亦即“国际法之规则采用为行政法之一部”①古德诺:《比较行政法》,白作霖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法部门划分只是法律和法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由学者提出并论证的教义学上的类型化活动,正如“公私法的划分只对法律救济途径的认定有意义,只是对法律制度所作的法律教义学的划分。”②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0页。行政的源起远早于这种法的部门化现象,“以”法行政的理念与实践也是法的部门化之前的事。同时,法在生成之初是不分部门的,这一点在英美法系显现得更加突出,“是以英美除宪法及普通法律之外,无特称为行政法者。”③古德诺:《比较行政法》,“日本译文凡例”第1页。我国历史上曾有“诸法合体”、“行刑不分”的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官员”和“官府”包揽行政、司法、外交等多种事务,自然要“诸法并用”。
但是,前述“史实”并不能诠释当下法现象的正当性,当下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需要从法与行政的理论本身去寻找理由:
1.各部门法在原则、理念上的相同性和相通性。任何法部门都尊崇人权、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最基本的法律理念,这些理念处于整个法域的顶端,是部门法得以生成与发展的理论“根基”,这也决定了各部门法在基本原则、规范、制度上的相同性和相通性,为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提供了理论前提。
即使在公私法分立的情况下这一法现象也难能避免,“由于公法和私法具有共通性,私法规范(特别是民法)在某些条件下可以适用于公法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①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5页。在同为公法或者私法的各部门法之间更是如此,“行政法和刑法固然不同,但存在许多交叉情况”②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第215页。,较具代表性的是,不少国家的检察机关属于行政机关,但其活动却以刑法为根据。
2.行政事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行政之法跨部门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行政的内涵与外延。行政的内涵与外延一直处于演进过程当中,以至于“不能从现代的‘行政’术语理解其以前的含义”③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第59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的法依据。如在不少大陆法系国家,“刑政”是“行政作用”的组成部分,只是“原则上属于司法范围”而已。④范扬:《行政法总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7页。二是行政事务的性质,如目前我国有关行政机关司职行政裁决、调解等准司法职能,主要依据民商事法律,这也合乎管理的理性和自然法则,管理必须贴近所管之事的自然属性,管人需适度顺应人性,管物要照顾物理,管事则需顺乎事理。三是行政关系的复杂性,即使在公法的核心领域,法律关系也常常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公法主体与一个私法主体之间点对点的调整关系,而被看作由大量相关的规范、信息、债务及均衡措施形成的综合关系。⑤弗里德赫耳穆·胡芬:《行政诉讼法》(第5版),莫光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6页。随着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复杂性和立法细密度的不断提升,行民、行刑交叉案件越来越多,加之经济、效率、便捷等理念的不断拓展,附带审理、一并处理以及程序合并等情形也越来越普遍,一个行政案件的处理往往要用到多个部门法的原则、原理、规范、制度等,这同时也促成了部门法之间共同治理、分工衔接的和谐关系。
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始终与行政权的扩张性和行政事务的广泛性、复杂性相伴随。美国自上世纪初开始,裁判私人之间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的权力授予了个别行政机关,认为“现在行政机关应当具有审理所有类型的民事案件的裁判权”,纽约州《机动车辆和交通法》甚至设立了交通行政法院,接过了由刑事法院行使的交通犯罪审判权。⑥参见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60 62页。德国也曾出现过“行政司法”膨胀的现象,“裁判可能是所有行政活动的一半”,以至于“凡不是民事法院的活动,就是行政。”⑦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页。在法国,“行政机构根据公共事业的需要,可实施一系列措施以行使某些司法权力及某些权利”,进而使行政机构拥有了一定的司法权。⑧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册),龚觅等译,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72页。
3.法源共享,立法节约。法源共享是世界各国处理部门法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日本民法中包含了“法的一般原理”或“法的共同规定”,从本质上说后者又包含了行政法。⑨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健民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67页。法国行政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遇有无成文法规定的情况,便适用一般法律原则,而一般法律原则中不少是来自民法规定。行政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很多概念和制度受到民法学的启发或者直接于移植于民法。⑩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页。规范与制度缺位往往会给学科发展带来掣肘,理论移植与借鉴便成为基础薄弱学科发展中的“常事”。
各国无一例外地将“特别法优先”和“法源共享”作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法律与经济良性结合的必然要求。其中,特别法优先的原则“让立法者省下为特殊情形而明文排除一般法的功夫。这个原则所涉及的并不是逻辑上的要求,而是涉及立法经济(Gesetzesökonomie)以及语言经济(Sprachökonomie)的要求。”⑪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页。各部门法之间具有共性的领域,只要一个部门法率先作出规定,其他部门法就可以直接适用,避免重复立法以及立法领域的物质、时间和制度浪费,真正实现各法域间“求同存异”。
4.行政立法的调控范围。随着行政立法功能与范围的不断演进,行政机关不仅有权制定“行政性”的规范,而且可以制定民事、经济、劳动甚至刑事等其他部门法规范。德国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授权制定某些刑事法规(Penal Ordinances),针对构成犯罪行为的事实和要件作出具体规定。①参见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页。在我国,尽管行政性法规不能直接规定犯罪,但“实际上具有间接地规定犯罪的功能,是认定犯罪的规范依据。”②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的逻辑展开》,《法治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3期。以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为例,其中作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刑法第96条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解释为“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在这里,行政立法实质上具有了“涉罪”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产出刑事法。
5.行政机关的身份与名义。权力的行使者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唯一身份,随着行政范围的演进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行政机关也会以非权力名义进行活动,“当行政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行为时,才可以适用民法”,此类情况发生在国家“以私人参与经济的形式出现”之时。③参见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第121页。同样,当行政机关处于合同一方当事人时,尽管不同程度地享有指挥权、中止与解除合同权、制裁权,但除此之外主要“受私法调整”④Pascal Martin,comments on the decision of the frenchcour de cassation,first civil division of december 17,1996,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administrative contracts,P.P.L.R.166 169(1997).,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法院对此都予以确认。
同时,行政机关也会依法“司职”某些刑事职能,如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条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
上述各种情形会引致两个法律效果:一是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而且必须依据刑法、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进行活动;二是必要时,行政机关可以制定涉及民商事、刑事等方面的立法,二者共同促成了行政之法的跨部门性。
二、其他部门法作为依法行政之“法”的条件
并非任何时期的所有部门法均可以为行政所用,能为行政所用的部门法,也并非其所有规范、原则、理念等均可用,而是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1.其他部门法规定蕴含一般法理。法有部门之分,但有共性,包括相同性和相通性,前者主要存在于原则、规范、制度等“硬法”层面,如法的位阶、送达程序等;后者主要存在于原理、理念、方法等“软法”层面,如法的安定性、违法成本应大于收益等。如此一来,起步较早、理论与制度相对完善的部门法就会在法的共性领域先行一步,而这恰恰为理论与制度相对落后的法部门提供了法理基础甚至是规范与制度的直接“套用”。
以行政法对民法的借鉴为例。民法是一般法理的源头,约翰·亨利·梅利曼甚至认为:“法律的一般理论和原则主要产生于私法”,“适用于整个法律制度的一般法学理论是由民法学家发展起来的”,“民法是大陆法系法学家的思想发源地”⑤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73、79页。。私法生成基本法理的传统和理念在普通法系更是毋庸言表,强大的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经济等加重了私法在英美法体系中的分量,就连行政法也一度埋没在私法理念、原则、规范、制度体系中,诚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然则英美之所以不认行政法者,非因英美无行政法,宁可谓由于英美学者法律不分类,诚有如世人所知之缺点也。”⑥古德诺:《比较行政法》,第4页。行政法上的诚信理念、委托、合同、指导等基本法理无不源于民法或与民法密切关联,公权力活动适用私法毋宁是“法理上的回归”。在法国,“私法对行政的适用性直到某个时期(1920年)曾是一种例外。但今天,私法的比重大大增加,而且成为一种越来越经常的考虑。”有学者甚至认为,对诸如工商业等某些公共部门而言,“私法的适用是一般原则,而公法的适用只是例外。”①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第十九版),廖坤明、周洁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页,第18页。在我国,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弱权力、弱强制行政及参与行政等理念,更加密切了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依法行政中的私法适用、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行政合同的合意性、行政指导的民法解读等命题引起热议;在实务中,人民法院审理民行交叉案件、行政合同案件、行政指导案件时更多的是依据民法。随着弱权、还权、放权以及权力权利化倾向的不断拓展②参见柳砚涛、刘宏渭:《行政权力权利化研究》,《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公私法之间资源共享、求同存异会更加明显,私法对行政的适用性也越来越普遍。
2.行政法无特别规定,需要从其他部门法获取依据。行政法无特别规定是其他部门法适用于行政的前提。日本有关于法技术性约束的原理“只要行政法规中没有特别规定,就适用于行政上的法律关系。”③盐野宏:《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8页。对于符合一般法理的问题,行政法无须另行创设理论、规范与制度,这里的适用次序为:行政法有特别规定的,从特别规定,即使该规定的效力位阶低于其他部门法规定;行政法没有特别规定,但确需有别于其他法部门的,从行政法理;行政法不需要有特别规定的,从其他部门法规定,其他部门法没有规定的,从一般法理或其他部门法法理。
鉴于立法程序的繁琐性、时间的冗长性和利益博弈的困难程度,一种新兴行政关系和行政事务产生之后,法律往往不能及时调整到位,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相关部门法的法理和规定加以解释和临时规制,如行政合同对合同法的“借用”、行政指导在法理上对民法中邀约—承诺理论的借鉴、行政行为成立对民法上意思表示规则的采纳、行政处罚适用规则中对刑法上从轻减轻等规则涵义的“套用”等。
3.不为行政事务的本质或行政法理所排斥。行政法适用其他部门法的前提是所用规范与制度不为行政事务或行政法理所排斥,正是因为各部门法之间存在“同理”和“不同理”两个领域,所以制度设计上一般将其他部门法在行政依据层面的功能表述为:“同理”部分为“依据”、“依照”或“参照”,如送达法律文书、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等;“不同理”部分则排斥适用,如公权利行使受限、行政争议一般不适用调解等。在法国,公产所有权与民法上的所有权“不同理”,因而“公所有权在公共使用所必要的范围内排除私法的适用”④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306页。。在公法学者莱昂·狄骥看来,各部门法乃至公法与私法之间应尽可能“求同”,而将“存异”限缩到最小范围:“有理由作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但不应该赋予这种区分本身并不包含的意义”⑤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0页。。该观点基本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公法与私法以及各部门法之间以“求同”为主旋律的关系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97条规定,行政审判“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如果据此得出凡是《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有关规定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这里的“有关”并非“参照”的充分必要条件,“有关规定”在性质和法理上不为行政法理所排斥才是关键因素。例如,行政诉讼将相对人争讼期间设定为“起诉期限”或“起诉期间”而不是“诉讼时效”,因而与诉讼时效相匹配的时效中断等情形不应适用于行政诉讼。正如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崔某浩与射阳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工商行政确认上诉一案中所做的认定,《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与工伤认定的申请期限属于“两种法律、法规性质不同,调整的对象不同,适用的范围不同”⑥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行终字第0026号行政判决书。,因而不能相互替代和补充。
三、其他部门法在依法行政中的功能定位
即使其他部门法在行政依据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有“依据”、“参照”、“引用”、“援引”等不同功能区分。
1.依照、依据、根据。行政机关依据其他部门法行政在我国已有零星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0条和《行政强制法》第38条均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法律文书。有的高级法院在内部审判规则中规定:“行政机关针对民事权益纠纷居间裁决引发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除了根据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根据《民法通则》和有关民事法律政策进行合法性审查。”①参见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事实上,《行政诉讼法》第52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的规定,实质上就是为行政诉讼依据其他部门法预留空间,这也同时明确了行政立法、执法、司法等一切行政法活动均可以有条件地依据其他部门法。
2.适用。“适用”是“依照”的延续和外在形式要求,按照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第63条关于“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某些要式行政行为,法律不仅要求有法律依据,而且必须将该法律条文写到相关法律文书当中,如《行政处罚法》第39条要求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机关适用其他部门法规范在域外已有长期的制度实践。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过去的十年,民法的原则和规则广泛地适用于行政法当中”,与此相呼应,“一些权威而专业的行政法庭应该学会解释和应用民法规则”,公共机构“同样受制于民法”,尤其是在其“身份、财产、与其他机构的关系领域”,而且,某些行政措施如果违反民法规范将导致无效。②Denis Lemieux,the role of the civil code of québec in administrative law,18,Can.J.Admin.L.&Prac.143(2005).
行政适用其他部门法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隐形”适用,此种适用并不必须将其他部门法的规范、制度、法理等现于法律文书当中,如对民法中法人概念的适用、刑法中从轻规则内涵的适用等,此种适用一般表现为行政、司法者的主观心理活动。二是“显性”适用,即将被适用的其他部门法条文、规则、理念等现于法律文书当中。一般而言,在要式行政行为、涉及定性处理内容、作为裁判依据、解答法律依据质疑等情形下,必须在文书中列举被适用的其他部门法依据,以实现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全面性和说理性。当下司法实践中,对其他部门法规定的“显性”适用在文字表述上一般称作“参照”,这里的“参照”实质上就是对有关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得出肯定结论后的直接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将《若干解释》第97条规定中的“参照”改为“适用”就印证了这一观点。但是,鉴于该条“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中“等”字的存在,导致将“参照”改为“适用”受到质疑:凡是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都能适用民事诉讼法么?所涉问题难道绝对不会与民事诉讼产生法理上的排斥性么?由于行政机关作为恒定一方当事人,所以行政诉讼必然有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地方,如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调解与和解中的公益考量等。据此,笔者认为应当具体细分“参照”与“适用”的不同情形。
3.参照。200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内部材料《〈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之释义》)中对“参照”做了如下解释:“参照不是简单的参考并依照,而是参考之后决定是否应当遵照办理”,“参照并不意味着法院在适用的规章问题上可以任意裁量。人民法院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必须适用。”③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内部材料),2000年,第132页。据此,“参照”寓意参考、审查决定是否适用,且对合法有效的必须适用。
当下需要拓展“参照”其他部门法的范围,以弥补行政法的两个不足:一是行政法作为学科起步晚,理论基础薄弱,许多理论必须借用或“参照”其他部门法学科。二是受前项制约,行政法的若干规范、制度等缺位,难以应对行政实践的需要。
事实上,我国目前审判实践中已有行政参照其他部门法规定的情形。例如,在前程无忧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因商标异议复审行政上诉一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①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终字第1664号行政判决书。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则直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判断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实际上,类似于数额、规格、标准、定性、构成要件等规范的跨部门法参照适用,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并非少数,这也是弥补法部门间法源失衡的有效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通过司法解释“个案”来解决跨部门法参照的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法律的跨部门参照适用是整个法律适用领域的基本法律方法,理应由《立法法》等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作出规定;二是当下这种“个案”解决办法有悖于法律经济原则,随着各部门法之间在原理、原则、理念等方面“共性”和“同理”的不断拓展,法律的跨部门参照适用会越来越多,将导致法解释机关“应接不暇”;三是这种由司法解释“个案”解决的办法会造成法律适用标准上的不一致,因为同样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享有此类解释权,而这些解释很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4.法理上的参考。没有法理便没有法的表达与制定,更没有法的理解与适用,法理是法的灵魂,没有法理便没有法。这一点在依法行政层面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法理对于行政的永恒参考价值,在法治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在德国,对行政实践有直接适用功能的、与“可法典化”的“特别行政法”相对应的是“普通行政法”,其“显著特征是没有法典化,必须从浩若烟海的法律著作、司法判决和行政惯例中去寻找。”②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第6页。为此,公务员必须既是行政实务能手又是法学理论专家,“不仅要求忠实于规则,还要求忠实于作为这些规则之前提的公平和正义理论。”③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37页。其任务是将法律运用于行政事件并作出行政决定,这一“关联”和“嫁接”的过程离不开法理。
我国目前对“依法理行政”已达成共识,且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例如,在岳阳市蓝天冶金建材有限公司诉岳阳市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补偿案中,岳阳楼区人民法院认定,尽管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之前没有撤回许可应予补偿的规定,但“依照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合法财产权的一般法理”,判决被告对撤回许可过程中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给予相应补偿。④参见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3)楼行初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
事实上,当应对某一行政事件的行政法的“硬法”、“软法”、法理等一切“依据”缺位时,其他部门法的法理就会成为行政依据的“源泉”,这在行政法理论相对落后的我国是经常发生的和必要的,如关于行政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认定标准,执法机关不得不借鉴或直接适用刑法上犯罪构成理论来处置具体行政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采用基本法理支持己方主张的情形原告多于被告。究其缘由:一是当下行政执法仍以“条文法”为主要依据,被告行政机关没有寻求法理依据的权力、条件和习惯;二是某些立法确实存在有悖法理、常理等情形,尤其是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原告惯用基本法理来质疑其合法性;三是原告在质疑被诉行为合法性的过程中,苦于找不到其违反的法律条文,进而引用基本法理作为判断依据。我们希望更多地看到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依法理”行政或司法,这应当是强化法律执行和适用“理性”的应然路径。
5.司法解释作为依法行政之“法”。司法解释作为行政法的法源,并为行政设定规则,必须面对两个拷问:一是司法解释并非作为法的本质的“人民意志”,尤其是超出“适用性”范围的解释,充其量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司法意志”,在缺少针对司法解释“居外”监督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如何获得约束行政的正当性?前提是,正如莱昂·狄骥在评价“法国共和历三年宪法”时所宣称的,“一部制定法就是大多数公民或者公民代表的共同意志”①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9页。,行政的本质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而不是其他任何非民意的执行。二是如果司法解释能约束诉讼程序内的行政机关,倒也合乎“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法则,但司法解释约束诉讼程序之外的行政机关,意味着司法可以为行政“定规立制”,有悖于当下政治体制。
如果是在“规定权”范围内,司法解释完全可以阐释为法院囿于法律范围内所理解的人民意志,行政机关执行这种“间接”的人民意志,尚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如果是在“设定权”或“创设权”范围内,司法解释已成纯粹的法院意志,行政机关执行此种“非民意”的正当性值得质疑。尤其是,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根本没有经过类似于立法程序的民意采集、选择和集中程序,其“人民性”自然无处寻觅。更有甚者,在“法官造法”尚无足够制度依据的我国,近年来“法院改法”的现象层出不穷,仔细浏览一下相关司法解释,类似于创设诉讼类型、审判程序等“法外”创制性司法文件屡见不鲜。
据上,司法解释如属于适用性的“规定”,当属行政法的法源和有效解释,应当作为依法行政之“法”;如属于创设性的“设定”,尽管理论上屡遭质疑和抨击,但实践中却一直当然有效,并约束行政机关。这也迎合了《立法法》第87条所秉持的理论逻辑,该条关于“由有权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言外之意必然是,在改变或者撤销之前,该条所列的“不法立法”情形均是有效的。尽管有《立法法》第87条的制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申明了法院的规范选择适用权,其中对行政解释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态度是:“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②法[2004]96号。这一规定所揭示出来的法理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也可以以同样逻辑对待司法解释,即对司法解释经审查、有选择地参照适用?
为确保行政机关始终执行人民意志和法律解释准确表达人民意志,对司法解释区别对待是必要的,尤其是面对下述两种情形:一是立法解释萎缩、司法解释膨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很少作出立法解释,法律大都是在审判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二是司法解释确实在法律发展、权利保障、秩序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制度贡献。但不容否认,司法解释的功能越来越倾向于创制性的“设定”而不是适用性的“规定”,经常“用司法解释方法矫正‘制定法’中的错误”③罗斯特·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司法解释以“矫正”、补充等方式进行的法外“制度供给”颇值得反思。
6.《若干解释》第62条中“援引”、“引用”的涵义及质疑。《若干解释》第6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若干解释之释义》将前一句话解释为:“既然司法解释也是一种法的渊源,那么自然也可以成为行政审判的法律依据,本《解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将司法解释规定为应当引用的裁判依据。”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内部材料),第130页。法释[2009]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5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概言之,行政审判中应当适用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行政审判的依据。《若干解释之释义》将第二句话解释为:“规章属于法的渊源,……不但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以合法有效的规章作依据,而且法院在行政审判的过程中同样要作为裁判的依据。……发布规范性文件即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是宪法赋予行政机关的一项职权,而抽象行政行为对于不特定的对象能够反复适用,具有立法的性质,如果该规范性文件是合法有效的,……对法院的行政审判有着同样的拘束力。”①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内部材料),第132 134页。据此,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成为审判依据的前提是“合法有效”。
笔者以为,既然前述文件中提到的“法的渊源”或“具有立法的性质”是司法约束力生成的前提,那么为何司法解释可以直接作为审判依据,而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只有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可以被“引用”?违法的司法解释是否也可以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不需要像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一样,以“合法有效”为依据的实质要件,以参考审查为引用的程序要件?在当下司法解释屡屡具有“创制性”的环境下,在认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可能违法违宪的前提下,该问题值得深思。尤其是,既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直接适用,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为何不能直接适用?同样是法律授权的有效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有所差异。②笔者的观点是以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仍然有效为前提的,即我国仍然存在立法、司法、行政、地方四种法律解释为前提的。有学者认为:“《立法法》虽然没有明确废止81决议,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的原则,且81决议的法律效力本就低于《立法法》,因而81决议事实上已被废止。”同时,《立法法》在法律解释机制上已经向55决议回归,即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参见张立刚:《回归与发展:立法法对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意义》,《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但是,如果不给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直接适用而是参照适用的效力,那么必然会导致下级法院参考、审查并决定是否适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窘境。所以,为使当下司法解释直接适用的制度设计合乎理性,必须加紧设立专门的司法解释审查机制,降低行政审判直接适用违法违宪司法解释的几率。
四、行政法与相关部门法之间合理关联路径的搭建
为使当下其他部门法为行政所用的“星星之火”得以理论升华和制度完善,必须对“跨部门法”行政的将来进路有一个“总体规划”。
1.以宪法和基本法理为基础,进一步确认一般法律原则的普遍适应性。一般法律原则为各部门法所通用已成世界各法治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作为法治国家标志的一般法律原则是有效的法律”③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第200页。,确认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性和法律效力,必须摒弃法律条文主义,转而认同法的理念主义。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不再仅仅是“一个把既定的法律条文安放在一定的案件事实上的机械工具”④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而是变成一个以全面法律知识和良好法律素养为基础的法的精神、理念与理性的领悟者和实践者。这一点对于构建部门法之间的良性关系至关重要:各部门法在宪法、基本法理和一般法律原则的基础上“求同”,最大限度地做到理念、价值、原理、原则、规范、制度等资源“共享”,避免制度浪费;在法理上排斥的领域“存异”,各自构建本部门特色的法律理论、制度与规范体系。为凸显各部门法之间的“同理”和“存异”,当下法理学理论和教科书应设“分论”两篇:“公法基本理论”和“私法基本理论”,以便为“公法”和“私法”的部门法奠定“不同理”的理论基础。
2.法域衔接,“共建”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预防制度漏洞和失衡。法秩序是法部门合力的结果,各部门法必须本着“求同存异、合力治理”的精神搭建相互间新型关系。对行政法部门而言,必须与民法共建社会诚信、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与刑法共建违法犯罪行为预防与矫治体系,如执法与司法机关联席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程序介入制度、情况通报制度等①200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对全局观念、合力打击、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立案监督、联合调查等制度作了规定,不少地方和部门也为行政与司法“共建”关系制定了不少规范,但目前仍然存在制度不全面、强制力不足、部门利益严重等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理论研究不足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法域“共建”关系的构建形成掣肘。,尤其是折射行政法与刑法一体化理念的“行政刑法”、“行政刑罚”的理论与制度体系;与国际法共建诸如海洋维权、海域使用等领域良好的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与经济法共建市场经济秩序等。
3.弘扬法源“互补”关系。法部门之间并非界限森严,在部门交叉领域,部门法之间应该确立法源“互补”关系。例如,物权法就是民法与行政法的交叉地带,“物”主要是个民法概念,而“权”则肯定牵涉行政法问题,即使是民事权利,也必然涉及行政机关的确认、保障等行政法问题,上述现象直接造成物权法既非单纯的民法,也非纯粹的行政法,而是兼具民法与行政法两个部门法属性的“混合法”。这种法域交叉、资源互补的情形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处罚、行政证据等领域也极为常见。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这就开启了两种不同属性的机关、程序和法部门在证据种类层面的合作、共享和互补,既然行政“证据材料”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被使用,那么必然促进证据规则、标准等领域的适度“交融”;行政证据能够在证据要求、证明标准等更高的刑事诉讼领域得以使用,也预示着刑事诉讼证据在行政法领域使用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了《刑事诉讼原则在纪律程序中的运用》,开启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依法行政之“法”的新篇章。
4.确立法部门规定冲突的选择适用机制。法部门规定冲突的选择适用规则可能路径有三:第一,行政法自身规定优先适用,其他部门法作为补充,在行政法的下位法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不能适用其他部门法的上位规定,如行政法中关于行政合同的下位规定应优先适用于合同法规定,这是部门法冲突选择适用的首要规则。第二,在部门法之间“同理”和“交叉”地带应遵循“效力位阶说”,打破法部门界限,依照《立法法》第78条至第86条规定,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效力层次依次适用。第三,按照各部门法在依法行政中的功能以及行政法特别规定的有无,先“依据”、“根据”、“适用”后“参照”及法理上的参考价值。
5.厘清不同法部门之间的应有界限和“存异”关系,创设行政法特色理论与制度。以往行政法理论与制度领域盲目参照甚至直接适用了不少其他部门法理论与制度设计,忽视了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在某些具体制度领域的应有差异,也滞后了行政法自身发展,突出“个案”主要有:
第一,行政委托一味套用民法上的委托代理制度。行政委托不可以适用民事委托规则的理由在于,鉴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基础,行政机关并非行政权力的所有者,既非自身所有就不得任意授出。有学者认为,对于重要的行政事务方需采“法定委托”规则,不重要的行政事务可“任意委托”。②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3页。这实质上忽视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权力的所有者究竟是谁,非权力所有者无权转授、委托所受之权;二是权力委托永远是重要事务,权力的产生、行使、消灭等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因其所附属事物的轻重程度而改变。这也警醒我们必须加紧构建行政委托理论和制度。
第二,在行政违法行为领域盲目照搬犯罪行为理论与制度设计。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尽管在社会危害性、违法性、有责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同性和相通性,但二者毕竟在危害性大小、是否触犯刑律等方面存在“度”和“质”的差异。如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行政违法行为不以故意或者过失中某个特定主观状态为构成要件,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只能作为处罚幅度的“酌定”因素,不能作为处罚与否的决定因素;而刑法上某些犯罪只能由故意或者过失构成。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行政违法行为的矫治不能照搬刑法理论和制度。但是,囿于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和缺位,实践中这种“照搬”和“套用”屡见不鲜,如当下不少地方或部门已经或正在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其中大量抄袭犯罪构成和刑罚适用规则。
第三,在行政相对人权利方面基本套用民法上的“人”和民事权利理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乃至行政法理论、规范与制度体系存在的唯一正当性源泉,缺少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与制度体系只能算作是“半个行政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体身份特征是“一体两性”:作为民法上的“人”,俗称“私人”,享有私权利,作出民事行为;作为行政法上的“人”,是行政相对方,享有公权利,作出行政法行为。行政法上的相对人不能一味沿用民法中“人”的理论与制度,其对应的义务主体、法律地位、权利属性、行为效力等均有差异。总之,行政法必须加紧构建与相对人身份相匹配、以行政机关和公权力为相对方、立于公法基础之上的相对人主体、相对人权利、相对人行为、相对人程序、相对人责任、相对人救济理论与制度体系,改变“公法迄今为止仍然躲在私法的夹缝中生存”的境况,促进公法“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和方法”①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第8页。。
五、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一个年轻学科,我国行政法学起步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法理念、规范与制度的完善性,加之尽管行政法是规范载体和数量最多的部门法,但与行政的广泛性、多变性相比,规范量仍显“寒酸”,因而从法理与规范两个层面对其他部门法的“双重”借鉴甚至直接适用就显得尤其必要。依法行政不是传统行政法部门的“专利”,除了当下已获共识的“首先是依宪行政”之外,特定条件下也是“跨部门法”行政。
On the Intersectoriality of the“Law”in Administration by Law
LIU Yan-tao LIU Hai-xia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P.R.China)
The“law”in the administration by law includes not only the administrative law,but also other department laws,which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the resemblance and interconnection of department laws in the field of“seeking common ground”as to principles and ideas,the extensiveness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the sharing of sources of law and the complexity of administrative cases,etc.Other department laws must conform to conditions to be the bases for administration which are no special provis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implying the common legal principles in other department laws and not rejec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affairs’nature or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Functions of the“law”in administration of law mainly include“according”,“basis”,“application”,“reference”,and“reference in jurisprudence”.The administrative law shall speed up establishing such relations with other department laws as sharing, common application,co-construction,complementation and reserving differences,etc.
administration of law;intersectoriality;legal basis;conditions of use;associated mechanism
[责任编辑:李春明]
2014-12-16
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具体行政行为跨程序拘束规则研究”(13BFXJ02)的阶段性成果。
柳砚涛,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济南250100);刘海霞,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