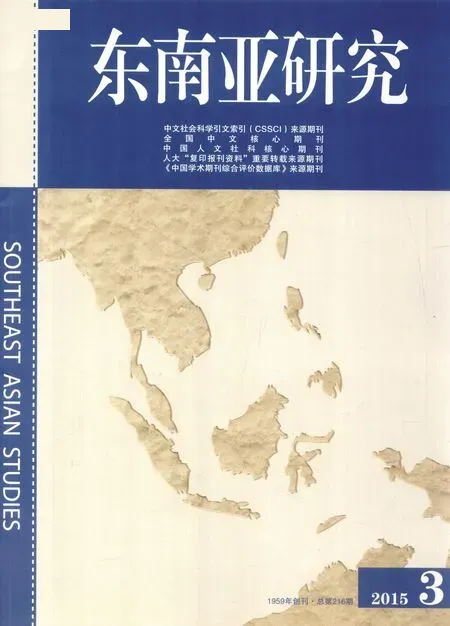东南亚国家跨境烟霾治理评析
2015-03-30程晓勇
程晓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510630)
自东盟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在许多地区公共问题上,东南亚国家仍然应对乏力,其中跨境烟霾污染问题就是一个让东盟饱受诟病的地区公共问题。在东南亚地区,农作物焚烧、工业废气和烟尘、汽车尾气、居民日常生活排放等原因都可能造成范围不等的烟霾污染,影响着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但最严重和造成跨国影响的烟霾往往与毁林辟地引发的森林火灾联系在一起的。东南亚国家普遍国土面积不大,国家之间陆地相连或是海域相接,一些严重的烟霾影响范围常常超出一国国界而造成跨国的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国家之间的纠纷和争拗,因此跨境烟霾问题成为困扰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典型地区公共治理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南亚国家自20 世纪90年代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和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举措是东南亚国家在2002年签署了一项旨在协调各国政策与行为以共同治理烟霾的《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 (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以下简称《烟霾协议》)。尽管如此,十几年过去了,东南亚国家对烟霾问题的治理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热带森林发生火灾,烟雾扩散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部分地区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这次事件再一次提醒东南亚国家烟霾问题的严重性和跨境烟霾治理的艰巨性。本文分析东南亚跨境烟霾问题的形成、跨境烟霾对东南亚国家造成的影响、跨境烟霾治理如何成为东盟的一项议程、东南亚国家烟霾治理的成效,并探讨影响烟霾治理效果的原因。
一 跨境烟霾问题的形成及其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虽然烟霾现象在东南亚国家并不罕见,但跨境烟霾问题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印尼加里曼丹省婆罗洲地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而极端干旱,当地烧荒垦地引起了几次森林大火,烟雾一直扩散到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等印尼周边国家,由于彼时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大,跨境烟霾问题尚未引起东南亚国家的重视[1]。20 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烟霾污染逐渐成为一个地区公共问题,引起东南亚国家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烟霾污染事件逐步增多,波及国家范围广泛,并且给相关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跨境烟霾污染事件为:1997年底到1998年,印尼发生森林大火,火灾持续数月,导致东南亚多国遭受烟雾灾害,对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和交通系统的影响尤为严重;2013年6月,印尼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民众和企业的“烧芭”活动①“烧芭”即用火烧森林,清出土地来耕种,这是印尼农业传统,每年旱季印尼各地的山林火灾多是“烧芭”引起。导致当地大片森林焚毁,大火引起的浓烟飘至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影响范围直抵泰国南部;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再次发生森林火灾,受害国家包括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另一方面,与烟霾污染事件频发相伴随的是东南亚国家政府和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与增强。20世纪80年代是环保意识在全球蓬勃兴起的时期,无数环保NGO 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都设立了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环保NGO 的分支机构,或是成立了本地的环保NGO。环保组织的宣传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环保意识。此外,经过30 多年的工业化发展,由于工业污染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在部分东南亚国家开始显现,当地人民越来越意识到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带来的损害,要求政府对空气污染进行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烟霾的“来源国”,还是受到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尤其是那些无辜受到影响的国家对此问题格外地敏感和在意。
东南亚的跨境烟霾问题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通常情况下,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烟霾的产生多与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排放联系在一起,例如1952年的“伦敦烟霾事件”。但是在东南亚,尽管工业污染和生活排放也会引发烟霾,不过这些烟霾事件大多影响范围较小,大多局限在某个国家的局部地区,很少会造成跨国影响。在东南亚,几乎所有造成大范围甚至是跨境影响的烟霾污染都源于森林火灾,这些森林火灾或是自然原因或是人为原因造成,如上举例的几次严重跨境烟霾污染事件都是如此。其二是目前东南亚地区有两个烟霾“污染源”,一个在缅甸西部和泰国北部山区,影响范围主要是湄公河次区域;另一个烟霾的“污染源”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影响区域包括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泰国。由于缅甸西部和泰国北部边境地区相对人烟稀少,使得后一个“污染源”成为东南亚地区跨境烟霾的主要源头。事实上绝大多数造成严重跨境影响的烟霾污染都源自印尼境内,在某种意义上,东南亚的跨境烟霾问题成了“印尼问题”,尽管印尼自身也是烟霾的受害国。印尼拥有极其丰富的森林资源,但森林资源保护不力,破坏严重。在印尼,一些棕榈园、橡胶园种植企业为了扩大棕榈和橡胶这类高经济价值的树木,采用火烧毁林这种“简单粗暴”的低成本方式来开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此外,印尼人口数量庞大,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资源趋于紧张,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便通过火烧毁林清出土地的方式来开辟耕地,种上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各种农作物[2]。这种方式在印尼被称为“烧芭”,长期以来,“烧芭”这种扩大耕地的方式已经成为印尼的农业传统习惯。每年印尼各地的山林火灾多是因为种植园焚林辟地和农民火烧垦荒耕作的“烧芭”陋习所引起的。
烟霾污染不仅给“源发地”国家,也给波及到的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给这些国家的民众健康和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以前述的几次烟霾事件为例,1997年由于印尼农民烧荒垦地所引起的浓密烟霾,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笼罩着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地区,最终造成约20 万当地居民因烟霾生病。浓雾还使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海陆空交通大受影响。在印尼,由于能见度降低导致了客机失事事件,在马六甲海峡发生数起轮船相撞事件,据估算烟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3 亿美元[3]。此次烟霾事件引起多个东南亚国家对印尼的批评。受烟霾影响严重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地方行政当局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于对印尼在控制烟霾方面的迟钝反应严重不满,马来西亚政府未经印尼政府邀请就自行宣布将派遣一千多名消防队员到苏门答腊帮助灭火,马来西亚的这一行为引起印尼严重不满,指责马来西亚的“鲁莽无礼”举动侵犯了印尼主权。在地区和国际压力下,经过外交磋商,印尼最终才勉强同意马来西亚的消防队员入境支援灭火。新加坡政府卫生和环境部长也直言希望印尼吸取教训,对国内的烧火垦荒行为进行严格整顿。泰国一些报纸批评印尼政府逃避责任,声称要采取“法律行动”。缅甸则有官员警告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将向国际法院起诉印尼索取赔偿[4]。面对此次烟霾污染给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印尼总统苏哈托两次向邻国道歉。
2013年6月,印尼苏门答腊发生森林火灾,火势严重时,苏门答腊岛上起火点多达200 多处,这次火灾引起的浓烟向四周飘散,影响范围直到泰国南部,最严重时陶公府的能见度只有3 到4 百米。印尼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造成新加坡、马来西亚“史无前例”的严重烟霾天气。在烟霾期间,新加坡空气中充满了树木燃烧的味道,新加坡民众为防范烟霾纷纷抢购口罩、眼药水、润喉糖甚至凉茶,政府要求民众尽量呆在屋里,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除了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外,浓雾还严重影响了新加坡的旅游和交通运输。另一受害国马来西亚的海路交通也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国际国内航班被迫暂停和延迟,首相纳吉布建议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引起呼吸系统疾病。此次事件引起新马两国政府和民众对印尼控制森林火灾不力的抱怨和批评,新加坡政府除向地区外国家寻求援助外,环境局局长还带领代表团前往印尼与印尼官员紧急会谈,要求印尼扑灭苏门答腊林火,新加坡媒体则呼吁国际社会向印尼施加压力[5]。面对新马两国巨大的舆论压力,印尼总统苏西诺被迫为本国林火造成的严重烟霾天气向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道歉。印度尼西亚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表示,印尼充分意识到苏门答腊岛空气污染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印尼政府和人民希望将责任者绳之以法[6]。
但时隔一年,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再次发生森林火灾,烟雾扩散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部分地区。新加坡空气污染指数在当地时间9月15日达到峰值,导致学校限制户外运动,托儿中心和幼儿园取消所有户外活动。此外,新加坡卫生部紧急出台特别计划,为在烟霾中患呼吸系统疾病的18 岁以下青少年和65 岁以上老人提供医疗援助。在马来西亚,受霾灾影响最大的柔佛州麻坡市和礼让市所有的中小学被迫停课。
二 东盟国家对跨境烟霾的治理
随着烟霾污染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受害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强烈敦促印尼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印尼国内受害地区的民众也要求改善空气问题。在巨大的国内与国外压力下,印尼政府为控制烟霾做了不少工作,譬如政府明文规定禁止烧荒,颁布了各种相关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各地政府学习讨论。政府收回了一些林业公司的许可证,对烧荒肇事者予以逮捕并严惩。农业部对那些通过别的方式清理森林获取田地的人给予帮助,包括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帮助等。在发生森林火灾后,印尼政府也责成相关部门立即扑灭林火。但是,由于多方面的限制,印尼政府的国内措施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首先,印尼地方政府执法不严的现象短时期内难以得到改变,而且“烧芭”作为一种地方传统,很难在短时期内用法律手段加以杜绝。其次,当地农民由于财力和物力所限,缺乏购买推土机等重型机械的资金,负担不起机器开辟土地的费用,尽管政府颁布了“烧荒”的禁令,但地方政府目前所做的更多的是教育民众不要大规模“烧芭”,避免火势过大影响邻国。其次,印尼缺乏足够的护林人员和消防人员,救火设备和交通工具也不充足,这些都是摆在地方政府和民众眼前的现实困难,这些因素使得每次森林火灾后的灭火控烟工作进展缓慢。除了在国内采取措施外,印尼也希望通过地区合作来解决烟霾问题,呼吁其他东南亚国家不要将跨境烟霾问题仅仅视为印尼自身的责任,而应视为地区问题,向印尼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提高其烟霾治理能力。
1992年6月,东盟国家在印尼万隆召开了森林火灾长期综合管控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ng-Term Integrated Forest Fire Management)。在此次会议上,东盟第一次公开承认森林与农地火灾引起的跨境烟雾是本地区的公共问题,需要通过地区合作解决[7]。随后包括东盟国家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等一系列与“治霾”相关的会议相继召开。东盟还在马来西亚和印尼成立了研究“治霾”问题的工作组[8]。同年,东盟宣布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应对跨境烟霾问题,并组建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气象预警网络来监控和预警跨境烟雾污染问题。1995年,东盟发起“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该计划包含鼓励成员国民众以非焚烧方式垦荒,以及在部分成员国部署监测森林火灾和紧急灭火的地面力量等多项改善跨境烟雾污染区域治理的一系列措施。尽管这一计划“雄心勃勃”,但存在不少缺陷。由于担心干涉成员国内政,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在承认“火烧清地”是引起烟雾污染的原因的前提下,主要强调森林火灾是引起烟雾污染的主要原因,没有把农业烧荒行为列入引起烟雾的原因。同时,为了避免干涉内政的嫌疑和引起印尼的抵触情绪,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避免指出印尼是东南亚跨境烟雾的主要“来源地”,而是将印尼与其他国家一道列为雾霾的受害国。总体上,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是向东盟国家中涉及跨境烟霾问题的相关国家提出了一个行动建议,并不具备任何的法律约束力。1999年,出于对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的补充,东盟为了杜绝成员国的农民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清理和获得农业土地,“鼓励”东盟成员国在各自国家的法律制度下实施“零燃烧”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在许多国家并未得到实施。
总体上看,20 世纪90年代,东盟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虽然东盟国家在合作治理烟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并搭建了一些合作的平台,但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各国的行动步调并不一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烟霾受害国希望印尼尽快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本国的森林火灾。但印尼由于种种原因,即无法在发生森林大火时采取有力的措施迅速扑灭火灾,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火灾隐患。
在雾霾治理迟迟未能取得明显成效的局面下,一些国家倡议设立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硬”规则和长效机制来约束相关国家的烟霾治理行为。这一倡议最初并未得到东盟国家的一致支持,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坚持下,东盟于1999年同意研究创设一个“硬”机制的可行性[9]。随后的几年中,东盟国家就确定跨境烟霾治理的法律框架进行了多轮的协商与谈判。在协商过程中,东盟国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规则的约束力与国家主权和内政的关系。按照东盟的传统规范,东盟国家不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政,在解决地区问题时注重协商一致和非正式外交。以印尼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担心在烟霾问题上制订“硬”规范,会为他国干涉内政制造便利,从而侵蚀国家主权。显而易见,印尼不会接受一个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容的协议。那么, 《烟霾协议》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印尼为何参加了《烟霾协议》的谈判并签署了协议?
事实上,《烟霾协议》的基本内容大体上与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保持了一致。例如,《烟霾协议》的第4、第7 和第9 条规定的协议国义务包括:制订出本国的指导原则、行为计划、和具体措施以阻止和监控可能引发跨境烟霾的火灾;火情信息交换;发展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和农业废弃物的市场。这些内容都已经在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中有所体现,并且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已经按照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采取了行动。因此,《烟霾协议》可视为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指导精神和具体措施的法律化,它的目的是以法律化的“硬”约束形式来督促个别国家采取行动,落实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的要求。《烟霾协议》强调协议国有责任监控和及时扑灭在其境内有可能引起跨境烟霾污染的火灾,协议国可以通过东盟跨境烟雾污染控制协作中心向其他国家请求援助或提供救灾援助。 《烟霾协议》还强调了预防机制和预防方法,强调通过各国努力和国际合作来监测防治由于森林火灾而引发的越境烟霾污染。根据该协议,东盟将设立越境烟雾污染协调应急中心,其职责是促进地区防烟霾的努力以及分布防霾资源。此外,东盟还成立了越境烟雾污染控制基金,由各成员国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基金提供贡献[10]。《烟霾协议》的第12 -15 条是关于紧急情况下的联合救助,根据协议内容,发生跨境烟霾污染事件后,协议国可以通过东盟跨境烟霾污染控制协调中心(the ASEAN Coordinating Center for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Control)提出援助请求或者提供援助。 《烟霾协议》第12 条指出,受到烟霾影响后,其它东盟国家可以提供援助,在提出援助建议后,援助的目标国应立刻决定是否接受援助,这反映了东盟国家中烟霾“受害”国的利益,以及它们干预印尼国内森林和农地火灾的意愿。同时,《烟霾协议》在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下,照顾了印尼的感受,例如第5 条和第12 条指出,(消防)物资、装备的援助和人员部署要得到受援国的同意。
印尼参加《烟霾协议》的谈判主要是基于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根据国际法规则,印度尼西亚有开发利用其境内自然资源的主权,但同时也有在其管辖范围内,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不能危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健康的责任。长期以来, “源发”于印尼的烟霾给周边国家的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危害了周边国家民众的健康,受影响的国家屡次要求印尼政府对火灾进行管控,这对印尼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其次,20 世纪90年代末,苏哈托政府下台后,印尼开始走上民主化改革之路,印尼政府比较重视回应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参加《烟霾协议》有助于缓解周边国家的批评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也是对本国要求治理环境呼吁的回应。此外,印尼参与《烟霾协议》谈判也有利于动员国内民众在防止森林火灾和治理烟霾上的资源和注意力。由于东盟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兼顾了各方的利益,经过数年的协商,东盟国家建立跨境烟霾治理机制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进展,2002年6月10日,10 个东盟国家在吉隆坡签署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按照《烟霾协议》签署时的规定,该协议于2003年11月25日正式生效,除印尼以外的其他9 个签署国家都在协议生效期之前批准了该条约,但印尼直到2014年9月才正式批准《烟霾协议》[11]。
三 东盟跨境烟霾治理的成效及其局限性分析
从20 世纪9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就开始寻求解决跨境烟霾污染问题。起初,烟霾受害国试图通过舆论压力和外交渠道督促烟霾的主要“输出国”——印尼去管控本国的火灾。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不奏效,直接的批评和一味的施压不仅未能迅速地解决问题,反而容易造成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印尼虽然承认源自于本国的烟霾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影响,但认为这只是偶然的现象,其他国家的反映过激。同时印尼认为如何管理本国的森林资源和应对火灾是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和指责。在1997年的跨境烟霾污染事件中,马来西亚欲派遣消防人员到印尼协助灭火,被印尼视为对本国主权进行干涉的“鲁莽”举动。而在2013年的跨境烟霾污染事件中,面对新加坡的强烈批评,印尼情绪反弹,多位政府高官的言论反映了印尼的这种情绪。例如印尼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表示,解决问题的途径应是合作,而非互相指责。人民福利统筹部长拉克索诺则回应说森林火灾是大自然的错,新加坡不该像个孩子一样对雾霾大惊小怪。新加坡提出愿协助印尼对抗林火的建议,也被印尼政府一口拒绝[12]。
随着跨境烟霾污染的频繁发生和负面影响的显现,印尼对烟霾问题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印尼意识到烟霾问题将影响东盟内部的关系和本国的形象。烟霾受害国也意识到跨境烟霾污染是一个地区公共问题,不是单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这一思想认识上的变化开启了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解决问题的道路。此后,跨境烟霾污染问题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单边问题进入到东南亚地区治理的范畴,在东盟合作的多边框架下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从东盟召开森林火灾长期综合管控国际会议,到东盟就烟霾问题设立专项工作组,再到成立高级别的联合委员会,进而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跨境污染治理合作计划,最终制订了具备法律约束力的《烟霾协议》,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治理手段的升级显示出东盟在跨境烟霾污染治理上的努力和力度的不断加强。然而,21 世纪以来数次严重的跨境烟霾污染事件表明东盟国家二十多年的努力并未取得理想的治霾效果。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
首先,就东南亚地区而言,跨境烟霾问题治理是一个责任与收益不平衡的结构。从跨境烟霾治理的责任上看,由于东南亚地区跨境烟霾主要来源于印尼,因此跨境烟霾治理的责任主要落在印尼身上,显而易见,印尼是烟霾治理成败的关键国家,其他东南亚国家只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从收益上看,尽管消除烟霾能够改善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偏远林地地区的环境,但印尼主要的人口聚集区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爪哇岛。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印尼而言,与发展种植业和农业来促进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较,改善这两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是排在第二位的。何况,治理烟霾需要面临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对印尼而言,控制火灾和治理烟霾涉及到本国的农业与种植业传统习惯、国内利益集团的掣肘和巨大的治理成本投入,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现状。
如前所述,印尼农民和经济作物种植园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焚烧毁林这种简单和低成本的方式开辟农业和种植业用地的习惯,与之相对应,印尼国内存在着烧林扩地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主要由生产棕榈油和橡胶的农场及相关企业组成。多年来,为了扩大棕榈和橡胶的种植面积,相关农场和企业不断焚烧森林以腾出土地。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最大的橡胶生产国之一,棕榈和橡胶产业在印尼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仅以棕榈油为例,2013年印尼棕榈油出口收入约为200亿美元,占2013年印尼全部出口总额1680 亿美元的12%[13],棕榈种植相关产业对印尼经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如果加上橡胶产业,经济作物种植业在印尼的国民经济中占据多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尼政府内部也对烟雾治理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协调署负责人就曾在回应其他国家对印尼的批评时,不无开脱之意地表示森林火灾是没人能够预知和阻止的自然灾害[14]。此外,印尼政府的管理能力限制了烟霾治理的效果,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实行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相悖的中央政令很难在地方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印尼出台过多部法律法规用以防止“烧芭”行为,但“烧芭”已经成为地方传统,当地农民也负担不起开辟土地的其他方式,缺乏购买推土机等重型机械的资金是摆在地方政府和民众眼前的现实困难。如果地方政府强力禁止以“烧芭”的方式开辟土地,将严重影响许多种植业工人和农民的生计。加之在印尼涉及森林火灾和环境保护的部门甚多,且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这些法令未能得到落实。概言之,烟霾治理的责任、投入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导致印尼既没有能力,也不急于在短时期内管控本国的森林与农地火灾及其引起的烟霾问题。
另一个导致东盟跨境烟霾治理效果不佳,尤其是《烟霾协议》未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是受东盟“不干涉内政”传统规范的制约。自1967年成立以来,“不干涉原则”就一直是东盟遵循的基本准则,并以明确条文或者间接表明的方式体现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 《和平自由中立区宣言》《东盟协调一致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东盟宪章》等一系列标识着东盟从成立到发展壮大的重要条约与章程之中。东盟在组织与运行结构中没有任何干涉或制裁机制,而是强调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东盟成员内部的争端。在东盟发展历程中,不干涉原则避免了东盟内部矛盾的扩大和复杂化,对东盟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适用于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不干涉原则难以适用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其他类型的地区公共问题。在跨境烟霾污染问题上,发生在印尼境内的烟霾对邻国造成了危害,但对境内森林资源的管理是印尼的内政,按照“不干涉原则”,其他东南亚国家很难对印尼的灭火和控烟工作“说三道四”,并且由于对邻国造成的烟霾污染并非印尼有意为之,烟霾“受害国”也很难找到介入的“着力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部分东南亚国家极力推动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来试图突破不干涉原则的约束,《烟霾协议》正是反映了这部分国家的努力。尽管如此,由于不干涉原则的“神圣性”和印尼的坚持,《烟霾协议》只能在法律约束力与不干涉内政之间做出调和,既考虑烟霾“受害国”的利益和协议的严肃性,也兼顾对印尼国家主权的尊重和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遵守。即便如此,印尼迟至2014年9月才正式批准《烟霾协议》,使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一治霾机制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结语
自20 世纪90年代形成跨境烟霾问题以来,东南亚国家在烟霾治理方面的努力已经超过了20 多年,经历了从单边治理到多边合作机制化治理两个阶段。20 世纪90年代的治霾经验表明,那些不具备“硬”约束特征的行动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跨境公共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推动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机制。从20 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为了制订出一个烟霾治理的“硬机制”,东盟国家先后经历了四轮协商,最终在21 世纪初形成了《烟霾协议》,这是东南亚国家在跨境烟霾治理上的重大突破。但是由于在跨境烟霾治理上责任与收益的不平衡,印尼缺乏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的足够动力。同时,由于国内政治环境和行政能力的掣肘,印尼并不急于履行《烟霾协议》,使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烟霾协议》并未落实生效。由于印尼是解决跨境烟霾问题的关键国家,印尼在履约上的拖延造成东南亚国家在跨境雾霾治理上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2014年9月,在达成《烟霾协议》12年后,印尼国会终于正式批准了《烟霾协议》,这或许为东南亚的跨境烟霾治理带来了转机。
【注 释】
[1]“Fire situation in Indonesia”,IFFN,No.26,January 2002,pp.37 -45,http://www.fire.uni -freiburg.de/iffn/country/id/id_ 35.htm
[2]Wolf Donner,Land use and environment in Indonesia,Hurst & Company London,1987.
[3]《印尼森林大火致烟霾严重污染扩散 新加坡叫苦不迭》,http://sg.xinhuanet.com/2014 -09/16/c_ 1269894 14.htm
[4]方舟:《大自然的报复——殃及东南亚的印尼森林大火》,《国际展望》1997年第20 期。
[5] Markus Hund,“ASEAN and ASEAN plus Three:Manifesta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http://ub-dok.uni-trier.de/diss/diss38/20030218/20030218.htm.
[6]《印尼呼吁东盟国家合作应对跨境空气污染》,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 - 06/20/c_ 116229145.htm
[7]Joint Press Release 5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on the Environment,Singapore,Feb.18,1992.
[8]Tahir Qadri,Fire,Smoke,and Haze:The ASAEN Response Strategy,Manila: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1,http://www.aseansec.org/pdf/fsh.pdf
[9]Paruedee Nguitragool, “Negotiate the Haze Treaty:Ration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ASEAN Agreement on Trans - boundary Haze Pollution”,Asian Survey,Vol.51,No.2,2011,pp.365.
[10]Fika Yulialdina Hakim,“Why Indonesia must ratify the ASEAN haze pollution Treaty”,The Jakarta Post,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3/07/14/why - indonesia -must-ratify-asean-haze-pollution-treaty.html
[11]“Indonesia ratifies bill on trans-boundary haze pact”,http://english.mep.gov.cn/News _ service/media _ news/201409/t20140917_ 289177.htm
[12]《印尼官员:新加坡偶有雾霾就抱怨不停》,《新京报》2013年6月24日。
[13]印尼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bps.go.id/eng/tab_ sub/view.php?kat = 1&tabel = 1&daftar = 1&id_subyek=08&notab=5
[14]Thomas Fuller,“Shifting Winds Lower Malaysia Pollution”,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9,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