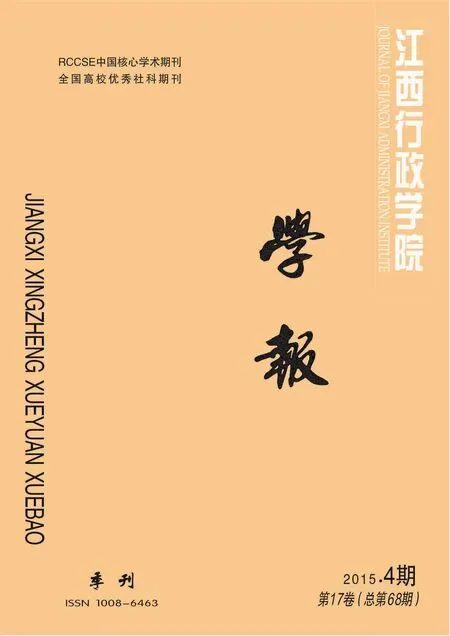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015-03-29陶国根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陶国根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江西南昌330003)
[摘要]社会资本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良好的契合性,它所包含的社会普遍信任、互惠互利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内容,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围绕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对社会资本进行整合和重构,有效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31
[收稿日期]2015-08-24
[作者简介]陶国根(1982-),男,江西南昌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事务管理研究。

2015年1月14日,国家发布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的重要部署。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研究对象,试图在进行两者逻辑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上,探寻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
一、理论阐释:社会资本的概念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是,一般认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资深教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第一位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进行初步分析的学者。他在1980年撰写的学术短文《社会资本随笔》中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P3)。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一个确定群体的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财产,这个群体有清楚的边界、相互交换的义务和相互的认可。布迪厄开启了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先河,此后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由此掀起了一阵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风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就因此感叹道:很少有一个科学概念像社会资本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且聚集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2](P529)。
1990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社会学领域理性选择学派主将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布迪厄的研究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3] (P354)。1992年,美国知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社会资本观。他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为网络结构中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取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4](P9)。1995年,日裔美籍学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社会资本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强调,“所谓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资本”[5] (P35)。199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iandro Portes)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加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资源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定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是社会嵌入的结果”[6]。2001年,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杜克大学教授林南从网络资源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加全面、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7](P24)。
但是,真正使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焦点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他以社会资本问题为核心,与同事一起对意大利中北部地区跟踪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调查研究。在此项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普特南于1993年完成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代表作品《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普特南也因此书从此享誉西方学术界。之后,普特南又陆续于1995年和1996年出版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弱和复苏》(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等作品。普特南完成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普特南在其作品中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8](P195)。因此,普遍信任、互惠规范与合作参与等公民价值观念是社会资本的基本构成要素。社会资本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主要体现在那些能够把亲戚、朋友、同事、家庭和社区结合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是一种可以推动社会行动和完成任务的重要资源。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中,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具有多重可解释性的概念。但是,无论哪一种内涵和解释,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总体上还是非常相似的,即普遍信任、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等。普遍信任对于社会资本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在社会结构中,普遍信任水平越高,合作就越广泛充分,就越有利于生产潜力的发挥和扩展,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增长就越快。互惠规范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它通过一系列奖惩机制的构建,形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约束,从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有利于推动网络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能够增强社会普遍信任,提高网络群体的信誉,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
二、社会资本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资源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兼具时代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制、运行机制的总称[9]。它强调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目标,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要支撑,以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驱动力,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作用,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的传播功能,在公众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得到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与引导。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修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探索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上世纪80-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它所包含的社会普遍信任、互惠互利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内容,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资源。
首先,社会资本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普遍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8](P199)。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存在的普遍信任关系,有利于增进共同体内部的信息传递,减少信息阻碍;有利于加强共同体内部的沟通与交流,达成一致共识;有利于增加共同体内部的互惠行动,降低交易成本。如果“社会中缺乏信任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阻碍。那些缺乏稳定和效能的政府的社会,也同样缺乏公民间的相互信任,缺乏民族和公众的忠诚心理,缺乏组织的技能”[10](P22)。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通过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合作的工作格局。可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方联动、互利共赢模式是当前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想选择。然而,信任是协同合作的基础,只有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协同合作,才能使协同者之间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从而达成协作的意愿。在一个共同体中,团队成员彼此间的信任感越强,开展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团队成员彼此间互不信任、相互猜忌,那么协同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小,甚至会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此,普遍信任是多元协作各主体功能有效整合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推进多元主体积极主动合作的有效粘合剂。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彼此信任,它们才会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过程中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由此可见,作为宝贵社会资本的信任要素,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是实现多元参与主体互动交流与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石。
其次,社会资本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互惠规范。作为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互惠规范,是公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为实现各自利益而逐渐形成的。一般认为,规范是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不是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规范,又被称为制度,泛指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是公民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逐渐形成的,主要体现为传统习惯、民风民俗、内心信仰、道德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多种形式的内在制度。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能止步于口号上和停留于文件里,需要实实在在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否则,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会流于形式,成为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作为社会资本核心构成要素的互惠规范,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必需的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健康运行离不开相关的政策法规、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政策法规、法律制度的建设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因此,必须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先手棋”和“当头炮”。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制度体系,把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地写入法律,有利于发挥法律的“刚性约束”作用,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参与主体的责任意识,让这种责任不再是一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虚幻责任,而是更加具体化。否则,就会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局性、长远性、方向性、公正性、效益性等大打折扣。所以,规范社会资本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制度保障,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必不可少。
最后,社会资本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公民参与网络。按照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人际交往与沟通网络所构成。罗伯特·普特南教授将这些网络统称为“公民参与网络”。 在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集,团体成员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间接的)就越多,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感就会越强越好,基于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概率也就越高。可见,对于建立普遍的社会信任而言,公民参与网络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垄断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其它社会主体无法介入或介入门槛非常高。但是,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承担主导责任,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供给主体,但却不是唯一的主体,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都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其中。因此,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制度安排由政府一元治理结构发展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共同治理结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特性,有利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广泛地反映人们的文化服务意愿和文化权利需求,并充分考虑人们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不断发生变化的需求,有效地避免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政府机构被错误地置于公共文化生活的中心。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三位一体”共同治理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网络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交流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公民参与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言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基础。
三、培育社会资本,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资本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间有着良好的契合性,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资源。因此,必须大力培育社会信任、积极发展互惠规范和努力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对社会资本进行整合和重构,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首先,大力培育社会信任。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著作《货币哲学》中曾谈到,“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11](P178-179)。信任作为个人和组织的“道德资源”,具有维系人与人、人与组织间认同感和忠诚度的功能。如果人与人之间普遍地相互猜忌、互不信任,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坠入瓦解的边缘。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逐步建立的人际信任关系,是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的动力源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的断层,一方面以关系、人品、声望等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信任保障机制逐渐失效,另一方面以契约、法律、制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信任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任度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社科院2013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就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为59.7分,比上一年的62.9分又有了新的下降。转型期社会普遍信任的缺失,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合作供给往往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大力培育社会信任,提升全社会普遍信任度,是建立健全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然选择。一是要实施全方位的系统化的公益价值观教育。通过公益价值观教育,可以提高多元参与主体的公益精神,摆脱个体狭隘的眼光,使人们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审视问题,并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帮助、协调共事。显然,公益价值观教育是提高社会普遍信任的有效途径,也是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的不竭动力,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共治结构的形成。二是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沟通交流平台。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在一个密集、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关系网络中的成员间易于形成相互信任[3](P332)。搭建公共文化服务沟通交流平台,拓宽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参与渠道,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网络,不仅有利于发展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信关系,还能够产生出第三方信任,使信任氛围在社会内部不断得到扩散和蔓延,并最终实现提升社会资本总量的目标。
其次,积极发展互惠规范。制度与规范是紧密相连的,积极发展互惠规范,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必须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为主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包括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同步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在制度理性的基础上强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正义与运行有效,必须以制度保障让亿万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获得文化实惠、共享改革开放文化成果并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之中[12]。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就是要在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相关配套制度,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由此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现代化,整个管理体系就必须法治化。但是,由于文化领域立法工作的总体滞后,导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缺乏法制保障,随意性比较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主要取决于当地主要领导对文化工作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因此,必须加快文化立法进程,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走上法治化的轨道。然而,文化立法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久久为功,付出长期而艰辛的努力。一要尽快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作为文化领域的基本法,对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目前,立法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组织起草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已经被列入全国人大2015年立法日程。二要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由于我国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被分散在多个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呈现出多元化特性,立法内容交叉、重复、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相关领域的立法,要善于发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的综合协调作用,打破不同职能部门的利益藩篱,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实现不同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法律的有效衔接。
最后,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的概念由罗伯特·普特南正式提出,在他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普特南将公民参与网络分为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和垂直的公民参与网络两种类型。垂直的公民参与网络,由于信息的垂直流动和成员关系的依附性,导致投机行为时有发生,难以维系网络成员的互信合作。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由于信息的水平流动和成员关系的平等性,使得共同体内的成员更趋向于合作,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公民参与网络作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交流的有效平台,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没有健全的公民参与网络,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协同合作的治理结构就难以实现。因此,构建公民参与网络是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一是培养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构建公民参与网络的关键在于培养和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由于受传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总体不强,多数人没有把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当成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结果造成了公众话语权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严重缺失。所以,政府要充分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舆论工具,在全社会开展各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民意识教育活动,推进政治社会化,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能力。二是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民参与网络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因此,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必须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文化类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多数是基于平等地位和权利主体的横向网络,更具民主和公共精神,不仅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组织基础,还具有所谓的“公民学校”的教育效应,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13]。因此,应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价值,纠正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认识偏差,转变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使非政府组织真正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包亚明.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Ostrom, Elinor and T.K.Ahn. 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3]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Ronald Burt. Structural Ho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6]A.Porte.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Rev.Sociology, 1998,(2):2.
[7]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9]兰凯军. 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路径[N].光明日报,2014-03-02(7).
[10]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11]齐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2]王列生.开放性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N].人民日报,2013-11-22(24).
[13]孟天广,马全军.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1,(3).
责任编辑李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