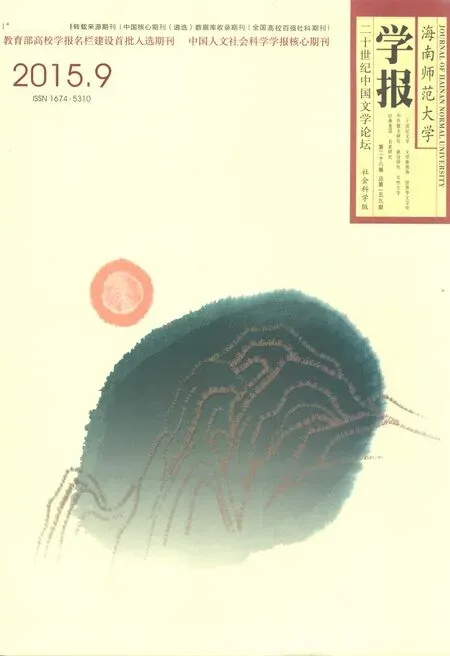历史与人生在疏证与校注中变得厚重——陈志平、熊清元《金楼子疏证校注》评述
2015-03-29阮忠
阮 忠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萧绎,也算是南朝梁代的奇人,552 年冬月,他在“侯景之乱”平息后登基为帝,不足三年,就在内乱外患中丧命,“敛以蒲席,束以白茅”(《南史·梁元帝纪》),享年47 岁,那是萧绎改元承圣的第三年(555)十二月。他曾说过的君子以富贵为不幸,真有一语成谶的意味。其实,萧绎虽然有政治野心,并不长于政治,称帝与败亡都因历史的机缘和一时的际遇,也离不开他好矫饰、多猜忌以及恶人胜己的性格。综其一生,萧绎应该更适合做一介文人而不是政客,五六岁时即能背诵《曲礼》、能诗,及长博览群书,虽苦于眼疾,仍勤学不辍,曾自言:“吾小时,夏日夕中下绛纱蚊绹,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又经病疮,肘膝烂尽。比以往三十余载,泛玩众书万余矣。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兹言是也。”(《金楼子·自序》)。而萧绎的著述之多,在梁代罕有匹敌者。《金楼子·著书篇》称,他著有《连山》《金楼秘诀》《周易疏证》《礼杂私记》《孝德传》等38 部,677 卷(实为666 卷),还不包括后来颇负盛名的《金楼子》。
萧绎初在南梁做湘东王时,自号“金楼子”,故仿皇甫谧之《玄晏》、葛洪之《抱朴子》以是名书。他好立言,欲以此建立名誉,名垂青史,在《金楼子序》里这样写道:“余于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由是年在志学,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萧绎本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梁简文帝萧纲的四弟,身为皇家子弟,出身高贵,诚如周公所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史记·鲁周公世家》卷三三)他最初不求“三不朽”的立德、立功,而取“三不朽”的“立言”,以臧文仲、曹子桓(曹丕)、杜元凯(杜预)为榜样,学王充“户牖悬刀笔”的勤奋著述精神,同时耻于西汉淮南刘安借宾客著《淮南鸿烈》、秦吕不韦仗门人撰《吕氏春秋》,而有志独立撰述,从15 岁开始从事《金楼子》的编纂,即所谓的“年在志学,躬自搜纂”;46 岁完成,这也是萧绎自己说的“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金楼子·聚书》)。萧绎说的“聚书”是图书的收藏,这一说法出现在《金楼子》里至少表明两点:一是《金楼子》的成书极可能是在这一年,因为次年他就悲惨地告别了眷念的人世;二是他收藏图书八万卷,这正是他《金楼子》一书的相当重要的文本之源。
陈志平在《〈金楼子〉研究》一书中说:“《金楼子》今存十四篇,共549 条,现在可以寻得出处的共345 条,抄袭比例高达62.84%。”这其实是萧绎独立编纂所致,照录原文或删削、修改后不变原意再编入书中,在萧绎以前也是常见的现象。萧绎由此导致的批评自当别论,这里要说的是,由于他收藏的书众多,选材入《金楼子》的结果,构成了《金楼子》的“兴王”“箴戒”等十四篇,每篇各为一个门类。清人张宗泰在《鲁岩所学集·书〈金楼子〉书后》对《金楼子》有一个概述,由此可知该书的基本内容如下:“《兴王篇》叙历代圣明之主,而终以其父武帝。《箴戒篇》叙古今乱亡之君。《后妃篇》说历代贤妃,而终以其母宣信后。《终制篇》明薄葬之义。《戒子篇》多格言至训,最可观玩。《聚书篇》述所得所写之书,凡八万卷。《说蕃篇》杂举古侯王善恶之事,以列劝戒。《立言篇》极修饰之功,而文亦博辩宏肆。《著书篇》所举撰著之书,及诸书序。《捷对篇》表古今应对之才。《志怪篇》辑异事异闻。《杂记篇》摭拾琐屑碎事。《自序篇》则自誉所长。”如是的编排,是旧时的体例。
上述除《自序篇》外,每一个门类的内容都相当丰富,像《兴王篇》《箴戒篇》等,皆通过历史的纵轴线,裒辑了许多相近的历史故事,揭示了许多生活道理,从而导致了《金楼子》重要的特点:博杂。有人称其为杂家著作,就是从这儿来的。对此,同样是在《〈金楼子〉研究》里,陈志平也略有批评,他说:“在这部书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儒家的影响,又可以找到对道家的引用;既可以看到作者对兵家的熟悉,又可以看到对佛教的兴趣,甚至于诵咒、占卜等方术,作者都曾学习。然而作者并没有将诸种思想和学说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想到将诸种学说总合在一起的办法就是摘抄,其结果是只见作者的博学,不见作者的创新。”而这与当时的学术风气相关联,其中理应有他父亲梁武帝萧衍的影响,萧衍就是一位好学而兼通儒、佛、道的帝王,著述同样丰硕,萧绎的《金楼子》怎逃得掉家传及社会文化趋向的濡染?
萧绎曾想借《金楼子》“成一家之言”,在我看来并未实现,录他人之言代其说话固然是文人习见的做法,但大量的摘录他人之言编入己书,不是“成一家之言”者应有的态度,但他因为这部书获得了名声则是真的。而这样博杂的《金楼子》,整理的必要是无庸置疑的,但一定会给疏证校注带来巨大的困难。志平君和清元兄亲历了这样的困难,他们以清乾隆时期的“知不足斋本”为底本,著《金楼子疏证校注》(以下简称《疏证校注》),并于2013 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问世。在这一时刻他们完全可以大松一口气的,却止不住在该书的“前言”中说:“《金楼子》内容驳杂,引事用典,错杂己意,加之后人辑录转抄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为正确解读和研究《金楼子》造成很大的困难,以至让人有难以卒读之叹。”我理解这种困难,也理解他们正是从中获得了疏证校注《金楼子》的巨大动力。在这一工作中,他们自呈用心:“此次整理,我们力争为学界提供一个新的方便使用的善本,为读者正确理解《金楼子》贡献一个可信赖的校注本,为学人研究《金楼子》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前言)这对陈、熊二人来说并非易事,耗时六年方毕此一役,可见用力之大。
刘跃进兄为《疏证校注》作序,归纳了该书的三个特点:一是疏证上,“作者仿前人校笺《世说新语》的方式,采取分段标号的形式,使检阅更加方便。……而后在校注中,将各类不同之处加以说明。这样处理,又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记载,从差异中寻求新解。”二是校勘上,“这些校勘,充分体现了清儒无徵不信的求是原则,作者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既省去许多繁琐考证文字,又可以理清出《金楼子》版本的流传系统。”三是注释上,“本书作者对于同时见于几部典籍的材料,均反复比对,选取最相同或相似之材料,或者选择撰著时代之最早者,若多种旧籍互可补充,则并存之。其余相同或相似旧籍,则注明‘亦见’、‘并见’、‘略见’云云,以供读者检索之用,而避繁冗。”这些都是很中肯的意见。在校注的形式上,作者受《世说新语》的启示,逐节编号、分段校注,果真是使读者阅读更为方便。不过,这是容易做到的事,最难的还是面对驳杂的《金楼子》所作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者并不畏难,经过努力,原本六万余字的《金楼子》在演化为《疏证校注》后,有了九十万字的篇幅,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料之书,这是十分难得的事。何况《金楼子》本身编入的前代典籍之文,或赖其得以流传呢。
对于《疏证校注》,作者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很大的意义。读者通过《金楼子》阅读,能知道萧绎叙录故事所本,无疑有助于对《金楼子》的认知和对相关文本的理解。作者为帮助读者,在疏证上“尽可能考明其出处,寻求其本源”。如《箴戒篇》第十四条“周厉王好利”,作者在疏证中引了《史记·周本纪》的厉王“好利,近荣夷公”和《国语》上的“厉王弭谤”,以见《箴戒篇》第十四条“周厉王好利”所本;又如《说蕃篇》第八条“昔藩屏之盛德者”,作者在疏证中引了《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河间献王传》、《汉书》传三十《艺文志》、《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说苑》卷一《君道》、《列仙传》卷上“玄俗”条、《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河间献王》等为证。这在《疏证校注》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是的行文风格也体现在该书的“校注”中,如《立言篇》第四十二条的“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昔燕昭重乐毅而惠王疑其能,魏武诛文举而曹丕收其集”。作者作注:“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引用了《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子产说的一句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说明出处而不另置一词。“昔燕昭重乐毅而惠王疑其能”引用《史记》卷八十《乐毅传》,又标明乐毅事迹详见《战国策》卷三十《燕策二》《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魏武诛文举而曹丕收其集”引用《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并标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由于作者引述的文字较长,不宜在这里再引述,但足以看出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具体做法。这使《疏证校注》更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和人生况味,而该书正是以此引读者入胜境的。同时,这一做法也极大地丰富了《金楼子》所叙的历史。应该说,把历史展开是古代学者为典籍作传笺时最喜欢用的方法,《春秋》之后而生“春秋三传”,固然有字义的阐释,但展开历史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做法,使读者得以了解故事的本事,不再凭抽象的记叙去想象历史的细节而真正地走进了历史。
这大概也得力于《金楼子》在很多时候的记叙或表达很简洁,它不把话说开或者说点到即止。如是有萧绎抄录的对象原本就浓缩,如《著书篇》第四十六条的“老聃贵弱,孔子贵仁,陈骈贵齐,杨朱贵己,而终为令德”,取自《吕氏春秋》的《审分览·不二》。也有萧绎在抄录的基础上又“删略节取”、“概括大意”,《杂记篇》第一条的“成汤诛独木,管仲诛史符,吕望诛任离,魏操诛文举,孙策诛高岱,黄祖诛祢衡,晋相诛嵇康,汉宣诛杨恽:此岂关大盗者?深防政术,腹诽心谤,不可全也”即是如此。这给校注者带来了再编纂的空间,因为这样的文字往往每一句都很深厚,使校注者大有可为。不过,作者要言不繁的校注具有两种风格,一种是以原作者的理论表述作注解,如“贵弱”,作者校注为:“《老子》第三六章:‘柔弱胜刚强。’第四十章:‘弱者道之用。’第七六章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另一种是以概括或总结性的语言作表达,如“贵仁”,作者校注为:“仁是孔子理想的道德境界。孔子之言‘仁’,著于《论语》最多。阮元《揅经室集·〈论语〉论仁论》:‘《论语》言五常之事详矣,惟论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见于《论语》者,凡百有五,为尤详。’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为一零九次。此孔子贵仁之一证。”二者相较,前者的实证让人有直接的感悟,后者的概括则多给人想象,激发人继续探究。这样说并不排斥《金楼子》有一些篇章展开陈述,让人容易明白事理,这与他对历史文献的抄录或说“照录原文”有关。如《兴王篇》第十二条讲述周文王的故事,抄录自《列女传》《史记·周本纪》等。《戒子篇》的第三条马文渊即马援戒子,本于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
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校注很自然展示了考证求真的功夫,如萧绎说自己聚书四十年,“得书八万卷”,作者说此非妄言,然后有下面的考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二十一》‘元帝承圣三年’载:西魏入侵,萧绎兵败,‘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此十四万卷包括萧绎私藏和得自建康之书。建康所藏国家书数,有‘七万’、‘八万’之异说。《南史》卷八十《贼臣传·侯景》:‘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载: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有云:‘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和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和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十四万卷书,除去建康所得,萧绎自己藏书确实不少。”这样的考证,力求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让读者更能明白历史的本色,当然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古代文化在战乱中的毁灭,这对于中华民族,是惨痛的损失和教训。可以注意到,作者所作的考证不限于历史事实,还有词义。如《兴王篇》第十一条“成汤姓子”的“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作者注:“干,各本同。《史记》卷三《殷本纪》作‘奸’。今按:干、奸均有‘干求’之意。《尚书·大禹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孔安国传:‘干,求也。’《说文通训定声》:‘奸,假借为干。’”这样的考证在比较和训释中见词义,词义益明而能旁通。如是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该书出版之前,台湾许德平先生《金楼子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所注甚简,而该书交付巴蜀书社并转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有许逸民先生的《金楼子校笺》(以下简称《校笺》)出版。相较而言,《疏证校注》做得最为完备,志平君在后来写的《〈金楼子〉研究》一书第五章“《金楼子》文本校释”中作了阐述。如失注者,《校注》未注《立言》的“明月之夜,可以远视,不可以近书;雾露之朝,可以近书,不可以远视”。《疏证校注》中作了疏证:“《淮南子》卷一七《说林》:‘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如补注者:《金楼子序》的“常贵无为,每嗤有待,闲斋寂寞,对林泉而握谈柄;虚宇辽旷,玩鱼鸟而拂丛蓍。爱静之心,彰乎此矣”。《校笺》注称“有待:《礼记·儒行》:‘儒者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孔颖达疏:‘言爱死以待明时’,‘言养身以行道德也。’”陈、熊二位的补注,增加了“无为:《老子》第三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有待:《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又五日而后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等,使所注更为翔实。如纠谬者:《戒子篇》有“单襄公曰:‘君子不自称也,必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吾弱年重之。中朝名士抑扬于诗酒之际,吟咏于啸傲之间,自得如山,忽人如草,好为词费,颇事抑扬,末甚悔之,以为深戒。”《校笺》注:“中朝,犹朝中。《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陈、熊注则引《世说新语·文学》的“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认定“中朝,晋室南渡以后对西晋王朝之称。”并引《晋书·王隐传》《世说新语校笺》为证。校注的失注和误注因校注者的学养己见或一时疏忽,总有可能发生,对其的修正、补注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必要的功夫,也是很有意义的。
话说到这里,《疏证校注》也有可以再完善的地方,如《后妃篇》7-5 的“或谓衣锦归乡”,作者注为“即‘衣锦还乡’,富贵后荣耀地回到故乡”,按全书的校注风格,此当为:《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还有说到方便读者,书眉除标明卷数之外,如能标明篇名,对于读者的翻检,会更便利一些。
总之,《金楼子疏证校注》是一部整理得很不错的读本,因为志平君和清元兄细密的功夫,让萧绎的《金楼子》少了谜团,能够以更清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使那一段历史与人生在他们对《金楼子》的疏证与校注中变得厚重。就此而言,二人的辛劳付出是值得的。
(责任编辑:王学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