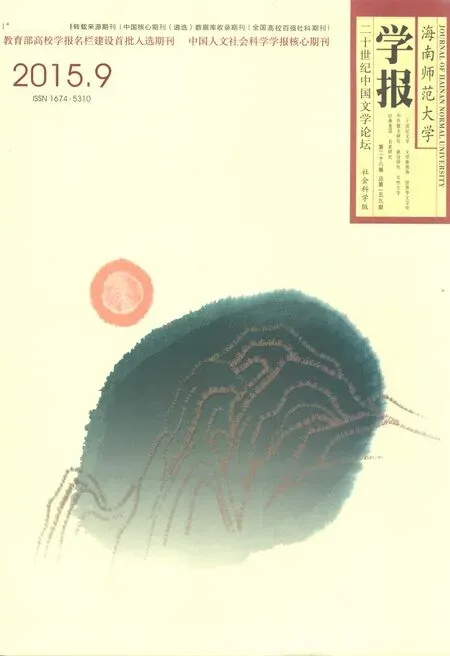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美学研究——当前中国美学界论争的批判性考察
2015-03-29王伟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350001)
20 世纪50、80 年代,中国美学界曾有过两次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在承认“美的本质”的前提下,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维度进行论证,形成了蔡仪派、吕荧派、朱光潜派、李泽厚派等不同的美学群落。如今,中国美学界再次掀起了火药味十足的大论争,“美的本质”依然是焦点话题。所不同者,它自身遭到了严重质疑,甚至被斥为“伪命题”。于是,在否弃者与捍卫者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往返辩驳。应予深入考察的是:对否弃者而言,美学研究走向了哪些不同的路径;对守护者来说,在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冲击下,“美的本质”发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它们各自又有什么意义与缺陷。
一、“美的本质”:一个伪命题
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学”始于1750 年鲍姆加登《美学》一书的出版。回溯起源,古希腊以来诸多思想家有关美的探讨无疑是其产生、建立的理论基础。而自柏拉图以来的两千多年之间,“美的本质”问题就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人们苦苦寻觅的扰人难题。直至1900 年,这种本质主义式的追寻之旅才戛然而止。从此,西方古典美学终结了,现代美学翻开了新篇章。[1]值得注意的是,主观目的与实际结果往往南辕北辙——“虽然西方现代美学都在标榜对美本质的否定或放弃,而事实上却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回答着何为‘美的本质’”。[2]譬如,美的直觉说(克罗齐),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美是客观化的快感(桑塔耶那),美是能激起性感的事物(弗洛伊德),如此等等。到了后现代反本质主义风起云涌时,西方美学才真正抛弃了“美的本质”这一形而上学的旧命题。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时段,中国美学界却热火朝天地走在探求美本质的征途之上,各路人马在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架内开掘出不同的美本质。不过,期间也有学者对哲人们的本质主义取径表示不满:“在美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亦即唯本质论是一种致命的思维癖性,它必然导致自以为是的算定论,表面看被陈述的理论很精致,逻辑上似乎十分周延,但实际上谈论的并不是美,充其量不过是美的影子。”但论者又认为“美的本质是一个准科学命题”,除了科学方法之外,更须以“悟性体验”去把握“美本身”。[3]20 世纪末,国内美学界逐渐形成了否定“美本质”命题的气候,李志宏、张法等学者堪称这股潮流中的健将。
20 世纪以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与分析哲学相继问世,它们将形而上学的命题贴上了“伪命题”的标签,也为语义-分析美学的诞生提供了哲学基础。在这种美学话语中,“美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命题。李志宏教授肯定了上述观念对国内外美学界的积极影响,又对其“在理论上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后期分析美学就重返定义“美”的不归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强调,“在语言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表示主观感觉状态的美概念被对象化、客观化,于是其原本的形容词的用法被改变成名词的用法,人们再从名词的一般认识出发,以为这一虚空的名词有着实在的对象客体内容,最终形成对于‘美’的误解”。[4]换言之,“美感念”是形容词向名词的转化,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天空、大地、河流等不同,“美”与世间任何的实体性事物都无法对应,因此,把“美概念”实体化的“美本身”或“美的本质”根本并不存在。应该说,这是李志宏反本质主义美学观的理论基点。近年来,他对此一再重申。譬如,“‘美’概念作为名词并不含有可以直接指代的对象事物,因此,不具备名词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实际上具有的是代名词性。以此为前提而形成的‘美本质’及‘美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是虚空的伪命题。”[5]他批评流行的美学体系“仍然把理论大厦建筑在关于美本质和‘美’的阐述之上。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混淆了‘美’字(即美概念)与‘美’(即美事物)的不同,把‘美’字的存在当成‘美’的存在。世上不存在叫做‘美’的事物,不存在美本质或美属性”。[6]另外,“‘美是什么’命题的形成过程是反逻辑的,是个伪命题,因此无论哪个学派做出怎样的解答都不能成立。”[7]李志宏不遗余力地抨击着美本质,与实践美学谱系中的诸多学派展开了仍在进行的激烈酣战。正是在这种论辩的过程中,其反本质主义的美学立场愈加鲜明而坚固。
李志宏劝告对方“悬崖勒马”——尽快放弃根本不能成立的“美是什么”命题,不要再在上面枉费心神,而是来一场美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把‘事物为什么是美的’这一问题重新设置为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具体而言,“美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是要解释审美现象,揭示审美活动的内在规律。落到具体问题上就是要问,美的事物是从哪里来的?事物为什么是美的?人为什么能形成美感?”[8]105与之前兀兀穷年的本质追寻相比,这种研究理路显得灵活而开阔。乍看之下,它与另一位反本质主义者的如下主张甚为相似:“对美学来说,就是要讲清楚,美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被解构的。具体来说,就是对自人类以来,各个文化、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美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人为什么要建构这样或那样的美,建构了这样或那样的美之后,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对心理影响是什么,在文化中有什么功用。同样,这曾经建立起来的美以后又被解构了,变得不美了,也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解释的。”[9]显然,美并非实体性事物,而是卷入了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漩涡之中,在与特定时空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阶级、道德等因素错综的关联中彰显出建构性。如果上述诸多关系项所组成的结构保持稳定,那么,美也将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继承性。反之,如果这一关系网络发生剧烈变化,那么,美就可能会有或整体或局部的变化,从而体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变异性。不妨说,一部美学史,就是美的观念在不同的文化场中“建构”与“解构”持续互动的历史——不难发现,“建构”/“解构”在精神、基调上和反本质主义美学尤为契合。让人有点儿意外的是,当李志宏教授正面阐述其“认知美学”理论时,以上观点中的政治经济学维度竟变得杳然难觅,而其中社会学的宏阔视野也在骤然间似乎缩小了。
他认为,事物是“内质”与“外形”的统一体,前者经由利害性需求的满足而引发肯定性情感,是为功利性的快感;后者经由知觉即形式认知而引起肯定性情感,是为美感。表现在审美上,有害事物引发否定性的丑恶感;反之,有利事物则引发肯定性的美感。“在事物有利性的基础上,事物外形已经在人脑中塑造出同好感相连接的认知模块;以认知模块为基础形成内在构造,人才能对相应事物的外形直觉地产生美感。”[8]108换句话说,事物要能产生美感,其内在价值必须对人有利,好感是第一步。第二步,其外形与已然成型的主体认知模块相吻合,从而引发美感。实际上,这两个步骤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将事物判然两分为外形与内质两块,并各自关联美感与非美感,不免有些机械。其次,把利害关系与美感/非美感直接挂钩固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可能遗漏了更为重要的方面。譬如,李志宏所举“狼”的例子。他认为,狼长期以来危害人类,形象丑恶,“不能被审美”;随着生态恶化,狼成了保护对象,危害变小,在生态环境方面显示出有利性。于是,“狼的形象也可以被审美了”。[10]问题是,这如何解释远古时期蒙古民族的狼图腾崇拜?对先民们而言,成群而凶猛的狼无疑是有害的。他们先是恐惧,再是敬畏,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亲属与同类。成吉思汗时期,甚至将狼视作神兽。退一步说,即便是有害事物,也仍然可以被审美,成为审美对象。譬如,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文艺热衷于将“美帝国主义”想象成“豺狼”。而今,“七匹狼”又成为中国消费市场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不难发现,仅靠利害关系,难以解释清楚审美史中的“狼”的变化。
再次,关于认知模块,虽然它是“动态发展的,有一定的弹性”,但这种弹性指的是其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功用,并未涉及其生成的具体环境。李志宏还强调,它是“大脑神经活动自动完成的,不为人的意识所觉察”,“尽管人的所有认知模块必有其形成的过程和具体的原因,但人们未必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觉察到;人对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知觉偏好,有的能找出原因,更多的是找不出原因”。[8]109鉴于美感是事物外形与认知模块共鸣而产生的,因此,在逻辑上,要说清楚美感的产生,就不能在认知模块面前止步,还须追究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普通的男男女女不明了自己的知觉偏好,那么,美学研究就有责任把它说清楚。毫无疑问的是,教育是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之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柏拉图《理想国》中说:“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11]从中不难看出,美学规范对于教育传承的依赖,美学成规对于人审美趋向的形塑。不言而喻的是,教育跟文化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纠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区别性的权力已经侵入到课程和教学的中心。”[12]既然如此,审美就绝非在真空中进行,绝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之事。正是秉持着这种观念,伊格尔顿坦率地说,自己在写作《审美意识形态》一书时,“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同时,“确实想驳斥这样一些批评家,他们认为,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任何联系都必定是令人厌恶反感的或是让人无所适从的”。[13]凡此种种,也都是我们讨论美感时不能刻意回避的话题。
二、“美的本质”:美学基石
针对中国当代美学领域中的美本质“伪命题”论调,张玉能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美的本质”是任何一种美学体系都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是美学研究的“灵魂”,它规定了一种美学研究的“基本性质、基本导向、基本原则”。换言之,“美的本质”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了这一环节,美学就根本不成其为美学。耐人寻味的是,他还强调“我们当然要反对本质主义,但是不能一概地反对研究和探讨‘美的本质’问题”。[14]特别需要注意,这似乎意味着他与反本质主义者多有共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对中外美学的反本质主义区别对待。就西方而言,他认为分析哲学“美的本质是个伪命题”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美学的质疑、反思和批判。就中国来说,“伪命题”不过是重复、贩卖“早已被提出者们都疑惑而抛弃的东西”罢了。问题是,如果中国美学界的“伪命题”攻击的也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美学的话,又有何不可呢?其实,在反本质主义者那里,张玉能“美的本质”恰是这样的东西。应该说,张玉能自己反对的“本质主义”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美学,但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在反本质主义汹涌如潮之时,对于本质主义,学人唯恐避之不及。究竟能否成功避开,重要的是要看美学研究的运思模式与问题设置等等。李志宏批判“美是什么”将“美”实体化,作为回应,张玉能提出:“美”确实并非一个实体或实体对象,否则,就会进入形而上学的死胡同。而“19 世纪中期马克思开始的‘现代实践转向’却从实践本体论的社会本体论出发,终结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路,而开启了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本体论的思路”。[15]38即是说,美是一种关系存在。正因如此,他指责“伪命题”论者用实体化的“美”来否定自己关系型的“美”,纯属“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关键在于,这种关系型的“美”是什么,有否真正关系化。依照其实践的理路,关系应该是社会实践中的关系,是制约“美”形成的关系网络。然而,在张玉能看来,关系或关系存在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性质状态,也就是把万事万物相互区别开来的内在规定性或者外在规定性,也就是现象和本质的性质状态”。[15]38让人困惑的是,这种内在规定性-外在规定性、现象-本质的二分法不正是本质主义的突出表征吗?其本质主义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宣称“人们必将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对美的本质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认识、有所前进,不断地接近美的本质的绝对真理”。[16]102“美的本质”如同一个先在的宝藏,等待着男男女女去挖掘,美学研究宛然一场永无止境的“寻宝游戏”。令人怀疑的是,世间有否这种光芒万丈的绝对真理?我们是否需要这种“大而无当”的真理?离开了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真理是否还能成立?显然,所谓的“关系”并未真正沉入实践,“美”当然也未被置入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进行考察。
更为令人瞠目的是,一方面,张玉能认为“否定美的本质和‘美是什么’的问题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是一种鸵鸟策略,不仅无益于美学理论探索和研究,而且还把自己理论的丑陋之处暴露无遗”,[15]41另一方面,他又认为“20 世纪90 年代的‘后现代实践转向’则把‘美的本质’引向了多层累、多视角、开放性的研究和探索途径,给‘美的本质’打开了新思路”。[16]98殊不知,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核心精神,正是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前提下,才有开放性研究的诞生。“美的本质”与“后现代”有着迥然相异的思维模式,它们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一边责斥反本质主义的丑陋,一边却又汲取其营养,为“美的本质”极力辩护。张玉能教授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之处,他甚至从德里达的“意义异延论”得到启发,推论说:“美的本质”并非固定不移、一成不变,而是一种不确定性,有的只是不断“异延”的“美的本质”的“痕迹”。在德里达那里,文本的意义最终也没法确定下来。相比之下,对张玉能来说,本质虽在延异,形成相对真理的痕迹,但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重演从量变到质变的传奇,接近绝对真理。问题是,回头来看,所谓的“绝对真理”不就是那个稳如磐石的本质吗?它又何尝“延异”过呢?而且,经历过“后现代实践转向”的美学,怎能容下“绝对真理”?因为“从哲学上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17]不难发现,在张玉能美学话语的内部,聚集了一些“旧瓶”与“新酒”之间尖锐的龃龉与冲突。这自然源于他对长期从事的美本质探寻工作依依不舍,却又试图撷取勃然兴起的反本质主义为我所用。结果必然是,反本质主义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何时就会引爆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美学大厦。同是主张本质的流动性,另一位学者指出:“不存在任何超历史、超现实的先在本质,所有的本质都属于流动的、不断生成的东西,美的本质随着主体审美与艺术实践活动不断展开,它总是指向于一种符合历史及现实的‘整体性诉求’(歌德)。并在这种诉求中获得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人类美的本质的探索历史与人类文明史同步。”[18]与张玉能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绝对真理”,所有“本质”——美学观念、规范、趣味等——都不能超越历史与现实,而是处于历史与文明的结构之中。拯救“本质”的类似做法还有,提倡本质不是绝对与永恒的,而是相对与发展的。[19]这些无疑已经倾向于放弃本质主义,只不过囿于惯性,仍对“本质”一语恋恋不舍而已。
杨春时教授也对“美的本质”问题情有独钟。他认为,传统美学依据的是实体本体论,“美”成为实体,而非对象。所以,“美的本质”问题不合理。应该转向存在本体论,“由研究美的本质改为研究审美的本质,而把美的本质问题从属于审美的本质问题”,“我们不谈论美是什么,而先考察审美的性质,作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意义的美的本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0]也即是说,放弃了美的本质,树立了审美的本质,两者并非一物,后者的解决为前者的解决打开了大门。蹊跷的是,在探寻审美本质的过程中,杨春时干脆不再区分,又将它们一锅煮了:“所谓美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审美的本质,而审美的本质也就是审美的意义。”[21]那么,如何“发现”审美的本质呢?杨春时认为有三步:先要采用现象还原的方法,进入审美体验,获得审美意象;继而一度反思审美体验,获得具体的审美意义——审美范畴;再是二度反思审美体验,获得更根本的、最一般的审美意义——审美本质。从对现实意识和现实观念的排除,以保证审美体验的纯粹性,到主体能动性的备受重视,丢弃制约主体的外在因素,再到时间停止、空间消失的大化境界,他一步步构建起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形而上审美王国。问题是,“人们不能轻易地将审美体验从所有非审美体验那里划分出来,也不能轻易地将审美体验与所有非审美体验断然割裂开来”。[22]即便区分了,也须铭记“康德给我们准确描述的美的经验具有康德所不知道的经济和社会的可能性条件”。[23]获取审美意义,反思不妨算是方式之一,但完全仰赖它就明显欠妥。毕竟,男男女女可以直觉把握的审美体验是历史的产物,“是艺术的体制领域和反复灌输的审美沉思习惯这两个方面相互支持的结果”,而它们都需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方能确立,[24]远非关起们来闭目反思那般简单。诚如布尔迪厄所言,追求纯粹的学者们往往“把自己的经验(一个来自特定社会背景的有教养者的经验)当作反思主题,但是,并未聚焦于这一反思的历史性,以及反思对象(即对艺术品的纯粹体验)的历史性。因此,纯粹的思想家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单一经验确立为适合于任何审美感知的超历史性标准”。[25]当杨春时教授将审美的本质定格在“自由”上时,超历史性就更为显眼。因为自由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词语,而是涉及到谁的自由、怎样的自由、多大程度上的自由等等棘手的问题。
另外,如果说审美的本质就是自由,那么,审美与自由还有什么区别吗?说审美是通向自由的桥梁是不是更为合适?一旦将自由作为审美的最高阶段,所有审美体验的“二度反思”必然如出一辙——坚持不懈地朝着自由的目标进发。关键是,纷繁复杂的审美体验需不需要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本质性规定?它们是否一定要进行所谓的二度反思?就同一个审美对象而言,当这个标杆指引下的审美体验与其它的审美体验之间并不完全相同时,如何处理?譬如,杨春时以《红楼梦》为例,指出:一度反思得出了它的具体的审美意义——一个人生的悲剧,二度反思就可以让我们在人生命运的痛苦体验中,领悟对自由的追求。问题是,它如何看待其它对《红楼梦》的审美体验,譬如:自叙传,人情小说,阶级斗争,着意于闺中,彻头彻尾之悲剧,揭清之失、悼明之亡等等。
三、“美的本质”:折衷与回避
如若“美学基石”与“伪命题”是看待“美的本质”问题的两个极端,那么,还有一些较为温和的意见与做法在此间游移。譬如,朱立元教授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他认为过去美本质的讨论往往把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作为美学研究最核心的问题,这对美学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提问方式和思考理路本身就是二元对立的,易于陷入本质主义泥沼。所以,他认为“美的本质”不是不能讨论,而是不应将其实体化、固定化、抽象化。在实际的研究中,“美的本质”风光不再,被“美是怎样生成并呈现出来的”所替代,“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及其现实展开——审美活动、审美实践”成为美学研究新的重点。除了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范式的转换——从现成论到关系论和生成论:“从根本上说,美学所遭遇到的一切哲学问题都导源于人生在世这一人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总问题。因而美学的哲学基础应当从马克思以实践为中心的存在论及关系生成论出发,突破主客二分的现成论思维方式,深入到人与世界一体的本真关系中,深入到人的生存实践即人生实践中,深入到人与世界双向生成的境域中,体悟、反思和探讨人类无限丰富和永恒变动的审美关系和审美现象。这就是人生在世的关系论所展示出来的美学研究的哲学视野,这也就是实践存在论美学所依托的哲学基础。”[26]显而易见,“关系”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关系,是男男女女与大千世界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关系,是在复杂变动中不断生成与发展的关系。与张玉能区分现象-本质的“关系”相比,这种对“关系”的定位显得十分到位。简而言之,所谓“关系”,就是特定历史时空、特定关系结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中,美是不断被建构与解构的东西,永恒的“美本质”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美”如此,“文学”亦然。不过,朱立元先生并未把这种精神贯彻到文学中去,转身又对文学的“审美本质”呵护有加。他表示赞同如下说法:“在过去千百年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文学的形态和概念怎样变,作为文学‘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并没有根本改变。”[27]即是说,审美本质足以跨越历史时空,成为界定文学、解释文学不变的标准。问题在于,审美果真是文学不变的本质的话,那么,何以汉朝会把《诗经》的首篇《关雎》释为“后妃之德”,而如今我们则将它看作一曲爱情的礼赞?很明显,至少在汉代,审美并非解释文学的标杆。当人们热情地坚守“审美本质”的脆弱堡垒时,有必要重温比格尔的告诫:“审美理论家们也许会竭其所能,以求获得超历史的知识,但当人们回顾这些理论时,就很容易发现它们清楚地带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如果审美理论具有历史性,那么,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那种企图阐明这种审美理论的作用的艺术批判理论,本身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换句话说,它必须将审美理论历史化。”[28]可资对照的是,朱立元也强调不应寻求永恒不变的本质,还明确说“中国古代有诗、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等等文体,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逐步被以审美为共同特质的‘文学’概念统摄为一个整体”[29]。既然如此,又如何能说“审美本质”是亘古不变的呢?审美能够有效概括从古到今的文学,并非它没有改变过的理由,因为审美是一个回溯性的标准。
此外,叶郎教授早就不满于陈陈相因的美本质研究,认为作为美学研究对象,它太过形而上了,“必然超越归纳与综合,而进入纯粹思辨的王国,因此会忽略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30]所以他转向审美活动,着重探究审美形态、审美意象、审美感兴、审美文化、审美体验、审美发生等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他将“美”置于历时与共时的多重关系网络中进行研究。他还另辟蹊径,借助探讨中国传统美学“美”在意象的命题——“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它能够“照亮一个真实的世界”[31],强调并不存在什么实体化的“美”,“美”既与人的审美活动息息相关,同时又并非纯粹主观的。从研究理路上看,叶郎的美学力图在接续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建构能与西方美学形成对话关系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美学。
目前为止,美学界的反本质主义成效显著,即便是那些曾经的本质主义者也放弃了美本质的宏大叙事,退而主张美本质的多元化。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学者口上说着要摒弃本质主义,但一俟遇到具体的研究,却又时不时地回到本质主义的老路。总起来看,反本质主义的目的是要解构形色各异的对美学问题的形而上学玄思,转向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美学问题,转向生龙活虎的美学实践,转向美学与现实的复杂纠葛。正因如此,美学才会接纳商品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等诸多新的课题,成为一门开放的学科,一门富有活力的学科。事实证明,没有了永恒不变的美本质,美学学科不仅并未垮塌,反而在实现了问题式转换之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焕发了新的勃勃生机。
[1]张法.重新定义1900 年以来的西方美学[J].求是学刊,2013(2):110.
[2]莫其逊.西方美学美本质研究的哲学基础[J].思想战线,1999(4):84.
[3]徐宏力.论美的模糊性[J].社会科学,1989(2):68,70.
[4]李志宏.“美是什么”命题辨伪[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2):6.
[5]李志宏.美本质研究将怎样终结——再论“美是什么”是伪命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61.
[6]李志宏,等.根源性美学歧误匡正:“美”字不是“美”——兼向张玉能先生及实践美学谱系请教[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42.
[7]李志宏.“美是什么”的命题究竟是真还是伪?[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1):121.
[8]梁玉水,李志宏.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对话的路径与理论建树[J].文艺争鸣,2014(8).
[9]张法.为什么美的本质是一个伪命题——从分析哲学的观点看美学基本问题[J].东吴学术,2012(4):44.
[10]李志宏.认知科学美学与审美机器人[J].晋阳学刊,2012(2):56.
[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08.
[12]〔美〕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13]〔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
[14]张玉能.实践转向与美的本质[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2(6):6.
[15]张玉能,张弓.为什么“美的本质”不是伪命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5).
[16]张玉能.后现代实践转向与美的本质[J].河南社会科学,2014(1).
[17]〔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18]邹诗鹏.美的本质:消解、追问与回归[J].求索,1995(3):59.
[19]孙伟科.“美本质”的思辨[J].南都学坛,2000(5):50.
[20]杨春时.关于美的本质命题的合理性问题[J].中文自学指导,2005(2):15、17.
[21]杨春时.审美本质的发现[J].学术月刊,2014(5):102.
[22]〔英〕舍勒肯斯.美学与道德[M].王柯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20.
[23]〔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08.
[24]〔美〕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M].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
[25]〔法〕布尔迪厄.纯美学的历史起源[C]//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7.
[26]朱立元.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J].湖北大学学报,2014(5):31.
[27]赖大仁.当前文学面临的危机不容忽视[J].学术月刊,2006(6):43.
[28]〔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9.
[29]朱立元.后现代主义文论是如何进入中国和发生影响的?[J].文艺理论研究,2014(4):14-15.
[30]叶郎,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
[31]叶郎.美是什么[J].社会科学战线,2008(1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