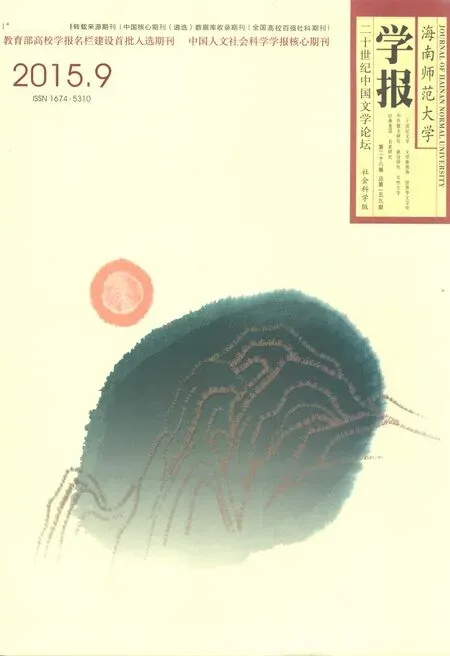新世纪“反右”题材小说的三种倾向
2015-03-29刘煦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5310( 2015)-09-0041-04
收稿日期:2015-05-15
作者简介:刘煦( 1992-),男,河南确山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57年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历史强制地造就了一个特殊人群:右派。“反右题材小说”就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文学词语。“反右”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反右题材小说”已经蜕变成一个相当成熟的小说类型。我们在不同时期“反右题材小说”的参照阅读之中可以发现,新世纪之后的“反右题材小说”呈现出了比较明晰的三种倾向。
一、结集或长篇成为偏爱
“反右”题材小说反映了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多样化昭示。“一场反右运动,就这么将中国知识分子定了‘形’,也将中国社会民主不复存在的状况写了‘形’。可以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极权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 [1]在对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上,早期的小说家有自己的考虑。张贤亮在《绿化树》的题记中这样说:“我要写一部书。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2]张贤亮所说的这一部书就是《唯物论者启示录》,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政治诉求浓郁的名称没能成为9部“中篇系列”的总概括。但早期的“反右”题材小说作者们是有用“部”代替“本”或“篇”来表达苦难的意识可见一斑。这种中短篇结集,成为内部互相联系的多声部复调的构思,在新世纪的“反右”题材小说这里基本成为了现实。
杨显惠的大部分小说,2000年春季首先在《上海文学》连载,后来才集结成册出单行本。《夹边沟记事》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而此书又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合称为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中国一九五七》又分为四部分:京畿秋千架、清水塘大事记、御花园遥祭、我乐岭人物志,以35万字的篇幅叙述了“右派”分子周文祥如何中了“引蛇出洞”的政治陷阱到辗转祖国偏远地带四处劳改的历史悲剧。单就对于苦难的篇幅处理来说,大部头的长篇叙事是作者偏爱的类型,俨然已成为深重苦难量化之后的隐喻。评论家雷达说:“长篇被称为‘生活长河’小说,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于是,称它为百科全书,为纪念碑,为史诗,视它为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标志。这种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的经典性表述。” [3]
为什么新世纪“反右”题材小说会以浓重的大长篇来傲视以往时段的“反右”题材小说?应该有几个原因。首先,“反右”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沉淀“反右”的历史,为小说成型提供了时间保证。早期的“反右”题材小说还脱不掉政治话语的痕迹,很大原因是由于历史事件的余威尚存,作者本身还没有完全从政治话语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更自由的时间仍然没有开始。新世纪的到来,使得“右派”小说的作者意识到“反右”这段历史似乎发酵到了一个可以出炉的地步,这发展成为一个契机,带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精神上路,长篇就历史性地成了首选。
其次,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大趋势的催化,历史已经不再单纯的是职业性研究者案头的工作,而且成为普通大众的审美热点,民间审美与精英文化可以坐在一个桌子上谈话,“反右”题材小说隐含地存在巨大的读者群。在市场需求的驱使之下,中短篇分量似乎不足,戳不到读者的兴奋点,长篇更易受到关注,起到反响。随着市场化多样化的到来,学界专才的精英意识不再起主导作用,民间大众审美的多样性与之并行不悖,使得长篇小说功能扩大,为“反右”题材小说的作者提供了方便驾驭的叙述形式。
再次,新世纪的“反右”题材小说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已经积聚到一定程度,思想上趋于饱和,似乎已经到了不写长篇不足以抒郁结、展才情的地步,于是顺着世纪末总结反思的东风大写特写。不少“反右”题材小说产生于世纪之交,虽然发表在新世纪,但构思阶段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长篇写作井喷的习惯在此时得到了承袭。写作者主观上有浓重的表达欲望,这成为长篇大部头的“反右”题材小说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叙述态度渐趋客观冷静
个体苦难在尘埃落定之后就上升到了历史的反思。真正的反思需要客观,需要冷静,真正的反思是巨大疼痛之后对伤口的复查审视,而不只是简单消毒处理。陈忠实在《白鹿原》开篇就引用巴尔扎克的话用来强调: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反映在“反右”题材小说这里,实际上就是对本民族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的一个回顾与反省。评论家们习惯于将上世纪80年代的“反右”题材小说定位于“反思”之列,并将这种论调在文学史教材上定格。30年过去了,我们重新审视这批80年代“反右”题材小说的时候,发现作品带给人们的反思色彩并非那么浓重,“右派”小说家们本身的“右派身份”这一基本属性所蕴含的不平之气渗透到作品里,更多地是杂糅了集体无意识,并且受到政治、法律、历史等客观条件的规约,其价值更多体现于小说史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究其原因,只是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艺术化还原,而非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而我们所渴望的叙述真实却是韦勒克说的那样,“小说虽然没有真实那样奇异,但却比真实更具有代表性。” [4]
不可否认,“反右”的历史降临在每一个“右派”身上都是个体的苦难史。当“右派”乃至整个民族被时代政治裹挟,被残酷迫害以至于失去个体生命的价值,这种痛苦和创伤是巨大的。伍尔夫说:“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5]那么大的悲痛,难道还要求客观冷静?答案是肯定的。甚至更加要指明的是,越是惨痛的记忆,越要被我们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铭记,否则不仅是对过去的亵渎,也是对后世之人的不尊重不负责。张贤亮在《张贤亮自选集·自序》中不无自负地坦言自己有一定的敏感性和超前感,在“性”“城市改革”“中学生早恋”“知识分子下坡路”等方面的写作,都是“第一个”,“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6]今天我们当然不必先去纠结张贤亮话语的正确性与否,就“反右”题材小说来说,张贤亮的确起着某种先驱作用。这种先驱作用首先表现在以“右派之身”写“右派之事”。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张贤亮这一批被打倒的“右派”复出之后当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是新世纪之前一些时段的“反右”题材小说审美价值所在,前人之述备矣,这里不再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期伊始,“反右”题材小说的作者们还是有不少禁忌的。这种禁忌明显地表现在对“党”和“革命”的充分认同。张贤亮在给李国文的信中说:“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 [7]牢狱灾难和贬抑经验教会了张贤亮小心翼翼的生活智慧,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王蒙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激情呐喊:“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我们属于党!党的形象永远照耀着我们!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向着党。” [8]从《布礼》中的钟亦成到《蝴蝶》中的张思远,从《春之声》中的岳之峰到《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王蒙笔下“右派”故事的建构及其艺术形象的创造大都以自己为“原型”并伴随了小说家本人在艺术方法上的多样性探索。作为“反右”亲历者,王蒙毫不犹豫选择了近乎政治英雄的主人公形象,这就使得小说文本逃不开“自叙传”色彩带来的局限。联系王蒙后来的文学创作以及政治走向——步入文学要津,走上政治高位,直到2002年出版《青狐》实则是对革命男性的某种正名,七八十年代的发声呼喊也许更容易理解王蒙的创作心理对政治语言有所保留的倾向性。近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恰切的描述:“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的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9]种种经历和禁忌决定了早期的“右派”小说家们不可能以一种扎实冷静的叙述态度进行创作。所以要打破禁忌局面,实现更客观更具有普遍性的“反右”题材小说的叙述,需要新人出现。
新世纪的“反右”题材小说写作情况有所不同,“已经没有那些‘右派’作家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而是以直面人生的态度,将历史的大幕全然拉开。” [10]作家本人非“右派”,甚至根本没有亲历“反右”年代,显然,他们对于“反右”事件的了解完全来自教科书、民间传闻、网络搜罗等间接经验。换句话说,新世纪“反右”题材小说的叙述者与作者是“分离”的。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夹边沟记事》的扉页书影上着重显示“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报道”,意在强调它采取的是一种类似报告文学式的叙述手法,叙述者与作者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分离,读者也不再受制于作者的观念及情感的牵绊,由于文本是由讲故事的“我”,即作为作者的“我”所采访的历史见证人所讲述的,这样一来就实现了读者和文本进行自由的“对话”,而此时的作者“我”和读者都是听者,在表层叙述里地位是平等的。这种更加客观、更具有普遍性的叙述视角拥有了更真诚更理性的立场和态度,其表达效果是80年代“反右”题材小说所达不到的。《中国一九五七》是一部“右派”的精神档案,正是通过“右派分子”周文祥的遭遇来对“反右”历史乃至到“文革”结束的历史的回顾,给仍在辛辛苦苦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探索人性秘密和真理过程的当代人以警醒反思。“尤凤伟没有把反右题材处理得声嘶力竭或血淋淋的(很多人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没有因为自己对这段历史有特殊的承担,就在小说中哭喊着要人记住什么,而是通过绵延在语词中的那些触手可及的真实,悄悄地把读者带回到历史的现场,使他们与那些受难者一起感受那种脆弱、无告的心灵节律。” [11]暴力和血的事实并非只有“以暴制暴”的表达才准确,相反,一种润物无声的心灵律动史应该饱含客观的警醒。正是身份上的“不亲历”,才为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提供了可能。这也恰如杨显惠所言“只有后来者的书写才能使‘反右’叙事真正具有深刻性,才能逼近历史的真相” [12]。我们向来所持有的历史观应该是历史并非一个个的历史事件的集合,而是整个人类精神延续与发展的过程。历史从来就不是过去,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不仅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和时代的缘故,而且是为了整个过去和整个未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世纪“反右”题材小说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所贡献的“不只是在‘创新’‘时代文学’,也不只是在反思‘国家文化’,而也是在思考‘社会文明’” [13]。
三、民间意识的凸显
如果说叙述态度是小说建构起来的皮肤,那么民间话语意识则是新世纪“反右”题材小说”内部的肌理。张贤亮塑造的章永璘形象从追求劳动者身份认同到恢复知识分子身份“记忆”的自我重构,这一艰难历程是在审视与被审视的“爱情”掩盖之下实现的。这对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①只重视宏大叙事而相对忽略个人心理的微妙变化来说是一种进步。《绿化树》中的马缨花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是张贤亮小说中两个突出的女性形象。马缨花的“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爱情名言。但我们反观这句话,似乎脱胎于古代戏文的语言充斥着理想化的爱情色彩。不仅女人在张贤亮笔下是理想化的,章永璘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也是理想化的。他既渴望马缨花的爱情滋润,又时时不忘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用《资本论》进行自我超越。“白天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14]“朵连格莱”式生硬的词语常常越权进入文本,强行使故事主人公蒙上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无不显示了一个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叙述身份。
由于张贤亮的处理方法是大段的《资本论》原文在文本中的多次复现,以至于某些情节出现明显脱节生硬的现象,使得章永璘的理性意识过于出位,成为政治传声筒的流弊产物。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黄香久,张贤亮仍然没有消除这种理性主义者的烙印。章永璘对黄香久缺乏对马缨花那种“宝石般的指纹”的感动,始终停留在“性大于爱”的程度,采取的是“你是什么男人都可以,我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行”这样的言语报复,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身份的禁锢,对章永璘来说,这是隐藏在心底的阶级理由,任何时候只要需要都会拿出来作为自己超越的借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抛弃女人而去追求所谓的更高理想。一直存在理性主义者气质的根本原因是作者张贤亮本人的知识分子身份所具有的理性情结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嫁接。正如许子东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张贤亮在玩味苦难时,却一直没有摆脱某种‘士大夫’意识,处境即便再险恶、忏悔再严厉,潜意识里仍有一种与众不同甚至超越平民的落拓感。” [15]张贤亮在小说创作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影响了民间意识和人文精神无法得到更客观的处理方法。这种缺陷在新世纪小说这里得到了某种弥合。在苏州大学演讲时,尤凤伟提到“在历史学家失语的情况下,作家不能漠然置之。而文学对于历史的呈现与诘问,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责任” [16],“我知道我的这本书的未来品质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的真诚度”。 [17]这种真诚实际上就是向历史真实致敬。如何表达这种真诚,毫无疑问,尤凤伟采取的是一种民间话语的方式来言说和讲述。“一部小说表现得现实,即它对现实的幻觉,它那使读者产生一种仿佛在阅读生活本身的效果,并不必然是,也不主要是环境上的、细节上的或日常生活上的现实。” [4]我们之所以感觉新世纪“非亲历”比之前“亲历”更加真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意识渗入的结果。
新世纪“反右”题材小说的写作者通过反思历史来反思当代,用民间的视角来揭示出被主流意识压倒或曲解的个人世界。在《中国一九五七》中,通过民间意识的渗透对“反右”历史的回顾,给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苦苦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探索真理的迷茫中的现代人以内心的震撼和灵魂的提升。真正优秀独立的民间作家都是能坚持自己个人价值,与自己内心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新世纪“反右”题材小说民间意识的凸显着重表现在拯救方式的变化——从他救到自救的蜕变。早期“反右”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在反思自己罪恶之身的同时,一般采取借助于超越性的精神源泉进行他救,如《灵与肉》中的章永璘对照《资本论》进行救赎,《布礼》中的钟亦成“虔诚地等待着空中伸来的饶恕之手” [18]。新世纪的“反右”题材小说知识分子的拯救方式发生了变化,多采用自救,其创作十分明显地体现了站在民间立场上的个人精神自由,这种民间意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五四”自由精神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