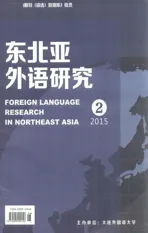论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关于“华夷思想”的谬误
2015-03-29范业红
范业红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论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关于“华夷思想”的谬误
范业红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在日本学术思想史上,有诸多关于国家主体的论争,其中一个重要论辩主题就是“夷夏之辨”(即“华夷之辨”)。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些学者对“夷夏”问题十分敏感,其中古学派的山鹿素行意图否定“中华”或“中国”之称专属汉土,认为日本亦是“中华”,即为“中国”。其著作《中朝事实》①是一本典型的相关“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著作。在该书中素行欲从“皇统论、水土论、武威论”等角度证明日本乃高于“外朝”中国的文明之国。但素行并非完全否认传统儒家价值观下的华夷观念,从这点上来讲,《中朝事实》中似乎有着两种华夷观念的交融。本文试通过这种观念交融来探究《中朝事实》的特色,并揭示素行在解读中国式华夷思想时所产生的思想谬误。
山鹿素行;《中朝事实》;水土论;武威论;皇统论1
一、《中朝事实》的写作成因
在言及近世日本的对外意识时,两种华夷观尤为值得关注。其一为传统的中国(儒教)华夷观,另一个则是以中国华夷观为模板而创出的所谓的“日本型华夷思想”。两者都是以自身的价值基准为依据,将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进行有序差别对待的“本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以“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作为判断“华”与“夷”的基准,而后者则更倾向于从“皇统一贯”和“武威”等的角度来确认自身的“中华”地位。
山鹿素行是在论及“日本型华夷思想”时不可避谈的一位江户时期的思想家,可称为日本“破宋学之嚆矢者”(转自田原嗣郎,1970:454),其晚年作品《中朝事实》是江户时期儒者的中国论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②,在这部作品中素行试图完成展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正统性、独特性与优越性这一“壮举”。
从书名可知这是一本以日本为“中朝”、把“神话”当作“事实”,强烈表达国家主体性的书籍。此书分为上下两部,通过各个篇章的详述进而得出结论,“真正的世界中心并非中国,而是日本”。素行将中国经典中常见的“中国”一词所指涉的对象和内容进行了大胆、狂妄的转换,以“皇统一贯”和“武威”观念为依据,主张日本优越性的“日本主义”思想。素行将“中朝”日本视为“文明”之国的依据追溯至“神代”和古代,他妄想借此段历史来证明日本即“中国”,同时也是最文明的先进之国。
素行曾被德川幕府流放到赤穗,在途中他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而著书《配所残笔》。在这部书中就已经蕴含了欲著《中朝事实》的意图。素行(1940:592)自认曾经“好异朝之书物,日夜勤于勉学”,由此而“不觉中感异朝之事诸般皆宜”、“本朝乃小国,何事皆不及异朝,圣人也只出于异朝”,这种想法“不限于我等,古今之学者皆如左样,慕异朝之事”,然而“近比始觉此乃谬误”。而之所以陷入这种“谬误”,是因为“信耳不信目,弃近而取远,不及是非,是学者之通病”,于是乃“于中朝事实详记之”。
在《中朝事实》的自序中素行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该时代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美”,而只是一味地嗜读中国经典,一味地敬慕中国。对此种倾向不甚认同的素行发出“‘中国’(指日本)的水土卓尔于万邦,人物精秀于八纮”的自我赞美。这也可以说是素行向“日本中朝主义”(转自堀勇雄,1959:243)思想转换的开始,其中已经有了“日本型华夷思想”的端倪。
“恒观沧海之无穷者,不知其大;常居原野之无畦者,不识其广,是久而狃也。岂唯海野乎?愚生中华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之经典,嘐嘐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丧志乎!将尚异乎。”(山鹿素行,1940:226)
但在《中朝事实》自序中值得注意的是,素行并没有完全否定儒教的华夷观念。正如他说自己“生于中华文明之土”那样,实际上仍然是以“中华文明观”为前提。儒教的华夷观是以“礼”作为“文明”的指标,素行也仍然是以“礼”之有无来区分“中华”和“夷狄”。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素行“固然强烈地认同日本文化与政治,却也怀有炽热的中国情怀。素行虽力倡日本为‘中朝’,但他却也‘师周公孔子’”(转自黄俊杰,2010:47)。
盖人之为人,本朝之为中华由此礼也。夷狄亦人,而其国亦治;禽兽亦物,而其群亦类。然所以为其夷狄也,为其禽兽也,不由礼而行之也。人而无礼,则不异于禽兽;中华而无礼则不异于夷狄。故神圣建教于初,天神惩戒于无状,以正其礼矣。
(山鹿素行,1940:305)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礼”,虽身为“中华”亦不免沦落为“夷狄”。这种想法仍是基于中国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文明观。“华夷思想”的发展轨迹是与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华”与“夷”的划分上,文化礼仪可以看成是唯一的标准。在“礼”这一标准下,“华”与“夷”的地位不再固定不变,由此看来素行的“华夷”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素行基于这种“文明”观,错误地提出只有日本才是“中华”的错误观点。
二、“始”关照下的“文化自信”
对于当时中国是世界中心的地位,素行无疑是心存不满并抱有怀疑的。素行企图确定这一质疑产生的合理性,为此他借用了日本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因为他认为这本书是唯一可以作为谈论古代日本史的资料来源③。
素行只引用了讲述最古老时期的篇章,也就是“记纪”神话中所记载的关于诸神创造宇宙、人类等的传说。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历史记述,则利用得较少。所谓的“历史的开端”才是素行更感兴趣的内容,对他而言,这些开端不仅具有可以解释一切的效力,也构成了日本特点的基础。他只是要借此段历史来证明日本从建国伊始即是“中国”,同时也是文明先进之国,而历史进程对他而言,就相对无关紧要了。
《中朝事实》共分为十三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以表达对《日本书纪》的尊敬作为结语。若说这本书是以表达敬意的形式而撰写的,这也并非夸大其辞。该书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章节的安排,抑或是作者本身的评论,都表明了作者企图证明日本“皇统”优于中国正统的写作意图,并在其中加入了作者本身的评论。整本书都在一味地试图证明自天地之始到日本宫廷繁荣的历史,其最终目的在于展示日本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是上天意愿的实现,从而得出臆想的荒唐结论:“本朝即中朝,日本才是中华”。
“始”是《中朝事实》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它是论证日本之所以为“中华”的一个关键。这个词用来证明,日本是一个与中国相比独立的场所,是作为所谓“文明”之国而诞生的。所谓的“始”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作者在除了论及天地生成的“天先章”之外的所有章节中,都提到了“始”:
“谨按是中国分国境定诸道之始也”(中国章);“谨按是中国定其主之始也”(皇统章);“谨按是置神器于别所之始也”(神器章);“谨按是中国学外国之经典之始也”(神教章);“谨按是人皇定中国建极诏治道之始也”(神治章);“谨按是武官之始也”(神知章);“谨按是置国史之始也”(圣政章);“谨按是詠歌之始也”(礼仪章);“谨按是赏罚之始也”(赏罚章);“谨按是东夷征伐之始也”(武德章);“谨按是祭祀社稷宗庙之始也”(祭祀章);“谨按是外夷投化之始也”(化功章)。
(山鹿素行,1940:238-362)
其“始”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文治武功的各个方面,力图证明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政体,在国家初创之际就已万事俱备、条理井然,“中华文明”制度业已开始④。素行(1940)貌似细心地指出,从最初的君主开始,日本就已经存在儒家道德的理念及规范,而彼时的中国文人对何为儒家道德还一无所知。在儒家道德的教化下,日本率先制定出完备的礼仪制度。日本政府据此实行仁政,周边蛮夷因其教化而自愿归顺。也就是说,素行在文明准则的设定上并没有脱离中国的概念范畴,只不过是基于这一中国化的概念错误武断地判定日本更值得拥有“中国”的称号。
多次出现的“始”所要体现的便是如此。盲目地断定日本的文明是在与中国文明毫无瓜葛的情况下产生并发展的。换句话说,日本文化的确立并非以对中国文明的汲取为先决条件。素行排除了那种中国文明辐射、教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中心主义”,强调了日本相对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自古以来就具有完备的文明体系。换言之,素行认定中国与日本分别拥有各自不同的天下,即“两个天下”。
这与江户时期的大部分儒者的想法无疑是相左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日本游离于文明礼教之外乃是他们苦恼的根源,也正因此而催生出对中国的无限向往与憧憬。素行之前的藤原惺窝、林罗山,乃至与素行同时代的儒者们大多抱有日本乃“夷狄”的观念,他们接受中华文化,研读经典,是中华传统儒家思想的忠诚信奉者。当然另一方面,“以源生于日本的先天性的感情、风俗与文化价值为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也使德川时期的日本儒者们倍感中日文化传统拉锯的压力”(转自黄俊杰,2010:50)。而素行则做出了大胆的翻转,将日本称为“中朝”并以之为“事实”予以证明。如前所述,素行终其一生所能,也无法离开儒学,即便他在后期以讲授兵学为主业,也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圣贤之道。实际上他反对的并非儒学本身,而是那些学习儒学之后,丧失自身主体性、甚至忘记自己是日本人的学者(转自张崑将,2008:131)。素行反对这种民族自卑的思想,认为日本绝非夷狄,而是“礼数”整备的“文明”之国,并妄图从古代及中世的史书中寻找证据。
《中朝事实》中的“华夷观”本身并没有脱离中华的“文明观”,那么如何解释另一个文明之国——中国的存在就成为素行需要解决的问题。素行对此的观点是,虽然作为“外朝”的中国与日本基本上是各自独立产生的,但从同为“文明之国”的角度来说,两者并无大不同,可谓是“其揆一也”。
凡外朝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大圣,亦兴中州往古之神圣,其揆一也。故读其书则其义通,无所间隔,其趣向犹合符节,採挹斟酌则又以足辅助王化矣。窃按,誉田帝虚已徵百济博士后,中国广通外朝之典籍,知圣贤之言行,是乃住吉大神之赉也。
(山鹿素行,1940:265)
但是,从“外朝”中国摄取包括汉字在内的诸多文化礼教又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比如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汉字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古代文人的竞相学习,对此作如何解释是儒者素行面临的又一难题。对此素行自欺欺人地设想出一套自我解决方法:首先他相信日本是有自己的文字传统的,因为从文字起源来看,“有言语则终有文字之象”(山鹿素行,1940:325)。并由此推断,文字的产生与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岂唯中国外朝乎”(山鹿素行,1940:325),不过是存在语言程度的高低之别罢了。因而日本古代也是存在文字的,日本的政治家、学者也曾经用日本的自有文字进行创作,只不过在孝德天皇时期“鞍作乱悉为灰”(山鹿素行,1940:327),日本固有的文字因此没有流传下来罢了。
或疑,外朝不通我而文物明,我因外朝而广其用,则外朝优于我。愚按否,自开辟神圣之德行明教,无不兼备,虽不知汉籍,更无一介之阙。幸通外朝之事,取其所长以辅王化,不亦宽容乎。何唯外朝而已。凡天下之间,详知并蓄校短考长待用无遗,从事是适,量之大也。内外相持,人物以成,若护短拒外,非君子所为。况外朝与我一其致,而其历世尤久也,其封域太广也,其人物众多政事损益也。足共以观之乎。是所以中州之冠八纮也。后世勘合绝,不修邻交之好,亦我无不足,可并考也。
(山鹿素行,1940:266)
素行认为“中朝”日本虽然自开辟以来就已经“神圣之德行明教无不兼备”,但取他者所长补己之短却也显示出日本度量的“宽宏”,并强辩说学习外朝文字并不能就此否定日本“文明”的独立性。
最后,素行掩耳盗铃地认为,包含汉字在内的儒家文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优越文明,是可以超越国界而为中国与日本所共有的文明。并且对于这一优越的文明,并不是普天之下任何国家都可以分享的,只有中国与日本这样高等之国方有资格。虽然中国与日本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政治个体,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同属于一个世界,即儒家文化世界。
三、“皇统”及“武威”背后的民族“自豪感”
对于素行来说,其所主张“文明”论还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的核心要素,就是日本皇统的“万世一系”。这也是素行的“中国论”所列举出的一个重要条件,即“皇统”的神圣性。
在日本多数学者看来,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可以追溯至远古并绵延至永远的,这一“记纪”神话所创造的国体观念烙印于日本儒者的思想当中,并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几乎没有儒者否定过天皇制,并且当他们在论及中国经典中的“易姓革命”“汤武放伐”等问题时,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强烈的日本主体意识,这其中也包括山鹿素行。
素行(1940:245)在“皇统章”中说“中国定其主之始也”,其中所谓的“中国”是指日本,而“主”则是指天皇系谱。素行以“记纪”神话来证明日本是由诸神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与中国的天下相独立的另一个天下。这个“天下”最初是由天神创建,其后的经营则是天皇所为。《中朝事实》的很多章节都有对古代天皇制的“神圣性与优越性”的相关论证。所为证明的就是,日本有神圣的传统,日本优于中国就在于这一“皇统”的神圣性。因此如果要就孰为“中国”进行最终定义的话,素行认为“神圣一其机,而外朝亦未如本朝之秀真也。”(山鹿素行,1940:236)也就是说,日本是比中国更有资格称为“中国”的,这在素行那里成为了一个“神圣的事实”。
本朝唯卓而于洋海,禀天地之精秀,四时不违,文明以隆,皇统终不断,其名实相应可并考也。
(山鹿素行,1940:233)
三纲立行,则身修家齐治平之功,坐可以俟之。帝建皇极于人皇之始,定规模于万世之上,而中国明知三纲之不可遗。故皇统一立而亿万世袭之不变,天下皆受正朔而不贰其时,万国禀王命,而不异其俗,三纲终不沉沦,德化不陷涂炭,异域之外国岂可企望焉乎。
(山鹿素行,1940:250)
素行所要说的是,所谓的“三纲”这一文明指标是通过皇统一贯得以实现的,这与数度王朝交替的“外朝”中国相比,“本朝”所具有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之所以可以成为所谓的“上国”,是因为其具有“天壤无穷”的神敕,且与“天地之德”相一致。不受“外国之贼”“四夷”的侵扰而连绵的皇统因与“天地之德”的同一而备受礼赞,但也需要注意皇统存在的连续性并不是无条件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素行的“皇统一贯”的正当性归根到底仍然还是中国式的文明观。只不过是不同于“外朝”中国“夫外朝易姓殆三十姓,戎狄入王者数世”(山鹿素行,1940:250),因“戎狄”的侵略而王朝断绝,民族单一的岛国日本并不存在危及“皇统一贯”的因素,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外部。
素行的《中朝事实》之所以成为“日本型华夷思想”的一个典型,除了由“皇统一贯”所代表的日本“优越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武威”。作为“武国”的日本,其优越性并非如中国的华夷观念一样,是靠“天”这一超越诸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观念予以正当化的,而是仍然将眼光放到了“记纪”神话中古代日本的起源上。其神性的根据就是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在创建国家时所使用的“天琼矛”。
谨按神代之灵器不一,而天祖授二神以琼矛,任以开基。琼者,玉也,矛者,兵器也。矛以玉者,圣武而不杀也。盖草昧之时,拨平于暴邪驱去于残贼,非武威终不可得也。故天孙之降临亦矛玉自从是也。凡中国之威武,外朝及诸夷竟不可企望之,尤有由也。
(山鹿素行,1940:252)
八大洲之成,出于天琼矛,其形乃似琼矛,故号细戈千足国。宜哉中国之雄武乎。凡开辟以来,神器灵物甚多而以天琼矛为初。是乃尊武德以表雄义也。
(山鹿素行,1940:341)
在“神器章”中,将“天琼矛”置于三种神器之首,就显示出“天琼矛”的重要性。对于“威武”的强调也显示出与中国的华夷观念的不同之处。以“天琼矛”作为“中国(指日本)之威武”的依据,在同时代的吉川神道也可见。但将神话作为“武威”的依托,似乎也显示出对“武威”的理论还抱有一种踌躇和怀疑。因为在以中华意识为前提的儒者的观念中,如果从“文明”这一价值基准来看的话,“武威”一词本身就难于去除夷狄的印记。但是从素行的兵学思想来看,那些儒者们对“文明”世界的憧憬,不过是一种追求新奇的偏颇之说罢了,重视“武威”才是理所当然之道。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真诚地学习朱子学的朝鲜,儒学在两个国家中显示出不同的特征:比起“孔孟之道”的兴衰来说,日本更珍视对国家的归属意识,而李朝朝鲜则似乎更以“儒教的兴衰”为己任(渡边浩,1997:121)。江户时期的日本在抗拒作为外来思想的儒教的时候,体现于“神国”或者“皇国”的本国优越观念,在江户时期日本民众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武国”观念。建立幕府统治的日本是由武士所领导的国家,儒教中的德治主义在日本的现实中难于实现,因此所谓的“日本型华夷思想”或者“日本中华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武威”的特征(前田勉,2006:106)。比如,素行认为与朝鲜半岛各国是通过“武德”形成的朝贡关系,并援引《日本书纪》中神功皇后“三韩征伐”的神话,将现实中本为对等外交关系的朝鲜强行改变为屈从于日本“武威”的支配与服从关系。
传统的中国式华夷观认为夷狄若具有礼教也可为中华,身为夷狄的他者自发地依从并最终同化于优越的礼教文化,这一以文明的有无为根据的华夷观是开放的。而以“武威”为支撑的“日本型华夷观”与他者的关系则完全是敌我之别,通过力量的优势排除或者征服异己,如若不具备相应的实力则会谦卑地服从于对方。这实际上也显示了“日本型华夷观”的一个特点,即“中华”与“夷狄”之间因为缺乏应有的流动性而具有封闭性的特点。“武国”日本正因其为“武威”之国,因此比起靠礼教文化统治的中国来说,更能以“武威”的方式来维持“安定的体制”。同时,素行作品中“武威”理论的产生也有来自于外部的影响,即1616年作为中华“夷狄”的满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而汉族所建立的明王朝随后迅速走向灭亡。新的王朝的建立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日本发现文野之别可以通过力量的强弱得以转变,这也成为了《中朝事实》中“武威”优先理论的一个契机。
四、“水土论”视角下的自我主张
素行在企图力证日本乃中央之国这一中心论点时,还举出了“水土”论这一根据。素行(1940:237)在“中国章”中有“天神谓伊奘诺尊伊奘册尊曰,有丰苇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循之,延赐天瓊矛”的引文,该文实际上是引自于《日本书纪》。这句话表明,在《日本书纪》成书之前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存在一个国家,通过其拥有的修饰语判定它就是日本。对于素行来说,“中国”这一称呼来源于“苇原中国”,《日本书纪》指出“中央之国”指代日本这一观点是自宇宙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的事实,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的正当性也因由于此。该“中国”一称在这里并不是指政治意义的古代中华帝国,而完全与地理环境相关,也就是指“水土”。
愚按,天地之所运,四时之所交,得其中,则风雨寒暑之会不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称中国。万邦之众唯本朝及外朝得其中,而本朝神代,既有天御中主尊,二神建国中柱。则本朝之为中国,天地自然之势也。神神相生,圣皇连绵,文物事物之精秀,实以相应,是岂诬称之乎。
(山鹿素行,1940:234)
独本朝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正南面之位,背北阴之险。上西下东,前拥数洲而利河海,后据绝峭而望大洋,每州悉有运漕之用。故四海之广,犹一家之约,万国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况鸟兽之美,林木之材,布缕之巧,金木之工,无不备。圣神称美之叹,岂虚哉。
(山鹿素行,1940:237)
素行的“中”是处于“万邦”之“中”,是得“天地自然之势”之“中”。而中国与日本就是在万邦中得此“中”的两个可产生优秀人物的国家。需要注意的是在“万邦”中具有相对意义的“中”。“外朝”中国虽然与日本一样得天地之中的位置,但与作为岛国的日本相比,于地理方面却处于不甚有利的位置。日本正是因为地理条件的优越,才能够确保“圣皇连绵”及皇统一贯,才能够“文武事物精秀”,免于来自“夷狄”的侵略。日本的“得其中”使政治安定,三纲不遗,这与易姓革命政局动荡的古代中华帝国相比,无疑是更具可称为“中国”的资格的。
由此可见,素行并未否认外朝的中国也是在空间地理上得其中的国家,而故意强调日本也是“得其中”,则是为了提醒当时嗜读中国经书的儒者们,切勿丧失自己的国家主体性,并以“天御中主神”建中柱于国中的神话依据来加以强调。进一步说,这种“天地自然”是带有“世界之中”的意味,也多少带有日本神道的自然精神,日本是神国,是高于外朝的“中国”。这样又从“水土论”的角度把日本置于中华之上了。
素行对自己的设问:“儒与释道,共异国之教,而异中国(指日本)之道乎?”进行了如下回答:
愚谓:神圣之大道,唯一而不二,法天地之体而本人物之情也。其教异端者,皆因水土之差,风俗之殊,五方之民各有其性,以不同。唯中华(指日本—笔者注)得天地精秀之气,一于外朝,故神授之,圣受之,建极垂统,天下之人物各得其处,殆几于千年,而后住吉大神赐三韩于我,初外国之典籍相通,以知一其揆,其曰神教其曰圣教,其皇级之受授天下之治政,犹合符节,自是通信修好,摘其经典,便其文字,以为今日之补拾也。如佛教者,撤上撤下,悉异教也,凡西域者,外朝之西藩也,其水土偏于西,天地寒暖躁湿甚殊,民生其间者,必有偏塞之俗。
(山鹿素行,1940:370)
这段文字从“水土风俗”的角度,说明中国的儒道和日本的“神圣之大道”乃是“其揆一也”(刘长辉,1998:360),而佛教因其“水土偏于西”而被视为“异教”,并不适合中国与日本。这里素行的用语不应匆匆看过,他称日本之“道”为“神圣之大道”,日本之“教”为“神教”或“圣教”,以此来区别中国(即他所说的“外朝”)的“儒道”或儒教。也就是说,在日本的“道”“教”上特别冠上“神”“圣”或“神圣”等的用语,是为了与中国基于“人”的“道”或“教”相区分。素行试图极力主张日本有自己独特的“神圣之道”,它虽然与中国的“圣人之道”相同,但“神”“人”之间无疑存在差别。基于“神之道”的日本,自然有其“神迹”与“神教”。与之相比,中国“圣人”的“道”或“教”,则全部记录于《六经》或《四书》当中,虽然也有论及上帝或者神等部分,但经过儒教理性的处理后则变为彻底的“人”之“道”或“教”,这就是素行《中朝事实》所要区别的中日不同之处。而中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素行的缪证就是基于自然水土之不同,从而凸显日本的主体性。
凡外朝其封疆太广,连续四夷,无封疆之要,故藩屏屯戍甚多,不得守其约。失是一也。近迫四夷,故长城要塞之固,世世劳人民。失是二也。守戍之徒,或通狄构难,或奔狄泄其情,失是三也。匈奴契丹北虏易窥其边,数以劫夺。其失四也。终削其国,易其姓,而天下左衽。大失其五也。况河海之远,而鱼虾之美,运转之利,不给。故人物亦异其俗。如啖牛羊,衣毳裘,坐榻床可以见之也。况朝鲜撮尔乎。
(山鹿素行,1940:236)
夫外朝其地博而不约,治教盛则所画惟泛,守文不明,则戎狄据之。
(山鹿素行,1940:321)
这里论述了中国与日本相比,在地理、军事等方面的劣势。正是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所以容易受到夷狄的军事侵略。素行也基于地理的立场,否定了中华和夷狄之间转变的可能性。按照中国传统的夷狄观来说,根据“文明”的有无,夷狄可以上升为中华,而中华也有可能沦落为夷狄,也就是说中华和夷狄之间的差异是流动性的。素行自身也认为“人而无礼则不异于禽兽,中华而无礼则不异于夷狄”(山鹿素行,1940:305)。但是,他却将着眼点放在自身是否居住在某处,认为只要居住地不发生变化,就不存在有华夷之间位置变更的可能。
并且,如前面所说的“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所说的那样,这种地理上的优越性更多地是作为军事上的优势加以认识的,这也可以算作是《中朝事实》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素行认为中国之所以数次改朝换代是因为国土广阔容易受到夷狄的侵略,乃“地博而不约之失”(山鹿素行,1940:322)。他认为王朝是否连续,与是否遭受侵略息息相关,所以重要的是保卫国土使之不受外国侵扰。在这里,“皇统一贯”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国祚连绵不断这一现象本身上,而是因为证明了日本从未受过外朝的侵略而凸显出其不凡的价值。素行的理论是,因为日本水土的特殊,加之重视“武威”,才能够不受外国侵略,皇统连绵。而与之相对,作为“外朝”的中国则因为拥有广阔的国土,而容易受到外族的侵略,所以数度王朝更迭。也就是说对于素行来说,皇统连绵乃是不受外国侵略而衍生出来的结果。
峙水土海洋,绝封疆众域,后东北前西南,背阴向阳,四时不违,气候尤顺。而人物精秀不混万邦。四夷强悍竟不得窥其翻屏。万世连绵,其皇统永不异。是因水土之正中,而人民皆英武刚和。
(山鹿素行,1940:223)
也就是说,基于“水土”的“武威”理论是优先于“皇统一贯”的。这和“皇统”自身的不具价值、只因与“天地之德”相一致而存续是不无关系的。皇统并非无条件地永远存在的,也有断绝的可能性。那么,该如何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在素行看来,就是要巩固疆域,加强军备。这样就可以不受外国的侵略,保持皇统的连续。
五、结论
日本自我定义为“中华”的理论,自律令时代起就可散见于各典籍中,只是由于17世纪传入的儒教以及不断巩固的德川幕府中央集权,使当时的儒者们面临了一个难题,即如何解读与舒缓中国与日本作为相独立的政治实体各自称为“中华”之间存在的矛盾与争夺。而山鹿素行极力所要论辩的就是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因此《中朝事实》不仅仅是要显示出“日本型华夷思想”的思想意向,更通过如上的“皇统论、水土论、武威论”等方面的诠释来试图解构中国传统华夷思想中“孰为中华”的问题。素行主观臆断式地因日本各方面的“得其中”而得出日本优于地理上的古代中华帝国、更具有资格被称为“中华”的结论。但不得不说素行“抛却了日本以外的任何依凭,试图直线地画出日本土地上的‘中国’衍生图而不太计较这种笔法有没有过度的人工补造色彩和牵强附会”(转自韩东育,2006:52),也就是说素行在进行自我主张的时候,完全忽视掉曾经来自于中国的文化继承,主观臆想式地勾勒出脱离实际的日本框架,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思想意识上的局限与偏颇。
注释:
① 参考版本收录于1940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編 第十三巻』。《中朝事实》全文以汉文书写,本文以原文形式引用。
② 山鹿素行由儒学的《四书》、《五经》启蒙,少年时期开始学习兵法,到青年时期可以说兼学儒、释、神、兵、老庄等五种学问。31岁以后撰写有关解释兵书的作品,兵法思想逐渐凌驾儒学思想之上,已有怀疑朱子学的倾向。直至41岁正式怀疑宋学而提倡古学,因遭信奉朱子学的当权者保科正之的猜忌,终因在《圣教要录》中怀疑朱子学而遭流放近十年,之后日渐倾向神道学,日本主体意识日渐强烈。
③ 《日本书纪》仿造中国正史的编年体形式,叙述了从天地分离到持统天皇在679年退位之间的大事件。
④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朝事实》中,这些开始都仅仅是列举,并没有论及相互的关联及历史的演变。比如,以封建郡县论来说,素行举出了“景行天皇四年条”作为“人皇封建之始”(神治章),而紧随其后,又举出“成务天皇四年条”作为“天下为郡县之始”(神治章)。但何时开始从封建之世转到郡县之世,这里并未明确说明。在《中朝事实》中,之所以记述了封建之“始”和郡县之“始”,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确定这些制度在古代的日本业已存在的事实。
[1] 田原嗣郎.1970.日本思想大系32 山鹿素行[M].東京:岩波書店.
[2] 堀勇雄.1959.山鹿素行[M].東京:吉川弘文館.
[3] 前田勉.2006.兵学と朱子学・蘭学・国学[M].東京:平凡社.
[4] 山鹿素行.1940.山鹿素行全集 思想編 第十二巻[M].東京:岩波書店.
[5] 劉長輝.1998.山鹿素行:「聖学」とその展開[M].東京:ぺりかん社.
[6] 渡辺浩.1997.東アジア王権と思想[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
[7] 韩东育.2006.山鹿素行著作中的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关联[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50-54.
[8] 黄俊杰.2010.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 张崑将.2008.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兵学与阳明学为中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Study on Yamaga Sokou’s Fallacy of “Hua-Y i Thought” in Chucho Jijitsu
Yi-Xia distinction,also known as Hua-Yi distinction or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debate of nationhood in Japanese academic history. Some scholars in Tokugawa period were very sensitive to the “Yi-Xia” issue. Yamaga Sokou, a great intellectual in Japanese medieval group, strongly opposed the use of “Zhonghua”or “Zhongguo” as a designated name for Han’s territory. His idea can be fully certified by his famous book Chucho Jijitsu ( Actual Facts about the Central Realm), which is a typical work relevant to the “Hua-Yi Thought” in Japan. In his book, he advocates that Japan is a great civilization superior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ries to prov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mperial reign, nature’s preference and military power. Meanwhile, he does not deny Confucius’ “Hua-Yi Thought”in his book. Actually, two academic though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book. This thesis tries to explore the unique features of Chucho Jijitsu and reveals how Sokou explains Chinese Hua-Yi thoughts on Japanese behalf.
Yamaga Sokou; Chucho Jijitsu; nature’s preference; military power; imperial reign
I06
A
2095-4948(2015)02-0084-07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关于日本近世思想家‘华夷之辨’思想论争的研究”(L12DSS002)的阶段性成果。
范业红,女,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世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