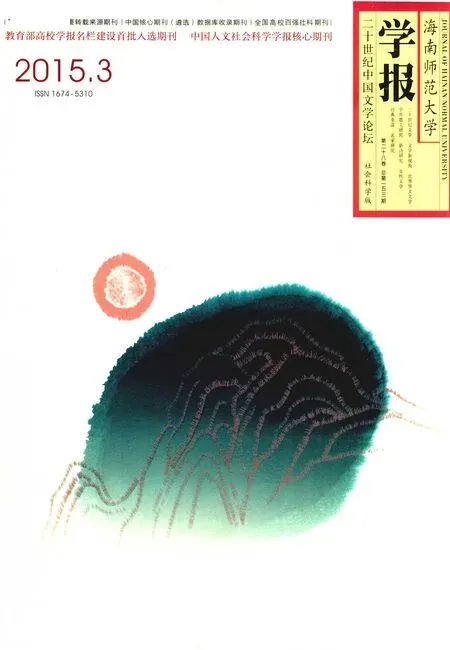科学的人文品格:论鲁迅的“立人”科学观
2015-03-29王初薇
王初薇
(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516007)
恐怕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文学家像鲁迅那样与自然科学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少时曾入水师学堂,后入矿路学堂,再远渡日本学习医学,可以说,他的青少年阶段都是与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求学之时,正值科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之际,时代主题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作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生成,自然科学知识在鲁迅个人的成长及思想精神的形成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许寿裳就说过:“鲁迅是革命的文学家,是民族革命的战士,而且也是个科学家。”[1]尽管鲁迅无意于严密完整的理论建构,他的思想由于聚焦中国的现状而缺乏某种形而上的系统性,然而,当我们回溯他早年的认知历程,会惊奇地发现他对人性、人的精神层面问题的体认与思索,恰恰是伴随着他对自然科学(尤其生物学关于人的起源及发展历史)的深入了解而展开的。科学始终是鲁迅人文思想的一个清晰而强大的背景,是鲁迅精神得以构建的重要基石,因而在进行早期鲁迅思想的研究时,对鲁迅与科学的关系进行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一、从“实业救国”到“文化救国”:鲁迅科学历程的必由之途
要考究鲁迅之与科学这一关系,须联系当时作家所处的大、小两个背景来进行阐明。19 世纪下半叶直至20 世纪初,由于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欧列国的资本主义飞速发展,领土扩张的欲望也开始在全世界铺展开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目标。面对列强的鲸吞蚕食,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割地赔款,残喘图存——种种丧权辱国的行径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刺激,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作了各种各样的思考和实践,为我们熟知的各种阶级力量也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如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性质的“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本阶段的中国政治史蔚为壮观。而在政治变幻更迭的同时,也始终贯穿着经济上“实业救国”、文化上“科学救国”这样一条明晰的线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做着引进科学理论和思想以保障民族、国家富强的工作,但过于频繁的社会更迭和过于集中的思潮命题局限了他们的视野,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的先天缺陷,最明显的是过多地把时间精力放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等某些被认为是救国之途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震撼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民族兴盛的巨大力量。因而在天朝帝国分崩离析的危亡大势下,中国兴起了一股富国强兵的热潮。“实业救国”论者意识到惟有发展实业才能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状况。因而教育也被作为实业的一个领域,许多新式学堂得以投资兴办,借传授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中国的科学。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水师学堂,开始接触自然科学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为数不少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其他的文化名人都曾经有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历,例如,文学家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等都曾留学日本,而且一开始也是学医。理、工、农出身而后转向文学的更不乏其人:胡适学农,成仿吾学造兵科,张资平学地质科,洪深学烤瓷工程,李初梨学的电气专业等等。可以说,鲁迅之与自然科学发生联系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反映着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从个人选择的微观背景来看,则鲁迅之选择自然科学又有其主观的因素。当时鲁迅还只是绍兴乡下的一个少年,本来照常规,像他这样破落下来的大户人家子弟的一般出路是“学幕僚”或者“学钱业或当业”,以便“将来混口饭吃”[2]。而进洋学堂、学洋务,则被目为“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最次选择。但当时洋务派兴办的学堂可以免费读书,这对于家道中落、生计拮据的鲁迅也不失为一个适合的去处。因此在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时,鲁迅毅然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3],离开家乡绍兴到南京进了洋务派兴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后又改入矿务铁路学堂。鲁迅进入新式学堂是他接触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新科学)的开始,他不仅认真学习了矿物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即物理)、测算学(即数学)及绘图学等科目,[4]还在课余大量涉猎人文类书籍报刊,阅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留日学生杨荫杭创办的《译学汇编》等新书报,在拓宽科学视野的同时也发展了自我的世界观。正如钱理群所言:“鲁迅一生有几次重要的空间转移,每一次转移都对他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产生重大的影响。”[5]61从为军事培养战备人才的水师学堂,到为经济培养能源人才的矿路学堂,最后远渡重洋先学救治国人肉体的医学,再到学习拯救国人灵魂的文学,完成了“军事科技——经济制度——文化精神”这样几个层面的更迭。“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共和,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富强的道路上经历了由工艺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认识变化”,[6]鲁迅的求学经历恰恰印证了中华民族百年求变图存所走过的历程,鲁迅心灵的极大丰富性是以其不可复制的人生为基础的。探索鲁迅精神,就不得不对其人生经历进行分析解读,科学哲学意识在鲁迅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深入探讨鲁迅的科学历程有重要的意义。
留日期间是鲁迅与自然科学接触最为紧密的时期。到日本的第二年就厚积薄发写下了《说鈤》《中国地质略论》《科学史教篇》等科学论文,并与同学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翻译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求学中的鲁迅在外国一边阅读科学著作进行知识输入,一边又将这些著作向国内译介以作知识输出。以矿物质和新元素为开端的科普论文的创作与科幻小说的翻译显示了鲁迅对科学的浓郁兴趣,以及对自然科学之于改造国民精神作用的重视。中国的内忧外患促使当时留学东洋和西欧的知识分子踊跃向西方学习,希望借以警醒国人反思以往对于科学的陈旧认识,在科学技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鲁迅即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1906年鲁迅仙台学医期间的拟购德文书目保留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所列的128 种书中,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占了68 种以上,范围涵盖了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矿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其课余阅读面之广可见一斑。[7]32-33直到晚年,他对自然科学的热忱不减,仍然大力购进建筑学、科学哲学、植物学、医学、天体物理学等书籍。正如孙郁所言,现代中国作家中,像鲁迅这种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哲学知识准备的人是十分少有的。[8]可以说理性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鲁迅终其一生的价值哲学的重要支撑。但如果单纯以“爱国”和“科学”来笼统概括其早期著述活动则无疑失之偏颇,鲁迅此一时期的创作有着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从1903年的《说鈤》到1907年的《科学史教篇》,鲁迅经历了一个从关注自然科学研究表象到关注科学史发展模式,再到注重科学家的主观思维(在早期文言论文中鲁迅称之为“理想”、“圣觉”)也即人的精神层面的不断深化及升华的过程。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在这里融会贯通,体现为悖论统一的张力场。剖析二者所形成张力场,我们可以透视出鲁迅“立人”科学观的品格与本质:以“人”为根柢。
二、“科学”与“爱国”:早期论文思想的原初价值
关于鲁迅1902年到日本之后的著述,一般来说是以1906年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为转折点,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1903年至1906年,二是1907年至1909年。[5]67诸多研究著作都重在发掘后一阶段的意义,把鲁迅连续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5 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作为鲁迅早期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此一时期鲁迅在东京集中的文学活动表明他已明确将文学启蒙作为矢志不渝的志向。相反地,对前一阶段学界则较少论及,或是认为在此期间青年鲁迅在形成自主意识之前仅有零星的文学活动,没有特别的文化学意义;而对于发表在《浙江潮》上的《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带有科普性质的文章,以及《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译作,则视为出于其爱国激情和对科学的盲从而发愤慨之言的浅层文本,只需“科学”、“爱国”二词便足以概括。
其实,这种研究思路存在着偏颇之处。基于思想一脉相承的性质,深入研究上述最早的鲁迅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些早期论文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具有作为原初思想载体的关键性意义。一是对事而发,目的性强。《中国地质略论》应时事而作,有南、北两个具体的背景事件,即当时浙江的“争刘铁云条约”和东北的护矿斗争,两者都是官商勾结,盗卖国家的矿产资源。[9]鲁迅在文中不仅批判他国的狼子野心,更批判了国民图小利、昏昧不醒的短视。而《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的翻译,也是为了响应当时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欲以小说启蒙民众——即所谓的“新民”。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说:“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0]在这里,启蒙是核心,文学只是传扬科学的载体,表达了鲁迅对于文学与科学关系的最初认识。二是主观色彩异常浓烈。《中国地质略论》通篇以“吾”自称或代称国家、民族,强调匹夫之与家国同呼吸的爱国主义精神。“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此一细事,而令吾惧,令吾悲”、“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11]5像这样将自我与家国紧密联系、直抒胸臆的词句,在鲁迅后来文章中再没有出现过,与其后期冷峻理性的文风大相径庭。对于别具用心的外国学者借旅游、探险之名来勘探中国矿产资源以备该国侵略之利的行径,鲁迅在文中“恒为毛戴血涌”,并发出了“中国将以石炭亡”的振聋发聩的吼声,[11]18并毫不讳言自己写作时“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甚至“掷笔大叹”。三是感情的复杂激切,通篇行文满含沉痛与愤懑。有对祖国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的由衷自豪,也有对他国欲窃取我矿产的焦虑和批判,更有对国人为蝇头小利而变卖宝贵资源的痛恨——多种情感杂糅其中使得全文激情洋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能说是简单的科普论文,全文字里行间充盈着一腔爱国义愤,连一向“不悔少作”的鲁迅后来都为自己早期作品中的激昂情绪感到“耳朵发热”[12]。自然,在这些文本中“科学”和“爱国”始终是突出的两个核心词,但是却很难找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使它们得以发生联系的本质性因素,而这些都源于鲁迅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与日后的鲁迅强调个性主义,强调个体之于国家、民族的独立意义不同,青年鲁迅把群体的人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认为“群之大觉”是启蒙的终极目的。这种对国家、民族群体觉悟的期待,藉以强大民族、国家来提升国民精神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某种急功近利的情绪,但也体现了鲁迅对于中国人文化生存状态的否定以及突围的渴望。
鲁迅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意图是明显的,并有将“出路”具体化和明确化的努力。例如中国号称“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却连一幅精确的地形图或地质图都没有,“此一细事”使其“悲惧”交加,认为这是能窥测一国之国力是否强盛、是否文明的依据。他认为:“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虽曰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矣,而惟地质学不发达故”,[11]6将挽救中国的理想落实在了向国民普及地质科学知识上。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天下,但对自己的国家却知之甚少。没有建立起民族自知,也就无由产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爱国之情就会如无根之萍般空洞虚无。一个连自己都不了解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无法在日益澎湃、一日千里的历史大潮中存在、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的。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如果没有对国族整体的了解把握,没有对自身在世界上处境的清醒认识和感受,则无由爱,也无由奋发,这就是鲁迅早期译介域外文化、宣扬科学、呼号国族自强的目的所在。而这股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也预示着鲁迅必然会从单纯强调技术性的科学升华到关怀人性的价值观上。
三、由科学现象入思想变革:与洋务派的分道扬镳
封闭了多个世纪后的老旧之中国在被迫睁眼看世界,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时,出于后知后觉的落差,其内心的恐慌与焦虑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紧迫感也明显地体现在异国求学的青年鲁迅的著作中——“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瞿然”二字及强有力的反问,对科学与文明的渴盼溢于言表。鲁迅曾形象地将“自然之力”(即未经开发的大自然)比作一匹尚未受驯的野马,科学则成了人类得以“发纵指挥”这匹野马,使之俯首听命的器械;于是“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13]25,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因为科学而顿时焕然一新,而人类的幸福也由此而生。然而鲁迅并没有为当时强势的西方物质文明所遮蔽,而是在加速全球化进程的科学大潮中,看到了它目的性极强的唯科学主义态度的发展趋向。这也是鲁迅之所以脱离洋务派的关键原因。
虽然洋务派兴办的学堂为少年鲁迅打开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大门,但他却反过来对洋务派引发的盲目引进科学技术的运动以及这场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变化进行了深刻反思,青年鲁迅对这种科学至上主义保持着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中西对于科学的理解存有根本差异,国人之索求科学,原因在于“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自鸦片战争以来,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终于被打破天朝帝国的迷梦,当时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图存发奋的捷径,他们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见识了坚船利炮的威力,认为这是西方科学使然,因而以科学技术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当时以科学来“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并逐渐形成了规模浩大的政府、官方的推动机制。据统计,官派赴日留学的人数在1902年夏天仅有二三百,到了1906年,猛增至两万。当时留学生中重实务、轻文艺的倾向非常明显,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学习法政、警察、农、工、商、医、陆军、教育等专业,而学文学艺术的只有一个上东京美术学校的,据说搞文学“将来是要饿死的”[14]。而这其间又混杂了一些“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15]的自私自利之徒,鲁迅一针见血地披露了他们借科学以营私的虚伪。《偶感》一文中提到:“‘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但是“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这是科学这一“异域文化”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横向移植过程中,遭遇固有的传统封建畸形文化的阻挠而出现的特有现象。“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16]科学在“东渐”的过程中被工具化和歪曲化了,作为科学本质的“研索”求真的精神,也已被实利挤压得荡然无存。因而这个时候的鲁迅已经一改留日前期纯粹的武力强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将洋务派、维新派所提倡的从“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等工商政治的社会实体层面救国的言新之论称作不值一提的“辁才小慧”“尘芥”“枝叶”,认为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一旦被“巨奸”所利用,就成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的闹剧。实际上当时中国许多地方包括矿权在内的国家民族权益,已由乡绅、买办转手卖给了帝国主义者。洋务派官僚以开发为名,“科学”这时就成了官商勾结卖国营私的名目和掩饰。
科学在中国的异化远不止如此。科学本是人类进行精神探索的行动,体现了人类的精神成就;在科学世界里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可敬的,他们在修补世界、拯救世人,却往往收获荒谬的回应——“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17]拿破仑作为统治者,杀人无数被尊称英雄,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作为牛痘接种技术的创始人,不知救治多少人,却默默无闻。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科学的价值和应用效果也有所不同。“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18]在对比中看出国人科学观念的匮乏和扭曲,也从另一个侧面见出愚昧与无知。更有甚者以科学来对异见者进行侵略和征服:“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19]科学的利弊,选择在人,人才是科学价值的决定者。
由此可见,鲁迅对科学是没有直接的好坏与正误判断的:用于反人性的战争和迫害,是科学之祸;用于救治国人之昏庸蒙昧,则是科学之福——关键在操控科学之“人”。人是科学精神的缔造者,也是科学应用的践行者,更是科学价值的决定者,惟有秉承人性的科学精神才能创造出伟大而有益于人类的科学文化来。面对当时这样一场“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的科学狂潮,鲁迅直指其偏误在于“外状固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此种流于表象的模仿学习,无异于舍本逐末毫无意义。鲁迅曾经分析过:“夫欧人之来,最眩人者,固莫前举二事(按:即‘兴业’和‘振兵’)若,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叶耳。寻其根源,深无底极”,深虑中国知识分子所认识的“科学”,只不过是一条富国强兵的终南捷径,耽于“兴业”、“振兵”这些“一隅之学”以求富国强族之效,是难以达成长远之功的。尽管当时鲁迅的科学著述《中国矿产志》得到清政府有关部门的首肯: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清政府农工商部“通饬各省矿务议员、商务议员暨各商会酌量购阅”;后又被清政府学部批准作为“中学堂参考书”[7]2,但在文中处处可见其游离于体制之外对中国既有的科学发展政策提出的诸多质疑和批判。因而可以说鲁迅对洋务运动以及它所发起的实业救国思潮是渐趋怀疑的,当洋务派知识分子沉浸在科学技术所构筑的关于国族复兴的幻梦时,鲁迅却时刻警惕科学主义者盲目追求实用效益对于民族精神的无益甚至损害,并将表象(即所谓“科学成果”)背后的更为深远的“人”的要素——包括人的研索精神和实践力量推到人们面前。“本柢”与“葩叶”的对比[13]33凸显出鲁迅对科学背后“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视,也表明鲁迅在留日时期其思想脉络已经从根本上与洋务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
鲁迅从既定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现行的洋务思想中分离,并独立出自我意识用以构建关于世界文化的思想框架,这个过程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何在呢?客观来说,这是由中西知识分子对于各自文化系统中的科学传统的传承差异所引致的。从目的来看,虽然鲁迅与洋务派知识分子都重视科学技术的学习,皆欲以科学为利器来振兴国族,但从实现途径的设计来看,二者却有着枝叶与本根的区别——一欲从军事经济方面强其国力,一欲从精神思想方面立其国人。洋务派官僚知识分子以“西学为用”思想维护当时的皇权政治,是出于“国家主义”意图的。他们重视的是如何从西方科学技术成果中剥取表面的使用价值,以便更好地为清王朝的长久统治服务。而作为留日学生的鲁迅,跳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怪圈,也抛弃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虚无承担,转而进入西方文化的内核,审视其观念性的文化本质,看到科学发展中所包含的人的本质力量——因而鲁迅发现的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性基础,他认为与其急于引进西方的洋枪洋炮,还不如首先“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否则“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20]。强调文明的发展应该是精神为先,重视对个人心性的选择,这就是鲁迅之区别于中国以往旧式知识分子的本质性因素。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鲁迅和洋务派都从弱国子民的忧惧走到了“科学兴国”、“实业兴国”的强声,但在科学、实业兴国表象背后却分别挖掘出了关于如何强国的不同依据和途径,鲁迅更多地将科学升华为人的一种精神,而视其实际效用为与之相生的副产品,在平素的认识与实践中不应本末倒置。
总而言之,对于鲁迅而言,科学本质上是精神存在而非物质存在,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他更注重的是精神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带来了一种现代的、全新的生存模式,而这种生存模式与当时老旧之中国的社会构成是格格不入的。青年鲁迅正是异常敏锐地看到了科学背后的“人”之精神作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质,因而不绝呼号“立人”作为其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命题,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这个梦想。而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官僚知识分子“重视的不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性基础,而仅仅是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直接使用价值。这带来了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畸形化,也带来了中国国民对于科学技术的畸形化的意识形态”。[21]时至今日,中国科技的政治性背景仍然是一个显性的现象,科技的发展被诠释为外在的需要而不是内在的精神追求,“求知”与“求强”不可避免地被人为地捆绑在一起。鲁迅在百余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并且“科学强国”的口号仍然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彰显着科技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挤压和掩盖,这都是值得我们再次反省和重新定格的。
[1]许寿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C]//马会芹.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3.
[2]周启明.鲁迅与中学知识[C]//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91.
[3]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
[4]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C]//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400.
[5]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严搏非.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C]//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183.
[7]刘运峰.鲁迅全集补遗[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8]陈漱渝.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374.
[9]程麻.鲁迅留学日本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55~56.
[10]鲁迅.月界旅行·弁言[M]//陈漱渝,肖振鸣.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第1 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36.
[11]鲁迅.中国地质略论[M]//鲁迅全集: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鲁迅.《集外集》序言[M]//鲁迅全集:第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13]鲁迅.科学史教篇[M]//鲁迅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马力.鲁迅在东京从事文艺活动[C]//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 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87.
[15]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
[16]鲁迅.偶感[M]//鲁迅全集:第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6.
[17]鲁迅.拿破仑与隋那[M]//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6.
[18]鲁迅.电的利弊[M]//鲁迅全集:第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
[19]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M]//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
[20]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6.
[21]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15-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