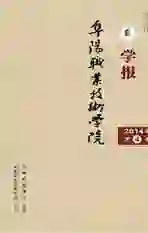作为态度的抗争
2014-12-23李朝朝郑鹏程
李朝朝 郑鹏程
摘 要: 人类思想本身有其作为本能的自欺性,而在鲁迅的“立人”主张里,鲁迅以一种作为态度的抗争使这一思想的自欺性得到了解决。
关键词: 鲁迅;自欺;“立人”思想;抗争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6-0062-06
1930年代,鲁迅曾与“论语派”进行论战,指其空灵雅致的背后是自欺欺人的虚无。学者彭小燕在《启示信仰与解构虚无——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一文对此进行分析,指出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对中国知识阶层的“自欺、虚无”境状进行了揭示,并将鲁迅杂文解剖下中国知识阶层的虚无行迹分为两类:一是自欺欺人,甘于虚无无为,混世游世,却又俨然以现代“学者”“教授”“革命者”“性灵本色”等面目出现,此可谓中国知识阶层的精神性自欺自迷相;一是追逐物质利益、世俗权威,却同样扮以各式“卫道”之相,自觉而有意识地欺人欺世。[1]139本文试图回归单纯的思考,平静地对上述提到的思想的自欺性进行考察,并以此分析鲁迅在批判中所透射出的“立人”主张对思想之自欺性的解决。
一、鲁迅思想的自欺性
(一)世界本虚无
鲁迅1924、1925年以来借《野草》反击生存虚无,并对知识界的“自欺、虚无”状况进行抨击,不仅是出于对知识阶层这种无意真正介入现实的自欺感到痛恨,更多的还因为揭开自欺面纱之后在发现的虚无世界面前自己感到的无助和辛酸。学者靳丛林介绍日本早期鲁迅研究者竹内好时提到“他所反抗的实际上并不是对手,而是针对他自身中无论如何也解除不了的痛苦。他从自身中取出那种痛苦,放在对手身上。然后,他就打击这种对象化了的痛苦。”[2]112作为知识阶层的一员,鲁迅身上不可避免也会沾染这种虚无主义情绪:“……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3]194鲁迅用诚和爱对待自己和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时时解剖别人的同时,也在深刻地解剖自己,使自己的灵魂时时处在痛苦的煎熬之中。”[4]57在这种被竹内好称为“接近宗教的罪的意识”的反省中,这个敏感的思想者只得“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3]194
自十九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我们在历史的“谁是谁非”的争论中冷静下来之后,终于因谁也不信而进入另一层界,并可以较清晰地审视这种是非争论,进而思考这个被置于“是”或者“非”或者“非是非非”“也是也非”的所谓信仰之下的世界。无论多么有力的信仰都不免沦为被解构的命运,加之生产力发展之迅速,以致时间和习惯都无法再掩饰和抚平人们的恐慌,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悟到世界本来的虚无面目。既然一切皆可被解构,那么一切便是被定义,那在一切都被揭去的虚无之下,我们还该信奉些什么?或者说,我们是否还能在信仰的自欺里安然?
(二)自欺之于虚无的解决
然而,话说回来,同人的缩手反应一样,思想的自欺性也是一种本能。为了避免坠入虚无的深渊,思考者只得借助思想的自欺,暂且躲在信仰里,以避免虚无之消极情绪的骚扰。正是出于这种生存下去的本能,人们借助自欺的思想构筑了这个世界。为了维护这个因群居需要而出现的集体的社会,我们灌输给自己道德、法律之类的社会规约,给我们的社会规定标准,在标准评判机制下,有人因符合规矩而受褒扬,有人因违背规矩而遭唾弃,甚而也必然有如祥林嫂这般的人被碾死于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在一个更高的不易察觉的层次,将这种内在的标准或者信仰形象化为艺术。德国美学家康拉德·朗格有一个命题:“艺术就是有意识的自欺。”[5]27如建筑这一凝固的艺术形式,便是人们灵活运用自己思想之自欺的代表。例如古希腊神庙,更确切的再如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建筑,人们在自己思想的某种信仰指导下创造了这些建筑,而通过建筑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所带来的人的感官的快感,信仰转了个圈回到人们的思想,使它的追随者如醍醐灌顶般一次次确认着它,这种自欺的享受让人如沐春风,乐此不疲。在此,信仰让人认识自己存在的意义,而真实可感的建筑之类艺术则时刻强化着这种认识。
(三)对思想自欺性的试分类
在上文对思想的自欺性做了简单介绍之后,读者便能较容易地理解开篇便需强调的事:这里的自欺是基于一种人类的思想本能而谈,是个中性词。虽然本文以鲁迅对知识界自欺欺人的批判入题,但我们并不介入任何批判或者对批判的批判,毕竟我们已经试着说明信仰下的信奉和必然引发的对另一信仰的批判同出于思想的自欺,可我们是否如鲁迅批判的那样在做着些“放弃真正的是非之论、真实的意义诉求”[1]139之类的虚无的事?这当然可以看做一种对本文的很好的批判。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暂把思想的自欺分为个人的自欺和社会整体的自欺两方面。前者指有意识的自欺,指思考者在虚无世界面前的混世态度,如鲁迅的《端午节》中方玄绰的例子: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将来的少年是否会威压自己的儿孙与现在的因见老辈威压青年而愤愤本没有关系,可当事者通过这种看似很有关系的理由为自己的妥协找到了解释,从而心安理得,不致被自己的无所作为所困累。后者指无意识的自欺,指在社会这一机制下与被灌输的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观念相关的自欺,如鲁迅作品中艰难度日却仍要香炉和烛台去社会信仰里寻求安慰的闰土,如捐了门槛后因获得安慰而“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3]120的祥林嫂。当然,鉴于社会本由个人构成,此种分类必然会有交叉。因此,这里的“个人”特指没被社会集体规约同化的部分,而这里的“社会整体”仅指为了集体的存在而不得不去维护稳定时属于文化专制的部分。
邓晓芒基于对自我意识的分析,认为人在骨子里头就是一种自欺的动物,他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欺的结果,总要假装相信某些东西,得出上述结论的:“何谓自我意识?简言之,自我意识就是把自我当作对象看待。这就需要‘自否定,将自己‘一分为二,即自身分裂为体验的我与被体验的我、评价的我与被评价的我、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5]28邓晓芒不仅对自然界中唯一需要“做”的人这一特殊生物如何践行信仰的自欺进行了哲学上的阐释,而且启示了我们一种自我否定机制,而这一机制对理解鲁迅对于思想自欺性的解决是个前提。
二、鲁迅对思想之自欺性的意义
稍加思索,细心的读者便要有这样的疑问:鲁迅是否也处于一种信仰的自欺当中,只是以“打破信仰”为信仰?在此,我们以对上文另一遗留问题的解释介入对这个问题探讨,即本文是否在做着“放弃真正的是非之论、真正的意义诉求”之事。本文开始已对思想的自欺进行介绍,可我们却没有细说文字介绍之外的意义。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自欺,我们都需关注它自身的目的。若非得就思想的自欺性给本文分类,本文显然已不能归为无意识,可它又并非如有意识的自欺那样出于为己谋私利的目的。相反地,本文十分真诚地对待这个事实并试图进行解释,以求那“真正的是非之论、真正的意义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显然也有别于老庄式的逍遥无为,可以说,此篇拙文一定程度上属于“三界之外”。对这一问题进行这般看似嗦的解释是要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事件的本质往往在于它的目的,而事件的意义往往又要超过事件的本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进入对本段所提问题的解决。
(一)从“鲁迅研究之谜”看鲁迅行动的意义
学者谢泳在《鲁迅研究之谜》中引出一个被称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却总是被专制利用?”[6]120这一疑问显然涉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但本文试图将文学和政治继续抽象化,以期引起更深层的思考。在介绍了思想的自欺性之后,我们可再做些对“意义”进行解构的尝试。这里的“意义”,一般指某事件的有用性,但这种有用性对他者或后世产生影响的过程却往往不再受事件本身控制,在盖棺定论对其进行评价时往往已被曲解,而之后附丽于旁观者和后来者的评价而存在的意义,往往并非事件本身所实有。这种评价中必然有的主观性,对于如鲁迅这样的公众人物,则得由掌握公众话语权的主流文化进行发挥。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便免不了要被利用,至于这个将“专制”单列为疑惑点的“鲁迅研究之谜”,事实是,本就无所谓反不反专制,能被利用是关键。为说明自己的价值体系去找些例证做口实则是后话。鉴于理论本身也带有的自圆其说的自欺性,这样的例证俯拾皆是,进行让人信服的理论证明也亦非难事。
毛泽东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7]698时至今日,这个评价仍是存于普通大众脑中关于鲁迅的印象,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到社会主流文化中“权力者的力量、知识者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实际运动的力量、社会的综合力量”。[8]120在此,我们其实还可引用另一有趣的事实对这种认识进行切实的证明: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介绍,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后高压的文艺政策下,鲁迅被视为“文艺骗子”“文学界的妖孽”“土匪大师”,其作品被列为禁书,“整个社会似乎都感到鲁迅这个人压根儿不曾存在过,谁也不敢公开接触”。[9]
在看清处于被评论位置的“意义”之后,我们不妨再往外一层,将这种认识冷静地放到历史境域去思考:任何时代都不乏可被放于被颂扬或被诟骂位置上的“名人”,历史远去,他们都成了被贴上“意义”标签的文化符号。如秦桧的标签是“卖国贼”一样,邱少云、董存瑞的标签是“爱国英雄”。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系统通过对这些真实人物的艺术式宣传,强化着各自定义的意义。在此,另一事实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另一个现实问题:“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0]43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对鲁迅的评价,那么,既然孔夫子被拉下圣坛后鲁迅又被抬上了这个位置,那面对将孔子、鲁迅之类符号被拉下神坛或拉出妖潭后仍有被附上新意义的新符号出现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对待?
(二)从鲁迅的“立人”目的看鲁迅行动的本质
1.是“孔”还是“教”
基于上述对思想自欺性的分析,结合鲁迅作为“批判封建孔教的战士”这一认知,我们提出一个疑问:鲁迅批判的是“孔”还是“教”?我们应该知道,鲁迅并非只是批判,他还在整理,批判某一具体文化现象时的不留余地同对封建文化的全盘否定是两码事,我们发现了他对某一现象的深恶痛绝,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去臆想他对全部封建文化的决绝态度,纵向的程度和横向的广度总在感性的“度”上有暧昧,实质上却是天壤之别,鲁迅只是按自己的价值判断行事,仅此而已。“鲁迅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用大量精力认真整理、研究、分析传统文化遗产,发掘其中那些仍有活力、可资借鉴、可能实现转型发展的成分……鲁迅用了差不多三十年(大部分)的时间,整理了二十二部古籍,包括《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1]127鲁迅也并非像乱撞的无头苍蝇一样,毫无选择地对传统一律打倒。例如,鲁迅批评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大团圆”“十景病”是粉饰现实、制造瞒和骗的大泽,但对《红楼梦》却非常赞许,认为其“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12]338因此,从鲁迅的这种选择中,我们不难分析出鲁迅批评传统背后的态度:鲁迅竭力打破“瞒和骗的大泽”,以劝人回归真诚,鲁迅反对在粉饰现实的文学里自欺欺人,是劝人关注当下。
那么,联系鲁迅的“立人”目的,打倒“孔教”的要旨便不在“孔”,而在“孔”背后代表的文化权威,在于意图将有着独异灵性的个人收编于自欺的主流文化的那个“教”,“吃人”的也不是“孔教”,而是抹杀人性以求稳定的社会意义上的广义的专制文化。民众在自我定义、自我评判的自欺的主流文化体系里受着瞒和骗的诱拐,做着思想的奴隶,这才是鲁迅真正批判的。毕竟,教人做思想之奴隶的自欺文化体系不打倒,独异的人便立不起来。即使这个“孔教”打倒了,另一什么“教”也会继续作祟。这里要拿来做例证的事实是:破“四旧”的年代,人们至少是两千年来受“孔教”压制最少的,可是,人的思想真正独立了吗?
2.打破与建立
按照惯常思维,被冠以“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之“主将”的鲁迅,在批判传统儒家文化之后试图建立“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3]56的新文化是很易接受的。但是,且不说这种新文化只是一种理论的设想,单说认识到鲁迅是在打倒“教”而不是“孔”之后,我们便不能再认为鲁迅试图建立的是另一称作“新文化”的“教”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鲁迅是要建立什么?
尽管我们常说“不破不立”,但在鲁迅这里,打破却未必意味着建立,人们往往在迫切想知道实际“建立”了什么时忽略了“打破”本身的启示意义。周作人曾援引美国文学史家福勒特在《近代小说史论》中的见解,指出“某种的破坏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设”。[14]75鲁迅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的“建立”不是急着输入些不解释涵义的名词或者简单地介绍些“主义”,而是关注最真切的现实,在“论时事”“砭锢蔽”的不断“打破”中教人怀疑、教人理性,以“立人”为目的,呈现毫无伪饰的真实。在这里,始终“打破”的态度代表着始终怀疑,只有教人始终怀疑才能启示人们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我”。怀疑之后的“我” 的选择则不断将这种对独异的“我”的认识确认下来,而对“我的选择”的坚持则能促成“立人”的最终实现。因此,所“建立”的并非鲁迅在自欺的理论下臆想的,而是在不断“打破”中竖起的无数个“我”自己选择的。自欺下“建立”与“打破”的悖论在鲁迅的“立人”思想里很好地得到了解决。
3.现在与未来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疑问,拷问我们:黄金时代的信仰在捉摸不定的历史面前本就虚妄,现实的人们又仍要受苦,真正的光明在何处?鲁迅认为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只有走出虚妄的信仰理论下怪诞的自欺,关注当下人的“活”,解决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在信仰的诱拐下做些看似有理由实则是自欺的逃避,未来人的“活”才有可信得过的出路。况且,未来人的“活”也并非就得以现在人的“死”为代价,更何况,倘若总将美好寄托于明天,总活在这样的自欺里,那每个时代不都是教人“死”的?那这许给人“活”的信仰,岂不是教人乐于“死”的奴化工具?如伊藤虎丸的说法,“鲁迅在这种终末论式的‘个的自觉中,不仅拒绝了一切权威和教条,同时也拒绝了一切未来希望,而只是执着于现在”。[15]300鲁迅的启蒙并不是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许给人们多么美好的未来的梦,而是教人在改善现实中切实体会到自我,不断确认着自我的力量,以达到“立人”目的,毕竟,当人们都本着自我生活,世界也就明朗起来了。
正如在“是马上脱下唯一的棉衣给将要冻死的人,还是坐到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16]27这一选择中我们该选择前者一样,鲁迅呈现未来的方式是“执着于现在”,如果这是一个悖论,鲁迅用“立人”思想又一次给我们做了解释:唯有看似没有追求地“执着于现在”,切切实实去做些对于改变当下有用的实际的事,人们才能发现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别人直接告知或者书本理论里预测甚至是臆想的能动性,人们才会知道只属于自己的个性在哪里,从而明白自己对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只有这样,人们从绚丽如云朵、缥缈也如云朵的理论自欺中真正醒过来。醒来之后的人们做好属于自己的事(这里的“做自己的事”并不是一种自私,毕竟每个人的“自己”里都会有包容和为他人),发挥只能自己去发挥的意义,那么,不管历史要流往何处,未来都是光明的。因为那是人的未来,在那里,人的自我得到发挥和认可,人们对自己和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有清醒的认识,人们不会被因维稳而存在的社会道德、法律等规约蒙蔽了双眼,道德、法律之类主流思想也不会去做些维稳之外的旨在愚民的事。
4.绝望与希望
鲁迅在《野草·希望》中引述过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希望》之歌:[13]178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丢掉你。
有人认为这只是鲁迅的一时自嘲,他终还要回到自己的希望里去,其实不然,这至少说明鲁迅意识到了里面的问题,而关键就在于“意识到”这个层面:要么彻底信仰,要么决然离去。这里自嘲里的徘徊状态,其意义在于它可以把这两个极端都解构掉而进入另一层次。这种始终处于自我否定状态的本源性自觉是可怕的,它不仅会把既定的许多认识解构掉,还会跳出来把解构掉既定认识的思想本身也解构掉,从而坠入空洞的虚妄,这种状态如竹内好评论文学时说的那样:宛如旋转的球体的轴心一般,以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的形态存在着。[17]75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渺远罢了。”“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50人只是因希望而行走么?不是的,只是在行走而已,或者说是因行走才有了希望,就像自行车,不是先立起再走而是因为走才得以立着。鲁迅拒绝希望之自欺,只着眼于当下切实需要做的事情。鲁迅拒绝希望,拒绝坠入一厢情愿的理论的自欺里,如鲁迅之拒绝希望并不意味着放弃一样,其之后的拒绝绝望,也并不代表着奋起,毕竟奋起又是新一轮的希望的自欺。在这种看似空洞的彷徨中,其意义已无关绝望或者希望,而是始终保持的“拒绝”态度。
至此,我们从鲁迅的“立人”目的入手分析他的行动,对某些认识进行廓清,我们看到鲁迅如何用诚和爱对待自己去剥掉所有理论的伪装和既定思维,以便看清赤裸裸的现实,以及如何用诚和爱苛求自己去跳出用瞒和骗编织的关于未来虚妄的空想和希望而做些切实的事。
三、鲁迅对思想的自欺性之解决:作为态度的抗争
“他的一生构成了一个悖论,那是死与生、回忆与现在、绝望与希望、乡村与城市、文学与启蒙、文学与政治之间充满了张力关系的结合体。但是,这种悖论并不意味着静态意义上的两极对立之间的‘辩证联系,它是以一种特别的动态方式表现的:他并不后退,也不追随。他先使自己与新时代对决,依靠‘挣扎来涤荡自己,再把涤荡过的自己从那中间拉将出来。”[18]37鲁迅始终在自我否定中保持这种挣扎,始终要把涤荡过的自己拉将出来,因此,面对与无处不在的混沌的自欺,任何“抗争”在鲁迅这里都不是方法,如“打破”一样,它的目的也不是“建立”,相反,“建立”反而会抹杀“抗争”的意义。以“立人”为目的,鲁迅将动态的“抗争”凝结成一种静态的态度,使他得以独立于思想的自欺之外,鲁迅不仅没有坠入以“打破信仰”为信仰的自欺,而且以至死不宽恕的坚持态度启示了我们一种始终作为态度的抗争。
竹内好在阐释鲁迅对孙文的倾倒时说:“对于一个永远的革命者来说,所有的革命都是失败。不失败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成功不叫喊‘革命成功,而是相信永远的革命,把现在作为‘革命并没成功来破除。”[2]117其实,这并不仅是一个所谓革命阶段的问题,在任何一个人为定义的革命阶段我们都可以说革命取得了一定程度胜利,但同理,我们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革命失败了,这恰恰证明了革命应是一种态度、一种过程。 “对于鲁迅来说,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无穷无尽的重复与循环,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势必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评者,因为当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了那种历史的循环——这种循环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鲁迅倡导的始终是那种不畏失败、不怕孤独、永远进击的永远的革命者。对于这些永远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只有通过不懈的、也许是绝望的反抗才能摆脱‘革新——保持——复古的怪圈”。[19]17对大多数人而言,对矛盾的解决可以是矛盾双方的平衡,平衡所带来的安定足以让人们暂不去关心矛盾是否得到解决或者是否有催生新的矛盾的必要,可对于鲁迅却不行,新的矛盾解决了鲁迅的“抗争”也不会停止。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20]28结合康德的这段话,我们会想到前文“意义之外的其他”一节最后有待解决的疑问。当我们把鲁迅作为态度的抗争抽象出来,而不只是将其看作“打破旧”与“建立新”之间的方法途径,我们不仅发现了鲁迅对思想之自欺的最终解决,而且也启示了作为思想之行者的知识分子去解决历史怪圈的办法:将抗争独立出来,并将其始终保持为一种态度。
参考文献:
[1]彭小燕.启示信仰与解构虚无——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J].齐鲁学刊,2008(1).
[2]竹内好.鲁迅[M].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3]鲁迅.呐喊[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4]靳丛林.竹内好的鲁迅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邓晓芒. 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6]谢泳.胡适还是鲁迅[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林贤治.鲁迅如何被利用[J].鲁迅研究月刊,1998(10).
[9]田波澜.鲁迅形象在台港澳地区的“变迁”[N].2013-5-19.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温儒敏.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J].北京大学学报,2001(4).
[12]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福勒特. 近代小说史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5]符鹏.作为方法的日本鲁迅研究——以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为中心[J].文化与诗学,2009(12).
[16]鲁迅.坟——鲁迅杂文精选.[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17]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三联书店,2005(3).
[18]孙歌.竹内好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汪晖.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四(上卷)[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20][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