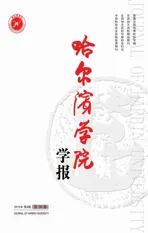青岛租界设关征税缔约探析
2015-03-29杨秀云
杨秀云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1897至1898两年间列强在中国强占的五处租借地中,九龙、广州湾和威海卫未另设海关,其进出口管理和关税征解,分别由设于这三处租借地周围的九龙关、粤海关和东海关的分支机构,按对外国进出境事务办理。但胶州湾和辽东半岛则先后建立了租借地海关:青岛海关和大连海关。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租借地的中国海关税收成了当时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和清政府密切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赫德代表清政府与德国驻华使臣反复晤商,签订了一系列有关青岛租借地设关征税的章程。已往学者尚未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笔者尝试对此领域做一探析。
一、《青岛设关征税办法》的商订及续订附件
1898年德国利用前一年发生的山东巨野教案占领胶州青岛,强租离胶澳海面潮平周遍100里之地,租期九十九年。根据《胶澳租借条约》有关设关的规定,赫德与德国使臣就青岛征税设关事宜进行了反复晤商。
德国原拟将胶州作为互市之场,不设关征税,旋拟在该处建立德国税关。[1](P9)随后决定将其辟为自由港,[2](P212)欲参照香港的自由港制度,把胶州湾租借地发展成为德国在远东的商业根据地。《胶澳租借条约》第五款规定,中国原有税卡设立在德国租地之外惟所商定一百里地之内,此事德国即拟将纳税之界及纳税各章程,与中国另外商定,无损于中国之法办结。[3](P739)据此,德国需保护中国海关在胶州的利益。所以,胶州青岛租于德国之时,中国拟在该处设关征税。当时拟有两项办法,“一系沿青岛陆路各边隘设关卡稽征出入货税。此法用人既多需费亦巨,且稽征亦无把握,商货更多留难;二系即在青岛海口设关稽查出入各货,惟征税之法入口者须俟转运内地出口者已抵海口方能起征”。后经德国亨亲王议定,即照第二法办理。[4](P3936)
德国意欲将胶州湾建设成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 +商业”根据地。[5](P46)有鉴于香港的境界税关之弊,1899年4月,德使与赫德协议,成立中德关税条约,以互相保护本国之利益为目的——即与自由港并生之租借地之经济利益与中国政府之关税收入——承认于租借地内设置中国海关。[2](P212)关于胶州设关一事,早在1898年春德国亲王到京,曾当面对赫德说,与其在胶州沿边地方多设缉私处所,不若在界内设关总理一切等语。并托赫德筹议办法,一面将所论情形详报本国。[1](P10)胶州征收税钞等事应如何办理,赫德也提及,后来与德国代表反复磋商议定,“可由中国在该处比照九龙等关,派税务司前往设关”。但要求“先允订明数端:一、应派德人为税务司。二、所有进出该口之各项货物,统归其一律办理。三、税则宜照通商税则,一律无异。以上各节若允行,即可照办。”[1](P9)赫德恐坐失机宜,特派宜昌关税务司德国人阿理文前往胶澳谒见德国巡抚拟议一切。德国巡抚遂同意在胶澳划出地址一段设立中国海关。[1](P9)
赫德即指明阿理文前往查明一切,随后阿理文拟定了《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赫德与德国使臣经酌商核实后,于1899年4月17日,与前德国驻京大臣海静签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共20条),主要内容有:第一,德国允于青岛地区设立海关,但应由德国人担任税务司,其他海关洋员亦应优先考虑德国人。第二,该关与德国官员暨德国商民等文函往来,均用德文。第三,输入胶州的华洋货物一律免税,若进口洋货复有胶澳租界运入中国内地,进口土货复由胶澳租界转运他口或出洋之时,则由中国税关照章征税,但租界内所产土货及由海路运来之物料制成品免征出口税。至中国内地各物运入德国租界内制成各货,其征税章程,嗣后酌议订办。[3](P884)第四,船钞之收支及泊船规费等项不属税关管理。第五,德国允于胶州界内青岛地方指定处所,足为中国建立海关,暨盖造各员住屋之需。第六,中国政府在胶海关不另设海关监督。[3](P885)同一天,赫德在致总理衙门的申呈中称,“现经筹定办法,缮立英、汉文各一份,彼此画押存案”。[1](P10)其所拟办法要义有五条:“一、该关所用洋员,应由总税务司由各处新关人员内拣调德国人前往。二、德国界内所产各物出口时,毋庸纳出口税;界内所用之物进口时,毋庸纳进口税。三、中国土货经过德界出口者,并经过德界入内地之进口货,若由洋式船只装运,应按通商税则完纳税项;若系华式船只,应按向遵之中国税则办理。四、凡通商各关监督应办之税务各事,暨办事之权,均归该关税务司一人掌理。该税务司所发入内地买土货之报单运照,暨运洋货入内地之税单等照,均与各关监督所发者无异。五、所定办法各节均属试办若日后查有应行修改之处,即可会商改订。”[1](P10)赫德认为对于上拟办法,若总理衙门以为然,即可照办。否则,只能在沿边地方设立缉私处所。[1](P10)
依据这个征税办法,德国以允许中国在胶州设立海关,换取了海关税务司及洋员用德国人,公文用德文,输入胶州的华洋货物免税,免交船钞收支及泊船规费,以及排斥中国海关监督等诸多权益。看重关税的赫德自然对此表示赞同,进退维艰的清政府也只好同意。4月26日,总理衙门回复,“该税务司所拟《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尚属妥协,惟六条、九条、十三条、十七条内有‘德国属界’字样,应照条约改为‘德国租界’。‘俟一律更正后,即由总税务司与德国驻京大臣商订画押,以便设关办理一切,并申报本衙门。’”[1](P11)赫德奉此与德国海静大臣函商,所改字样均可照改,并商定海关开办之期即可自7月1日为始。赫德请示派阿理文任该处新关税务司。
根据上述办法,经过赫德与总理衙门的一再商讨,并与德国使臣几经交涉,最后议定比照九龙等海关的做法,由中国派德籍税务司在胶澳租借地于1899年7月1日设立中国海关即胶海关,亦称青岛海关。《青岛设关征税办法》作为第一个租借地海关的征税措施,对日后其他租借地海关如大连海关设关征税起到了示范作用。自由港制度至1907年也被日本采用于关东州租借地。[2](P212)
既然德国政府允许中国在胶州界内设关征税,那么青岛海关应有发给内河行轮专照之权针对青岛海关设立以来,轮船在胶州租界航行的各种乱象及走私情况,赫德与德使穆默反复相商,于1904年4月17日,签订了《续立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附件》(共6条),以期规范德国租借地的轮船航行和贸易。它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所有轮船准其驶赴内港来往,但须遵守1898年所定《内港行轮章程》及后订相关章程;第二,持有牌照的华洋轮船主,可在青岛水面随意行驶和自由往返青岛和内地;第三,轮船出入青岛,船主须报关请单,完纳船钞。第四,防范偷漏、巡缉洋药走私、邮政推广事宜,德国应襄助办理。[1](P13)
二、《会订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的签订
《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试行几年后,德国和清政府都不满意,这是双方始料未及的。
德国方面,原以为通过把整个租借地都划为自由港的范围,并规定由海路运进青岛口岸的货物均不征进口税,中国内地土货运至青岛亦照此原则免税或完税等有利条件,可以为租借地吸引大量的资金和货物,谋得租界内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但几年的发展与德国预期目标——将胶澳建成一个繁荣的商业基地,“以是为东亚贸易之中心,造成第二香港”。[6]——相差甚远。原因在于:一是,这种优越的税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而只属于靠总督府的订单养活的德国商人。鉴于列强对华人的欺压和歧视,中国商人怕惹麻烦,对外国租借地“敬而远之”,多数不愿进入胶澳租界买卖货物,因此中外贸易多在租借地边界的税卡进行,而不是德国原来设想的“将中国商人吸引到这里营业,使得这块租借地的贸易获得发展”。[1](P105)这样,自由港税制不是搭起了桥,而是垒起了墙。二是,租界走私严重,免税区域范围广,而海关对于租界走私活动向来难以有效稽查,从而影响了正当的贸易,也妨碍租借地的发展。20世纪初,列强各国纷纷来华进行修约谈判,德国趁机要求对原《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进行修订。而在中国一方看来,德人是仿香港例以青岛为自由港,在租界内销用物品但不允许征税。那么胶海关之征税只能以租界运出为限,这样免税区域太过广泛,虽然设置税关,但多数的分卡稽查仍难防止漏税,而距离较远的地方往来检查官商均感到不方便。“事实将证明这个1899年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主要是因为没有适当的规定来检查来往于租借地和内地的货物。”[7](P361)
就这样,中德两国目的虽异,但都认为有改正税关协约的必要。于是赫德与德国驻京大臣决定协商改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双方商谈的改订内容及原因,赫德于1905年4月27日致函税务处作了解释。首先,赫德逐年列出了从1899年设关征税《办法》实施以来到1904年六年间每年共征货税数和其中的进口税,①“历观已往征数,年胜一年,从此办去,定可卜其日增月盛。情势虽系如此,然在关员稽征仍不能为确有把握,而商货亦尚不能转运自由”。[4](P3936)其次,指出了改订办法的内容。经德国大臣暨总税务司酌商,一致同意:“德国允在海边划一地界作为停泊船只起下货物之定所。凡出口货在未下船以前即完出口税,进口货除均用各物暨租地内所用机器并建修物料免税外,其余百货于起岸后未出新定之界以前即完进口税。关员在彼照章办理一切,德国相助无阻。一面由中国允每于结底将本结所收进口税提出二成拨交青岛德国官宪应用。”[4](P3936)再次,赫德解释了如此改订的原因。之所以在中国领土上设关征税,还要给德国提成,是因为“现在办法系凡货运出租地方能纳税,不出租地留用之货一概不征,倘将租地留用之货改为征税,此新征之税本应由德国官员自得也。”为什么是提交德国“二成之数”呢?在于“开议之初,按税务司所存案卷核计约有一成货留于租地之内不纳关税,而按德员所核计者,则称留有三成,嗣经两面复行调查,详核在关员知留用者为一成五,而德员亦知不及三成,不过二成二三,于是折中定为拨交二成之数。”[4](P3936)为减少清政府的疑虑和阻力,赫德诱使清政府,“如此订办是中国将向所未得之款拨交于人而收舍远就近,舍难就易之实数。自兹已往稽征既更有把握,税项当更增加,而商货之运输亦较昔自由无疑矣”。[4](P3937)最后,在德国大臣电询德国政府可否订办之时,赫德亦呈请税务处将所议条款一并呈请清廷裁酌。
后经赫德与德使穆默几经磋商,于1905年12月1日订立《会订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共八条,其要点有三:第一,由青岛德国殖民当局在租界内划定一无税区,区外由海关征税但海关应将每年所征税收包括鸦片在内的进口货物关税的20%交给青岛殖民当局,作为中国政府津贴青岛租地之用。第二,规定租借地免税货物种类,如一切军用物资、公众之用品、运入租界内的邮政包裹等。第三,租借地内各厂制成的各种物品,出口时按原料价格征税。[8](P336)次日,德国方面颁行《青岛德境以内征税办法章程》,嗣后经赫德接受。
这项章程保护了德国在租借地的利益,也大大促进了租借地工业的发展。表现在:一则无税区的划定消除了之前干扰保护区和内地间贸易往来的关税壁垒,吸引了大批商人到来,自然带动了货物周转和商业贸易发展;二则规定了大量货物的免税和租界地内工业产品出口的优惠待遇,德国可以直接利用廉价的中国原料在租借地加工,产品则无需海关查验即可直接销往中国各地;三则海关税收二成交殖民当局作为“酬答”的规定,可使殖民当局得以用中国的税款扩大殖民建设。所以修改方法实施后,自由港制度趋向完善,青岛口岸的工业和贸易得到飞跃式发展。1906年贸易总额达3 070多万两,比1905年增长了800多万两,大大超过了已往的增长速度。[9](P552)同时,修改办法划定的无税区由整个租借地缩小为青岛港区一处,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商人的竞争和关税的增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因参加欧战,青岛德军战败,日本强行夺取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的一切特权。1915年8月6日,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税务司缔结复设青岛海关之协约——《青岛重开海关办法》,日本完全继承中德间关于青岛海关之协约,遂自9月后复行设关征税。直至1922年,日本将胶州湾交还中国,胶海关才摆脱了它的租借地殖民地性质,但其半殖民地性质则并无改变。[10](P110)
三、余论
青岛设关及其旧关税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和外国自由港与中国商埠之间的矛盾。在租借地设立海关征税的方法举措迥异于中国其他海关,因为此等租借地在国际上的性质“实际上自租界国对于租借地之各种设施观之,与其对于殖民地之设施实无大意”。[2](P209)所以,租借地海关名义上仍为中国海关,但因各租借地占租国无视中国对租借地的主权,因而租借地海关实际只是占租国扩大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的一个工具。虽然就关税方面而言,租借地与中国缔有的特别规定有承认中国在租借地拥有关税主权,但清政府和赫德依然不能依靠所订章程完整地维护中国的关税及其他主权。
首先,清政府及赫德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任用租借地中国海关任职人员。近代中国海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税务司专断。根据1864年的赫德拟定的经总理衙门批准的《通商各口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各关洋员均由总税务司赫德任免、奖惩和调动。而《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虽然规定青岛海关为中国的征税机关,赫德持有海关人事任命权,但税务司及其他海关职员须用德国人。税务司及其他关务人员的任免,赫德名义上有决定权,但必须与德国或日本殖民当局协商决定,这实际上等于变相默认了青岛海关为德帝国主义所操控。这些规定公然违背了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很显然,也是一种蔑视国际公法的侵权行为。
其次,租借地海关,不是以主权国的中文也不是以近代中国海关系统官方通用的英文而是以殖民国的德文办事行文,这既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半殖民地海关行政方面的特点之一。同样,这对于一直标榜近代中国海关的国际性,实则操控在英国人手里和英国关员居多,并一直占据总税务司头衔的赫德来说,德国的反常做法,也是他难以接受和无可奈何的事情。
再次,“无税”的自由港或自由区制度的实施使德日获得诸多免税权。除了条约上规定的无税货物以外,凡在租借地内使用的多数进口货,均有免税之特权;对于制造品之出口也获得减免税之特权。由于租借地全部或部分作为无税区域,而又不设境界税关,无论租借地官吏如何襄助,仍不能达到充分防止偷运之现象,然而青岛海关还得对德国的襄助“酬谢”20%的海关收入。而在欧洲最早发达的自由港之制度“本以设置于本国内之港湾,或以殖民地为限”。[2](P215)而在中国,却将它置于租借地。
最后,租借地海关监督管理的异化。近代中国每一个海关都设有海关监督一职,虽然海关监督只是各口海关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在租借地海关设立章程里,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不予设立海关监督,而由租借国德国直接管理,连中国这种形式上的监督管理权也剥夺了
总之,19世纪末出现的租借地和租借地海关,是对中国海关主权的进一步侵犯,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更加深化了。
但是,德国以租界为自由港,又允许中国在这个地域内设置关税,以求两国利益的调合,这是国际法上的新例。德国抛弃其租地自由港制度,在高柳松一郎看来,它“采用其本国所行之自由区制度以便青岛占居中贸易之地位,俾有利于租借地工业之发展且更为中政府保护其关税收入也。约言之,即举租借地一并合于中国之关税领土,学者间所称为关税加盟者是也。”[2](P215)同时,依据协约章程:“自由区域之划定虽系租借地政厅之权限,而自由区内货物之移动及自由区与外界之交通,则概归中国海关管理;凡出入于青岛之货物,均于出入自由区域时征税。故关税行政上之取缔最能生效,而租借地境界线及他处之监视所(除关于帆船贸易者外)遂而裁撤之。”[2](P215)
注释:
①即“溯查光绪二十五年共征货税约三万三千两,内有进口税约一万八千两。二十六年共征约六万两,内有进口税约三万七千两,二十七年共征约十万八千两,内有进口税约七万五千两,二十八年共征约十九万八千两,内有进口税约十五万两,二十九年共征约三十一两,内有进口税约二十五两,三十年共征约四十三万两,内有进口税约三十三万两。”引自王彦威纂辑,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188,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1]帝国主义与胶海关[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2]沈云龙.高柳松一郎.近代中国史料集刊:第74辑中国关税制度论[Z].台湾:文海出版社.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1957.
[4]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188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5]寿扬宾.青岛海港史(近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
[6]淮阴钓叟.青岛茹痛记.新青年:第2卷第3号[N].1916-11-01.
[7]〔英〕魏尔特.陆琢成,等.赫德与中国海关(下册)[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8]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9.
[9]梁为辑,郑则民.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10]蔡渭州.中国海关简史[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