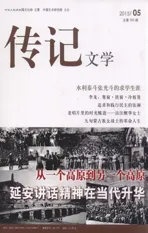散文研究领域又一次突破性收获
——评黄科安《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
2015-03-29古大勇
文 古大勇
散文研究领域又一次突破性收获——评黄科安《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
文 古大勇
黄科安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孜孜不倦于散文研究,先后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名家论》《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等学术专著,主编有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散文的民族化与现代化》。2013年,一本煌煌36万字的新专著《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书属于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从材料收集整理,到内容撰写完成,到增删修改打磨,再到最终付梓出版,整整历时八年,可谓是一本抽血敲髓、化精吐哺的生命之作。关于该著的评价,已有袁勇麟先生的《评黄科安〈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发表,该文认为《叩问美文》具有三个特色:“一是全面系统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外国散文译介的总体概貌”、“二是从‘译介’视角,探讨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 三是较为深入探讨周氏兄弟等人在外国散文译介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同袁勇麟先生的中肯评价,对这些特色,本文不再赘述。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叩问美文》还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或贡献。

黄科安著《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书影
不追“时髦”、“以史带论”的扎实持重文风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学术研究的倾向,即“以史带论”和“以论带史”。这两种倾向的形成最初受到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所谓“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的影响。“史料派”强调史料和材料是基础,论从史出,“论”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杜绝缺乏材料支撑的玄虚蹈空之论。“史论派”则强调理论在先,先有一个先验的理论,或先有一个“正确”的结论,然后竭力寻找有利于理论或结论的材料,而对不利于理论或结论的材料却置如罔顾,由此来证明理论或结论的正确。“史料派”与“史论派”各以“以史带论”和“以论带史”为主要的研究思路。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史料派”研究受到冷落,“史论派”研究则始终占上风,“以论带史”成为一种流行的研究方法,先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无往不胜的文学批评法宝,例如,毛泽东的“鲁迅论”成为彼时鲁迅研究唯一合法化的指导性纲领。新时期之后到8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恢复生机,“史料派”研究得到重视,陆续诞生一批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成果。但是好景不长,正如温儒敏先生所担忧:“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那种‘以论带史’的风气如今又有回潮。只不过这个‘论’不再是当年那种政治理论,而是其他宏大叙事理论罢了。现在学术生态不大正常,许多学者都很无奈,陷入了所谓‘项目化生存’的境地,做学问不是那么纯粹,而是太过受功利的驱使,这种新的‘以论带史’的方法因为比较好操作,好‘出活’,所以更有市场。那些简单摹仿套用外来理论、以某些汉学理路作为本土学术标准的所谓‘仿汉学’的风气,其实也是新的‘以论带史’”,“现代文学每年出版很多专著,实在看不过来。那种‘穿鞋戴帽’、以某种后设的理论框架去装一些作品或事例的;或者概念满天飞、花半天功夫无非证说了一点‘常识’的,几乎都成为‘主流’。我不太欣赏这些华丽而空泛的论作,宁可看点事实考辩之类”。
确实,温儒敏犀利而准确地诊断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最大病象,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功利化学术生态下,那种以某种时髦的西方理论作为先验的理论框架而寻找材料支撑,洋气扑鼻、华而不实的著作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在此大背景下,黄科安的这部专著表现出的学风和文风就显得难能可贵。它不赶“时髦”、不傍“先锋”,内容厚重扎实,文风朴实持重,能坚持“以史带论”的研究方向,不但重视材料的收集、挖掘、拾遗、补缺、考证和整理本身,而且其诸多立论亦建立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以史带论”,要求“论从史出”,“史”是“论”的基础和前提。作者也明白史料的基础性作用,重视史料的收集工作,他说:“为了做到论从史出,以事实为依据,本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者要潜心批阅大量的原始报刊。前些年,本人利用在中国社科院做博士后工作的有利条件,大量翻阅和复印几百种原始报刊资料,初步摸清当时知识者发表的散文译品概貌,并对其进行了甄别、收集和论证工作。”这“几百种原始报刊资料”,除香港、台湾地区的新文学报刊以及极个别冷僻的国内报刊外,几乎“一网打尽”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大陆地区所有译介外国散文的报刊,这是一个浩大的史料性工程,没有电子文献,没有重新整理而成的出版物,全是在发黄生霉、残缺不全、繁体字并且竖排、字迹模糊不清的原始刊物上寻找、收集、复印、抄录和整理,这是一个漫长而磨人的“笨功夫”,没有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坐“冷板凳”的耐力,是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的。这一史料性成果,主要体现在著作的“二十年代外国散文译介与现代散文的观念重建”、“三十年代外国散文译介与现代散文的视域拓展”、“四十年代外国散文译介与现代散文的偏至发展”等前三章内容中。这三章内容系统梳理了欧美、日本、俄苏等国散文作家作品的译介概貌,并将之置于中国现代译介史的背景下探求其流变的轨迹,完整地再现了外国散文被中国译介的动态化嬗变过程,填补了中国现代散文译介史上的空白。
当然,本书并非纯粹的史料考证类研究著作,一方面当然具有史料整理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史带论”的需要,也即是作者所说的“为了做到论从史出”。本著第四、五、六章主要以“论”为主,就是以“史料”为主的第一、二、三各章内容也穿插不同程度的“论”的内容。但是这些“论”的内容都是建立在充分确凿的“史料”基础之上的。例如,本书第一章提出,西方“Essay”对中国现代散文的话语形成和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以“自我人格”和“批判意识”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建构。作者随即以蒙田的《随笔集》、本森的《随笔作家的艺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现代随笔》、厨川白村的《走出象牙之塔》等为史料依据,阐释他们的文章中所涉及到“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个性的魅力”、“作者的自我”、“个人底人格的色彩”等关键词语对于中国现代散文“自我人格”思想观念建构的深刻影响;以厨川白村、青野季吉、有岛武郎、长谷川如是闲等人的史料内容为例,阐释其对中国现代散文“批判意识”思想观念建构的影响。
“域外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现代性转型”之学术命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散文研究属于传统文类研究,起步早。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前辈学者垦地开荒、筚路蓝缕,以及后来的年轻学者们的另辟蹊径、深化创新,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域外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现代性转型”这个学术命题前人不是没有研究过,打开中国学术期刊网进行查阅,不乏有关于这方面的单篇论文:或研究域外散文对于鲁迅、周作人、梁遇春等人散文创作的影响,或关注个案性现代散文家的散文中现代性内涵与域外散文译介的因果关系,或扫描外国散文译介的概况,或辨析有关散文文体内部各种纠缠不清的概念,或梳理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现代散文文类之关系;更有专们的著作研究鲁迅的《野草》与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关系……但是,这些都是颗粒、碎片、局部和细节。
如果说“域外散文译介与中国现代散文现代性转型”这一宏大课题是一个系统无缝、浑然一体的学术“建筑物”,那么,前者就是构建这个“建筑物”的砖石和泥沙,巍峨壮观的“建筑物”当然离不开砖石的堆垒和泥沙的黏合,但是,“建筑物”已经不再是砖石和泥沙的简单堆砌与组合,而经过重新的取舍、融汇、消化、锻造、生长,脱胎换骨为更高层次、富有独立自足意义的整体性存在物。从系统论的原理来看,整体虽然由部分组成,但正如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所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就是说,系统的整体性不是系统的部分要素之间的简单相加,部分一旦组合成整体,就产生了部分要素所不具备的功能和性质,形成了新的系统的质的规定性。《叩问美文》的学术意义就在于此——诚然,它的产生也是建立在众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但是,作者一旦赋予这些互不关联的、部分要素性质的前人研究成果以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眼光,在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框架内予以整合融汇和重新建构,就会产生一种点石成金的效果,升华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系统和新的质的规定性的有机生命体,成为“域外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现代性转型”之学术命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从该著的内容结构来看,显然具有“系统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特征。著作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属于“影响论”,按照历时性的时间顺序,梳理外国散文译介与新文学三个“十年”的散文现代性转型之关系,并以“现代散文的观念重建”、“现代散文的视阈拓展”和“现代散文的偏至发展”来描述“转型”之动态化进程。第四章属于“个案论”,重点择取现代散文史上的鲁迅、周作人、梁遇春、朱光潜四位散文家,研究他们散文创作或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与外国散文译介之关系。第五章属于“本体论”,从散文本体性的层面,重点研究“文学散文”、“闲话风”语体风格、“闲话体”小品文、“现代语体散文”、“艺术散文”、“何其芳体”散文等相关的散文言说方式和话语实践。第五章属于“结构论”,研究散文内部的结构性文类,即随笔、散文诗、报告文学、科学小品、传记文学等文类的产生与外国散文译介的内在关系。这五大部分构成了一个圆融独立的整体。而就每一部分来看,又由次一级的子系统和要素构成,形成了井然有序的三级系统。如第三章“四十年代外国散文译介与现代散文的偏至发展”,其二级“子系统”由“域外文学散文的译介与传播”、“西洋杂志文的兴盛与影响”、“苏俄散文的译品的崛起与独尊”构成,三个独立要素之间是按照“总论——分论(自由主义作家的散文)——分论(左翼和革命作家的散文)”的逻辑顺序排列。其三级“子系统”亦按照“总论——分论——分论” 顺序展开,“总论”部分先总体介绍左翼知识者对苏俄文学的译介,然后再分论“国统区”和“解放区”对苏俄散文的译介。这样,一个纲举目张、肌理清晰、逻辑严密、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规范性学术著作就呈现在读者面前。
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积极应对散文研究领域中一些长期悬搁的学术难题
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问题的缺失必然导致学术的研究流于过多地描述而走向浮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学术成果呈‘爆炸式’增长态势显得不很和谐的是‘问题意识’的缺失,这已引起学术界的严重忧虑,许多学者疾呼要强化‘问题意识’,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我们有很多著作,但没有很多问题。’”因此,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衡量一部著作学术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散文研究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大,成果多。但其内部仍然有一些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一些基本概念相互串门,夹缠不清,难于明晰厘定。一些文学现象丛生芜杂,复杂吊诡,难于把握本质。《叩问美文》一书能积极面对散文研究领域一些长期悬搁的疑难性问题,对相似概念之间的差异性缝隙进行小心翼翼的甄别,对诸多理论的“前世今生”进行客观的追本溯源,对种种问题所呈现的复杂“症候”进行科学的诊断辨析,对散文研究史一些陈陈相因的传统观点乃至一些权威的当下言说进行大胆的质疑辩驳,进而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一些具有个人见解的观念和主张,体现了作者苦心孤诣的学科建构意识。譬如,在散文研究领域,概念的厘定和规范最令人困惑。就是“散文”这一基本概念的界说至今仍没有取得一致,关于散文的定义就有逾十种说法。“散文”内部的一些子概念和相邻概念的界定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如随笔与散文、随笔与笔记、随笔与小品文、随笔与杂文、散文与小品文等概念之间的区别。本书作者面对这些学科因袭“难题”,没有消极逃避,而是迎难而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体现其具有主动解决学科难点的“问题意识”。如关于杂文和随笔的区别,针对学界有学者以题材的“软”、“硬”为标准作为两者的本质区别。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误读的结果”;并试图从杂文和随笔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来论证,认为随笔固然有表现“软性”题材的一面,但其“在硬性题材上的作用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如世界随笔史上的蒙田、培根、尼采、斯威夫特、厨川白村就是典型的例子;进而从鲁迅现代杂文观念的形成渊源加强论证,最后援引朱光潜的随笔分类观(议论随笔、抒情随笔和记叙随笔),认为狭义“杂文”大体等同于随笔中的议论随笔。在辨别随笔和小品文的区别时,认为晚明小品文篇幅短小,而西方的“Essay”却可以长达十几万字,不但具有“娓娓闲话”、如小品文一样的“母亲式的琐碎”,同时还具有以思想深刻和理性批判见长的“父亲式的琐碎”,从而得出随笔概念范畴大于小品文范畴的结论。由于作者的主张是建立在追本溯源、纵横比较、旁征博引、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所以观点令人信服。对一些有关散文的名家当下言说,作者也绝不盲从,敢于质疑,体现其独立思考的精神。譬如张颐武在《闲适文化潮流批判》一文中,认为林语堂等的“闲适派”小品是一种“‘现代性’的启蒙设计”,“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欲望和‘代言’欲望的一种表征”。本著作者则回到历史语境,联系林语堂的相关论述原文,既认同小品文的“以现代性为前提基础”的“启蒙话语的文化设计”,同时,也指出张颐武观点“是有缺陷的”,“排斥‘闲适’的趣味和格调,这就导致否认‘闲适’话语作为一种‘消费产品’和‘优雅的文人消费之品’,这显然有把‘闲适’的审美范畴净化和抬高之嫌,和林语堂所理解的‘闲适’含义有出入”。启蒙和救亡是中国现代文学两大核心主题,但却是经过最大“公约化”后的本质性特征,过滤遮蔽掉其背后众多微观的、细节的、感性的、生动的个性化内容。张颐武将“闲适派”小品纳入到以“启蒙”和“现代性”为中心的时代宏大叙事中,虽指出“闲适派”小品文与时代相关的“共名”性特征,但却忽视了其独具特色、不可复制和代替的个性化标志,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本质化”的思维误区。本著作者对张颐武观点的辩证理解无疑是切中肯綮之论。
译介属于一种“跨文化”交流,通常而言,“跨文化”交流会产生明显的“文化过滤”现象。“文化过滤是跨文化交流、对话中,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上发生变异。”这种“文化过滤”现象事实上本著也有提及,与萨义德所谓的“理论旅行”观点有几分相似,“理论旅行”提示人们在译介过程中,“哪些问题遭到排斥、限制和挪用”,而在中国,“翻译散文的‘理论旅行’又为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所制约,出现不可避免的误读、篡改和挪用”。事实上,无论是“文化过滤”中的“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还是“理论旅行”中的“排斥、限制、挪用、误读、篡改”,都是作为“跨文化”交流范畴内散文译介活动中最富有内涵的环节,如何还原这些环节的感性细节真相,如何破译这些环节的丰富信息密码,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叩问美文》对此有自觉的思考,亦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