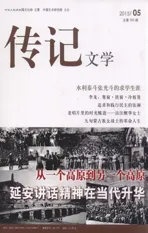《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边疆学研究:在非洲的故事
2015-03-29文蒋晖
文 蒋 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边疆学研究:在非洲的故事
文 蒋 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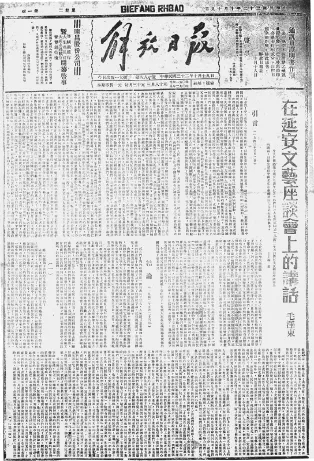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毛泽东讲话整理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今天对这篇历史文献的不断纪念和反思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第一个观点,大概反对的人少,同意的人多;对第二个观点,则可能同意的人少,反对的人多。我也持反对意见,但别有原因。反对者的理由一目了然:以《讲话》的观点指导当代文学创造的繁荣局面,确实有其局限性,《讲话》是一块“活化石”,放在显微镜下研究研究有其思想和价值,但我们要承认它的热度、它的光芒已经所剩无几。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目前国内外对《讲话》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前提展开,第一个前提在国内研究中很流行,即承认《讲话》的历史地位,承认它是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特殊阶段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左翼文学理论。国处危亡,家园不保,这个时候的文学家大多数会以救亡为文学最高使命,而顾不上闲情别寄,赏风吟月那一套文人雅士的士大夫情怀。但当救亡过后,国泰民安,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生产纳入市场体制,《讲话》的现实针对性也随之消减。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文学法则呢?这是国内《讲话》研究展开的前提。另一个前提则体现在国外研究上,即研究者都看到《讲话》曾产生的国际影响,它曾对亚非拉革命作家的写作起过指导性作用。外国学者想把这种影响说清楚,但是,有些研究者不认同《讲话》里提出的文艺主张,笔调常含微讽。
把这两种主要的研究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就看到,研究《讲话》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它的历史地位。国内研究者紧箍咒念得太紧了,把《讲话》当成了延安土特产,看不到它在国际上的流通。所以我不同意把《讲话》的发表仅当成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的看法。它其实是唯一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然而,对它的不断纪念和反思似乎又只是中国的现象,这和《讲话》应有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那么,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呢?这是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国内和国外的《讲话》研究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阐释,也就是缺乏一个根本的历史框架去安置《讲话》。《讲话》确实是中国的土特产,它提出的理想必须有特定的制度保证、特定的文化心理认同和特定的经济体制支撑。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或改变了,《讲话》的文艺理想就成为了空中楼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如果中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这个革命相配套的文艺思想也必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确定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研究和阐释《讲话》的内涵。
我自从2014年8月到南非的金山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接触非洲现代文学,这才对《讲话》在非洲作家那里的影响力有了了解。从这伸展出去,我又读了一些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艺术运动,才知道那边的黑人文艺家也有许多毛泽东信徒。如果再扩展一点,《讲话》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也是一个有趣而待展开的话题。按照这种方式,得到了一个我称之为《讲话》的边疆学研究的版图。将《讲话》从中国腹地移向亚非拉的丛林,把它的中国内涵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历史中展开,我们才可以看到《讲话》的历史位置——《讲话》其实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学最为系统的理论表述。第三世界反抗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的价值有多高,《讲话》的价值就应该有多高。第三世界反抗文学是世界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完全属于人文传统,不宣扬个人的价值,缺乏幻想性质,但它却是改变世界秩序的一种文学话语,是更加重要的阶级解放话语,而《讲话》就是这种话语实践的理论表述。
因此,《讲话》历史意义来自于第三世界反抗文学的整体价值。如果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的话,那么在这个进程里所产生的文学一定和西方的主流文学有着形式和内容上极大的不同。而且,这部分文学应该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主要形式来加以研究,而不应该作为一种落后的西方附属形式来对待。大的灾难会产生大的文学。如果这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第三世界更加灾难深重的话——想想非洲的饥荒、内战、贫困、独裁统治、艾滋病和最近的埃博拉,那么,第三世界就应该是产生大文学的地方。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是反抗性的,是为反抗各种各样的压迫,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而产生的文学。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这种反抗文学一个非常系统化的理论表述。
第三世界的文学或许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不同国家的文学实践面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困境。但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内容,即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命运和出路问题。中国革命是一场现代农民革命。把农民组织到现代国家中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中共文学革命纲领的《讲话》深刻地体现了这点,它明确提出现代文艺必须为工农兵(主要是农民)服务这个全新的文艺方针。它用阶级的语言,提出为谁写作这个只有从第三世界革命过程中才能产生的理论问题,从这个逻辑点出发,革命文艺里面的其他问题,诸如知识分子和农民关系,内容、态度、立场、党性,文艺的社会性、审美趣味和语言形式、西方文艺、民间文艺和士大夫文艺的关系等等,全都获得了一套完整的解答。这些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它的核心是否定了后者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观。
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是社会底层阶级要求革命的文学表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里,第三世界要求革命的社会底层和他们的压迫阶级不断变化。比如,对于黑人来说,压迫并不完全是阶级的,而且也是种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阶级和种族相结合的压迫模式。整个非洲的20世纪历史呈现了三个阶段的反抗形态。在60年代之前,是黑人反抗白人政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革命成功后,非洲大部分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内战和独裁统治,种族压迫变成了阶级压迫,反抗黑人统治阶层争取社会民主运动变成了非洲第二个阶段的革命目标,这个目标在80年代逐渐实现。第一个阶段的文学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总目标是一致的,这部分文学在60年代被集中译介到中国。第二个阶段文学和反独裁的政治目标相一致,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这种政治的文学表述。相比拉丁美洲,非洲独裁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为严酷,所以,反独裁文学基本由流亡英美的作家完成。独裁统治过后,就是非洲目前面临的问题。
《讲话》在这三个阶段的反抗文学里有没有起到过什么作用呢?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就我目前看到的资料而言,《讲话》对非洲作家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第二个阶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讲话》提供的是一套以阶级话语来理解文艺的目的和规律,它并没有涉及到种族压迫问题,而非洲现代文学的起源是西化的非洲知识分子用殖民语言书写的文学,这种文学安身立命之处是对抗西方文学对非洲人民的负面书写,重新唤醒非洲读者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的齐努瓦·阿契贝曾写过不少文章,阐述第一代非洲现代作家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写出和《黑暗的心》截然不同的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他尖锐地批评西方人描写非洲的小说不把非洲人看作真正的人:非洲在这类小说里不过是“一套装置与背景,非洲人性的要素是不存在的。非洲被缩减为形而上的抽象战场,是游荡于其中的欧洲人的致命危险。难道有谁看不出幸福的欧洲的变态的傲慢吗?他们把非洲当成道具去给自己狭隘的头脑注入一点想象的活力。这还不是问题之所在。这种态度持续地使其笔下的非洲人看起来没有人性。这类不把另一个人种当人看的小说能算伟大的小说吗”?因此,在阿契贝看来,非洲作家必须是读者的老师,他必须通过文学教育公民,“让我的社会重新获得自信, 抛弃长期形成的自悲和自贱的心理”。阿契贝认为非洲文学的本质是一种人学。他的观点比起他的前辈由法语区黑人艺术家和思想家倡导的“黑人性”文学有了新的发展。由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黑人性”文艺运动,虽然也是强调黑人文明的历史价值,但同时也是强调黑人艺术和其他色种人创造的艺术的差异,这样在反对种族主义的同时便陷入了另一种种族主义。经过萨特的批评,60年代之后,非洲艺术家不再将艺术区分为黑人的和白人的两种,而强调他们是人类共同的艺术。许多艺术家开始用现实的笔调描写现实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派从20年代纽约哈勒姆黑人聚集区兴起的“黑色文艺复兴”到70年代在南非兴起的“黑人意识”运动形成了共同的非洲人文主义思想,它们构成了非洲寻求国家独立过程中的种族解放理论,也是非洲主要的民族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阶级的问题相比是次要的,大批生活在非洲的白人无产者和工人阶级利益被对立起来,黑人无产阶级和白人无产阶级无法形成政治同盟。《讲话》在这种文艺思潮里难以发挥任何影响。
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非洲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看到的是独立后的非洲社会面临社会的贫富差距,执政的黑人形成和西方勾结在一起的权贵阶层,新聚集起来的财富流入统治阶层的腰包,民众无法享受应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这个时候,阶级的意识开始形成。文学家以南非的拉马、肯尼亚的恩古吉和塞内加尔的乌斯曼·塞姆班为代表,向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小说传统学习,用阶级的观点分析社会问题、描写社会问题。《讲话》在这个时候开始深刻影响非洲社会主义文学运动。
中国读者对于非洲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不太熟悉,对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如恩古吉和塞姆班等人的研究也不多,所以,为了不乱生枝蔓,下面将从一篇文章谈起,介绍一下《讲话》和这种运动的关系。
这篇文章是由尼日利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Omafume F. Onoge于1974年在加拿大一家杂志发表的,题目为《非洲文学中的意识危机》,此文写作时间和恩古吉彻底转向毛泽东思想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几乎同步。这篇文章的题目本身就很有意思,它的中心词是“意识”,对意识的强调而不是对文学写作现实局面的强调,暗示了作者知道在非洲并不具备社会主义文学生长的现实土壤。因此,社会主义文学只能在意识领域被率先构造出来。这种对意识的重视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更是毛泽东思想式的。除了这点,这篇文章的传播历史也十分有趣,它于1985年被收入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部重要文集《马克思主义和非洲文学》。这部文集的编辑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Georg M. Gugelberger。但文集里面的作者大多数是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的文章对比起来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身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Georg M. Gugelberger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卢卡契和布莱希特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而对中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明显陌生。他本人想使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概念在非洲文学内部区分出代表进步和代表反动的文学动向。反动文学的代表是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这本书所编选的文章基本都在找非洲其他作家来对抗索因卡的传统,这样,本书各篇文章就被一个中心思想所贯穿——现实主义。但很明显的反差是,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并不是那么熟悉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纷争不感兴趣。他们熟悉的是毛泽东《讲话》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主要是列宁、高尔基、托洛斯基、普林汉诺夫和日丹诺夫,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文艺主张。其结果就体现在这部集子最重要的文章《非洲文学中的意识危机》,Omafume F. Onoge在里面大谈特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非洲文学意识转变的几个时期,作者采用历史分期和理论分期两种框架来描述。历史分期强调非洲文学在非洲独立运动中和后独立时期的显著差异。他特别指出,第一历史时期文艺家的贡献是梳理非洲文化自主意识和自豪感,错误是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过于浪漫化,形成了文化本质主义,这样,阶级斗争的意识就被压制下来。第二个历史时期,产生了各种意识形态,但主要可以归于两个历史进程,一个是批判现实主义,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为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和阿契贝。这里,Omafume F. Onoge并没有将索因卡妖魔化,而是肯定其著作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他的文章最后呼吁,当前非洲文学创作的方向,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建反抗的文学。而毛泽东的《讲话》正是在最后一部分被集中引用。也就是说,他把《讲话》看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非洲学者对《讲话》的理解有很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第一,比如《讲话》最后部分尽管提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但毛泽东的想法在当时根本和此概念没有什么关系。第二,非洲学者包括Omafume F. Onoge本人也在文章里经常将毛泽东和托洛斯基的论述并置,根本不了解国内对托洛斯基的批判。这些都是这篇文章有趣的地方。
非洲学者是如何理解《讲话》和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关系呢?这其中的关键,是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问题,一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二是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文学的阶级性不是毛泽东的首创,但文学为什么人这个问题尽管是所有写作者都会自觉意识到的问题,但被毛泽东从阶级的角度提出来,是极大的创造。这个问题要解决中国左翼知识分子脱离革命实践主体——农民——的局限性,这是《讲话》的核心。非洲学者对此体验得就更为深刻。几乎所有非洲当代文学的困境就是它的自我封闭,缺乏和人民大众碰撞的问题。Omafume F. Onoge在文章里不断谈到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离,这个隔离被分为几点谈论:第一是殖民语言和大众语言的隔离。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创造出的非洲现代文学是不能为大众所理解的,它只是少数西化精英的文学。第二是精英和大众的隔离。大众识字率非常低,因此,如果文学不能口语化,不能表演,根本无法进入大众的文化生活。恩古吉前四部小说都是用英语创作,即使描写的多是肯尼亚吉库尤族的农民生活,他的母亲也无法阅读。这点最后变成他拒绝用英语写作,而采用吉库尤语创作的主要动因,和赵树理自叙坚定走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叙述使用同样的解释(赵父听不懂赵树理读的鲁迅的小说)。第三就是教育系统完全沿袭殖民教育,使得学生在大学接触不到非洲作家作品,只阅读由利维斯等制订的英国伟大经典。第四个隔绝就是出版业完全由西方出版商控制,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和影响了年轻作者的写作倾向,革命作品几乎没有发表的地方。这四种隔绝将为谁写作的问题提上了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层面。这才有了他们对毛泽东《讲话》认同的社会和历史前提。
毛泽东的《讲话》被引用了两处,第一段:“但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不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这段是用来解释非洲作家采取阶级分析来认识社会的合理性。Omafume F. Onoge尖锐地指出,非洲作家比美国黑人作家的处境要好,因为,美国黑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无法放弃种族压迫理论,因此阶级压迫只是一种次要的社会分析方法。而非洲解决了这个问题。Omafume F. Onoge在1961-1967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美国开始的,思想也是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成熟的。1967年后,他回到非洲在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家任教,因此对非洲和美国黑人运动是有实践认识的。他也一定看过毛泽东于1963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在该文中,毛泽东鲜明提出,美国黑人的斗争实质是阶级斗争:“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毛泽东196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再次指出:“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理论引导美国黑人的种族斗争,因为种族斗争不能成为第三世界革命理论,它排斥了其他有色人种的介入,将白人无产阶级拒之门外,看不清楚整个世界的压迫模式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奥巴马上台后为美国黑人和非洲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吗?压迫者不是个人而是制度,不是特定种族而是特定阶级,这是毛泽东革命理论的核心思想。将黑人民权运动和其他社会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形成第三世界革命理论。这个国际革命理论的形成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经过法农的贡献,再到毛泽东思想,逐渐将亚非拉人民以及第一世界的被压迫人民看成一个反抗的阵营,第三世界的概念至此超越了地域的疆界。
将毛泽东思想、法农和万隆精神结合起来,成为20世纪70年代非洲左翼文艺思想的政治出发点。如果仔细看一下Omafume F. Onoge对非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特点的总结,我们会发现它和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里面的思想遥相呼应。总结非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特点有如下五点: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视角认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在于清算资本主义体制。”第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在殖民主义制度里解释资产阶级剥削关系形成过程。”第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写作主题不是抽象普遍的人性,而是为农民和无产阶级写作。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乐观,必须相信广大的民众是改变社会的力量。他们在农民反抗、雇员协会和工人罢工的运动中看到改变的来临。”第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是泛非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些特点并不是从中国或者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中总结出来的,而是从毛泽东思想、法农政治理论里提炼出来的。
毛泽东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另一个影响非洲分析社会问题的概念,具有极高的使用率。Omafume F. Onoge引用它来分析非洲后殖民时代的阶级矛盾。他说,现在非洲的核心矛盾是人民大众(农民和无产阶级)与买办资本主义的矛盾。“买办资产阶级”的概念脱胎于中国实践,但对后殖民的非洲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共同的社会现实使得非洲左翼只有让世界看到,只有超越种族理论,非洲的革命才能成为亚非拉革命的一部分。非洲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看中阶级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是当时对非洲唯一可能的国际主义话语。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处境和亚非拉被压迫阶级的处境联系起来,企图将殖民压迫转化为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企图将非洲的解放作为全人类的解放之一部分,在这种视野下,阶级理论被提了出来。苏联在这种语境下不能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这个代表只能是中国。所以,Omafume F. Onoge指出,现在革命最进步的地方是亚洲,他指的是中国和越南。这也就是毛泽东的理论被用在结尾阐释的一个原因。
《讲话》对非洲作家的影响到底有多深,面有多广,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但是东非最伟大的作家恩古吉的文艺思想和作品所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不断从他的理论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在他1974年写的《文学与社会》这篇著名文章里,第二个注解就是来自《讲话》,是毛泽东关于艺术的阶级性论述那段话。在以后的文章里,也多次提到和引用《讲话》。恩古吉一生写作的主题是肯尼亚农民革命,即历史上备受争议的茅茅运动,他要阐释农民革命在构建以人民为主体的新肯尼亚所产生的历史贡献。而当时肯雅塔政府极力抹杀这段历史的存在,这就形成了肯尼亚知识界重要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争的双重历史叙述。结果当然是恩古吉被扔进监狱一年,随后流亡西方。但其一生写作主题都围绕着茅茅运动的历史,这使得他的作品和非洲文学主流形成极大差别。他这点和中国革命历史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因为茅茅运动在1953年就被镇压下去,十年后,肯尼亚独立。茅茅不是导致独立的革命,而恰恰是被镇压后独立才发生,茅茅是独立发生的前提。革命知识分子如恩古吉饱尝革命失败的迷茫和苦痛,围绕茅茅运动创造出的主人公形象的精神状态,颇似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那代人的心情。农民革命在恩古吉笔下从来没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革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进步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恩古吉几乎全盘接受了《讲话》思想,特别是文艺的阶级性和文艺为谁服务的论点,是理解恩古吉文学发展的根本点。恩古吉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民写的,这样,他在用英文写了前四本小说后,改用吉库尤语创作,并回归非洲口语文学传统。吉库尤并不是一种书面语言,所以恩古吉的工作就是要创造出吉库尤的书面语言。在《去殖民化的语言》一书中,他谈到了发明吉库尤书面语言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同时,他也谈到在使用自己的人民的语言写作时所获得的极大的解放感。因为茅茅运动是农民运动,茅茅战士使用的不是英语,而是吉库尤语。用英语描写他们的对话,而且写完后吉库尤人还看不懂,这种尴尬恩古吉忍受了几年,最后终于放弃英语,他说今后只用英语写文学研究,后来他干脆宣布,连文学研究也不用英语写了。《讲话》从来没有要求革命作家放弃普通话而使用方言写作,因为在中国,普通话被实践证明是保证各个民族和地区文化交流的最好工具。毛泽东只要求回到农民的语言写作。但这个问题在肯尼亚就成为了回到一个少数民族语言写作问题,因为除了英语,肯尼亚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恩古吉没有使用“东非普通话”——斯瓦希里语写作,表现了他的激进政治的一面。茅茅运动主体是吉库尤族人,所以他就用这个族人的语言书写。这是对毛泽东《讲话》语言问题的一个特殊处理。语言既是《讲话》中讨论文学形式时的重点,也是恩古吉创作必须做出的选择,不仅是他,整个非洲现代作家都面临是使用殖民语言还是自己民族语言书写的问题,这也是第三世界文学形成自己主体性必须面对的问题。《讲话》是从中国内部需求对这个第三世界语言形式问题所做出的一个说明。
《讲话》在今天依然有着庞大的生命力。举一个个人的例子。我在南非金山大学访学期间,曾上过一门非洲文学理论的课。课上讨论了南非女作家黑德的一些作品,其中授课教授引导大家讨论黑德晚年想重新发现和书写博兹瓦纳民间故事和寓言的努力。讨论在我看来进行得非常不得要领。因为,黑德的努力不过是用英语重写博兹瓦纳的民间故事,而且期待读者是知识分子。黑德的工作很像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对民间文学的发现和重构,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一种努力,这和恩古吉思想也和毛泽东思想是不一样的。我当时的发言是提出要从“为什么人”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看清楚黑德到底持的是什么知识分子立场了。发言过后,一名四年级本科生立刻对毛《讲话》表示了极大兴趣。他说“为什么人”是非洲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为白人写,还是为黑人写;是为中产阶级写,还是为底层人民写,都非常关键。随后我了解到,他年纪轻轻已经加入了非洲目前最激进的革命党组织——“经济自由战士”。这个党正因为表示代表黑人穷人的利益而获得底层支持,是草根党,口号是将所有白人赶出南非,重新收回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当时就感到,只有真正在底层进行群众斗争、走群众路线的党才会理解毛泽东《讲话》的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重新反思《讲话》,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把中国当代文学看成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学的一部分?如果脱离这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最根本性质的思考,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就会迷失方向,《讲话》当然也就会成为如有些人所说过时的东西。纪念《讲话》就是重新回到真实的和能动的现实政治中,找到文学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源泉。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示意图,其中的中央办公厅楼,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