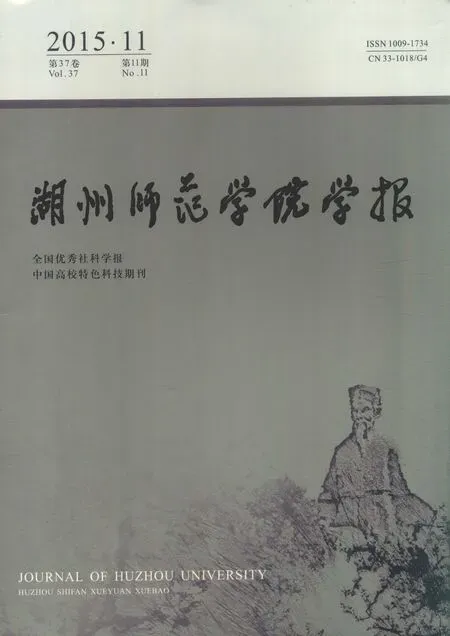清代预防民间宗教教化手段与措施探析*
2015-03-28周向阳
周向阳
(湖州师范学院 政治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一、清人对教化与邪教预防的认识
所谓教化,就是通过教育、文化、舆论等方式,以国家正统的思想学说和法令教育化导、培养社会成员,使其接受正统思想的熏陶,熟悉国家法令,不为异端学说所惑,从而形成有利于统治秩序的主体思想、价值观念的过程。儒家学者一直十分强调教化的作用,孔子提出“道之以德”(《论语·为政》)的主张,认为好的统治者治理国家,可以通过长期实行道德教化的方式,克服残暴行为,免除刑杀手段,即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他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和“仁爱”(《论语·颜渊》)精神。孟子则希望通过“教以人伦”,使人们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还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就教化的制度建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荀子重视教化的作用,也指出了教化的局限性。他希望通过教化来改造人的“性恶”,反对“不教而诛”,“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荀子·富国》)历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教化的功能与作用。清帝把教化放在治国治民的第一顺位,天命四年六月,皇太极谕侍臣曰:“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1](P24)清军入关以后,即以宣谕教化为治国之策,历代皇帝都不惮再三强调施行教化。顺治十二年,谕:“朕惟平治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2](P19)康熙九年,康熙帝谕礼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若徒事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在《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了大量清朝历代皇帝关于加强教化的上谕,谆谆告诫,不厌其烦哪怕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攻击,唯有通过改革才能救亡的情况下,教化为本的主导地位也从未动摇过。
在清代民间宗教盛行的情形下,为了有效治理宗教,清政府一方面制定了严密的法律,通过严厉的刑罚制度惩罚传习者,另一方面,毫不犹豫地祭起了教化的法宝,以期从根本上预防“邪教”。
清统治者认为教化不兴直接导致了民间宗教的兴起。西南大乘教案发之后,乾隆帝指责此与地方官不实心化导民众有关,“地方大吏及群有司果能留心化导,使小民咸知忠孝大义,则平时尊君亲上之心、睦姻任恤之谊皆根于至性,油然而生,岂有复从邪说、与群不逞之徒为伍、甘蹈法网者?”[3]天理教起事之后,嘉庆屡下谕旨,斥责官僚“于教化一事,则置焉不讲”,“官吏不修正教,无怪愚民习于邪教”。官僚不行教化,导致民众加入教门,实是诱民犯罪。[4](P354)既然民间宗教的兴起是教化不兴之结果,大兴教化,消弭“邪教”就得到了清朝统治者一致的认同。乾隆二十三年(1758),浙江道监察御史杨光立上奏认为,禁治“邪教”的关键在于官员厉行教化,“惟能禁之于未然,则教诫明而民志不惑,民不惑而奸人作慝之端无自而启矣。”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的禁治措施而言,教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端本正源的作用,所谓“于所属民人,实力化导,宣讲圣谕广训,务俾家喻户晓,久之人心感发,知仁而有所不忍为,知义而有所不敢为,则正教昌,邪说自息矣,”①军机处录副奏折,浙江道监察御史杨光立奏,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转见郑永华,《清代推行教化与治理民间教门之关系试探》,2014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网(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6363)。而每当大的“邪教”案发之后,朝廷上下就会有一波强化教化之言论,皇帝发布上谕,臣工通过奏折,一致强调教化,希望以正学来抵清邪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如乾隆十一年,西南大乘教案发后,针对御史马璟提出严行保甲以治“邪教”的建议,乾隆说:“为治之道,宜端其本,稽查保甲犹属末节”,他再次强调教化这个根本,要求地方官员“实心训迪,以治其源,俾奉法者益坚其向善之新,诚跃治者顿改其不训之习。”[5](P117)
二、地方讲约:清代官府教化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地方讲约是清代推行教化的主要形式。清廷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而且,还要求州县教官不时巡行宣导,如地方官奉行不力,由“督抚查参。”[6](P314)地方讲约主要内容是“上谕”。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颁布六条圣谕,即“教训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7](《序言》)这成为明代教化的最高准则。这种教化形式和途径也为清统治者所承袭。
顺治皇帝照搬朱元璋的六条圣训颁发六谕,到康熙时期,清朝的文治有所发展,六谕被发展为十六条圣谕,每条七字。雍正二年,皇帝将十六条圣训加以演绎,每条都敷衍至600字左右,化为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使这些规范更为具体、明白,更加可以操作。[7](P582)圣谕和《圣谕广训》成为清朝二百多年间中国社会最高的行为准则,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由官方集会宣讲,在讲解过程中还有各种仪式需要遵守。这种传统断断续续沿续到清末民初。[7](P581)在清代皇帝所颁发的这些圣谕、圣训中,防范异端邪说是其重要内容。顺治六条圣训中虽没有直接明确禁治民间宗教的条款,但“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在阐发之后,无不与禁治民间宗教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康熙圣谕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虽然“异端”一词具体所指含义不够明确,但应主要指淫俗、滥祀、“邪教”之类。[8]雍正帝后来在《圣谕广训》中对此条内容加以阐发说明,把民间宗教明确成为“异端”的主要内涵:“自游食无藉之辈阴窃其名以坏其术,大率假降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幻无稽之谈,始则诱取资财以图肥己,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农工废业,相逢多语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干名犯义,惑世诬民。及一旦发觉,征捕株连,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为罪魁,福缘且为祸本,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9](P290)这一精神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圣谕、圣训,是用简洁的文言文写就,一般百姓难以理解,所以,为了加强教化效果,官府一般会以多种形式,如韵文、白话等加以详细阐释,便于在百姓中宣讲。道光十九年,经两江总督陈銮等奏请,朝廷又将《圣谕广训》“撰有韵之文”,以便私塾学堂中的少年学生阅读记忆。另外,有清一代,还有多种白话解释圣谕、圣训本出现,其中有许多是由官方所刊刻。康熙十一年(1672年),浙江巡抚范承谟刊刻了《上谕十六条直解》,对十六条逐条分疏,都以白话书写,而且语言生动,修辞高明,约两万来字。据后世研究者所说,这些白话是精彩已极,如同评话说书,甚至可以品出方言的味道。《分讲十六条》,该书是江宁巡抚汤斌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所刊。康熙年间,安徽繁昌知县梁延年对圣谕十六条作了详细注释,并在后配有十多幅插图,辑成《圣谕像解》二十卷,以便于普通老百姓领悟接受。陕西盐运使王又朴则将《圣谕广训》直接翻译成口语,名为《圣谕广训直解》,成为众多《圣谕广训》白话解释本中最流行者之一。②关于清朝圣圣谕、圣谕广训的解释本情况及清代关于宣讲圣谕的具体制和做法,见周振鹤,《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81-632页。
清代圣谕和圣训的颁行和定期讲解,是清代对基层社会思想控制加强的表现。正如周振鹤所说:“康熙圣谕与雍正《广训》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与思想的规范化戒律,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要中规中矩,不得乱说乱动。”[7](P581-632)这有效地消除了民间宗教生长的思想基础。
三、颁发告示:地方官府晓谕民众的另一种形式
在宣讲圣谕之外,清代各级地方官府还经常以告示的形式,配合宣讲朝廷禁治民间宗教之法令,申明严禁邪教之意志。雍正十年夏至乾隆八年春,江西按察使凌燽因江西省“愚民惑于邪言,信从大成罗教及一切左道异端,汩没沉沦,”认为“人心即好异信邪,未始不怵刑畏法,”乃将《大清律例》中有关惩治“禁止师巫邪术”的相关律例“逐一摘出,并将奉宪查禁缘由,刊刷简明告示,贴于高脚木版,每里给牌一面,令保甲肩牌沿门传谕,”然后,“将示牌竖立保长之家。”[10](P198)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雅尔图听说河南地方教门流行,建议命令河南地方官员在认真清查,宣讲圣谕的同时,“并将邪教妖言煽惑人心律各条,朗畅讲解。”[11](P619-620)嘉庆十七年六月,给事中叶绍楏再次奏请“饬令各省督抚臬司出示晓谕,将律定罪名刊刷通衢”,并请“令各督抚体访各该省习俗所易犯而大干法禁者,一一摘录律文,明白晓谕,广为禁止。”①《清仁宗实录》,卷258。
许多官员任职地方时,始终把教化百姓远离邪教作为重要关注事件,同治年间任职浙江的汤肇熙每到一地,都发布告示,严禁邪教。如他任职开化时,将该县弊端以告示晓谕县民,第一条即为:“吃斋念经结盟拜会”,要求该地保严加稽查,“偕近邻飞即禀报本县,无分风雨星夜往拿。”[12](P619)当他移任平阳时,连续颁发《禁梅川庄等处吃斋聚党示》《禁吃斋拜会示》《臚欵禁除恶习示》《禁拜经示》等四告示,不惮反复告诫,冀民改邪归正。②[清]汤肇熙撰,《出山草谱》,卷一、卷三、卷四,四库未刊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刊书辑刊》,《十辑.四册》,北京出版社(清光绪十年昆阳县署刻本)。光绪年间,任职浙江湖州的宗源瀚闻当地有“有无为、大被、金丹、一字教种种名目,名为放生诵经而敛钱,聚众男女混杂大干禁令,”乃将违法之人拿获枷杖,并“掮牌宣示。”[13](P562)
四、知识分子讲解圣谕或著书立学教化民众
在地方讲约、官府告示之外,官员和知识分子著文立说,或对民间宗教教义进行驳斥,或对民众进行正面的训导,也是教化的重要形式。如嘉庆二十年,嘉庆帝就命令各省学政在赴地方主持考试时,细心体察当地老百姓容易受到“邪教”蛊惑的地方,撰写通俗易懂的文章进行规劝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豎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各俾家喻户晓,知所从违。至士为四民之首,该学政于接见士子时,尤当谆切训诲,使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倡率乡闾,身以先之,言以喻之。”③《清仁宗实录》,卷312。为此,山东学政王引之撰写了“阐训化愚论”“见利思害说”两文,河南学政姚元之写了“饬士子敦俗化乡愚说”。湖南学政刘彬士专门写了“辨惑告示稿”。此文包括“辨正邪之惑”及“辨利害之惑”两个部分,文中基本上采用里巷俗语的形式,只要略微讲解,就能使绝大多数人听得懂。文中指出“邪教”与“正教”的不同之处,说“做五伦分内的事,就是正教,不做五伦分内的事,就是邪教”,“邪教”私立名目,“先不过说是念经行善,未必就有无法无天的心思,后来邪教渐渐胆大起来”,不畏王法,竟成了“叛逆”大罪。刘彬士又说:“儒教劝人为善,朝廷尊重他,释教、道教也有修行忏悔的话,朝廷也不禁他,偏禁这些教,是甚么缘故呢?我今把这缘故说与你听。释教、道教虽与儒教不同,却都是图个安静,不敢生事害人,所以朝廷都不禁他。何为安静?大凡这三教都是有师徒,只是为师的不肯往四方去招引徒弟,有愿为徒的,却也受他,有不愿为徒的,却不招引他,这将来自然没有聚众的根子。这些入教的愚民未必都是思想为匪的,假若一旦有个匪徒或诱引徒弟为匪,或胁制徒弟为匪,也是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这就害了不少人了,可知道这诱人入教,就是他的邪处,所以朝廷定要禁他。”④刘彬士:《辨惑论说告示稿》,嘉庆二十一年。转自郑永华,《清代推行教化与治理民间教门之关系试探》。
地方官员黄育楩对于批判“邪教”更是不遗余力。黄育楩,甘肃狄道州人,历任宛平、三河、武清、清河、宝坻、广平、邢台、钜鹿县知县和深州、沧州知州,在任以知府选用,死于任上。[10](P1)黄育楩视民间宗教“大为民害”,在任时严加惩治。但他认为,“严禁邪教,而不将邪经中语详为辩驳,民既不知邪经之非,自不知邪教之非,虽尽法惩治,而陷溺已深,急难挽救。”因此,在清河任知县之时,就“刊严禁邪教告示,分作页数,以之粘连成篇,……装订成本,”并印刷了三万余本,“除分送邻封外,遍给清邑各村绅士,令与村民时常谈论。”[14](P3-4)当他被调任钜鹿任知县后,他“于邪经中择其主意所在之处,详为辩驳,务使有奸必发,无弊不搜,”定名为《破邪详辩》,对邪教教义逐一详加反驳。而且,此后,他又对在任职地方陆续收集到的邪教经卷加以辩驳,补充《破邪详辩》的内容,如《续刻破邪详辩》《又续破邪详辩》《三续破邪详辩》。由于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吏,有着丰富的邪教控制经验,所以,在对民众进行训导时,他指出,并非一定要以儒家的正统学说来教人。他认为,“古人立教惟重中人以上,不重中人以下。由于中人以上服古入官,制治得宜,则中人以下各相安无事之天,而且已成盛治也,以无邪教故也。今人立教既重中人以上,尤重中人以下,以此等人数不啻什这八九,使官不知教,而邪教之教得行于其间,始则聚众传徒,继则谋为不轨,……案复一案,而根株终难尽绝。总以无知愚民既信地狱,又畏地狱,邪经卷卷遂屡言地狱。……继而又捏出问成死罪即能上天之说,而刑罚且归无用矣。”既然在邪教的蛊惑之下,刑罚已经失去其威摄力,所以,他“欲另设一法以挽恶习,不必用儒教教人之法,而即用邪教教人之法。邪教以地狱教人,而人自乐于习邪教,吾儒亦以地狱教人,而人自不肯习邪教。”因此,当黄育楩得到宗王化所著的《邪教阴报录》后,“即急为刻印,遍为施舍,并多觅唱鼓词人,令赴各村详为唱说,凡闻见者莫不互相传论,而民情为之一变。此《详辩》之言立教当以下愚为要也。”[14](P92)
在官府、官员们著书立学对邪教教义加以反驳,并在社会广为宣传,教化民众外,儒家知识分子也纷纷著书立学,劝导百姓。明末清初的儒家学者颜元,就曾专门撰文揭批民间宗教,劝导百姓远离邪说。颜元认为:“世间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门,焚香聚众者,固皆鄙无足道。然既称门头,乱言法道,群男女废业而胡行,诱惑良民,甚至山野里皆遍,则其为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过不晓念佛看经之为非,不知左道惑众之犯律,妄谓修善而为之耳。若不急唤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则黄巾、白莲之祸恐即在今日之“皇门”“九门”等会,上厪国家之忧,下阬小民之命。”[15](P140)那么,什么是邪说左道?百姓如何才能加以辨别?颜元指出:“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说,不安为朝廷百姓而名为道人者,便是左道。”[15](P140)在他看来,左道、邪术不但怪诞不稽,而且违法,还破坏社会风俗和秩序,“古圣人经上说‘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又云‘七十非肉不饱”,是对人制下养老的物,若是不好,圣人便不教人吃了。……即如你们唤日光叫“爷爷’,月亮叫喊‘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们是百姓最小最卑,那可以名号?你看,北京纔有日坛月坛,天子纔示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况我们愚民,……又如你们把“日”改做‘晌’,把‘月’改做‘节’之类,……我圣人书上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孝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没有改就‘晌节’的礼,没有改就‘晌节’的文。你们私议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却犯大法。……律上说:‘妄谈天象者斩!’……又如你们男女混杂,叫人家妇人是‘二道’,只管穿房入室,坐在炕头上。不知我圣人的礼,男无故不入中门,女无故不出中门,叔嫂尚且不通问,父兄于女子既嫁而归,尚且以客礼待之,至亲骨肉亦必避嫌,哪有妇女往异性无干的人家去上会的礼?哪有异性无干的男子入人内室的礼?这大是坏人道,乱风俗,你们怎么不顾体面?”[15](P142-143)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可以说这是封建卫道者的卫道之心,但也从中可见儒家学者教化民众百姓远离民间宗教诱惑的诚恳之意。在清代小说中,有许多对民间宗教的描述,这些作者基本上都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将其指斥为“邪教”“邪说”,或字里行间,充斥大量“邪教迷人,蛊惑人心”的荒唐描写。[16]
另外家(宗)族也是教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几乎所有的家族都会在公开、正式的场合表示对邪教的憎恶与反对,甚至某些家族的族规、族约中还明确禁止族众传习邪教,如湖南宁乡熊氏光绪年间订立的祠规规定:“结盟拜会、习教……将来亲属领归,严加约束,立令改行。倘怙恶不悛、犯至再三者,公同禀请处死。”光绪年间四川《合江李氏族谱》订立族禁6条:禁当差、禁为匪、禁入会、禁从教、禁出家、禁自残。而且,一些家(宗)族在某些情况下也检举和配合官府查禁邪教。[17](P159-163)
五、启示与借鉴
社会学理论认为,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价值观是决定社会的目标和理想的普遍和抽象的观念。价值观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它为一个人的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甚至,有的社会学家宣称,价值决定着行动。一旦价值观形成,它们就成为个人行为选择和态度形成的指南。帕森斯认为:“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从某些方面看,人类后天习得的个性因素中,最稳定和持久的即是主要的价值倾向模式。”[18](P69-70)清代的教化手段,实际上是一种将主流价值观念内化的强化教育。所谓内化,是指某个人对群体或社会规范的认同。一旦社会规范的内化成功,它就会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继续遵守它,即使无人监视时也一样。内化是对越轨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最有效的途径。[18](P209)清代的教化如果成功,一方面能够将加强人们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认同与服从,对民间宗教等异端邪说进行自觉抵制。更为重要的是,教化使清政府避免了使自己处于同社会个人意志公开对立的境地,从而国家禁治民间宗教的举措不太可能惹起普遍的反抗情绪。在传统中国威权政治之下,民众与政府处于一种结构性的对立状态。而“在一个错综复杂、支离破碎的社会中,阶级的分歧阻碍了感情的顺利交流,这样冒犯者就能把他的过错躲入能够被宽恕的范围,来逃避同时代人对他的轻蔑和责难。”[19](P73)由于民间宗教的亲民性和贴近底层社会,教首和教徒又往往是贫苦出身,国家对民间宗教的清剿往往很容易引起民众关于贫富、阶级对立的联想,从而引起普通百姓的同情。最终清政府禁治民间宗教的努力可能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对立情绪。而教化则使民间宗教是“邪教”,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这一观念为广大人们所接受,避免了政府在禁止民间宗教时引起更大的对立危机。所以,清代预防民间宗教的教化手段和措施对当下我国邪教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王先谦.九朝东华录(卷1·第1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书.
[2]王先谦.九朝东华录(卷5·第5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书.
[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71)//清实录(第1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本.
[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9)[M].续修四库全书(第804册).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二)//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7)[M].续修四库全书(第804册).
[7]周振鹤撰集.圣谕广训[M].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郑永华.清代推行教化与治理民间教门之关系试探[EB/OL].2011-06-24.http://www.zhlzw.com/qx/li/477751.html.
[9]雍正.圣谕广训//周振鹤撰集.圣谕广训[M].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3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清]汤肇熙撰.出山草谱(卷一)开列条规示//四库未刊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刊书辑刊·十辑.四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清光绪十年昆阳县署刻本).
[13]宗源瀚撰.颐情馆闻过集.守湖稿(卷八)·词讼//四库未刊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刊书辑刊·十辑.四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清光绪三年刻本).
[14]黄育楩.破邪详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3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清]颜元.颜元集·存人编[M].王星贤,张芥塵,郭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孙逊,周君文.古代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及其认识价值——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考察对象[J].文学遗产,2005(5).
[17]潮龙起.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J].江苏社会科学,2006(3).
[18]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9][美]E.A.罗斯.社会控制[M].秦志勇,毛永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