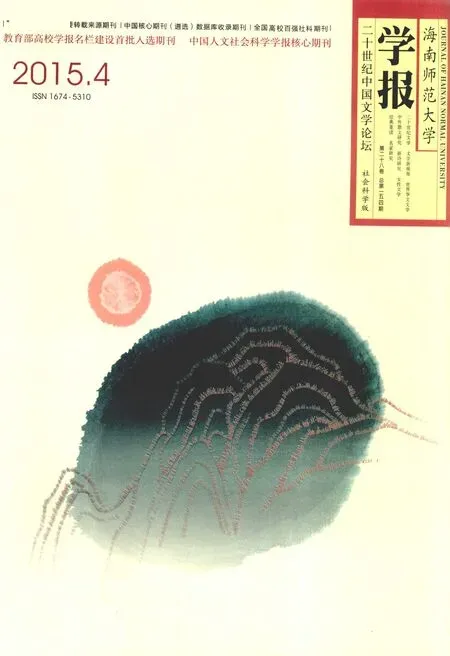李东阳与台阁体
2015-03-28薛泉
薛 泉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县)人,历经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在馆阁五十年,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作为馆阁之臣,他注定要与台阁体结下不解之缘。这是研究李东阳及其诗文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
台阁体又称“馆阁体”,指流行于供职馆阁官员中间的一种文体。明代台阁体产生于永乐时期,盛行于仁、宣之世,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乃其余波。[1]罗玘《圭峰集》卷一《馆阁寿诗序》称:“今言馆,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云。”明代台阁体,盖滥觞于明初之吴伯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吴伯宗《荣进集》提要即云:“(吴伯宗)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四库馆臣对明代台阁体风格概括,可谓言简意赅。其实,明初文人对台阁体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宋濂《汪右丞诗集序》云:
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镗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
宋濂以山林体为参照系,较全面地总结出台阁体的文体特征。就描写内容言,台阁体要反映“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就艺术风格论,台阁体要“其气丽以雄”,“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镗鞳”。更为难得的是,宋濂还朦胧地意识到台阁体风格成因:“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作为台阁重臣,宋濂对台阁体文体特征的归纳,当颇具代表性。
杨士奇、杨荣、杨溥是台阁体的代表。“三杨”于台阁体,主更凸显其理学视域下的文学实用功能。杨士奇《题东里诗集序》曰:“古之善诗者,粹然一出于正,故用之乡闾邦国,皆有裨于世道……下此为《楚辞》为汉、魏、晋,为盛唐,如李、杜及高、岑、韦孟诸家,皆诗正派,可以溯流而探源焉。”又,《玉雪斋诗集序》曰:“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汉以来代各有诗,嗟叹咏歌之间,而安乐哀思之音,各因其时,盖古今无异焉。若天下无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杜少陵浑涵博厚,追踪风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时高材逸韵,如李太白之天纵,与杜齐驱,王、孟、高、岑、韦应物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读其诗者,有以见唐之治盛。”皆谓诗文需“有裨于世道”,鸣盛世。杨荣、杨溥更是从歌颂昇平角度着眼,关注台阁体。杨荣《省愆集序》云:“自洪武迄今,鸿儒硕彦彬彬济济,相与咏歌太平之盛者,后先相望。”《杏园雅集图后序》云:“仰惟国家列圣相承,图惟治化,以贻永久,吾辈忝与侍从,涵濡深恩,盖有年矣。今圣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职朔望休沐,聿循旧章。予数人者得遂其所适,是皆皇上之赐,图其事,以纪太平之盛,盖亦宜也。”杨溥亦如是观之,杨荣《登正阳门楼倡和诗序》引杨溥言:“少保公(杨溥)曰:‘然吾辈叨逢盛时,得从容登览胜概,以舒其心目,可无纪述乎?’公遂赋二诗,予与诸公和之。诗成之明日,侍郎公又属予为之引,遂僣书此于首,俾观者知诗之作,所以颂上之大功也。”可见,在“三杨”看来,台阁体诗文主要功能在于“歌咏太平”、以鸣盛世。
宋濂、“三杨”之后,李东阳对台阁体文体特征予以较全面、系统的清理,其《倪文禧公集序》有曰:
文,一也。而所施异地,故体裁亦随之。馆阁之文,铺典章,禆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而要其极,有不能合者。……自高皇时,宋学士景濂诸公首任制作,而犹未得位。文皇更化,杨文贞诸公亟起而振之,天下之休养涵育,以暨英庙之初,富庶之效可谓极盛矣。……盖公之雄才绝识,学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达,卓然馆阁之体,非岩栖冗处者所能到也。
此处,东阳虽谓宋濂诸公台阁体“犹未得位”,但他对台阁体分类,尚未出其范畴。不过,李东阳认为山林之文、台阁之文二者“有不能合者”,这是宋濂上文所未言及的。而“得位”之台阁体,应当突出以下特点:其一,台阁体体裁应因地而宜。其二,应以适用为本,内容上要“铺典章,禆道化”,风格上须“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前者是对台阁体体裁内涵的新界定,后者承“三杨”而来。另外,他还从辨体角度,进一步阐释台阁体文体特征及功用,《倪文毅公集序》有言:
有纪载之文,有讲读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赋咏之文。纪载尚严,讲读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赋咏尚富。惟所尚而各适其用,然后可以为文。然前数者皆用于朝廷、台阁、部署、馆局之间,禆政益令,以及于天下。惟所谓著述赋咏者,则通乎隐显,盖人情物理、风俗名教,无处无之。
李东阳从适用层面,将台阁体分为“纪载之文”、“讲读之文”、“敷奏之文”,并指出其各自文体风格。在李东阳看来,那些“尚富”之“著述赋咏”,只要“适其用”,有益于“风俗名教”,即可囊括于台阁体范畴之内,三杨于此言之甚少。可见,李东阳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更为全面地梳理了台阁体的文体特征、政治功能,是继承中而有超越。
二
李东阳对台阁体之体识,远绍宋濂,近接“三杨”,尤其深受“三杨”之浸润。所以如此,与“三杨”所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三杨”生活在国家富庶、君臣关系融洽的宣、德时期。《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士奇传》云:“当是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三杨”与仁宗、宣宗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正是东阳向往的。李东阳《书赐游西苑诗卷后》云:
君臣之际,亦重矣。盖必有天冠地履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后上下交而德业成……我朝自皇祖以来,优礼儒硕,远超近代。凡一豫一游、一张一弛、严而泰、和而节者,皆于此卷见之。宣德之治,固有得于体貌之隆,信任之笃者,诚亿万世所当法也。东阳以后进菲才,备员左右,不能赞明良喜起之化,于此亦窃有感焉。
李东阳非常羡慕“三杨”时代君臣关系之融洽,以为此天下大治之基础。此实亦“三杨”台阁体赖以繁盛之土壤。其《书杏园雅集图卷后》又谓:
且自洪武之开创,永乐之戡定,宣德之休养生息,以至于正统之时,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称。庙堂台阁之臣,各得其职,乃能从容张弛,而不陷于流连怠敖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忧勤乎君,然后德业成而各飨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尽者。而要其极,有气数存焉。然则斯会也,亦岂非千载一时之际哉?
《杏园雅集图》是谢庭循于正统二年春三月绘制的馆阁诸公在杨荣杏园集会的一幅画,是歌颂昇平之作。六十年后,李东阳得之并于题文,表达出对“三杨”功业及其时君臣关系无间的景仰与渴望。
在台阁体文学功用上,李东阳与以“三杨”是一致的。仁、宣以后,“三杨”台阁体,“举世向风”(张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2]“三杨”所主张的台阁体应歌功颂德,“以纪太平之盛”,亦深得李东阳赏识,欲模仿“三杨”之举,以“鸣国家之盛”(《春雨堂稿序》),亦在情理之中。其《甲申十同年诗序》即言:
今吾十人者,皆有国事吏责,故其诗于和平优裕之词,犹有思职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归其乡,顾不得交倡迭和,鸣太平之乐以续前朝故事。则是诗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
李东阳以“和平优裕”之诗“鸣太平之乐以续前朝故事”,就流露出了对“三杨”其人、其事的认可与称颂。基于此,他特别欣赏“三杨”的诗文。其《呆斋刘先生集序》称:“永乐以后至于正统,杨文贞公实主文柄。乡郡之彦,每以属诸先生。文贞之文,亦所自择,世服其精。”杨士奇,溢号文贞。由此亦可见,李东阳所叹服的“三杨”台阁体诗文,亦有一定选择。
李东阳台阁体创作环境与“三杨”有所不同。“三杨”历永乐、仁宗、宣宗、正统四朝,其台阁体诗文亦相应分两个阶段。永乐时期为前一阶段。永乐大帝从其侄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后,为巩固统治,对建文旧臣大开杀戒,无情打击,朝廷上下形成一种恐怖政治气氛。大臣动辄获罪,轻者杖脊,重者屠戮。方孝孺即因不愿为其撰登基文,招致杀身之祸。据《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士奇传》,杨士奇曾两度被捕入狱。又据卷一百四十七《黄淮传》,杨溥、黄淮曾度过十年大狱生活。若不是成祖去逝,其牢狱生涯恐依旧。杨荣虽未遭牢狱之灾,但他不会不从同僚的遭遇中吸取教训,变得“乖”些。因此,此时台阁体歌颂功德有多少出于自愿,恐值得怀疑。而至仁、宣时期,情况大相径庭。时值封建经济繁荣,君臣关系良好,台阁体文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多是发生内心。李东阳所推崇的,多为此时之台阁体。
李东阳主要活动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特别是弘治一朝,其渴望的“宣德之治”局面终于出现。孝宗朱祐樘登基后,励精图治,改革弊政。君臣关系,他一改乃父做法,善于听取臣下意见,礼遇大臣,君臣关系相对融洽。其在位期间,曾一度出现史家称道的“弘治中兴”。李东阳生逢其时,对此深有感触,其《孝宗皇帝挽歌词十首》之七称:“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道合君臣义,恩深父子情。”在他眼里,孝宗是一位难得的有道明君,他自然要“以忧勤乎君”,以台阁体歌咏太平之世。
然而,李东阳生活的年代也是台阁体“余波”所及之时。正统以后,台阁体已流于末流,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倪文僖集》提要云:“‘三杨’台阁之体,至弘、正之间而极弊,冗阘肤廓,几于万喙一音。”卷一百七十《类博稿》提要称:“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卷一百七十一《空同集》提要亦称:“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制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这种局面是李东阳不愿看到的,他对台阁体末流的“缓弱”、“覼缕”(李东阳《叶文庄公集序》),甚是厌恶。台阁体诗文“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怀麓堂集》),这是文学发展自身规律所决定的。李东阳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动向,自觉开始以“变而求新”。
既然李东阳非常推崇“三杨”台阁体,那么他为什么不去努力恢复它呢?李东阳清醒意识到,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同一文体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不可机械模拟。《镜川先生诗集序》云:“所谓诗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声韵,例以格式,名虽同而体尚亦各异。汉、唐及宋,代与格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而或者又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矣,况未必似乎!”又《赤城诗集序》亦云:“诗之为物也,大则关气运,小则因土俗,而实本乎人之心。古者道同化洽,天下之为诗者皆无所与议。既其变也,世殊地异,而人不同。故曹、豳、郑、卫各自为风。汉、唐与宋之作,代不相若,而亦自为盛衰。”基于此,李东阳虽崇尚“三杨”台阁体,但选择了革新之路。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所谓“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盖着眼于此。
三
李东阳改革台阁体之功,明人张慎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何文毅公全集序》有言:
于时文章尚宋庐陵氏,号“台阁体”,举世向风。其后权散而不收,学士、大夫各挟所长,奔命辞苑。至长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学,权复归于台阁。盖起衰救弊之功,往往百余年而仅遇其人。
平心而论,李东阳反对的是台阁体末流,而不是要从整体上否定台阁体,其诗文本即“隐然有台阁气象”(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张慎言所谓“权复归于台阁”,不应是指回归到“三杨”时代之台阁体,而是经东阳改造过的台阁体。那么,他是如何改造台阁体的?《怀麓堂诗话》云:
秀才作诗不脱俗,谓之头巾气。和尚作诗不脱俗,谓之馂馅气。咏闺阁过于华艳,谓之脂粉气。能脱此三气,则不俗矣。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在此,东阳肯定台阁诗与山林诗是明代诗歌两大支脉,与上文他所说的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相互应。这表明,他承认台阁与山林是当时文学两大主流,二者皆不可或缺,与宋濂等人鄙视山林文学之看法有所不同。台阁与山林二体虽“要其极,有不能合者”,但不等于完全不能“合”。一旦能“合”起来,就会达到一种新的艺术境界,他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试图将二者尽最大努力“合”起来。《怀麓堂诗话》云:
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盖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贾浪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
显然,李东阳试图引入山林体以改造台阁体。那么,贾岛山林诗“失之野”,究竟“野”在何处?必须先弄清认可的是何种风格的山林诗。《怀麓堂诗话》云:“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淡,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原来他欣赏的是“丰缛而不华靡”、“悠远深厚”“无寒俭枯瘠之病”的山林诗。而贾岛因失意贫穷,往往以“刻琢穷苦之言”(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为诗,意境凄凉,恰犯“寒俭枯瘠之病”,如“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暮过山村》)、“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题长江》),即如此。这自然被李东阳视之为“野”。白居易“台阁之诗”又是如何“近乎俗”的?《怀麓堂诗话》云:“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乐府歌辞所载《木兰辞》,前首最近古。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得《竹枝》亦入妙。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涩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一般老妪可解之诗,其内容、语言之俚俗,可想而知,哪里还有“台阁气”可言?这对追求“质而不俚”风格、反对“庸言谚语”的东阳来说,当然难以容忍。
只有做到不野、不俗,才可能“能兼二者之妙”,李东阳认为李白、杜甫之诗恰好如此。那么,他又从哪些方面来阐明这一命题的?他羡慕杜甫、李白“律间出古”之风格,《怀麓堂诗话》云:“杜子美‘独树花发自分明,春渚日落梦相牵’;李太白‘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虽极力摹拟,恨不能万一耳。”李东阳崇尚李、杜远近浓淡适中的诗“意”:“如杜子美‘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不通姓字通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衔泥点涴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皆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与知者言,难与俗人道。”风格远近浓淡适中之诗,自然易避“野”与“俗”之嫌。他赞美杜甫忧国忧民的人格,崇尚其沉郁顿挫的诗风:“闭门颇笑陈无己,忧国谁怜杜拾遗”(《次韵答邵户部文敬,前后得七首》其二)、“杜甫不胜忧国愿,向来真与海波深”(次韵杨应宁久旱三首》其三)、“杜陵广厦万间同,千载江湖叹此公”(《苦雨后,和乔师召喜晴韵四首》其三)。这与其“禆道化”主张是一致的,当然与“野”、“俗”不可同日而语。他企慕李白“花下一壶狂李白,江头三弄老桓伊”(《次韵答攸县陈翁钺》)、“未倾李白金尊月,先坐王郎玉麈风”(《再叠答夏提学二首》其一)的飘逸洒脱,也就意味着李诗不犯“野”涉“俗”。不仅如此,东阳还能从整体风格上探讨杜甫、李白诗“兼二者之妙”。《怀麓堂诗话》又云:“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今观昔人所选,虽互有得失,至其尽善极美,则所谓凤凰芝草,人人皆以为瑞,阅数千百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焉。如李太白《远别离》、《蜀道难》,杜子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新婚别》《兵车行》,终日诵之不厌也。”这些为人熟知的诗歌,无论内容还是语言风格,皆深“兼二者之妙”,无需多言。可见,李东阳“兼二者之妙”说,是一多方位、多层次的有机整合体。为纠正台阁末流之流弊,引入“清耸奇峻”的山林之气加以调和,乃不失一可行之法。[3]加之崇尚“和雅冲泊,粹然不离乎正”(《青岩诗集序》)之文风,李东阳调和台阁体与山林体,自会追求一种既不“野”又不“俗”的雅正文风。此举虽有“起衰救弊之功”,但不过是台阁体回光返照,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其覆亡命运。因为,自成化以后,明代社会潜伏的各种矛盾已逐渐显现出来,台阁体赖以生存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台阁体已到了该退出明代文学殿堂之时,历史将这一使命赋予了前七子。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李东阳改革文体的筚路蓝缕之功,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所言“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
这里还必须特别说明,李东阳引入山林体文风改革台阁体文风,还与其强烈的山林意识、对诗歌言情功能的重视有关,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总之,李东阳从内容、功能、艺术风貌、文体分类等层面,比较客观、全面地探讨了台阁体的文体特征。他对“三杨”台阁体非常推崇,既有沿袭,又有革新,且前者有甚于后者。他引山林之风入台阁体,试图调和二者以纠台阁体末流之弊,但未达到预期目的,最终没能挽救台阁体覆亡之运。从整体上看,李东阳诗文多数“仍是台阁体的延续”[4]。尽管如此,李东阳改革文风的发韧之功,仍不可磨灭。
[1]左东岭.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J].湖南社会科学,2002(2):89-93.
[2]雪莱.伊斯兰的起义(中译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6.
[3]阮国华.李东阳融合台阁与山林的文学思想[J].文学遗产,1993(4):93.
[4]廖可斌.茶陵派与复古派[J].求索,199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