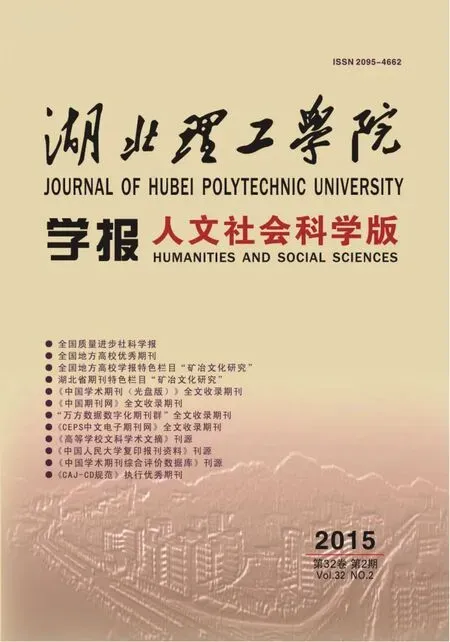论莫言小说的“言说策略”*
2015-03-28陈新瑶
陈新瑶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435003)
论莫言小说的“言说策略”*
陈新瑶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435003)
“小说写我”的叙事狂欢、长篇小说思想上的“众声喧哗”与“模糊地带”的存在、“诉说就是一切”的创作定位,这些独特的“言说策略”呈现出了莫言小说创作的个性。它们的存在,既体现了莫言对既定成规的反叛、对创作自由和小说文本价值多元化的追求,又显示出他在创作思想上的矛盾与冲突。莫言在政治、民众、自我与艺术之间的取舍与平衡,既让其作品充满了艺术张力,又给其小说写作带来了种种难以弥合的裂缝。
莫言;“言说策略”;反叛;矛盾与冲突
作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以其创作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显示了他的创作才情和艺术魅力。从1982年至今,莫言先后在多种场合表述过他的创作观点与创作感受。《诉说就是一切》、《用耳朵阅读》、《小说的气味》、《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他人有罪 我亦有罪》……在这众多的创作谈背后,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艺术才情且极度自信的山东汉子莫言,一个精力旺盛且充满着生命张力的莫言。在长期的小说创作之中,莫言逐步形成独有的言说风格。“小说写我”的创作立场的确立,不仅帮助莫言解决了小说的选材、叙述角度等问题,同样在小说人物塑造上也催生了众多与莫言内在精神极为相似的反叛者形象。对长篇小说思想多义性以及“模糊地带”的追求,让其作品在注重反映生活广度与复杂性的同时,却削弱了对作品思想的深度与基本的价值判断的关注力度。另外,将诉说视为小说与小说家的全部意义的看法,也让其创作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这些言说策略的使用,使其作品充满了魅力与变数。
一、“小说写我”的狂欢
莫言是一个激情型的作家,一旦创作灵感袭来,孕育在他心中多年的情思就会像流水一般哗哗向外流淌。写作《透明的红萝卜》,他只用了3天时间,而小说《红高粱》,他仅用6天就完成了。最让人惊奇的是长达43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他只用了43天完成,其创作速度之快,确实让人惊叹[1]541。在提及小说《欢乐》的写作状况时,他说:“小说写作之时我觉得都无法分行、分段,笔都赶不上思维的速度”[2]79。在2002年11月发表的一篇创作谈《自述》中,莫言多次表达了素材的发现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唤醒了我:原来狗也可以进入文学,原来热水也可以进入文学!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必为小说的素材而发愁了。从此之后,当我写着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3]29。丰富的人生经历为莫言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写作素材,也给予了他写作时的那份自信,更是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塑造与小说的叙述方式。
“小说写我”确实是一种令人兴奋与着迷的写作方式,据此,莫言不仅解决了写作素材的问题,同时还建立了一种更为坚定、更容易操控的创作立场。莫言是小说家,他更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我”成为大多数事件的叙述者。从《红高粱》、《红蝗》到《生死疲劳》、《蛙》,这些作品均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既便于作者对作品叙述内容、叙述时间、叙述节奏的安排与控制,而且它还能凸显或弱化、遮蔽人物或创作者的真实情感。不同的叙述者讲述各自所知的那一部分故事,众多的有限叙事串联在一起,就会在整体上形成全知叙事的表述效果。它可从不同的层面将不同的叙述者——“我”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他人与自身的叙述呈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以塑出几百个人物,……这几十本书合起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3]29初读这句话,大多数人会觉得它稍欠确切。因为一个拥有创作才华的作家,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些人物在性格、思想上也不可能全都趋同。也许,莫言所要讲的是,在一个作家所塑造的主要人物身上,均投射着作家本人的影子。事实证明,莫言笔下的众多人物与莫言一样,具有较强的反叛性和个人性。作为一个富有个性与创造力的作家,在首次接触到川端康成的作品之后,莫言就基本上确立了那条充满了质疑、叛逆、狂欢与自我陶醉的创作之路。作品《红高梁》中“我奶奶”、“我爷爷”身上奔涌着的野性而强悍的生命力,它首先来自于莫言内心深处要求挣脱既定的历史秩序与传统伦理规范的反抗力量,来自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莫言要求释放自我、寻找与追逐自我人生的强烈心理诉求。《金发婴儿》中那个长着翅膀飞上天的老头、《红煌》中窥视着大学教授勾引女学生丑行的“我”、《二姑随后就到》中那个命中注定与整个家族不共戴天的“二姑”、《生死疲劳》中那个死后进入六道轮回却始终忘不了前生往事的叙述者西门闹、《蛙》中那个无视民间道德伦理却一心只想为减少国家人口而奔命的“姑姑”及因迷恋敌台女播音员充满诱惑力的声音而驾机投敌的王小倜,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一股与生存环境、与命运相抗争的叛逆精神和异乎寻常的反抗力量,而这一切均来自于作家莫言内心的真实。
由于写作者与笔下人物在内在精神上的接近性,在写作之时,作家莫言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自我立场来发言,言说或表演成为了其笔下人物最主要的生命形式,在这个被莫言所操控的故事讲述过程中,作品中人物作为生命个体的真实想法常常会被作者所忽略或抛弃。这种现象在莫言的前期写作中就已显现。如在小说《红高粱》中,为了凸显“我奶奶”戴凤莲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对戴凤莲的形象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描写。如:戴凤莲与轿夫余占鳌在高粱地野合的情节、戴凤莲送儿子与心爱的男人去打伏击战的情节,这些极具伦理情感冲击力的情节在作者笔下却变成了单一的生活图景。投向余占鳌的怀抱,本是一场对未知命运的冒险;送儿子和情人上前线,这又是一场生离死别;可在这一切面前,戴凤莲却没有任何的犹豫与不安。莫言在极力凸显戴凤莲敢于反叛传统伦理道德、坚决反抗外敌入侵的崇高与伟大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女性的真实存在。戴凤莲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生命情感却被隐藏或遗忘。好在,在戴凤莲临死之前,作者为其安排了一段富有“天问”意味的内心独白,这段文字既呈现出了人物强烈的反抗意识,同时也从人的角度写出了戴凤莲对生命的不舍、对人生的眷恋,只可惜在整个小说文本中,像这类精彩的内心独白类的文字太少了。在随后的小说创作中,莫言并没有改变自己操控一切、高高在上的叙述姿态,相反却愈演愈烈。在《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这些作品中,几乎通篇采用了讲故事式的言说方式,人物的个性与情感表现均被叙述者牢牢掌控。而这一方式的采用,不仅易于弱化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同时也可能影响到作品理性反思力度与思想深度的不足。特别是当作品中人物形象与创作者莫言的情感关系更为亲近之时,莫言笔端的批判与反思意味就显得更为淡薄。众所周知,长篇小说《蛙》中的主人公“姑姑”——万心,就是以莫言的姑姑为原型,叙述者“蝌蚪”与现实中的莫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许因为这一关系,作品中“姑姑”身上的政治激情与英雄情结被放大,而她作为女性、长辈、医生的生命感受均被遮盖;叙述者“蝌蚪”作为丈夫、朋友、未来的长辈和侄子所应有的那份生命情感也被无端搁置,所做的只有叙述。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姑姑”与“蝌蚪”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为各自的过错赎罪,但在他们二人的忏悔中,读者并没有看到“姑姑”关于自身当年盲目的政治激情与极端、错误的工作方式的批判和反思,更没有读到作为知识分子的“蝌蚪”先生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遭遇阻力的深层原因的应有思考。如果说,“姑姑”的赎罪方式让人感到可笑;那么,“我”借助于诉说、写作来忏悔的方式更是让人觉得过于虚假。尽管作品中“姑姑”、“蝌蚪”与现实中的姑姑、莫言并非等同,但叙述者“蝌蚪”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肯定与困惑、对“姑姑”人生传奇的欣赏和遗憾,这也是作家莫言的政治认识与人生困惑。在宏大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强烈的生命意识面前,在上层政治与民间伦理面前,莫言在作品中没有做出孰是孰非的明确判断,他所作的只剩下“言说”,“言说”成为了他面向这个复杂世界的唯一方式。
二、“众声喧哗”与“模糊地带”
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莫言提出长篇小说应具有密集的思想,“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与绞杀。……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4]28。细读这句话,读者不难看出莫言关于长篇小说思想表达及其创作技巧的独特看法。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每一件事情均存在着它的多面性。强调作品思想的丰富性,这本没有错。可小说思想如果过于丰富,就很有可能出现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价值立场的难以把握、作品的思想驳杂等问题,或是非理性创作大于理性创作的问题。再者,在一个价值体系多元化或价值定位“有意缺失”的文本中,作者本人很容易被自己的叙述策略绕进去,甚至于某些时候会被其弄得手忙脚乱,前言不搭后语。例如,在《蛙》这部带有忏悔和赎罪意味的作品中,由于受到“模糊理论”的影响,小说关于“姑姑”的形象塑造前后出现了极大的反差,甚至其性格发展在最后却偏离了正常的情感轨道,让人匪夷所思。在遭遇“青蛙”事件之前,“姑姑”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为此她付出了青春和大半生的幸福,背负着沉重的骂名,可在这之后,她很快丢弃原有的政治立场。为了赎罪,为了让那些惨死在她手中的小生命早点投胎为人,她不顾一切,竟然为那些“二奶”、“小三”等无法正常、合法生养的女人打通生命的通道,变相地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抗衡。更让人惊奇的是,她竟与袁腮等不法分子沆瀣一气,参与到非法“代孕”机构的相关业务工作;甚至还参与到诱骗陈眉所生的孩子这一行动之中。“姑姑”晚年的忏悔与赎罪却因新的罪恶的出现而彻底瓦解。也许,作者莫言想通过“姑姑”思想、行为的转换来凸显生命至上的思想主题;但人物思想行为如此大的变化,却也让读者难以信服。因为“姑姑”当年犯下的罪恶,不仅仅是她毁掉了2 800多个尚未来到人世的生命,而且她还亲手毁掉了众多乡村女性及其家庭的幸福乃至一些不幸孕妇的性命。张拳老婆的死、王仁美的死、王胆的死,均与姑姑有直接关系。姑姑的忏悔应该是彻底的、全面的,她不仅要为那些不幸的娃娃祈祷,她也应该为那些惨死的母亲们祈福,她更应该为那些不幸的、依然活着的母亲赎罪。为了让自己的徒弟能做上母亲,她还无情地参与到诱骗陈眉及其孩子的事件中,这一情节的设计不仅损害了这一忏悔者的形象,同时也使得作品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偏差。
“众声喧哗”既有可能是各种同质性思想间的相互辉映,也有可能存在着不同观点间的相互冲突。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要将不同的思想因素融入同一文本之中,他本身就应该具有强大的、极具理性的文本驾驭能力,具有明确的价值立场。然而,莫言先生似乎只愿意去做一个诉说者,而不是思考者,更多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思考的任务交给读者。“……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5]84“作家的思想是通过人物的行为,通过人物的性格,通过人物而显现出来。作家应该尽量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去对人物进行道德和价值的评判,要让人物自己说话,要让读者自己感受。”[6]甚至他还认为:“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4]28当然,作家的创作动机与文本意义生成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一对等关系,但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生成并不能完全由读者来决定,创作者本身对一部作品的思想主题以及价值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创作量极其丰富,创作能力极为旺盛的作家,莫言的写作并非如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没思想、没深度;更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创作之时他主动地放弃了对作品思想的考虑。在他的众多创作谈中,关于历史与现实、农村与城市、他人与自我,他提出了很多看法和思考。之所以提出“众声喧哗”与“模糊地带”,莫言其实就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创作思想一元化、明确化,或让先行主题扼杀了文本意义生成的多种可能性。例如,在断断续续、耗时7年才完成的《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在不断调整小说的叙述结构与表现方式的同时,先后在文本中融入一些新发生的社会生活内容。如此一来,定稿后的小说文本远远脱离了莫言最初只想写“姑姑传奇一生”的单纯想法,而在多层面上显示出了它的创作价值。正如该小说责任编辑曹元勇先生所言,莫言的《蛙》至少在五个向度上显示出了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7]。特定时期中国乡村妇科医生“姑姑”传奇而坎坷的一生、中国计划生育状况的错综复杂、中日两国文学创作者的友情与交流、知识分子“蝌蚪”的忏悔与赎罪,这些不同的生活场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作者莫言对“姑姑”这一人物思想高度政治化的惊讶与痛惜、对几十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进程中乱象丛生的不满与愤怒,以及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决拥护和对个体生命不堪一击的无奈与悲痛,这些多样化的思想内涵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大大拓宽了作品的审美空间。
对于作品而言,文本思想意义模糊地带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拓宽作品的审美空间、丰富作品的内涵,但它也有可能使作者与作品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事实上,莫言的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四十一炮》及短篇小说《神嫖》、《红耳朵》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显示出思想价值体系的过于散漫、文本意义无从捕捉的尴尬。莫言先生也多次提到小说创作者对真实与历史的无能为力。他试图去消除小说创作者与历史、现实、社会人生的确切联系,他的这一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任何一个创作者不可能离开人世而独立存在,他的所有创作都与其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诉说就是一切”
“所谓的作家,就是在诉说中求生存,并在诉说中得到满足和解脱的过程。与任何事物一样,作家只是一个过程。”[5]83正因为如此,莫言的小说多以思想价值“模糊”或“空缺”的形式出现,也因之引起一些评论家的不满与批判。在众多的批判声音中,李建军先生的一段话显得尤为尖锐,“由于陷入一种严重的相对主义迷幻状态,所以,莫言无力创造和表现那种清晰、有力量的价值图景,也无法清晰地辨别美丑、雅俗、高下,缺乏一种创造性的审美平衡能力……”[8]文学、艺术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对于社会而言,文学、艺术自身所具有的教化和审美功能是其存在的最大理由;但对于部分的艺术家而言,艺术仅仅只为个体、为个人而存在。对于莫言来说,他更愿意接受后者。他认为,作家只是一个职业,小说本身也不一定非得承担起启蒙或批判现实等社会功能,艺术作品是表现艺术家创作个性的最好场域。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生活,事实上,艺术家当然也包括作家莫言,他们并不能脱离这个社会而独立存在。文学、艺术是人类公共的精神资源,它们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
“所有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用叙述的华美和丰盛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性格的缺陷,这算一个恒久的现象。”[5]83尽管,相对主义创作理论的存在成为了他人指证莫言小说创作价值不高的一个证据,可莫言关于作家、关于诉说、关于创作的理解却具有了自身的特色与另一层意味。诉说对于莫言的意义,就是其写作的全部意义。现实生活中莫言其实就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他试图去与外在世界作深入的交流,可又极容易被过去生活的阴影乃至于生活中的一些负面事件所纠缠。莫言总把自己比作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那个黑孩,沉默寡言的黑孩暗示着莫言内心的孤寂与安全感的匮乏。无论是其后娘、老铁匠、菊子姑娘还是小石匠,他们都不能给黑孩带来任何的安全感与依赖感;对于惨淡的现实,他只能报以麻木的身体行动,可他的内心世界,却永远保存着一个美妙的、奇特的生活想象。那个晶莹透明、玲珑剔透的红萝卜,那个浑身泛着金色光芒的红萝卜,那个有着金色的外壳与透明的银色液体的红萝卜,既承载着黑孩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想象与向往,同时也成为了黑孩放松自我、抵御外界混乱现实的最佳方式。与黑孩一样,在混乱的现实面前,莫言只能直视与默默承受,但在揭示与批判不堪现实的同时,莫言又不愿舍弃自己关于生命、关于生活、关于艺术的所有想象与追求,他既要站在普通老百姓与知识分子的立场去写作,又要站在自身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与艺术创作者的立场去写作,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创作总是力图在不堪的现实与美好的想象、写实与虚构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他的小说选材与创作主题大多贴近中国历史与现实,符合中国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以及主流文学的表达需求,可他的小说言说方式却不拘泥于规范,充满着一股放荡不羁的创作特性。叙述人称的不断转换、第一人称的言说方式、狂乱而野性十足的语言、对作品思想意义的有意隐蔽……这些均成为了莫言表达自我存在的一种独特方式。以上创作个性的存在,在某一层面暗示了现实生活中莫言内心的怯懦与“性格缺陷”,他无法从童年与少年时期苦难的生活阴影中走出来,更无力与强大的外在力量相抗衡。他需要在诉说与写作之中释放自己对社会与生活的不满、愤怒与恐惧,进而来平衡自己的内心;他更需要在创作活动中呈现自我力量的强大与人生价值。他精心打造了一个“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在那里,他就是至高的统治者——国王。这种带有“掩耳盗铃”式的生存方式,不仅是莫言一个人的生存真实,也是众多现代人的生存真实。在社会变动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参与者,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摆脱外力的冲击与挤压。人性是复杂的,可人心是向善的。坚守一份美好的信念,寻觅与发现生活中的爱、美与善,积极呈现社会光明的一面,这应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艺术家为社会、为百姓所尽的义务。作为一位著名作家,莫言有责任通过他的写作来为我们的社会传递正能量。
“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9]42莫言小说创作的所有价值呈现了莫言这个独特生命个体的存在,他关于人的原始、充满野性生命力的着力呈现,他关于现实人生杂乱无章、毫无理性的有限理解,他利用诉说和写作来证明自身力量的强大的生存方式,都是莫言为他自身及其所处的现实所画出的存在之图。一个作家可根据个人的理解来描写世界,可读者却不会按照作家的理解来理解其创作。在众多读者看来,莫言的小说创作存在着一个思想融合上的矛盾,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得站在政治的立场、公正的立场来写作;作为广大百姓中的一员,他又得从世俗的立场、民间的立场去写作;作为一个有才情的作家,他更愿意从艺术与自我的立场去写作。三者之间,他难以取舍,可又难以使之达到真正的融合。也许,他就像黑孩一样,一直在寻找着那个泛着金色光芒的“红萝卜”,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莫言在现实与自我之间不断融合的过程。
“我想一个作家的成熟,应该是指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所谓的风格,应该是一个作家具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不混淆于他人的叙述腔调。这个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一种独特氛围。”[10]3每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着力去寻求并形成自我的风格。莫言对多种小说言说策略的理解与运用跟他个人对自我风格的寻求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有着苦难的童年和少年经历的作家,一个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并希求在小说创作与故事讲述中来确证自我、反思历史与干预现实的作家,莫言先生对于小说创作重要性的认识尤为现实而满蕴着一份真诚。在从事写作的最初,莫言最大的希望是能通过写作过上一天能吃上三顿水饺的幸福生活,可随着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他更希望能在讲故事的同时形成自我的写作风格。无论是“小说写我”在小说选材、人物塑造、叙述方式方面的运用,还是对长篇小说思想的“众声喧哗”和“模糊地带”的刻意追寻,抑或是在借助于诉说来满足、实现自我人生的创作定位,这些均是莫言先生在小说创作方面不断走向成熟的明证。只是,文学既是“人学”,又是一门艺术。如何在满足自我与艺术创作之间保持平衡,恰当地使用各种小说“言说策略”,这条艰难的探索之旅,莫言先生还得继续去寻求。
一个作家的成熟,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能形成自我风格,除此之外,他还应该拥有独立而坚定的价值判断和深广的人文关怀。我们期待着莫言先生能从民间出发,从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与精神需要出发,写出更富有现实意义、更具创作个性、更合乎老百姓精神需求的小说作品。
[1] 莫言.生死疲劳·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 高昌.头上三尺有青天——近访莫言 [J].作家,1998.
[3] 莫言.自述[J].小说评论,2002(6).
[4]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J].当代作家评论,2006 (1).
[5] 莫言.诉说就是一切[J].当代作家评论,2003(5).
[6] (日)阿刀田高,莫言.小说为何而存在?[N].文学报,2012-08-30(5).
[7] 曹元勇.对生命的敬畏[N].文艺报,2011-09-19(11).
[8] 李建军.直言莫言与诺奖[N].文学报,2013-01-10(23).
[9]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
[10] 莫言.锁孔里的房间[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龚 勤)
"Narration Strategy" of Mo Yan's Novel
CHENXinyao
(Normal College,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3)
Some distinctive "narration strategies" show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Mo Yan's novel creation, such as narrative carnival of "material-driven writing", "multitone" and "blur region" ideas, and "narration is everything". On the one hand, these strategies reflect Mo Yan's rebellion against established rules, the pursuit of creative freedom as well as the diversified value of novel tex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embodies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Mo Yan's novel creation thought. His choice and balance between politics, people, self and art both let his works full of artistic tension and brought his novel writing with stitched cracks.
Mo Yan; Narration Strategy; rebellion;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2014-10-28
湖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艺术学理论”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3XKJS。
陈新瑶(1971— ),女,副教授,硕士。
10.3969/j.ISSN.2095-4662.2015.02.013
I207.4
A
2095-4662(2015)02-006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