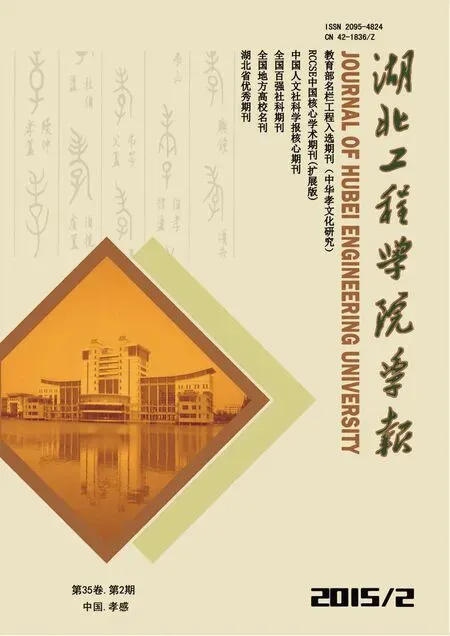论张执浩诗歌的语言策略
2015-03-27杨东伟
杨东伟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论张执浩诗歌的语言策略
杨东伟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张执浩是当下诗坛上一位比较重要的湖北籍诗人,其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语言的精到把握。诗人以“梦话”作为诗歌的语言生成机制与突破口,能灵活运用拟人、隐喻等各种修辞来提升诗艺,并注重运用张力美学来调整词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形成诗人独特的“离心诗学”。张执浩自如地运用各种语言技巧使其诗歌写作日益精进,但并不在语言迷宫里迷失方向,而是注重对汉语诗性特征的开掘。其诗歌写作拓展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责任编辑:余志平)
关键词:张执浩;诗歌语言;修辞;张力;离心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码:A
文章编号:号:2095-4824(2015)02-0053-07
收稿日期:2014-11-21
作者简介:杨东伟(1989-)男,湖北兴山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张执浩是当下诗坛一位比较重要的湖北籍诗人,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总是力避自我重复,在不断探索中寻求突破口,在调整中找准方向,其诗歌被评论家荣光启称之为“汉语的当代美声”。而今,正处于“中年写作期”的张执浩不仅诗歌产量较高,而且佳作频出,时常给文坛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其诗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对语言的精到把握,在他眼中,语言是诗人必须不断面临的“永远崭新”的问题[1],诗歌写作既是一个不断地“制造”与“克服”语言障碍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语言既是诗歌表意的手段也是目的。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技巧玩弄,张执浩立足生活的本真书写,从最基本的修辞入手,以语言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手段来实现对诗歌世界的建构。总的来说,张执浩是一个“智慧型”的诗人,他有一套独特的语言运用法则,能够通过语言的桥梁,让形而下的生活与形而上的诗歌完成对接。
一、方法与机制:在“梦话”中发酵的词语
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而言,精通语言如同精通一门古老的技艺,也就把握了某种言说的“可能性”。但当下的先锋诗歌似乎又重新面临着语言的难题,这种难题不在于如何运用语言,而在于诗人如何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如何通过语言的言说恰如其分地表达自我与进入世界,让语言与个人经验、与时代发生更为有效的关系。张执浩是一位有着强烈的语言自觉意识的诗人,在20多年的摸爬滚打中,他逐渐“培育”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生成机制,在通往“纯粹”的途中虔诚地求索。
在一次名为《长安不去了,我要回楚国》的访谈中,当张执浩被问及是如何创作出诸如“群山在望,你是我的白内障”、“我靠败笔为生,居然乐此不彼”、“原谅我这么老了,还在长智齿”这样经典的诗句时,诗人答道:“我经常胡说八道。”[2]看似一个平淡无奇的“胡说八道”却恰恰道出了诗歌创作的天机,对于张执浩而言,生活有时需要上升为诗歌,诗歌有时候则需要下降为生活,“胡说八道”正好打通了二者的交往之门,将语言与经验串联起来。
今生我无法克服梦游症/来世我要当木匠,走遍世界/只为找一截马桑木/打一副舒适的棺材,厚葬那些说过的梦话
——《小魔障》
语言兼具实用功能与自我创造功能,诗人是语言的梦想家,善于将语言的创造性功能发挥到最大。张执浩是一个善于“做梦”且喜欢“说梦话”的人,当现实的话语空间无法让诗人获得灵魂的自由时,他便以“说梦话”的方式向生活敞开自我。这样的梦话并非漫无目的,而是诗人想象、联想、潜意识的汇聚与喷发。在天马行空的修辞术中,一边让梦想飞驰,一边又寻找着与生活的最大公约数,并与之达成和解,以“梦话”为平衡点。所以,在笔者看来,“梦话”与“胡说”对于诗人而言关系重大,它们兼具了美学与诗学的双重意义,有时是诗人灵感的触点,有时是诗意的母腹,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语言策略承担着表情达意的重任。
细读张执浩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梦话”在诗中大致分为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情境的梦语,即诗人通过语言为我们设置梦中之景或者是梦幻与现实交融的场景;另一种则是诗歌语言本身的梦语性质,这些语言带有呓语、胡说八道、不着边际的特征,而正是这样的语言才让张执浩显得独特和引人注目。
生一个字,将她含在嘴里/生一个词,将她放在纸上/生一句话,将她铭刻于心/——一个这样的人,这样自恋/像孕妇,抱着自以为是的肚皮/在大街上晃来晃去/每天都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声音/涂抹天庭,云在飞,但翅膀是我借给他们的/而在下面,奔跑的云影,像/无足怪兽,当他们路过花坛时/我才留意到一位小女孩的哭泣声……
——《我每天都在生儿育女》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诗歌创作都像是诗人在做一场“语言的梦”。但张执浩的“梦语”则有其独特的气质,初看起来都略显“癫狂”,既像疯人语,又像神经质,而这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在这首诗中,诗人将写作过程比作生儿育女,足以看出诗人将写作看得异常神圣,珍视万分。但接下来“像孕妇,抱着自以为是的肚皮/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则将这神圣的场景拉回到世俗生活之中,语态略显俏皮与滑稽,颇有自我调侃与消解的意味。诗人用“自以为是”修饰“肚皮”,让整首诗顿时活泛起来,这种想象性的组接与搭配已经成为了张执浩的“招牌菜”,看似有些“无厘头”,事实上,这是诗人精心“策划”的结果,他通过对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词语进行改造,使其意义发生漂移,然后通过诗意的逻辑使之重组,最终生成新的美学内涵。这样不仅使原来的语词获得了意义的再生长,更是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云在飞,但翅膀是我借给他们的”这一句看似不合逻辑,其实是诗人充分发挥想像的结果,让外部事物随着主观意志自由奔跑。诗人通过这首诗反思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并探讨了生活与写作之间的微妙关系。很明显,诗境是诗人的冥想之物,也即“梦语”。语言略显“乖张”,彰显出了诗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智慧。
张执浩是“词语的梦想者”,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词语的运用方式之上。例如经常不按常规出牌,有某种剑走偏锋的冒险气质。他惯于旧瓶装新酒,赋予旧词新的意义和充足的想象空间,让“所有的感官都在诗的梦想中苏醒,并形成相互的和谐”[3],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曾称这种语言的狂欢为“梦想的诗学”。这种语言有时看似是胡说八道,实际颇具哲理,渗透着诗人对生活的参悟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因为你单薄,所以时代越来越胖/因为你越长越像儿子,所以我们理解/为什么亲爱的父子迟早都要分道扬镳
——《有赠》
这种“非逻辑”的“因为……所以”结构在语法学意义上是讲不通的,因为二者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在诗歌中恰恰正是诗意的生长点,张执浩故意省略了这因果关系中的其他线索,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迫使读者去思考,去补充其中的意义。个人与时代、父亲与儿子这些复杂而纠葛的关系正是隐藏在这些被省略的东西之中,探究意义的过程也就转变成发现诗歌、发现诗意的过程。这种语义的“断裂”现象,不仅体现出诗人对词语本意的独到理解,更能展现语言在诗意的逻辑中所产生的意义“延宕”的效果。
“胡说八道”是张执浩特有的天赋,但却并非无凭无据的胡思乱想,而是以真实的生活作为根基。诗人拒绝对这种天赋的滥用与挥霍,强调从自身的经验开始将诗歌写作向前推进。在精神探险中完成语言对经验的想象与改写,又让经验在语言之中获得诗性的展开与升华。无论是在梦中与父亲同眠时的亲切与眷恋(《与父亲同眠》),还是为了高压锅的减压阀而纠缠于生活的无奈之中(《减压阀》),诗人的语感与经验从未发生分离,语言被落实到具体的形象与意象之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诗人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更可以透过这种“疯癫之语”窥探到诗人的精神秘密,他的内心话语,他的无奈、挣扎都能尽收眼底。张执浩让作为工具的语言和心灵的语言达成了统一。这之中既蕴含了高超的诗歌技艺,也透露出了其表现世界与表现自我的方式,诗人以语言为触手抚摸万物生灵,在未知与已知之间求证着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诗人都有着敏锐的语言嗅觉,但并非每一位诗人都能从语言中找到自我。这是因为,他们大多沉迷于“发散式”的语言扩张,忽略了径由“聚合”之路回到语言自身,抵达灵魂的最深处。简言之,大多数诗人惯于外部想象,张执浩则善于在语言内部作深刻的沉思,“胡说八道”不仅是他的梦想的“制造器”,更是一面剖析与反思自我的镜子,所以他的诗歌不仅关涉生活,更关涉灵魂。
我和你的关系永无澄清之日/我曾是你,穿过你,像那件不再合身的布军衣/当胸前的纽扣绷落,我和你的合同/已经到期:我在白纸上写下/一个新生儿的名字,从那一刻起/你就缩回了我的英雄牌钢笔内
——《曾用名》
“曾用名”是诗人虚构出来的身份,它意在指认自我与内心,现在与过去,自我与父辈之间等多重关系叠加的复合体,这本是一个玄之又玄的话题,但在诗人笔下,所有的关系都有它特属的对应物。“合同”、“布军衣”、“纽扣”这些源自生活的词语在这里有了它特定的意义。中国古典诗歌注重“炼字”,在张执浩的诗中,动词的作用也显得十分重要。“崩落”、“缩回”等词语的使用让诗歌显得有力量感,让静止的关系活动起来。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诗人如是写道:“我在这张白纸上面牵引着你的身体/我这样来回扯动这些/笔画,这些胳膊和大腿/像是在放映一场皮影戏”,“牵引”、“扯动”、“放映”等词语在诗人笔下如同长了翅膀一样,有了震慑人心的冲击力。这些词语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敲击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那根琴弦,这时的语言不再只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外在之物,而是内化为一种精神的力量,获得了超越自我的穿透力而深入我们的灵魂深处。
在张执浩看来,“当‘写什么’和‘为什么写’都不再是问题,当我们只剩下了‘怎样写’的时候,文学就走到了自己的末日”[4],也即是说,如果把语言仅当作写作工具或者“方法论”的话,文学就不会有突围的出路。对于张执浩而言,语言必须是与生活、与爱、与自我经验密切相关的,更深层地讲,语言既是一种形而上的指引,也是一种精神的归宿。诗人充当了一个“梦游者”,他的使命就是以“胡说八道”的方式说出了这些关于词语、关于生命的奥秘。当词语经过“梦话”这个转换器,语言便与世界发生了置换,诗意也就此诞生了。
二、修辞的升华:以“诗学的隐喻”为中心
任何修辞学家都不会比诗人更精于修辞学。事实上,正是因为诗人的存在才让世人对修辞的兴趣日渐浓厚。张执浩在语言修辞上的造诣是读者有目共睹的。纵览张执浩的作品,几乎每一首诗都包蕴着形态各异的修辞技巧。从拟人到比喻,从对偶到夸张,从明喻到隐喻,张执浩酷似“语言的上帝”在其间穿行自如,似翩鸿,若游龙,它们宛如一件件华美的外衣,将诗歌打扮得高贵典雅、风情万种。
首先,张执浩精于拟人之法,他的拟人是将物与人的根本共性统一起来,从而在物我交融的层面上把握语言的精妙,是让语言进入生活、进入心灵的再生产,它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与多重解读方式,让生活由单一、乏味走向多元与重构。
那些年陆续走失的人/已先我一步藏身于此/那些长相孔武的大理石/坚信过去就是未来的结石,变化的/只是神的面具/高黎贡山远大,自律/白云有野心,从不显山露水
——《南昭诗篇》
随意从张执浩的诗集中挑出一些句子,我们都会被这些神来之笔迷倒。“长相孔武”与“大理石”搭配;“过去”与“结石”等同;有野心、但从不显山露水的“白云”。诗人将物当作人来写,让无生命的事物瞬间有了生命与灵气,且情状各异。与此同时,诗人惯于在语言中注入丰富的情感,让他们替自己说话。其实,张执浩从未停止过抒情,甚至每首诗都在抒情,而他的方式则是通过对语言的改组,将自我情感投射到其他事物之上,让情感在作为对象的他者身上流露出来。诗人的拟人打破了固有的语法规范,将词语的用法推向了创新的轨道,让语言在新的语境中恢复活力与新鲜感,并营造出“陌生化”的视觉效果与心理效果来打破读者的惯性思维,让诗歌在“难度写作”中展现其神奇的一面。
你笼罩着这块一清二白的田园
——《垂而不死之歌》
一条河在你脚踝处拐弯,你知道答案/在哪儿,你知道,所有的浪花必死无疑
——《终结者》
火车提速了,荆楚丘陵依然牵肠挂肚
——《为什么不再写麦子》
粉身碎骨的想法/前赴后继的想法
——《如果雨一直下下去》
张执浩对词语的搭配非常讲究,特别是对四字成语的运用,他总能以故为新、妙语迭出,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一清二白”、 “必死无疑”、 “牵肠挂肚”、“粉身碎骨”、 “前赴后继”等这些词语大多是用来修饰人的状态,但诗人却能够将其恰如其分地嫁接到无生命的事物之上,让其获得了一种鲜活感,这既是独到的拟人手法,也是笔者在上文提到过的语言“漂移”现象。语言的意义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被无限延伸,以至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容易过度使用其引申义,遗忘其本义。而张执浩对拟人的运用让这些词语回归其本来面目,以真相示人。例如:“牵肠挂肚”在习惯思维中意指十分惦念,放心不下。由于语言的频繁使用,产生了某种“自动化”的审美疲劳,在张执浩眼里,必须让其回到本义才能让真正的诗意复活。荆楚丘陵蜿蜒的样子正类似于人类肚肠的形状,这里的“牵肠挂肚”既是比喻也是拟人,看似信手拈来的词语实际上蕴含了诗人独具匠心的运思。
其次,明喻也是其诗歌重要的修辞手法。明喻作为比喻的一种类型,是传统的修辞方法,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化冗长为简洁。张执浩的明喻兼具这些公共作用,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个人经验的独特性。
而风还在吹,石榴将落未落/像我的父亲,似有若无/像摊放在面前的闲书,仿佛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生活,却受制于这双莫须有的脚
——《重阳一幕,或莫须有》
诗人惯于在诗歌里营造一种“边界式”的感觉,即这种状态经常处于两个事物相邻的边缘,但他们既非此,也非彼,而是一种被悬空的、奇妙的中间态。这样的感觉新颖奇特,且不易用文字表述。但是张执浩却能用明喻将他们清晰地展现出来:将它比作故去多年、似有若无的父亲,比作小说里似真似幻的人物。他在比喻中完成了画面的转换,将这种微妙的感觉具体到日常生活之上,使之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在诗人看来,明喻是通向表象世界的一条捷径,它将意志图像化,使文字的意义从模糊性中解脱,以一种通俗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超越了其原有的价值而向着诗学的道路进发。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诗人明喻使用得过多,则会导致某种油滑、花哨和流于表面,但张执浩并非如此。他在追求新颖的基础上,也注重对比喻的深度开掘,保持着诗歌应有的严肃性。在一首《无题》的诗中他这样写道:“我正在拉开与故乡的距离,越来越像/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人/越来越像/手边这把钢卷尺/你们看不见我身心分离之苦”,“距离”本是一个长度单位,诗人将它比作“死无葬身之地”的人和一把“钢卷尺”,这是将线性的、抽象的事物浓缩到一个具体的事物之上,这种比喻掷地有声,丝毫没有轻浮之感,张执浩极喜将词性的程度极限化,如“死无葬身之地”等句子的频繁使用,这些“绝对”诗语的使用往往给人一种压迫感,使得诗歌更加入木三分。
第三,张执浩并不是将种种修辞手法作为诗歌的目的,而是将其作为手段,借此来建构“诗学的隐喻”的诗歌理想,以隐喻纳万有“是更高层次上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认知模式。它是探索和表现人类复杂微妙的生命和精神的秘密形式,是本真而深刻的艺术感知的形式”[5]113,是将诗歌与个体生命、人类共同体甚至宇宙运行关联起来的艺术化境。张执浩将世界作为本体,将语言作为喻体,通过语言来反映世界,将世界这个庞然大物装进语言口袋里,再用隐喻后的语言将世界“吐”出来,被“吐”出来之后的世界自然而然地便带上了诗人的自我意识,是一个被重新创造过的世界。所以,“诗学的隐喻”不再只停留在一般的修辞格层面,而是文本和世界相互表达的一种方式,它是张执浩诗歌所呈现出的最大的语言特色。拟人、明喻等语言学上的修辞手法都是围绕着“诗学的隐喻”这个核心的观念在运作,诗人正是借助更高层次的“诗学的隐喻”观照生命与世界。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 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 这里,在这里, 我愿意/ 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 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 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 我真的愿意/ 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高原上的野花》
写作二十多年,这是张执浩最钟爱的一首诗,它蕴含了诗人对生活的最高向往与愿景。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隐喻统摄诗人二十多年的写作。这个长满野花、宁静自由的高原是诗人对内心、对世界的一种假想,这里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但并非脱离现实。小美女喻指所有美好的事物;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喻指祖国的和谐有序,自我内心平静安宁。诗人愿意在这理想国里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在这里自由写作。这个巨大的隐喻系统概括了诗人写作的起因与目的,也指明了写作的出发点与终点。这是对写作秩序的某种向往,也是诗歌精神的还乡之愿,这种隐喻既指向诗歌写作本身,又对人类生活给予某种方向性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隐喻并非凌空虚蹈,而是从生活的点滴开始,从事物本身出发,缘自事物的本性,直接抵达人的内心。
蚯蚓伸缩着,每一次曲展都传达出/另外那个世界的信息/潮湿的黑泥缓缓松开,又紧紧合拢/为了活下去,他放弃了另外半截生命,我也在放弃你,直到你/再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只是在心中/让我蠕动,像一粒米那样盲目?你有两个儿子,你知道么?/可你不知道/他们共用着一种疼
——《那半截蚯蚓去了哪儿》
张执浩不止一次写到“蚯蚓”,这种奇怪的生物当被斩成两截的时候,二者都能重新生长并完好地活下来。其实,诗人是借蚯蚓的生存方式来探讨自身与“内心工地”里那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如同十指连心“共用着一种疼”。实际上,相互分离的自我并不一定能同时感受到生活中的幸福和欢乐,但最深刻的疼痛往往是肉体与内心所共有的,最入心入骨的疼不是肉体之痛,而是由灵魂的不安与刺痛传递给肉身的,这种关于“存在之思”的疼痛才能让肉体与灵魂获得统一。达到统一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获得平静之心,但至少意味着诗人在精神上向真正的“自我”更接近。无论是“蚯蚓”还是诗人常常独自抚摸的“肚脐”,都是诗人借来隐喻自我的来历与去处的意象。它们看似平常,而又独特,诗人关心的不只是异于自我的外部世界,更关心自己的内心,由“蚯蚓”与“肚脐”等意象搭建起来的隐喻系统,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在用词方面,巧妙独特且颇具神韵,表达着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既不刻意伪饰,也不故作姿态,贴切自然。隐喻在张执浩的诗歌中既不表现为意识形态标签,也不表现为某种文化象征,而是表现为对生命的深刻体证,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以及对自我的形而上的超越。因此,这种“诗学的隐喻”的核心便是将各种修辞手段恰到好处地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近年来,张执浩进一步提出“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诗学观念,这是从诗与思的高度提升诗歌语言对生活的反应能力,更是将“诗学的隐喻”这一理念灌注于生活的最好诠释。
对修辞技巧的运用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的智慧。张执浩的修辞有时离经叛道,有时汪洋恣肆,有时又深沉含蓄。他从来不在单一的修辞方法上一条道走到黑,而是尽量寻求变化与创新,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特有的个人印记。最重要的是,他并不为语言和修辞的花哨所累,而是在精于修辞的同时,以“诗学的隐喻”为根基,为语言寻找存在之根与回归的家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离心诗学:在错位与张力之间
相对于许多诗歌语言的向心运动而言,张执浩似乎从来只愿做离心运动,这类似于后现代主义诗学对中心的偏离,向边缘撤退。诗人的语法、句法似乎有意与“内容”、“意义”等拉开距离,让词语与词语之间、词语与意义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犹如一根被拉开的橡皮筋,在这种力的作用下感觉与经验之间的正常逻辑被打乱,诗意获得的时刻正是这橡皮筋被猛然松开的那一瞬,这样的效果正是诗人充分利用了语言张力的结果,并通过含蓄韵致的表达将我们领进了一个美妙的境界。
自美国批评家艾伦·退特提出了“张力说”以后,“张力”便进入了诗歌研究的核心,并成为一个最难捉摸的术语。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语言的张力无外乎是通过对语言进行编码而形成的词语之间、句子之间、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力的关系。所以,张力论总的来说是一种关系论。一个优秀的诗人总能精准地拿捏语言之间的关系,张执浩在语言方面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能自如地运用语言关系,例如转折、递进、否定、对比等,并且进行创造性地发挥,通过词语之间的有效建构为我们设置种种错位的场景,营造某种“陌生化”语言秩序,从而将语言之间的张力最大化。
在梦中,你来过两次/一次太美,另外一次/神经质/——写小说的人这样写道:/“高潮将至,而你依旧口是心非”/而真正遥远的/不是爱,是爱无力/真正伤感的是/我太老,你太小/我不是没有想过/把父女关系转换成男女关系
——《记梦》
一首在“梦中”完成的诗中出现了多组对应关系:“高潮将至”与“口是心非”的不协调;“爱”与“爱无力”的不对称;“我太老”与“你太小”时间错位。诗人没有让“高潮将至”与心中快感同向奔涌;也没有让爱与爱的能力呈等量出场;更没有让两个相爱的人在年龄上符合实际。事实上,诗人通过语言为我们设置了一种情绪受挫的场景,让每一组事物都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效果,那么,多组关系所产生的力相互作用便会激发出更大的冲击波。这便是诗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既彰显出词语与词语之间相互拉扯的力量,又制造出了一种“不谐和音”,让诗歌“尽可能地远离对单义性内涵的传达”,并“成为一种自我满足、涵义富丽的形体”[6]。与此同时,也在这种场景的错位中重新定义生活的真相。
在张执浩眼里,人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与周围的事物共同构成了巨大的关系网,语言亦是如此。所以,在他的诗歌中,无论是词语、句式,还是情感的呈现都是以关系组的方式出场。黑与白,生与死,顺从与抗拒,人类与动物……复杂的世界被张执浩简化为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他们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的共同体,如果撤销其中一者,剩下的也将不复存在。
从今往后,你我形同陌路/生与死再无瓜葛
——《几念闪》
已婚的人仿佛未婚/死过一次的人显得神采奕奕
——《在青年旅馆》
长江喧哗,带动了藤椅,摇窝/他们手忙脚乱,我们手足无措
——《看三个德国人在青年旅馆造船》
木马在我的世界驰骋/永远和你没有关系,永远是/这样:舌头伸出去/遇到的却不是舌头
——《木马颂》
语言与生活具有某种相同的真实性,即二者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荒诞性。正如“大江东去,我掉头向西”中的不合作,不仅体现了语言的悖论性,更是一种锋利的反讽。这种句子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但却句句出彩,从搭配到修饰越来越精益求精。无论是“你”与“我”形同陌路,“生”与“死”再无瓜葛,还是“已婚”与“未婚”,“他们”与“我们”,“死”与“神采奕奕”的尖锐冲突,这种种对立的场景都是运用语言之间的矛盾关系营造出来的,从书写的内在语态和语言感情方面来看,诗人基本很少直抒胸臆,不会轻易让感情自然倾泻,总是通过有节制的叙事,让读者结合自身体验挖掘语言内部的情感,很显然,诗人习惯用正反对比的方法为我们安排错位的生活场景,错位的情绪、错位的感觉,甚至是错位的心灵。而读者却都愿意在这种有难度的理解中享受被“刁难”的快乐,咀嚼那种由心理落差而带来的余味,思量着“舌头伸出去/遇到的却不是舌头”,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对立是诗人运用的最为普遍的语言关系,这是诗人解释世界的方式,但语言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变化多端,诗人尽力发现并创造着语言的多样性。
生活成就胖子,圆脸嘟嘟多好/可我形销骨立,无富贵气,无暴力/在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
——《无题十六弄之三》
这种句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转折与否定的结合。用“可”作为转折,显示了前后两句的语义“断裂”现象,紧接着“无富贵气”、“无暴力”的否定语态更突出了与前者的反差,这表明了诗人对常规、对世俗的一种叛逃,或者说与生活的不相容性,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转折构成的对比来澄清自我,表明自己的精神立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否定句式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世界,与此同时也否定自己,而推翻这一切固有的逻辑之后再来重新定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言张力的显现不仅需要预设一个语言关系场,更需要让这种场产生的合力被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让语言的力量将情感、将生活带动起来。这才是张力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他们在你的脸上蒙上一张黄纸/他们在你的新居里撒下石灰/他们让我抱着你的遗像漫山遍野地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你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我们曾经是骨肉相连的人/三年了,我试图在梦中见到你/我甚至为此睡进了你曾经睡过的位置/那里,还存留着你身体的烙印/你的偏头疼、你的胃病、以及你的/因失眠而在黑暗中形成的特有的坐姿/三年过去,泥土吞噬了/蒙在你脸上的那张黄纸、你的双眼皮/以及那些把你吞噬了的癌细胞/我试图梦见你,却梦见我自己从梦中起身/走到黑暗的中心,轻轻地/抓挠着空气、直至空气变形/变成你做梦的样子
——《做梦》
诗歌开头的三句,连用四个“他们”形成一个排比句,强调母亲死亡这一事实的必然性,以及诗人心中强烈的不妥协。诗人仍然动用了语言之间的关系,即“他们”的主动性与“你”和“我”的被动性所形成的对比,其实“你”和“我”并不愿意遵守“他们”为“我们”制定好的死亡法则。在这里施事者与受事者的主观愿望存在不和谐的因素,诗人通过语言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秩序的不满。接下来的诗句基本都是运用语言的顺承以及递进关系,让诗人的怀念之情在母亲“睡过的位置”、“身体的烙印”、“偏头疼”、“胃病”、“特有的坐姿”等图景中展开。从这些意象的使用可以看出,诗人对语言的提炼都是源自真实的生活。诗人两次提到“我试图梦见你”,虽然一直都在叙事,但“试图”一词却是在抒情,诗人把情感点凝聚在“试图”之上来表达对死去的亲人深深的留念。之后的“起身”、“走”、“抓挠”看似平常,却用得生动传神,这是因为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全部凝结在这些动词之上,每一个词都浸润着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因为词语的情感化,使得诗歌有着贴近人心的温暖,词语的智性与诗人的内心产生了共鸣。
说到底,张执浩的离心诗学是将语言从司空见惯的逻辑中剥离出来,重新安排它们表演的顺序。也就是说,诗人在内心中对已经存在的语义关系有一种深深的抗拒,他总是试图制造某种语言的“不谐和音”让诗歌呈现出凹凸不平的图景。笔者在上文提出张执浩诗歌语言具有某种“癫狂”性质的命题也在这里得到印证。隐藏在凹凸不平的语言现象之后的是诗人对生命的体证,他调整着词语的间距,句式的长短以及诗歌的内在节奏,使得每次的出场都有急有缓、张弛有度,语言的这种张力带来了独特的“张执浩式”的诗意,在实现语言诗化和文本诗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心灵的诗化,也让这种写作方式成为诗人抵抗世俗中的污浊和无奈,抵抗心灵钝化的武器。
自80年代末至今,张执浩的写作在几经变化之后越来越显得成熟与稳重,但是语言却仍维持着那种富有“延宕”意味的风格,这是诗人特有的气质赋予语言的一种色彩。而他对语言精益求精的追求也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写作过程,这其间他不断地对自己写过的诗歌进行修改,对字词句打磨与翻新的工作似乎从未终止过。从这种意义上讲,张执浩的诗歌写作具有“未完成”的意义,在不同时段重新面对以前的作品,对其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一首诗歌永远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处于一种“行进”的途中,这种“未完成”是诗人不断面对自我、不断重新上路的一种见证。在完全意义上抵达一首诗的过程中,诗人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保持着好奇和善于发现的眼光。“在时下放逐激情和温情的写作中,张执浩对诗歌的本真追求,对爱和美的发现、探寻,是对于人心人情的理解和抚慰。”[5]114这种理解和抚慰首先是语言上的,在语言上获得一种感动的力量之后,才能将这种力量延续到生活与生命之中。从80年代的诗歌狂欢到新世纪的“网络写作”,张执浩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在与时代保持共鸣的同时,也坚持着自己特有的写作方式。毫无疑问,这种持续性写作已经具备了文学史意义,有待于史家的挖掘与深入。而张执浩却从未关心过这些,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步伐稳步向前。这也是惯于沉潜的写作者必备的精神素质。笔者相信,张执浩一定会握好语言这根火炬,在诗歌的版图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张执浩. 关于当代诗歌语言问题的笔谈:二[J].广西文学,2009(1):90.
[2]张执浩、康宁.长安不去了,我要回楚国——张执浩访谈录[J].三峡文学,2013(5):23.
[3]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M].刘自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8.
[4]张执浩.苦于赞美[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320.
[5]梁桂莲,刘川鄂.饱含着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张执浩诗歌艺术论[J].江汉论坛,2009(1).
[6]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M].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