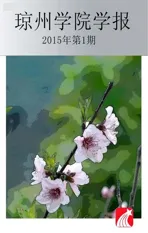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2015-03-27
(山西大学 文学院,太原030006)
一
汉晋之际的经学消长,皮锡瑞指出“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1]105。郑玄的著述之学始于永康元年(167年)的“客耕东莱”;旋后禁于党祸十四年,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作《六艺论》,遍注三《礼》,其间郑学大成;灵帝中平元年,党禁事解,郑玄又注《论语》《尚书》《毛诗》等经籍。此时郑玄声名鹊起,他却“屡征不就”。据史载,郑玄党徒遍天下,郑学行世而诸家经说并废,堪称是郑学的“小统一时代”。不过这个时代并不长远,及至魏晋已出现王肃经学与郑学分庭抗礼的局面,两派党徒互相辩难,王学因与司马氏政权的姻亲关系而稍占上风。皮锡瑞又指出:“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驳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龂龂于郑王两家之是非,而两汉颛门无复过问。”[1]109他意思是说,魏晋经学史越过了今古文家法相争执的汉学时代,时人普遍关注的是郑、王之学的优劣短长问题。
至于王肃辩难郑学的确切原因,在今天仍是难以论定。皮锡瑞对此也存有疑问,他说:“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1]106在这里,皮氏仅从汉学家法上辨明王学的渊源,然而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方面,王肃将要成为一个逞一时之意气的人物。又或者认为王肃为争得官学地位而与郑学立异,实则王肃的政治立场及观念差异之使然。龚杰较早地指出,王肃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改造了儒家的天道观,他主张无为而治,强调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满足,这些都和郑学的政治学说有着明显的区别。①参见龚杰《简论汉魏的郑学与王学》一文,《人文杂志》1989年第1 期。也有学者认为,郑学过于保守的忠孝观念导致其与时代的隔膜,而王肃“主张六天归一,圜丘合一”的观念,反映了天下渐趋统一的历史进程。②参见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 页。所以在司马代魏之后,“通于权变”的王学便充当了礼制改革的先锋。
颇有意味的是,魏晋嬗代之际的政治斗争表现在经学意识形态的领域,高贵乡公曹髦颇好郑学而不喜王氏,与拥立王学的司马氏政权恰成水火。曹髦尝以《尚书》郑氏义问难王学博士,针对《尚书·尧典》“若稽古帝尧”一语,曹髦同意郑玄“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的说法,而博士庾峻竟以“肃义为长”应对,王肃之义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对于这桩学术史公案,后来孔颖达曾辨之甚明,在他看来,“稽古帝尧”是表彰尧帝能够以史为鉴,择善而从,随宜更化,师古而不泥古的意思。其云:
言‘顺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无得失,施之当时,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于今世,乃顺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顺是不顺非也。……高贵乡公皆以郑为长,非笃论也。[2]
然则,曹髦为何取用“经无此训”的郑氏义呢?《高贵乡公传》记载他的即位诏书中称:“昔三祖神武圣德,应天受祚。齐王嗣位,肆行非度,颠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纳宰辅之谋,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3]132应当说,曹髦取用郑学的“稽古同天”之义来强调曹魏“应天受祚”的宗主身份,其用心是十分显豁的。再来看司马炎逼迫魏废帝曹奂所作的禅位诏书,里面全是对司马氏功绩的溢美之词,曹奂自称是一个退位让贤的君主。①《晋书·武帝本纪》载:“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祗,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由此观之,王肃的“顺考”之说强调“顺是不顺非”的历史理性,并不排除曹氏禅让天下的政治预期,这样也就实在地为司马氏篡魏打了掩护。曹髦素有中兴之志,忌恨司马氏的专权跋扈,因而在他主政其间,郑小同(郑玄孙)享有“五更”之誉而死于司马昭的鸩酒,王肃虽以文武功业而未列“三公”,竟死于“今皆未也”的憾恨之中。
二
郑王之争在魏晋嬗代之际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以王肃要极力消除郑玄的经学影响。除此之外,还牵涉到汉末以来经学系统内部逐渐明了的简约化与纯粹化的主题。王肃自称“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3]419。对此皮锡瑞尚存疑虑,令他费解的是,为何同一个学宗竟然生成郑、王两家互相攻讦的别子。事实上,王学果真出自贾马,但是须明了这种渊源关系究竟可以落实在何种层面之上。
在《礼记正义》之中,孔颖达辑录王肃好贾马之学的几个方面,有这样几条值得注意。
第一,《礼记·郊特牲》疏云:“《圣证论》以天体无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指其尊极清虚之体,其实是一;论其五时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为六天……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4]892-893第二,《祭法》疏云:“张融以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刘向、马融之论,皆以为《周礼》圜丘,则《孝经》云南郊,与王肃同。”[4]1508第三,《王制》疏:“其禘祫大小,郑以《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为大事。若王肃、张融、孔晁皆以禘为大,以祫为小……刘歆、贾逵、郑众、马融等皆以为然。”[4]457第四,《郊特牲》疏:“社稷之义,先儒所解不同。郑康成之说,以社为五土之神,稷为原隰之神,句龙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谷之功,配稷祀之……贾逵、马融、王肃之徒,以社祭句龙,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4]919-920第五,《月令》疏:“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4]579以上几条包括祭天之礼、宗庙祭祀、社稷之义,以及《月令》的作者等方面,涉及到宇宙观指导下的人间秩序和大一统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孔颖达仔细地将它们胪列出来,提示我们:在事关王朝意识形态与国家礼制建设的根本处,王肃学说确是与贾马相通,而与郑学大异的。
而在进一步地讨论中,郑王之争还涉及到一个“返本清源”的魏晋经学史主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在贾、马、郑、王一系的古文经学发展史上,该如何认识贾马之学所代表的古学精义,又该如何为郑学定位的问题。王肃在《孔子家语序》中说:
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日: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5]
这“义理未安”之处,首先就表现在郑玄竟认为孔子是一个“野合而生”的圣人,他还认为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祖契,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周祖稷。此类圣人感生的神话在汉代多为今文经学与《纬》学所信奉。后人评价郑玄的经学地位,往往就要批评他以《纬》释经,破坏了古文学的家法。《隋书·经籍志》云:“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行于世。……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6]《隋书》认为,古文学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的人文理性,这是毛公、贾逵所代表,王肃、王弼所力图回返的经学传统。钱穆先生指出:“其时,光武尚图谶,今学经师几乎无勿言图谶者。图谶之于后汉,抑犹阴阳灾变之于先汉也。惟古学家则不言谶。”[7]包括刘歆、扬雄、桓谭、尹敏和郑兴俱以“非谶”著称,马融、贾逵虽习谶纬之学,实则并不信纬,也不曾以纬乱经。①参见曾德雄《谶纬与东汉学术》,《人文杂志》2010年第6 期;李俊岭《马融的学行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理论学刊》2007年第2 期。总之,郑玄以纬释经败乱了“实事求是”的古文家法,而王肃返还古学的努力也就表现为与郑学之间信谶纬与退妖妄二种的对立。在东汉反谶纬思想不绝如缕,尤其是汉末理性主义的氛围之中,王肃的这种思路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在晚清学人看来,郑玄的败乱家法主要是一个混乱今古的问题。廖平在《今古学考》中指出:
今古之分,郑君之前无人不守此界畔。伏《尚书》、三家《诗》无论矣。何君《公羊解诂》不用古说,其解与《周礼》不同者,皆以为《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礼》,此今学之派也。至于许君《说文》用古义,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说目之,屏为异义。至于杜、郑(郑兴、郑众父子)、贾、马,其注《周礼》、《左传》、《尚书》,皆不用博士说片言只字。……今古之混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王肃)。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魏晋之间厌其纷争,同思画一。郑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胜,力返古法,足以摧击郑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厉。[8]42
许慎、贾逵、马融等人最号“通儒”,在廖平看来,他们注经往往今、古文“并行而不害”,使人观其会通而得其主宰,并不存在混乱今古,甚至以今篡古的问题。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也持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王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也。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1]106由此可以判断,汉晋之际的经学历史无论如何都不能绕过郑玄的影响:按照晚清学者如廖平、皮锡瑞的意见,后起的经学家应当分别家法,各还其旧,即“删其混合以还杜、马之旧”[8]42;若王肃等却走了另外一条路线,他的混乱今古较之郑玄尤甚,但是的确剔除了郑玄谶纬经学的消极影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古学理性。
王肃学术直接源自以宋忠、司马徽为代表的荆州学派,史载这个学派出现了不少“问难郑说”的学者。比如王粲就不满意郑玄的《尚书》学,曾著有《尚书问》来问难郑氏义。《三国志·李譔传》更记载:“(李譔)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3]1026李譔与王肃分居蜀、魏,都“善贾马而不好郑氏”,当是体现了荆州学派的普遍宗尚。荆州学派是宋忠主持下的一个古文学派,汤用彤先生指出它是汉代经学转向魏晋玄学的一个中间环节,其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1)“荆州学风,喜张异议,要无可疑。其学之内容如何,则似难言。然据《刘镇南碑》称表改定五经章句,‘删刬浮辞,芟除繁重’,其精神实反今学末流之浮华,破碎之章句”;(2)“夫宋氏重性与天道,辅嗣(王弼)好玄理,其中演变应有相当之连系也。又按王肃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解。张惠言说,王弼注《易》,祖述肃说,特去其比附爻象者。此推论若确,则由首称仲子(宋忠),再传子雍(王肃),终有辅嗣(王弼),可谓一脉相传者也。”[9]荆州学派有治《易》的传统,宋忠、王肃、王弼一脉相承,并且如汤先生所云,荆州《易》学重玄理而不重象数占验,表现出“疾虚妄”的理性精神与清通简约的学风,直接开了魏晋玄学的先河。将王肃经学置于荆州学缘的背景下来衡量,一方面他要清除郑学的谶纬神话思想,一方面则在郑玄之后继续“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努力,每一个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晚清学者所指认的“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还没有成为汉晋之际的经学主题。
三
王肃著有《毛诗王氏注》《毛诗义驳》《毛诗问难》《毛诗奏事》等,专门问难《诗经》郑氏义,但是都已经亡佚了。清人马国瀚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从中只能窥见王肃诗经学的大致面貌。
马国瀚对王肃诗经学有一个总体的评价,他说:
其说申述毛旨,往往与郑不同。案郑笺《毛诗》而时参三家旧说,故《传》《笺》互异者多。《正义》于毛、郑皆分释之,凡毛之所略,而不可以郑通之者,即取王注以 为《传》意,间有申非其旨而什得六七。[10]208
“其说申述毛旨,往往与郑不同”,这是对王肃诗学的中肯的评价。至于皮锡瑞所说的“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1]107的现象,其实是不多见的。如《小雅·车舝》“以慰我心”之“慰”字,《毛传》与马融皆训“安慰”之意,王肃则依从《韩诗》之今文说,释“慰”为“愠”。又如《小雅·雨无正》“沦胥以铺”之“铺”字,王肃依从《韩诗》释为“病”字。又如《陈风·东门之枌》“穀旦于差”之“差”字,王肃从《韩诗》释为“嗟”字。王肃诗学的主旨是申毛驳郑,争毛郑之得失而已①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诗序自古无异说,王肃、王基、孙毓、陈统争毛郑之得失而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 页。,这和他“善贾马而不好郑氏”的礼学阐释之思路和性质是一致的。洪湛侯在《诗经学史》中认为“王肃论诗多申毛驳郑”,如《卫风·考槃》《豳风·鸱鸮》《小雅·正月》之“申述毛旨”,《小雅·巧言》之“补充毛义”,《齐风·敝笱》《椒聊》之“述毛驳郑”等等。[10]211-213史应勇将可供完整比较的郑玄、王肃经注辑录出来,并附于《毛传》原文,共得二十八篇,其中能够显豁见出“申述毛义”之旨的有二十三篇之多。②参见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49—323 页。简博贤先生也认为王肃翼《传》有功:“郑氏笺《诗》,多以三家易毛。陈乔枞著《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考得一百二十二条,皆以三家今文改毛之古文也。子雍述毛,故凡《笺》之所改,必据毛与夺。毛氏古义篡乱于三家,而厘然可徵者,子雍翼《传》之功也。”[11]这些都说明,在魏晋古学复兴的潮流之中,王肃是以回返《毛传》之旧的态度进行诗学建构的,他对郑玄的诗学的驳难是出于维护古学纯粹性的考虑,很难被指认为片面地与郑学立异的意气之使然。
王肃申毛驳郑,不单是依从了《毛传》的名物训诂与章句大义,亦且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清通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
王肃申毛驳郑的诗学观,最突出的一点是不信谶纬神话。《诗经》中有两篇关于帝王身世的记载,即《大雅·生民》与《商颂·玄鸟》,都被今文经学附会成帝王感生的神话,独《毛传》并无一点神秘怪诞的气息。其释《生民》“履帝武敏歆”曰:“履,践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也。歆,飨。”[12]1056意思是说,高辛帝夫妇去祭祀,妻子姜嫄跟在他的后面,踩着丈夫的足迹,迈着敏疾的步子,去向上天祭飨。又如《毛传》释《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曰:“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12]1444这又是说,在燕子纷飞的初春时节,高辛帝夫妇去郊媒祈子,后来妻子简狄怀孕生下了契。《毛传》都是关于高辛帝夫妇祭祀祈子的史录,但是当郑玄多从三家易毛之后,两首诗歌都被附会成了帝王无父感生的神话。郑玄《笺》曰:“祀郊媒之时,则有大人神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覆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往,如有人道所感己者。于是遂有身,而肃戎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名之曰弃。”[12]1056又说:“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12]1444认为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周祖稷,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祖契。就如其说,则商周先祖都是天帝的子孙,是五行精气凝结所生,他们的文武功业完全是天命所赋予的。对此,王肃诗学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稷、契之兴,自积德累功于民事,不以大迹与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载籍之所以为妖,宗周之所以丧灭。”[12]1064王肃从马融之说,以为后稷为帝喾之遗腹子,“帝喾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帝喾崩后,十月而后稷生,盖遗腹也。虽为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为众所疑,不可申说。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弃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12]1064。在王肃看来,商周的先祖都是父母所生的人帝,他们是凭借“积德累功于民事”的努力而获得王号的,并非天帝的所与。
郑信谶纬而王退妖妄,这是郑王之争的一个结点,又集中地反映在对待“感生帝”说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上。“感生帝”说虽然高扬尊君抑臣的名教政治,却常常成为乱世诸侯受命称王的依据,又常常为乱世的实在情形所击碎。汉末三国时期,袁术应“谶语”称帝却迅速败亡,曹操“性不喜天命”而取得成功,从荆州学派走出的政治家多有崇尚刑名、志在革新者。③参见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 期。这是一个角智角力的时代,彼时理性主义思潮与天下一统的趋势相互鼓荡。王肃诗学的反谶纬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其次,郑玄以礼笺诗,泥于《诗序》,繁复而迂曲;王肃则揆以人情,遵循《毛传》的文本解说,清通而简易,能得诗人之本意。
欧阳修最反对郑玄诗学的“不近人情”,所著《诗本义》就提到了一个“郑不如王”的例子。如《邶风·击鼓》一篇,原是卫人怨怒国君州吁“用兵暴乱”之辞,其中有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郑玄笺云“军中士伍相誓约之言”,王肃则认为是“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欧阳修取用王义,在他看来,“卫人暂出从军,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岂宜相约偕老于军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说为得其义”[13]。郑玄笺诗要回到《毛诗序》的历史意义那里去,有意无意地漠视了诗中显豁的室家之情,将《击鼓》附会成从军士兵之间的互相约定之辞。
又如《卫风·考槃》:“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郑玄以为诗人独居山涧,“长自誓以不忘君之恶,志在穷处,故云言”,也是根据《毛诗序》“刺庄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的意思引申而来的。但是揆诸原文,其实见不出这层讥刺之义,王肃就认为:“穷处山涧之间,而能成其乐者,以大人宽博之德。故虽在山涧,独寐而觉,独言先王之道,长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执德弘,信道笃也。”[12]220在王肃看来,诗人抱道穷处,乐在其中,并非“刺庄公”的政治用心之使然。
再如《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裏。”《毛传》曰:“兴也。绿,间色;黄,正色。”《毛诗正义》云:“毛以间色之绿不当为衣,犹不正之妾不宜嬖宠。”郑笺改“绿”为“褖”,云:“褖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礼制也。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众妾亦以贵贱之等服之。鞠衣黄,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纱为里。今褖衣反以黄为里,非其礼制也,故以喻妾上僭。”《毛诗正义》引王注曰:“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显。”[12]118
以上三例解说被后人反复加以衡量,他们归纳出郑王之争所产生的文化根源,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郑玄信从《诗序》,王肃遵循《毛传》,实则《序》、《传》有别,由此两家的解释路线也就很不相同。这一点,清人洪承珙说得明白:“《序》是推本作诗者言外之意,诗词则止专美硕人,犹《简兮》亦止美硕人而《序》云‘刺不用贤也’。……《郑笺》泥于《序》下之说,以诗词之‘弗忘’即为刺君,故不能无语病,若《毛传》,就诗释诗,有美无刺。说者既以毛、郑同议,过矣。”[14]144《毛诗序》推明诗人的言外之意,定下了诗歌的美刺主旨,郑玄泥于《序》说,曲为辩护,故而脱离文本意的情况时常发生。如《邶风·击鼓》和《卫风·考槃》两篇,郑玄绕过言内之意,径直附会到《毛诗序》的历史意义那里去。再来看《毛传》与王肃的诗学阐释,他们的小学训诂与兴义阐发都是较为平实的,王肃所体认的“室家之情”与安贫乐道的心志都能够从诗歌文本上较为顺畅的见出来。洪承珙反对“毛郑同议”,认为两家的诗学阐释有“言内”与“言外”之区别,这是很有见地的。
其二,郑玄以礼笺诗,王肃揆以人情。关于郑玄以礼笺诗,后人称之为“按迹而议性情”。胡承珙《毛诗后笺》云:“案篇名《绿衣》,从毛为是。此与内司服绿误为褖者不同。郑学深于三《礼》,往往以礼笺诗,所谓按迹而议性情者以此。《毛传》‘绿,间色;黄,正色’,以喻嫡妾,甚为确当。”[14]76在他们看来,礼制为“迹”,诗言“情性”,郑玄笺诗的基本思路乃是要从诗中映证礼制的内容,甚至不惜改字以从礼。如《绿衣》一篇,郑玄根据周代的祭服制度改“绿”为“褖”,认为褖衣本来是以素为里的,诗中却以黄为里,故有“以喻妾上僭”之意。再来看《毛传》和王肃的解释,都认为绿为间色,黄为正色,以喻正妻与众妾之间的尊卑名分,诗中以间色之绿为衣,故有“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显”的意味。相比较而言,郑玄以礼笺诗,实则以诗证礼,从诗中破解礼制的密码,不如王肃诗学来得通情达理。又如《击鼓》一篇,欧阳修称王说为人情之言。在他看来,州吁发动这场不义之战,卫国已是民怨沸腾,安有“相约偕老于军中”之理,倒是王肃所谓“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是比较顺畅的。
四
王肃诗学在魏晋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孔晁、孙毓等人申王驳郑,王基、孙炎、马昭、陈统等人主郑攻王。这场著名的郑王之争没能从根本上撼动郑玄的经学地位,但是王肃诗学不信谶纬神话,能够结合文本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想,的确击中了郑玄诗学的某些弊病,在客观上也反映了汉晋之际渐趋清醒的人文理性,回应了诗经的自身阐释需求。然而,王肃诗学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如果我们注意到经学史上有一个辨析毛、郑之异同的学术传统的话,则王肃的申毛驳郑自当有发源之功。东晋之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虽然王学的地位急剧地衰落,但是它代表的这种回归《毛传》古义的倾向却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北史·儒林传》序称:“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15]洪湛侯认为,南北朝的经学史“就五经而言,‘诗则并主于毛公’,分歧最少。南朝传宗《毛传》,北朝兼用《毛传》、《郑笺》,此其微异而已。”[10]221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1][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M]//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
[3][晋]陈寿.三国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张涛.孔子家语注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527.
[6][唐]魏征.隋书:卷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9:637.
[7]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47.
[8]廖平.现代学术经典·廖平卷[M].刘梦溪,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2.
[9]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8-79.
[10]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简博贤.王肃诗学及其难郑大义[J].台北:孔孟学报,1979(38):131.
[1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宋]欧阳修.诗本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95.
[14][清]胡承珙.毛诗后笺[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2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