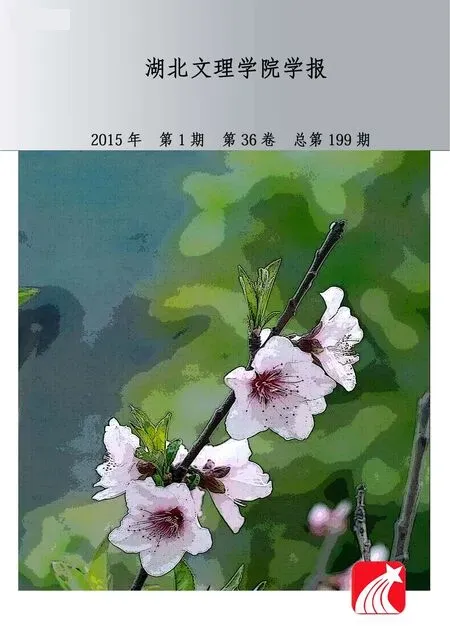《瓦尔登湖》徐迟译本和王家湘译本的对比研究
2015-03-27陈曌赟
陈曌赟
(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瓦尔登湖》徐迟译本和王家湘译本的对比研究
陈曌赟
(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从翻译策略和用词风格两方面对比分析《瓦尔登湖》的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徐迟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尽量保持了原作的句法结构;王家湘主要采取意译的方法,更加着眼于文字的流畅自然,必要时改变了句子的结构。在用词风格上,徐迟的译本含蓄典雅、隽永恬淡;王家湘的译本平实自然、轻松活泼。两个版本各有美妙之处,但纵观全局,笔者认为徐迟的译本更能传递出原作的神韵。
《瓦尔登湖》;徐迟;王家湘
《瓦尔登湖》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和散文家亨利·梭罗(1817—1862年)的代表作。1985年,此书名列《美国遗产》杂志评选出的“十本塑造美国人性格的书”之榜首。经过100多年的流传,该书现已成为美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出了150多个版本,被翻译成40几种语言,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之一。《瓦尔登湖》被引入中国以来,已经有数十位译者对其进行了翻译,每个译本也是各有千秋。[1]各个译本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或平实轻快,或清丽婉约,或书卷气浓郁甚至晦涩。
然而,一种译文的得失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西方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翻译的任务在于寻求出发语(原作者)和目的语(译作者)在信息转换上的最贴切的自然等值。”我国翻译界老前辈钱钟书先生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风味”无疑包含风格,他和奈达的主张是一致而又十分明确的:要求取得译文风格与原作风格的一致。倘若按福楼拜所说,“风格就是生命。这是思想的血液”,那么,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即保存了原作的生命;反之,无异于断其生命之源——血液。再现原作风格的重要性可见一斑。[2]
本文选取了徐迟和王家湘的两个译本,一方面对比了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和用词风格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对梭罗的《瓦尔登湖》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赏析。
一
例1:Sometimes,having had a surfeit of human society and gossip,and worn out all my village friends,I rambled still farther westward than Ihabitually dwell,into yetmore unfrequented parts of the town,“to fresh woods and pastures new,”……The fruits do not yield their true flavor to the purchaser of them,nor to him who raises them for themarket.[3]176
徐译:有时,对人类社会及其言谈扯淡,对所有村中的友人们又都厌倦了,我更向西而漫游,越过了惯常起居的那些地方,跑到这乡镇的更无人迹的区域,来到“新的森林和新的牧场”上……水果可是不肯把它的色、香、味给购买它的人去享受的,也不肯给予为了出卖它而栽培它的商人去享受的。[4]194
王译:有的时候,过多地与人相处和闲谈,厌倦了村里的所有朋友,我便向西信步走向比我惯常居住的地方更远的去处,来到镇里人更少去的地区,“去到新的森林和新的牧场”……果子并不把自己真正的滋味献给购买它们的人,也不给为了送到市场去卖而种植它们的人。[5]176
(一)从翻译策略上看
徐迟尽量保持了原作的句法,采用顺译的方式,把整个句子分割成若干个意义单位,逐一译出,再用增补、删减等手段把这些单位自然衔接,形成完整的意思。在衔接意义单位时,徐迟主要采取了将介词动词化的翻译策略,如将“than”译作“越过”,将“into”译作“跑到”,使得译文既忠实又流畅。王家湘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将“than”译作“比”,虽意义不错,但稍显呆板。
(二)从用词风格上看
无论是徐译的“友人们”、“更无人迹”,还是“栽培”、“出卖”,都透出浓浓的书卷气,而王译的“朋友”、“人更少去”、“种植”、“送到市场去卖”则更加平实简单。在徐迟自序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从徐迟的这段话,至少可以明白一件事——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书。王译的用词虽通俗易懂,但也许与原文艰深晦涩的气质并不相符。
二
例2:The scenery ofWalden is on a humble scale,and,though very beautiful,does notapproach to grandeur,nor can itmuch concern one who has not long frequented itor lived by shore;yet,this pond is so remarkable for its depth and purity as tomerita particular description.[3]178
徐译:瓦尔登的风景是卑微的,虽然很美,却并不是宏伟,不常去游玩的人,不住在它岸边的人未必能被它吸引住;但是这个湖以深邃和清澈著称,值得给予突出的描写。[4]197
王译:瓦尔登湖的景色不很起眼,虽然很美,却谈不上壮丽,不常来的人,或不在湖边居住的人也不会对它有多大的兴趣;虽然这个湖是这样深,这样纯净,值得加以特别的描写。[5]178-179
(一)从翻译策略上看
徐迟还是采取了一贯擅长的顺译,准确流畅;王家湘采取了意译,译文与原文有所出入。翻译策略的不同使得两个版本的译文有所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三处:
1.“humble”意思是“谦虚的、简陋的、卑微的”,徐迟明明觉得瓦尔登湖的风景很美,却用“卑微”来形容它的景色,既贴合“humble”的原意,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一种深沉而敏感的抒情;而王家湘将“humble”意译为“不很起眼”,虽平实,却少了几分细腻的情感。
2.“is so remarkable for”,徐迟将其直译为“以…著称”,简洁准确;而王家湘将其意译为“是这样的...,这样的…,”稍显模糊。
3.(1)从意义上看,“nor can itmuch concern”中“can”表可能性,“nor can it”的意思是“不太可能”,徐译的“未必能”恰与其相对应,都有推测之意;但是王译“不在湖边居住的人也不会对它有多大的兴趣”是一种肯定的判断,与原文的推测意味不相符。(2)从句式上看,徐迟所译的“未必能被它吸引住”虽是被动句,但是重点还是落在“它”上,与原文中“it”作主语意义一致;然而王译以“人”作主语,将重点落在“人”上,相比之下,徐译更加准确。
(二)从用词风格上来看
无论是徐译的“卑微”、“游玩”,还是“深邃”和“给予”,都比王译“不起眼”、“来”以及“深”和“加以”更有神韵。一部作品的“神韵”是弥漫、荡漾于作品中的一种气质,它是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是具体可感的。因为“神韵”客观存在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它附丽于文学作品的形体之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实现的。自从19世纪50年代发表以来,《瓦尔登湖》就以它清新、质朴甚至有些晦涩的独特神韵吸引了大批读者,而徐迟译文中浓郁的书卷气以及徐迟深厚的文字功底都较好地再现了原作的神韵。
三
例3:The real attractions of the Hollowell farm,tome,were:its complete retirement,being,about two miles from the village,half a mile from the nearest neighbor,and separated from the highway by abroad field;its bounding on the river,which the owner said protected by its fogs from frosts in the spring,though thatwas nothing tome;the gray color and ruinous state of the house and barn,and the dilapidated fences,which put such an interval betweenme and the last occupant;the hollow and lichen-covered apple trees,gnawed by rabbits,showingwhat kind of neighbors Ishould have;but above all,the recollection Ihad of it from my earliest voyages up the river,when the house was concealed behind a dense grove of red maples,through which Iheard the house-dog bark.[3]83
徐译:霍乐威尔田园的真正迷人之处,在我看是:它的遁隐之深,离开村子有两英里,离开最近的邻居有半英里,并且有一大片地把它和公路隔开了;它傍着河流,据它的主人说,由于这条河,而升起了雾,春天里就不会再下霜了,这却不在我心坎上;而且,它的田舍和棚屋带有灰暗而残败的神色,加上零落的篱笆,好似在我和先前的居民之间,隔开了多少岁月;还有那苹果树,树身已空,苔藓遍布,兔子咬过,可见得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邻舍;但主要的还是那一度回忆,我早年就曾经溯河而上,那时节,这些屋宇藏在密密的红色枫叶丛中,还记得我曾听到过一头家犬的吠声。[4]92-93
王译:霍洛韦尔农场的真正吸引人之处,对我来说,是它与世隔离的位置,离村子约有两英里,最近的邻居在半英里之外,而且有一大片田地将它和公路隔开;它紧傍一条河,农场主说,河上的雾使田地在春天不会受到霜冻,虽说我对此并不在意;灰色的房屋和谷仓极其残破的状态,还有失修的栅栏,全都拉大了我和上一个居住在此的人之间的间隔;被兔子啃食、树身空洞布满苔藓的苹果树显示出我会有什么样的邻居,尤其是我最早乘船沿河而上时对它的那段记忆,那时房屋掩映在浓密的枫树林中,我听到从树丛上传出来的家狗的吠声。[5]83
梭罗的这段文字将情、景、事结合起来,十分美妙。
(一)从翻译策略上看
徐迟仍然采取顺译的方法,而且保留了原文略显零碎的句法特点,采取骈散结合的句式使译文更加有韵律,如“还有那苹果树,树身已空,苔藓遍布,兔子咬过,”、“那时节”,字里行间弥漫着诗意。王家湘采取了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式。
笔者拟指出王译的三处不妥,以供探讨:
1.“about twomiles from the village,half amile from the nearest neighbor,”英文对仗工整,笔者认为译者不妨遵循英文的句式,将其译成对仗工整的中文,如徐迟的“离开村子有两英里,离开最近的邻居有半英里”。但是王家湘在译第一句时主语是“它”,第二句便将主语改成“最近的邻居”,笔者认为,这既改变了原文整齐的形式,又未在意义上增添新的色彩,实属不必。
2.在“the gray color and ruinous state of the house and barn”中,“the gray color”和“ruinous state”应是房屋和谷仓的共同状态,徐迟将其译为“它的田舍和棚屋带有灰暗而残败的神色”,而王家湘将其译为“灰色的房屋和谷仓极其残破的状态”,笔者认为徐迟的译文更加准确。同时,徐迟将“gray”译作“灰暗”而不是王译中的“灰色”则更传递出了房屋和谷仓残败的意象。
3.“interval”的意思是“(时间的)间隔”,徐迟译作“岁月”,不仅准确,字里行间还透露着民国文风,白话里亦有一丝古董气,译出了散文特有的恬静韵味。王家湘将其译为“…之间的间隔”,一方面表意欠准确,让读者不明白是拉大了空间的间隔还是时间的间隔,另一方面语言太过平实,缺少神韵。
(二)从用词风格上看
徐迟的“遁隐”,特别是“溯河而上”无不表现出他深厚的文字功底,而通观王译,虽与当今的语言习惯并无二致,但却少了梭罗在瓦尔登畔静谧当中的寂寞感。
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将两个译本进行深入对比。通观两个译本可以看出:
在翻译策略上,徐迟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尽量保持了原作的句法结构,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傅雷在谈到风格翻译时说过:“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傅雷主张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句法。[2]在徐迟的译本中,句子欧化的现象比较明显,比如说被动句的频繁使用、“一+量词”使用较多、连词的频繁使用以及含系动词的句子较多,然而,这种欧化现象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并且为译作平添了几分异国情调;而王家湘主要采取意译的方法,更着眼于文字的流畅自然,必要时改变了句子的结构。
从用词风格来看,徐迟的译本含蓄典雅、隽永恬淡,静谧中有些寂寞;王家湘的译本平实自然、轻松活泼,爽朗中有些俏皮。徐迟的用语比较古典,带有明显的个人特点和民国时期的时代印记;王家湘的用语更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然而,纵观全局,笔者认为徐迟的译本更胜一筹,因为他对原作整体风格的把握更加准确。不否认徐译当中有个别错译和漏译,对某些句子的把握,王译可能更准确。但是《瓦尔登湖》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神韵,这种寂寞、恬淡、艰深的神韵。只有准确把握了这种神韵,译文才能更好地传递出原作的精髓,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徐迟的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1]戴丹.从翻译美学角度比较《瓦尔登湖》两个中文译本的意象传递[J].读与写杂志,2011(2):40-42.
[2]许钧.关于风格再现——傅雷先生译文风格得失谈[J].南外学报,1986(2):57-61.
[3]Thoreau H D.Walden[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4]梭罗H D.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梭罗H D.瓦尔登湖[M].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Com parative Study of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Walden by Xu Chiand W ang Jiaxiang
CHEN Zhao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 441053,China)
This paper compares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Walden from these two aspect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language styles.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Xu Chimainly adopt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tries to keep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originalwork in the selected sections in this paper while Wang Jiaxiangmainly adopts free translation and change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originalwork if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smooth and natural effect.On language styles,Xu Chi’s version is subtle,elegant,tranquil and thought-provoking while Wang Jiaxiang’s version is plain,natural,light and pleasing.Each version has its ownmerits.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however,the author thinks Xu Chi conveys the charm of the original work better.
Walden;Xu Chi;Wang Jiaxiang
H059
A
:2095-4476(2015)01-0055-04
(责任编辑:刘应竹)
2014-11-24;
2015-01-08
陈曌赟(1985—),女,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