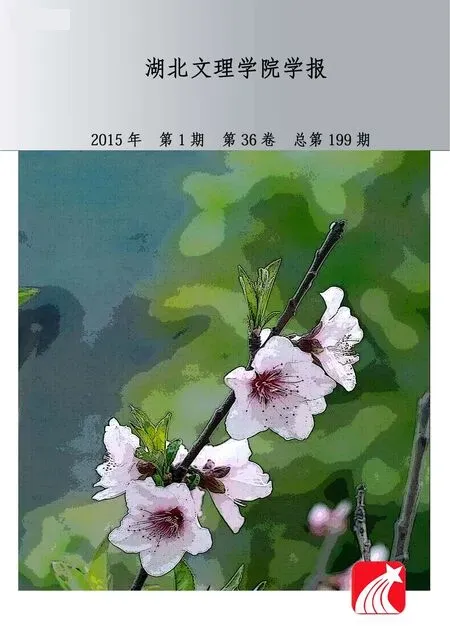论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的分类思想
2015-03-27邓肖潇龚天平
邓肖潇,龚天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的分类思想
邓肖潇,龚天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详细地论述了正义概念的内涵及其种类。在总体上,他把正义分为一般正义和具体正义。一般正义是相对于公民与整个城邦和社会的关系而言的,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合乎法律;具体正义是相对于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它要求在公民之间实现公平。他把具体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涉及的是钱物、财富、荣誉,还包括权力等可分配之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强调比例平等;矫正正义旨在维护人们经济交易中的公平和根据法律纠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同时,他还论述了回报正义、政治正义和家室正义。他对正义的分类是迄今为止关于正义种类的最为透彻的解剖,即便在当今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正义主题的讨论,尤其是他关于正义种类的划分,更成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无法绕过的永恒话题。
亚里士多德;正义种类;一般正义;具体正义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正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第一次从伦理学上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正义问题。在继承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古希腊思想家的正义思想的基础上,他深入地思考了何为正义、正义如何可能等社会的正义伦理问题,其目的在于构造一个以正义、平等为原则的社会,从而挽救当时正在日益趋向衰落的城邦。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详细地论述了正义概念的内涵及其种类,是迄今为止最为透彻的解剖,即便在当今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正义主题的讨论,尤其是他关于正义种类的划分,更成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无法绕过的永恒话题。科罗特(Richard Kraut)指出:“在政治哲学中,没有比正义更重要的美德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把正义作为政治活动的美德是十分恰当的,且给予了全面论述。”[1]本文试图论述他对正义的分类思想,从而彰显其正义思想的内在意蕴和时代价值。
一、一般正义
考虑到正义范畴之复杂性和正义与不正义的多种含义,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正义做不同类型的区分。他把正义分为两种:一般正义和具体正义。在考察正义问题时,他首先考察的是正义的性质与范围,而这一问题表明的是一般正义。按照伦理学的研究方式,只有把某个研究对象的一般意义搞清楚,才有可能把这个对象的特殊意义搞清楚,因为一般不过是对特殊的归纳和抽象。亚氏的一般正义是相对于公民与整个城邦和社会的关系而言的,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合乎法律,在他看来,守法就是正义的,而违法就是不正义的。一般正义实质上是个体正义,而个体正义是个体的德性或品质的表现,因而他又通过论述个体的德性来论述一般正义。在他看来,只有个体具有正义的德性,才能在城邦中是有德性的、正义的。所以,他首先继承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把正义理解为一种德性这一思想遗产,同样把正义看作一种品性、品质,一种完满的德性。
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地说:关于正义与不正义,“我们先要弄清楚它们是关于什么的……是何种适度的品质,以及它是哪两种极端之间的适度”[2]126。在这里,他首先就把正义界定为人的一种品质,而且是合中道的品质。既然正义是一种品质或德性,那么在研究它时就应该采取与研究伦理德性一样的研究方法。
在界定正义的含义时,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人在说正义时,“都是指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而对于正义的反面即不正义,他说“也是指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做事不公正,并愿意做不公正的事”[2]127。那么,以什么东西为标准来判断正义与不正义呢?亚里士多德把这一标准确定为法律和平等。他说:“我们把违法的人和贪得的、不平等的人,称为不公正的。所以显然,我们是把守法的、公平的人称为公正的。所以,公正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2]128-129这就是说,正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是否守法,守法即为正义;二是人是否讲究平等,讲究平等即为正义。为什么要以法律为标准来判断正义与不正义?因为“所有法律规定都是促进所有的人,或那些出身高贵、由于有德性而最能治理的人,或那些在其他某个方面最有能力的人的共同利益的。所以,我们在其中之一种意义上,把那些倾向于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看作是公正的。”[2]129但是,法律还要求一个人做出别的行为,如勇敢的行为、节制的行为、温和的行为,而在其他的德性与恶方面,法律还要求一些行为,禁止一些行为。因此,守法作为一种正义,是一种总体的德性,“是对于一个人的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2]13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正义常常被看作德性之首,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德性的总括,正义是最为完全的,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正因为它是完全的,所以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既能对自己运用其德性,也能对邻人运用其德性。即是说,正义标志着一个具有这种德性的人既能公正待己,也能公正待人。特别是在公正待人的问题上,一个人更能显示自己的正义德性。因为正义“所促进的是另一个人的利益,不论那个人是一个治理者还是一个合伙者”,“对他人的行为有德性是很难的”[2]130-131。那么,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把正义界定为一种总体的德性和品质呢?
我们知道,“如何成功地过幸福而高尚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非常关心的问题,而这也注定了德性的问题也是他要关注的问题。“德性”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本意是指某一事物的特长、功能和用处。人们一般把德性与人的本性进行类比。就人的本性来看,自然特性是其中之一种,自然特性也就是一个人所具有的自然德性。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功能是其自然特性,然而它并不是仅仅人类才具有,其它动、植物同样也具有,因此德性也就并非专指人之特性,而是包括存在于世界的所有生命有机体都具有的。但不同的是,世界上一切生命有机体中,只有人才具有理性功能,具备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相适应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或社会特性不同于自然特性,它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德性。照德性的含义来看,一个人的德性与这个人特有的功能密切相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人的德性是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而不是这个人的某个单一的具体器官的德性或功能。勿庸置疑,他是在运用动物学方法提出对德性的理解。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把德性与知识直接等同,实际上取消了德性,即使承认德性的存在,但这种德性的根源只能从灵魂的理性部分去寻求,这实际上又局限了德性而使其枯竭。苏氏的这一缺陷被他的学生柏拉图消除了,柏氏在灵魂的各个部分寻求德性,认为德性分有灵魂之各个部分,但这实际上又把德性和善理念混同了。亚里士多德则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说:“德性属于灵魂”[3]358,即是说,德性是灵魂的德性,而非肉体的德性。随后,亚里士多德又在具体解剖、分析灵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理智德性到底是什么。他说:“德性是那些有某种用途或效用的事物最好的排列、品质或能力。”[3]355如果一个人具有了这种品质,那么他就相应地具有稳定的性情,也就相应地会产生好的行为。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把德性与品质钩连起来,用品质来解释德性,那么品质又是指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品质是人表现出来的一种较为稳定的行为倾向,而正义同样也是一种品质,它作为一种完满的品质是确定不移的。他说,正义的人行为必然公正,而且他会有明确的意愿去做公正的事情,这就表明,正义的人必然具有健全的理智和情感,即健全的理性和情感判断能力,否则正义的人就无法进行正确而合理的观察和判断。因此,正义作为一种完满的德性而呈现,是城邦公民开展伦理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公民所具有的这种正义品质或德性对于他们的行为具有着重要作用,这可以促使他们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地做出合乎正义的行为,而且能够保证他们的这种行为有始有终,能够言行一致,而他们的幸福也可以从这种做正义之事的行为中得到满足的。所以,正义的人是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人是幸福的人。在此,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德性和幸福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具体正义
在论述一般正义后,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具体正义。具体正义是相对于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他看来,具体正义要求在公民之间实现公平。他把具体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分配正义是指“表现于荣誉、钱物或其他可析分的共同财富的分配上(这些东西一个人可能分到同等的或不同等的一份)的公正”[2]134。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正义强调因人而异的分配,即相同的人应得到相同的待遇,不同的人应得到不同的待遇;平等的人应得到平等的待遇,不平等的人应得到不平等的待遇,即“得所当得、失所当失”。分配正义的实质是强调“比例平等”,“合比例的才是适度的,而公正就是合比例的”[2]136,它根据社会不同成员间的价值来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他们之间对社会财富、荣誉、安全和其它物品进行分配。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分配的过程中要以配得为基础,“配得”是指一个具体的人因他的优点和长处所配享的东西,即使他们所要的是不同的东西。分配正义要根据所值进行分配,它强调不同的人分得不同的物品,平等的人享有平等的对待,不平等的人就应该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不公正中包含着不平等,公正中包含着平等。”[2]134因而平等的必然是正义的。所有过多的或不及的行为中存在一个适度,那些不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事虽然是不平等的,但在二者中也存在一个适度,即平等。那么,正义的人是不是要在交往中对每个交往的主体一视同仁,无论他是好人还是恶人?当然不是,因这会被看作是阿谀奉承者所做的谦卑之事,真正的正义是要根据价值来对待,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正义的和有德性之人的行为。
那么,如果分配过程中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争吵时我们怎么办呢?亚里士多德提出两条对策:“第一,应该依多数人或多数更有财产的人的意见而定。第二,假如两者数额相等,这种僵持局面——可以通过抽签或其他类似的办法来解决。”[4]89平等也有两种:一种是与数量或是数额有关;一种则是与价值有关。前者是指数量的大小或多少,后者则是一种与比例有关的平等。然而,平等与不平等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个同等的人在财富、地位、贡献上的均等或不等,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他们所占有或分得的份额的均等或不等,而是指两个人在能力、贡献上的比例与他们所得或占有的份额的比例的均等或不等,是这两种比例上的关系。正义的必然是平等且适度的。作为适度来讲,正义涉及到过多与过少两个极端;作为平等而言,它与两份相等的事物有关;作为正义本身,它关系到具体的、特定的个人。所以正义包含四个要素,即与正义相关的人是两个,与正义相关的事物是两份。而这两个人与两份事物之间也要均等,因为两个人与两份事物之间的比例要相等。假设两个人不平等,他们所分享的份额就肯定会有差等之分,当然,他们就不会分享到平等的份额。对于同等的人来说,正义和德性是属于共同拥有的部分,这就是平等和同等。如果对平等的人给予不平等的待遇,对于不平等的人给予同等的待遇,这就如平等的人分得或占有不平等的份额,而不平等的人分得或占有平等的份额,就会发生争吵。而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导致的:一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平民制主张一切公民都是自由人,人人平等;寡头制的根基就是不平等,人们在财富和荣誉方面的不平等导致了一切方面的不平等。二是大家持有的观念不同。在一个方面比如勇气上与人相等的人便认为在其它方面也与所有人相等。三是地位与身份的不同。奴隶与主人之间,奴隶就是主人身体的一部分,奴隶就不应该反对主人,否则就是一种极大的不正义。“公正是灵魂的德性,在于它按照价值来对每人分派。”[3]459即公正的特点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价值来对他或她进行分派,以沿袭的习惯和法律、成文的律令为标准,在重大问题上判断对错、发现真理,并使它们保持一致[3]461。根据所值原则来分配是大家所乐意的,也只有按照各自的价值来分配才是正义的。即是说,分配正义主要体现在对公共物品或财物要按照各自提供物品的比例和所作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正义以平等为桥梁或中介。当然,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属性,根据他们个人的情况来分配就有两个不同的标准——适合和贡献。亚里士多德举例说:“长笛应该给予谁,当然应该给予会吹的人,这就不是根据身高和出身好,而是根据贡献——熟练的演奏表现。这里就有适合标准,这不是不平等。”[4]205
分配正义还要考虑不同社会制度和政体。民主制注重自由身份,寡头制更看重财富或出身高贵,贵族制则青睐德性。所以分配正义在于成比例,同时根据所值、适合以及贡献来分配。不顾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能力大小和技术熟练程度来分配是极大的不正义,违背了应得和价值的要求,是对那些配得的人的一种打击。
矫正正义是指“在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2]134,旨在维护人们经济交易中的公平和根据法律纠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其价值诉求在于人与人的平等。它以亚氏的理想政体为基础,他在《政治学》中把政治团体的组合方式归结为三种,并认为政治团体无论采取哪种组合方式都必定属于其中的一种,第一种是“所有的公民必须把一切完全归公”的组合方式,第二种是“完全不归公”的组合方式,第三种是“一部分归公,一部分仍旧私有”的组合方式[5]43-44。矫正正义的宗旨就是矫正私人交易中的错误,在于给交易中的双方平等的待遇,维护交往双方的平等地位,或者是通过法律重新恢复先前交往中被破坏了的平等。“不论是好人骗了坏人还是坏人骗了好人,其行为并无不同。法律只考虑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它把双方看成是平等的。它只问是否其中一方做了不公正的事,另一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是否一方做了伤害的行为,另一方受到了伤害。既然这种不公正本身就是不平等,法官就要努力恢复平等。”[2]137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交易中发生争执和抱怨的时候要去找法官的原因。去找法官也就是去找一个衡量过度与不及、多得与少得的中间人,法官就是公正的体现和正义的代言人。找到了法官就找到了多得与不得的中间,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公正也就是某种中间,因为法官就是一个中间人。法官要的就是平等。”[2]138交往中的两个人处在一种完全平等的地位,交易才能公平地进行。
矫正正义是在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尊严和人格的基础上依循算术的比例。平等就是过多与不及的一种恰乎其中,人们认为这就是正义,就是均等的两份,平分的两份。就像我们不应该在较少的部分中再去获取更多,而是应该在较多的部分中取更多以补给较少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应当在较少的一分上加上它不足于中间量的部分,从较多的一份中拿掉它多出中间量的部分”[2]139。如果在交易中得到的多于自己原有的部分是得,得到的少于自己最初的那部分是失,那么不多也不少,还是保持自己原有的那份就是应得,在数量上没有得失。正义就是关于得与失的中间,既没有得也没有失,是在违反意愿的交易中得与失之间的一种适合。矫正正义就是纠正人们之间相互损害的行为,从而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依循算术的比例原则,更加侧重所受损失的多少,不强调人在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把矫正正义进一步做了细分。他说:“矫正的公正又有两种,相应于两类私人交易: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2]134第一,对出于自愿的私人交易的矫正正义。这是指“出于意愿的交易如买与卖、放贷、抵押、信贷、寄存、出租,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出于意愿的,是因为它们在开始时双方是自愿的”[2]134。而这种矫正正义就是指对这些出于自愿的交易中出现不好的结果的矫正或纠正而体现出的正义。在出于自愿的交易中,自愿的矫正正义就是行为者双方达成协约后,对这种获利行为不加以干预。在交易活动中,活动双方依据事先商定的协议,并自愿遵守协议来从事交易活动。第二,对违背或不是出自意愿的私人交易的矫正正义。这是指那些“秘密的”和“暴力的”私人交易,亚里士多德做了列举,属于前一类的如“偷窃、通奸、下毒、拉皮条、引诱奴隶离开主人、暗杀、作伪证”等,属于后一类的如“袭击、关押、杀戮、抢劫、致人伤残、辱骂、侮辱”等[2]134。而这种矫正正义就是指对这些违背意愿的交易中出现不好的结果的矫正或纠正而体现出的正义。
三、回报正义
由于认识到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都不同,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回报正义。他说:“不折不扣的回报既和分配的公正不是一回事,也和矫正的公正不是一回事”[2]141,其原因在于“许多时候回报都与公正有区别。例如,如果一位官员打了人,就不该反过来打他。而如果一个人打了一个官员,就不仅该反过来打他,而且该惩罚他。”[2]141回报正义是指商业服务交易中出于意愿的、基于比例而不是基于平等的回报的正义[2]141-142。就此看来,回报正义实际上也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具体正义中的一种正义类型。但是,它与具体正义中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又是相区别的。至于说到亚氏是按什么标准区分出这种正义的,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并没有说明,这也反映了他在对正义进行分类时的矛盾。
亚里士多德认为,回报正义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比如城邦即是由成比例的服务回报联系起来的。这等于是明确指出了回报正义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即它是社会关系得以确立的桥梁,是社会得以建立的中介。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期待以恶报恶、以善报善,这种回报正义是通过交易实现的。“正是交易才把人们联系到一起。”[2]142
回报正义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具有许多环节。“成比例的回报是由交叉关系构成的。”[2]142亚里士多德强调,回报正义中的“比例”实际上就是交易的东西必须是等值的,其正义性是由其价值在比例上相等决定的。所以,交易虽然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不平等的人之间,但是他们所交易的东西必须是可以以某种方式比较的,必须通过交易达到平等。正是如此,人们发明了货帀这种中介物。但货帀是适应人们交易的方便而产生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交易呢?亚里士多德非常正确地指出:“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由某一种东西来衡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需要。正是需要把人们联系到了一起。因为,如果人们不再有需要,或者他们的需要不再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交易,或不会有这种交易。而货帀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了需要的代表。”[2]144从这里,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言说的回报正义实际上是对古希腊时期商品交换现象的描述和理论总结,同时也与他提出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相呼应,天才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本性,深刻地猜测到了需要构成人的本性。
在明确货帀对于交易的重要作用后,亚里士多德说:“货帀是使得所有物品可以衡量和可以平等化的唯一尺度。因为,若没有交易就没有社会,没有平等就没有交易,而没有衡量的尺度也就没有平等。尽管对千差万别的事物不可能衡量,对它们却完全可以借助于需要来衡量。”[2]145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交易对于社会建构的基础性地位,只有交易才提供了社会形成的可能性,而评判社会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则就是平等。只有在平等价值指导下构成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而平等不过是比例适度,每一个人的付出与获得对等、比例相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公正是一种适度……一个人要是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进行分配时不使自己得的过多,使别人得的过少,或不使自己受损害过小,使别人受损害过大,而是达到比例的平等;要是在两个其他人的分配上也是这样做,他表现出的品质也就是公正。”[2]146从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正义上的基本观念,即得所当得、失所当失。所以,无论是在分配正义、交易正义和矫正正义上,还是回报正义上,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正义观都是一以贯之的。
四、政治正义
亚里士多德根据作用范围的不同,把正义分为政治正义和家室正义,其中政治正义是指适用于生活在法律之下的、有平等的机会去治理或受治理的公民之间的正义。他说:政治正义是“自足地共同生活、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数量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公正”[2]147,而不自足的以及比例上、数量上都不平等的人们之间不存在政治正义,只存在某种类比意义上的正义。因为正义只存在于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间,只有建立起了法律关系社会共同体才有正义与不正义可言,法律才是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标准。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分为基础的。所以,他的政治正义又可直接指称为法律正义。
前文已述,正义就意味着得所当得、失所当失,相反,不正义就意味着得所不当得、失所不当失。“不公正的存在又意味着不公正的行为的存在,尽管不公正的行为并不总是意味着不公正。不公正的行为就在于在好处上使自己得的过多,在坏处上使自己得的过少。”[2]148由此,亚里士多德把政治正义延伸到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治理问题上,他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不应该由一个人来治理,而应该由法律即政治正义来治理。如果由一个人来治理,那么这个人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治理,最后他会成为一个僭主。然而,政治共同体的治理者必须是正义的护卫者。既然如此,他也必须是平等的护卫者。如果治理者被认为是正义的,他就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因为他只取相称于其所配的那一份,是在为他人的利益而工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正义又意味为着别人的善。所以,“对治理者必须以荣誉和尊严来回报”。否则,如果治理者不按政治正义即法律来治理,在物质利益追求上不满足于此,就会成为一个僭主。
他还以根据的不同,把政治正义分为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自然正义是指以自然为根据的正义,它是一种永恒的、普遍的正义。他说:“自然的公正对任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认。”[2]149约定正义是指以法律为根据的正义,它与自然正义相反,是一种具体的、可变的、相对的正义。他说:“约定的公正都是为具体的事情。”[2]149针对有些人认为所有的正义都是约定的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对是对的,比如在神的世界这个说法也许就完全不成立。神的世界是不变的、永恒的,其正义是完全的自然正义,而具体的现实世界,所有的正义都是可变的,当然其中有自然正义,但是这个世界占绝对优势的还是约定正义。因为约定正义是由法律和约定而来,而法律和约定虽然具有制定和实施的一致性及对所有人的要求的一视同仁性,但它们是可变的、人为的。“人为的而非出于自然的公正也不是到处都相同的。”[2]150正义规则与具体的正义行为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正义规则因其普遍性而是一,正义行为因其特殊性而是多。
五、家室正义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家室正义是与政治正义相对应的一种正义,它主要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亚里士多德对它着墨不多,只是为了清晰地阐明政治正义而顺便提出。他说:“父亲和子女间的公正不是政治的公正,而只是与它类似。”[2]148原因在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东西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正义。他自己的东西,如一份动产,就好比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尚未成年而独立的孩子也是如此,然而,没有人会愿意伤害他自己本人,因此,一个人对于他自己不可能不正义。所以,在家庭里只有类似于政治正义的家室正义。因为政治正义是根据法律来调节相互关系的正义,而正义虽然“在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中比在父亲同子女或主人同奴隶的关系表现得充分些。这种公正是家室的公正。”[2]149对于政治正义和家室正义的区分,廖申白教授在注释中做了如下说明:“政治的公正,即进行着出于意愿的或违反意愿的交易、分享着城邦共同财富的公民间的公正,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正;家室的公正,即丈夫与妻子间的公正,是半意义上或准意义上的政治的公正;父子间的以及主奴间的主人的公正只是在类比意义上才是政治的公正,因为它其实不是政治的。”[2]149这种观点是符合亚氏本意的。
[1]KRAUT RICHARD.Aristotl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On Aristotle’s Theory about Categories of Justice
DENG Xiaoxiao,GONG Tian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ristotle carefully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s and categories of justice in The Nicomachean Ethics.In fact,Aristotle divided justice into two kinds:general justice and specific justice.The general justice asks for citizen’s legal statements and actions.The specific justice asks for fairness between the individuals.The latterwas divided into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corrective justice.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involvesmoney and goods,fortune,reputation and rights,emphasizing the proportional equality ofmembers of society.The corrective justice aims to safeguard the fairnes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rectify themutual hurtbetween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law,stressing the equality of people.At the same time,he discussed the reciprocal justice,political justice and domestic justice as well.His classifications of justice is the most lucid analysis so far.Even if in the contemporary,his ideas also have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iscuss of the theme of justice.Especially,his division of justice has become the everlasting topic between themor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ristotle;Categories of justice;General justice;Specific justice
B82
:A
:2095-4476(2015)01-0027-06
(责任编辑:陈道斌)
2014-12-18
邓肖潇(1989—),女,湖北公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研究生;
龚天平(1968—),男,湖北公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原理,经济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