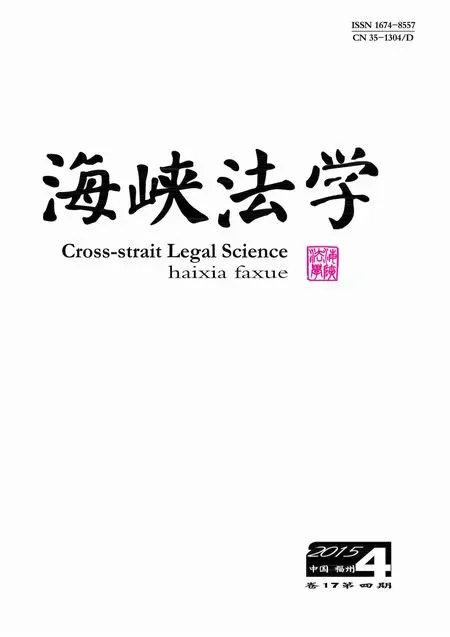从决定论到互动论:罪刑关系模式的反思与调整
2015-03-27郝艳兵
郝艳兵
从决定论到互动论:罪刑关系模式的反思与调整
郝艳兵
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坚持定罪决定量刑、罪先刑后的罪刑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单向度地考察罪与刑的关系,过于简单化、直观化,未能科学把握罪刑关系的实质,导致在刑事司法上出现了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片面追求定性的准确性,而忽略了罪刑均衡原则的贯彻,导致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量刑不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必要对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予以反思和调整,站在罪刑一体化的立场重新审视罪刑关系,改变罪与刑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罪刑互动的罪刑关系新模式,通过罪对刑的正向制约和刑对罪的反向制衡实现罪刑法定在制约下的罪刑均衡目标。
罪刑关系;决定论;互动论;罪刑法定;罪刑均衡
一、导论:疑难案件所引发的罪刑关系反向思考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罪刑关系应当坚持定罪决定量刑的范式,先定罪后量刑,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基础,量刑是定罪的延伸和结果,罪刑关系的这种正向制约关系可以说在传统刑法教义学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量刑反制定罪”的反向制约关系则被认为是只存在于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等特殊的罪数形态下才有存在的意义。①郑延谱:《量刑反制定罪否定论》,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第130页。笔者将这种传统观点概括为罪刑关系决定论。理论上对罪刑关系的反向思考较之罪刑关系决定论的通说立场无疑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仅有的一些微弱的声音也很快湮没无闻,不足以引发学界的足够关注。2002年阮齐林教授在《绑架罪的法定刑对绑架罪认定的制约》一文中曾提出:“解释法律的终极目的在于使案件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而不在于使犯罪的要件符合我们的理解,也不在于使它以什么样的罪名受到处理。如果从法律原则上讲,就是使罪行受到的处罚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②阮齐林:《绑架罪的法定刑对绑架罪认定的制约》,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35页。进而,他主张对绑架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与绑架罪的法定刑相称。该文虽未明确提出“量刑反制定罪”这一命题,但其中蕴含的思想不言自明。冯亚东教授则在《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一文中提出有必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确认“以刑定罪”的刑事规律,具体到司法层面,“对大量处于罪与非罪临界点上性质两可的案件,‘以刑定罪’的规律至少无意识地真实影响着司法者对行为性质的定夺。”①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28页。冯亚东教授虽然明确提出了在司法上应当肯定“以刑定罪”的逆向思维方法,但其更多地是从罪与非罪的意义上予以展开的。裘霞、李佑喜作为长期从事司法实务的检察官则明确将以刑制罪作为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予以提出:“以刑制罪,作为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旨在通过对法定刑的比较分析来加深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以正确认定犯罪行为的性质。”②裘霞、李佑喜:《以刑制罪: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44页。但这几篇文章在当时都未能引起学界对罪刑关系反向思考的足够关注。
以许霆案为肇始,“量刑反制定罪”理论开始成为刑法学者的“宠儿”,赞成或者反对这一理论的文章大量涌现出来。许霆案中,一审法官从严格规则主义的裁判立场出发,得出了符合法律规定却不合乎公众判意的结论。从形式正义的层面上来看,一审法官的判决是依照刑法教义学演绎得出的结论,因而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但从实质正义的层面上看,由于对许霆的量刑严重偏离了社会公众对实质正义的体认,因而的确可以说判得不合情理。③许霆案的发生再度掀起了学界对“以刑制罪”这一定罪逻辑的回归。尽管绝大多数学者在绝大多数场合更为强调“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但在依照刑法教义学得出的结论在结果上有疑问时,又偏向了“实质正义”和“结果正义”。围绕着许霆案定性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定罪逻辑的运用。部分学者基于结果导向的思路将许霆的行为界定为侵占罪或者信用卡诈骗罪等法定刑比盗窃罪低的犯罪。参见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第457~479页;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60页。许霆案的产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重定罪轻量刑”、“定罪决定量刑”的司法逻辑演绎而生的必然结果。从定性的角度观之,法院判处许霆盗窃罪得到了大多数刑法学者的肯认,从量刑的角度看,无论是学者的专业判断还是民众的常识判断,一边倒地认为一审对许霆的量刑过重。在围绕着许霆案所引发的诸多讨论中,高艳东教授独辟蹊径,力倡“量刑反制定罪”,他认为:“刑事责任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刑法结论,如果根据犯罪构成判断出的罪名会使量刑明显失衡,就应适度变换罪名以实现量刑公正,让罪名为公正的刑事责任让路,不能把准确判断罪名作为优于公正量刑的司法重心。”④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第459页。梁根林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刑从(已然的)罪生、刑须制(未然的)罪的罪刑正向制约关系并非是罪刑关系的全部与排他的内涵,于某些疑难案件中亦存在着逆向地立足于量刑的妥当性考虑而在教义学允许的多种可能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应的妥当的法条与构成要件予以解释与适用,从而形成量刑反制定罪的逆向路径。⑤梁根林:《许霆案的规范与法理分析》 编者按,《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5页;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59~160页。“量刑反制定罪”理论对罪刑关系所进行的反向思考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对此最有力的质疑在于量刑反制定罪理论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刑事法中的铁律,为了追求量刑公正而突破罪名及对应的构成要件的限制更是对刑法教义学的背弃。⑥参见郑延谱:《量刑反制定罪否定论》,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第135页;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第40页;张明楷:《许霆案的刑法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50页。有学者认为,严格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量刑不公,但为了追求量刑公正,就擅自改变罪刑关系配置的基本逻辑的做法,却又意味着向后退了一大步,赋予法官改变罪名的权力,法官就会把自己的意志变成“法源”,从而可能打着量刑公正的旗帜,葬送来之不易的刑事法治。⑦参见姜涛:《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载《法学家》2012年第4期,第80页。法理学者朱苏力教授也对量刑反制定罪的理论进路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种置刑法教义学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于不顾的做法,等于退回到了以社会危害性来定罪量刑的老路上,同时放弃了规则约束容易导致司法为个人直觉或民粹正义所左右。⑧参见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100~101页。
量刑反制定罪这种反向思考罪刑关系以求得个案量刑公正的理论进路尽管在理论上招致了种种非议,但却是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自觉或者不自觉采取的定罪司法逻辑。在孙伟铭案、张明宝案、长安街英菲尼迪车祸案以及刘襄等生产、销售瘦肉精案等司法个案中都能够看到“量刑反制定罪”的司法逻辑的运用,而这种司法逻辑的运用并非一以贯之的,而是充分回应刑事政策和民众判意的产物。对此,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提出了批评:“审判实践中通过‘以刑制罪’来实现公众舆论要求严惩犯罪的诉求,是功利主义的裁判观,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①徐光华:《公众舆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适用》,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第109页。实践中对量刑反制定罪的青睐和理论上对此的激烈批判应当理性地去看待,既不能一味指责司法实践枉顾刑法教义学,也不能对理论上的批判置若罔闻。必须看到,量刑反制定罪在当下中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疑难案件中,严格规则裁量主义所追求的一般正义、形式正义和个案中所蕴藏的个别正义、实质正义发生背离的现象并不罕见。在个案中当依法定罪量刑明显违背罪刑均衡的刑法基本原则时,司法者如果无视这种量刑不公必然会导致刑法的适用丧失公信力,因而必须转而寻求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个案量刑公正的现实路径。对罪刑关系进行反向思考无疑契合了这种需要,同时也比较符合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因为在人类的经验世界里,感知正义是通过刑罚来实现的,只有罚当其罪、罪刑相称,人们才会觉得对犯罪人的判决是正义的。刑法理论必须对罪刑关系反向思考路径的正当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辩驳,同时为司法实践疑难案件所引发的罪刑失衡问题提供教义学框架内的解决方案。
二、罪刑关系决定论的困境:立法的有限性所引发的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背离
罪刑关系决定论认为,定罪决定量刑,定罪是量刑的起点和前提,量刑则是定罪的目的和归宿,只有定罪准确,才能公正合理地量刑,正确的定罪是合理量刑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障。②参见胡学相著:《量刑的基本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罪决定刑,罪先刑后就成为理论上的公理和司法实践的当然选择。然而,罪刑关系决定论单向度地考量罪与刑的关系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直观化的思考结论,并未能科学把握罪刑关系的实质,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导致刑事立法上出现罪刑不均衡的立法例,如《刑法》第397条规定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适用同样的法定刑,而二者一个为故意犯罪,一个为过失犯罪,再如第398条对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适用同样的法定刑;在刑事司法上则出现了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片面追求定性的准确性,而忽略了罪刑均衡原则的贯彻,导致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量刑不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进行理性的反思。
(一)罪刑关系决定论的先天不足
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司法活动的两大基本任务,定罪是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事实和法律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司法审判活动,量刑则是在定罪的基础上根据犯罪事实和情节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刑罚的种类和刑度的司法审判活动。从定罪和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基本环节来看,定罪在先,量刑在后是应当坚持的司法裁量程序。从应然的意义上讲,定罪准确确实是量刑正当的前提和基础,坚持定罪在先,量刑在后的顺序并无不当。然而,这只是理想状态下演绎出的结论,在个案中依照成文刑法典,根据司法的三段论演绎推理得出定罪结论,在定罪结论的基础上根据犯罪事实和情节得出的量刑结论却偶尔会与裁判者或者社会公众所感知的罪的轻重难以匹配,出现罪刑失衡的感觉,进而会对刑罚的公正性产生怀疑。究其原因,乃在于法律规则所代表的一般正义和形式正义在一些特殊的个案中与个案所蕴藏的个别正义和实质正义产生了背离,这种背离导致依法量刑却无法实现量刑公正。而量刑公正却是刑法的生命线,如果适用刑法得出的刑罚后果明显与公众对罪刑轻重的认识相违背,那么刑法将失去公众认同感。因而,量刑的公正性应当成为适用刑法的目的和归宿。正如学者所言:“刑罚的正当理由植根于由报应所体现的人类道德情感和社会公正理念,刑罚以蕴含在报应之中的公正理念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公正是刑罚的唯一价值诉求。”①董淑君著:《刑罚的要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在罪与刑的关系上,必须认识到罪只是刑的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定罪与量刑共同服务于刑罚的公正性这一终极目的。罪刑关系决定论并未从根源上把握罪刑关系的本质,形式化地认为罪决定刑无疑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因而存在理论的先天不足,无法有效回应现实需要。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看到了“刑”之于“罪”的重要性。早在西周时期,立法者就确立了“以刑统罪”的刑书体例,《左传·昭公六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被公认为是西周时的成文刑书。对于何谓“九刑”,理论界有不同认识,但多数观点认为,“九刑”既是九种刑罚的总称,又是刑书之名。如杨伯峻认为:“九刑者,九种刑罚之谓,昭六年《传》,亦为刑书之名。据《汉书·刑法志》及《尚书·吕刑》郑《注》,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加以流、赎、鞭、扑四刑也。”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35页。即《九刑》是按照墨、劓、刖、宫、大辟和流、赎、鞭、扑九种刑罚来确定篇名的。在“以刑统罪”的体例之下,刑书主要规定的是各种刑罚手段及审判原则,其中虽然也包括一些罪名,但比较笼统,且罪名和刑罚之间并无固定的对应关系。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具体的违礼行为应定何罪并给以何种处罚,需要断狱官自由裁量。虽然“以刑统罪”的刑书体例在我们今天看来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但其重视刑罚、对罪刑关系的反向思考的特点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中蕴含的“以刑定罪”的司法逻辑的运用在今天重新引起学者的重视并非偶然。
(二)罪刑关系决定论的实践困境
罪刑关系决定论由于其先天的重“罪”轻“刑”的缺陷,导致其画地为牢,在司法适用时将“罪”与“刑”人为地切割开来,考虑定罪问题时只考虑客观事实是否和犯罪的构成要件合致,即便在遇到行为有多个罪名和构成要件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也仅仅局限在传统刑法教义学的框架内进行闪转腾挪,单纯依照自身对刑法教义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判定行为的性质问题,而丝毫不考虑行为人可能面临的刑罚轻重问题。只有在定罪问题获得自以为“是”的解决之后,才会按部就班地依照罪名对应的法定刑,根据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决定裁量的刑罚。这一司法裁判进路由于将罪之判断和刑之裁量截然二分,定罪之后机械地根据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法定刑的规定裁量刑罚的做法在疑难案件中常常遭遇罪刑失衡的困境。
疑难案件包括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疑难的案件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疑难的案件。本文所谓疑难案件仅指法律适用上的疑难案件。疑难案件(hard cases)源自法律上存在瑕疵,从而导致裁判者在适用法律上的困难。③Ronald Dworking, Hard Cases, in his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81-130.疑难案件的形成可能基于下述原因:一是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二是规范之间存在冲突;三是可能存在某些案件需要法律上的调整,但却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规范予以适用;四是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有可能会违背规范的条文原义。④参见[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著:《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在疑难案件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或者符合何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疑问,此时若仅从构成要件的教义学分析出发去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往往很难妥当解决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即便定性符合刑法教义学,但得出的量刑结果却可能不当。如在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支洋等7人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并支付嫖资,其行为均已构成嫖宿幼女罪,分别判处各被告人14年、12年、10年、7年的有期徒刑及相应的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嫖宿幼女罪还是强奸罪。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基本犯刑罚为 3 年到 10 年有期徒刑,存在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奸淫幼女多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幼女、轮奸、致使幼女重伤、死亡等加重情节时则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从两罪的构成要件来看,实施嫖宿幼女的行为必然同时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在习水案中,由于不存在《刑法》第236条第3款规定的加重情节和加重结果,因而法院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并无不妥。但如果类似的案件中由于嫖宿幼女行为致使幼女重伤、死亡的,如何定性处理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显然,如果此时不考虑量刑问题,仍然适用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势必会导致罪刑失衡的状态。
造成这种实践困境的根源在于罪刑关系决定论认为要实现罪刑法定,就必须在刑法分则条文中依据行为类型、法益类型以及对法益的侵害程度的不同,设计出不同的符合罪刑均衡原则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组合。只要立法者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司法者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认定犯罪,在此基础上按照法定的刑罚进行刑罚裁量。亦即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罪名是以类型化为基础,一旦罪名变成了规则的一部分,并引导出法定刑的配置,这就成了严格规则主义的一部分,不可逾越,这是法条主义和罪刑法定的题中应有之义。”①姜涛:《批判中求可能:对量刑反制定罪论的法理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9期,第123页。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罪刑阶梯,一方面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不可能规定得像楚河汉界一样泾渭分明,面对错综复杂的生活现实和法律规定,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仅仅依靠对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教义学的分析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只是对某一类危害社会行为危害性程度的概括和预估,这种概括和预估难免挂一漏万、失之片面,对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如果机械依据相对应的法定刑进行量刑,在个案中容易出现罪刑不均衡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罪刑阶梯的配置归根结底是人类既有实践经验的产物,罪刑关系在具体的个案中不均衡的情形在所难免。如最近颇受关注的广州白领冯某购买34支仿真枪被定走私武器罪一案②参见“白领购仿真枪被定罪,申请死刑要求用该枪执行”,http://news.sina.com.cn/s/2015-05-22/071431863080.shtml? from=wap,访问日期2015年5月22日。中,由于冯某在香港购买的34支仿真枪依照大陆对枪支的认定标准属于真枪,根据其犯罪事实,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认为按照法条判决过重,罪刑不相适应,遂依照《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决有期徒刑8年,但这一判决在上诉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后,广东高院却做出撤销一审判决的裁定,原因并非是广东高院认为判决罪名有误,而是认为深圳中院的一审量刑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不当。这一案件一审和二审法院在量刑上产生了分歧,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深圳中院的判决的确量刑不当,但从实质正义的角度观之,走私仿真枪支较之走私杀伤力巨大的真枪的行为危害性程度要轻微许多,判处冯某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又的确量刑不当。无独有偶,四川一名19岁少年也因为从台湾地区购买24支仿真枪被认定犯走私武器罪,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作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这些个案折射出了法律规则所代表的形式正义和个案中蕴藏的实质正义的尖锐对立。司法者如果无视这种对立,案件的裁判将很难获得量刑公正的评价。
罪刑关系决定论者举着罪刑法定主义的大旗,无视立法上的缺陷,坚持从立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和相应的法定刑出发去裁量案件,这种做法在构成要件不明确等存在立法缺陷的个案中就可能得出量刑失当的结果。罪刑关系决定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对为了追求绝对意义上的罪刑法定,限制法官以追求实质的处罚公正为由任意地变换罪名。但罪刑法定原则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然认识到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可取,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被广为接受。严格规则主义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只能是镜花水月,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成为必要。在成文法国家里,“法律一经制定便落后于社会现实”虽然略显夸张,却也并非妄语。成文法典和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静止与变动、有限与无限的张力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张力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空间,使法官不得不面临选择:遵循严格规则主义成为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抑或奉行有限制的自由裁量主义成为戴着镣铐跳舞的舞者。遵循严格规则主义的进路在大多数案件中能够获致妥当的结论,但在疑难案件中却也时常面临着严格规则主义所获得的形式正义、一般正义和个案中所蕴藏的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背离。由于立法的有限性,无法兼顾到个案中所可能蕴含的差异化情境和要素以及在这种要素影响下的个别正义诉求,这也就决定了期待立法为实践中具有差异化的个案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立法应当以追求法律的确定性为最高旨归,但司法不能只追求法律确定性的实现而无视法律的适用性。职是之故,奉行有限制的自由裁量主义成为现实的选择。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法律的适用者必须从活生生的案件事实中去发现建立在常理、常识、常情基础之上的朴素正义,以此为指导去解释和适用法律。而这种朴素的正义在刑事法领域更多地源于对刑罚的感知,因为刑罚是一种易感触的力量①[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判决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刑的公正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刑反制定罪为从实质的角度去理解和适用刑法规范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进路。
三、罪刑关系互动论的发生机制:罪刑均衡目标下的正向制约与反向制衡
基于罪刑关系决定论先天的理论缺陷和立法的有限性所导致的罪刑关系决定论在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以及量刑反制定罪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具有的解释力,有必要对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予以反思和调整,改变罪与刑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罪刑互动的罪刑关系新模式。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之间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均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探讨不多,但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罪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罪刑法定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之法定是通过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予以实现的,“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使得国民在评价自己行为时具有预测可能性,从而防止法官基于处罚必要而突破类型性的制约,造成法官擅断的不可欲后果。”②赵希:《“量刑反制定罪论”不违反罪刑法定》,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51页。刑之法定则是在犯罪对应的构成要件的基础之上配置与其危害性程度相应的刑罚来对其进行法律评价。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形式侧面所要求的法律主义和实质侧面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共同完成罪之法定的任务,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所要求的禁止绝对不定(期)刑和实质侧面所要求的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和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共同完成刑之法定的任务。可见,罪刑法定原则追求的是罪刑关系的一体化,罪与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刑法的规定来看,包括罪状(法定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二者是内在的统一体。作为司法三段论推理前提的法律规范应当从罪刑一体化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割裂开来。罪状(法定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各自独立、相互无涉,但在认识论上进行深层考量就会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彼此不可分割的整体,都只能在以对方为参照系、互为关照的前提下才能被精确认识和把握。此外,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上来看,均衡的刑罚配置亦是其题中之义。可见,罪刑均衡原则虽然是独立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外,但后者事实上却包含前者。罪刑均衡原则要求刑罚的轻重要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罪刑均衡的实现既要求刑事立法上合理进行罪刑配置,又要求刑事司法注重罪刑均衡的动态实现。立法上均衡的罪刑配置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司法上罪刑的一体化考量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关键。前已述及,由于立法的有限性导致立法上无法实现完全的罪刑均衡,立法上的罪刑配置难以在错综复杂的具体个案中实现最终的均衡。如何实现罪刑均衡原则的司法化成为理论上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立法上的修改完善固然是治本之策,但在立法完善之前,司法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题。此时,唯有借助法律解释方法来寻求现有立法框架之内最妥当的解决方案。必须认识到,立法上针对具体犯罪所规定的法定刑种类及其幅度是根据该种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和可能的犯罪情节加以规定的,因而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罪刑一体化,注重通过法定刑的比较分析来准确把握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事实时,心中当充满正义,目光既要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①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说第1页。,又要不断往返于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之间,惟其如此,才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的刑法正义。
立足罪刑一体化的视角去审视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的关系,应当对二者的关系做出如下界定:罪刑均衡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对罪刑均衡目标的追求不能脱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是追求罪刑均衡原则的前提,罪刑均衡原则是适用刑法的终极目的。在这样的关系指导下,对于罪刑关系也当重新认识:罪与刑并非各自为战的存在,亦非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罪刑关系决定论或者量刑反制定罪理论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才是对罪刑关系的最完整、最科学的揭示。
(二)罪刑关系互动论:罪对刑的正向制约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被视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格言化表述。这一表述表明,现代法治国家是先有成文刑法,然后才有犯罪,其后才有对犯罪人施加法律规定的刑罚的问题。因而法治国刑罚权的运作必然要遵循成文刑法犯罪刑罚(权)这样一种逻辑顺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法律规定之前,有无数的类型(刑事学上的类型),立法者将这些行为进行取舍选择,规定成为法律上的犯罪定型。”②张明楷著:《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这种法律上规定的犯罪定型就是构成要件,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是实现罪之法定的关键所在。立法者在规定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之后,根据犯罪行为所侵害法益的重要程度、对法益的侵害程度配置相应轻重的刑罚,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罪刑组合模式。
前已述及,罪刑法定原则追求罪刑一体化,既要定罪准确,又要量刑适当,实现罪刑均衡。定罪准确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所产生的要求,只有准确定罪,才能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如果无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势必会导致构成要件所具有的犯罪个别化机能不复存在,刑法规定不同的犯罪就失去了意义。这无疑是开历史倒车,回到了我国古代“以刑统罪”的老路上了,现代法治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将受到极大的戕害。力主“量刑反制定罪”的高艳东教授认为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犯罪构成的形式内容和罪名设置并无刚性规则,追求定罪的准确性实质上是形式的罪刑法定和法律精英构建“专业槽”以实现专业垄断的需要。③高艳东:《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第165~166页。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论者认为只要量刑适当,即便适用的犯罪构成是错误的,如把票据诈骗罪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也无碍该判决书成为优秀判决书。①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第459页。这种观点无异于承认为了实现量刑公正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如何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目的正当和手段正当不能互相置换,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即便是为了实现正当目的也是违法的,这是现代法治的常识。那种为了追求量刑公正,不惜突破以构成要件理论为代表的刑法教义学的限制的做法意味着放弃了法律的明确性和确定性,退回到了偶然和专断的状态,从而很可能导致打着实质正义的旗号葬送了数百年来人类在刑事法治上所取得的成果。必须重视定罪的准确性,这绝不是华而不实的炫技,而是为了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使得国民能够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在行为前依照成文刑法进行预测。即便论者所言“量刑才是刑法重心”,也不能推导出“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让路”这一结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罪刑相适应不能突破构成要件定型性的限制,追求量刑公正不能随意突破构成要件的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定罪对量刑具有制约作用,不能为了量刑公正而随意定罪。
概言之,罪对刑的正向制约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种犯罪都对应着与其危害性程度相匹配的法定刑,法官需要根据行为人构成的犯罪来选择其对应的法定刑种类和幅度;二是量刑不能随意突破犯罪构成要件定型性的限制,而必须接受其制约和指导。
(三)罪刑关系互动论:刑对罪的反向制衡
罪对刑的正向制约关系是基于法治国刑罚权的运作逻辑而产生的,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仅仅对罪刑关系作单向度的考察并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在现象发生学意义上,犯罪与刑罚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一方消散则另一方必然失去存在依据——没有犯罪当然不会有刑罚,没有刑罚也不会有犯罪。”②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26页。显而易见,犯罪与刑罚之间具有相互定义、相互证成的作用。刑罚的存在正是犯罪行为区别于民事违法、行政违法等其他违法行为的根据。从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对所有的犯罪都规定有刑罚,即便规定了免除刑事处罚也是以针对该种犯罪规定了刑罚后果为前提的。因而,“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的格言可以贯彻到我国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之中。从刑事立法层面上来看,某种危害行为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不仅是由该行为本身的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决定的,还需要考虑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即“应受刑罚处罚性”。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曾经对不适于刑罚处罚的情形做了精当的概括,认为在下列几种情况 不应当施加惩罚:(1)惩罚无理由;(2)惩罚必定无效;(3)惩罚无益;(4)惩罚无必要。③[英]边沁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7页。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所要求的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也表明在刑事立法时必须对立法权予以限制,只能将那些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显然,刑罚对犯罪的反向制约作用在刑事立法上有鲜明的体现。
在司法层面上,固然要遵循罪对刑的制约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刑对罪的反制作用,这种反制作用主要体现为刑法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或者说刑对罪的反向修正。准确把握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实现定罪的关键,然而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明确的客观标准,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也并非是纯客观的、与价值无涉的判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构成要件类型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类型”,而是一种“规范类型”。④杜宇:《刑法规范的形成机理——以“类型”建构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6页。因而,掺入了价值判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只能具有相对明确性。围绕着许霆案,专家学者们对罪名认定所产生的诸多争议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面对错综复杂的个案,特别是疑难案件,案件事实往往处于构成要件类型的模糊地带,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常常难以清晰划定。对于犯罪之间的界限问题,张明楷教授指出,刑法理论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所提出的观点往往缺乏法律根据,曲解构成要件,没有现实意义,徒增认定难度。妥当的做法是绕开犯罪之间的界限问题,正确解释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对案件事实由重罪到轻罪做出判断(有时也可能由轻罪到重罪做出判断);并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准确适用刑法条文。①张明楷:《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87页。冯亚东教授也敏锐地指出,在罪与非罪的判断发生困难之时,需要另辟蹊径,采取逆向的“以刑定罪”的思维方法:“面对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各种不法行为,实在难以在危害量上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正向的思维无法应对生活现实,逆向的思维及处置方式自然形成。”②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28页。二位学者虽然面对的问题不同,一个面对的是此罪与彼罪区分难题,一个面对的是罪与非罪模棱两可的问题,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刑制罪”的解决进路。之所以如此,概源于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手段,量刑是定罪的延伸和目的,二者最终都是服务于刑罚公正这一终极目的。从刑罚公正性的角度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无疑是刑法目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终极解释标准。因此,本文所谓“以刑制罪”或者刑对罪的反向修正指的是一种刑法解释方法,通过考量刑罚的必要性、刑罚的严重程度来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以合理划定个罪的犯罪圈。需要指出的是,以刑制罪依然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在解释时不能突破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更不能为了量刑公正而牺牲定罪的准确性。
结语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认为对于罪刑关系的认识应当摒弃罪与刑的二元对立、罪刑关系决定论等错误观念,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重定罪轻量刑、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应当站在罪刑一体化的立场重新审视罪刑关系,认识到罪与刑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进而确立罪刑关系互动论这一立场,既坚持罪对刑的正向制约,又坚持刑对罪的反向制衡。惟其如此,才能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刑事法治的基石性原则的同时,兼及对罪刑均衡原则的追求,实现刑罚公正这一刑法适用的终极目标。
D924.1
A
1674-8557(2015)04-0045-09
2015-05-27
本文系教育部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产品犯罪的刑法规制》(项目编号:12YJC820033)的阶段性成果。
郝艳兵(1983- ),男,河南济源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苏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