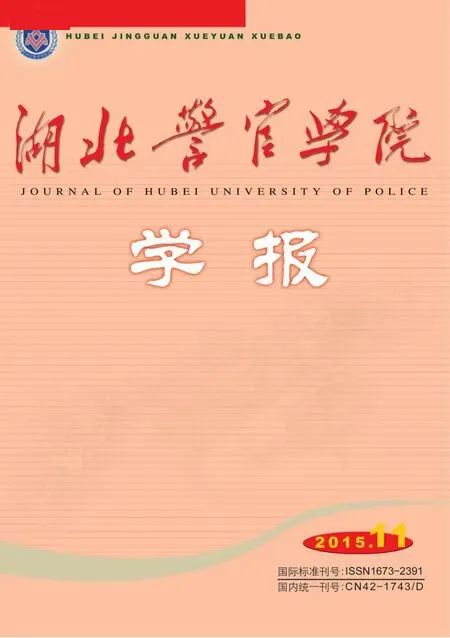我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简论
2015-03-26陈志豪孙锦奕
陈志豪,孙锦奕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学院,上海200050)
据新闻报道,近十年来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从侦查阶段到审判阶段皆有冤假错案出现。如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审判阶段仅以口供定罪的“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仍定罪的念斌案。目前对造成冤假错案的法官如何追责成为了新闻媒体和民众关心的话题。
冤假错案自古有之,历代统治者为了稳固其统治,基本上都建立了司法官吏错案追究制度。“法官出入人罪”制度是其责任制度的核心,历代传承。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都从其统治的需要出发将司法官吏责任制度条文化,力求监督司法,实现其相对的公平与正义。本文将通过西周至明清的相关律法探究古代司法官吏责任制度,希望通过对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法官错案追责制度的建设有所启示。
一、西周的“五过之疵”制度
西周以前的夏、商两代,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国家制度比较简单、粗糙。随着经济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西周时期国家制度趋于完善,包括司法机关和诉讼制度在内的司法体制逐渐成形、成熟。在西周的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天下的最高主宰,故西周的最高审判权自然掌握在周天子手中。《周礼》中,有关于“及刑杀,告刑于王”[1]的记载,《礼记》中有关于“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的记载,说明了周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司法控制权。将个别“刑杀”案件谨慎地控制在周王手中,体现了适应天道要求、慎罚的法制思想。根据相关记录,西周时期大司寇、小司寇是中央的司法官员;在地方,各级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有相对独立的司法管理权。从西周时期的司法体制来看,其一方面保持着地方能动的司法管理权,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将司法管理权集中于中央。
《尚书·吕刑》是反映周穆王时期刑事政策的比较可靠的文献。《尚书·吕刑》中有“五过之疵”的规定。“五过之疵”是要求司法人员,在司法审判活动中遵循“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的办案原则。“五过之疵”制度,原文为“五法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意思是:凡是司法官由于依仗官势、私报恩怨、受女人影响、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这五个方面的原因致使裁判有失公平、公正的,法官就要受到与被判罚的“犯人”相同的处罚。同罪同罚的司法官员法律责任追究制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体现了最为朴素的报复原则。该制度旨在惩罚司法官的故意枉法行为。这是西周奴隶社会确立的法官责任制度,其根据审判经验,总结出了五种司法官故意枉法的行为,并规定了处罚方法。其在成文律法上确立了司法官吏“出入人罪”的“其罪惟均”的责任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二、秦代的“阿法”制度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皇帝独揽国家权力,控制司法机关,天下大事皆可由皇帝决断。史料记载,始皇帝“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①《汉书·刑法志》。。其一方面说明皇帝亲力亲为许多事务,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拥有判断裁量刑事案件的权利。另外,秦代在中央和地方各设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将司法权细化以便于管理。
秦代的枉法裁判称为“阿法”,“阿法”包括“不直”、“纵囚”和“失刑”。“不直”和“纵囚”是故意犯罪,“失刑”是重大过失犯罪。秦代的“阿法”制度较西周的“五过之疵”制度进步的地方在于其将司法官责任追究扩大到了过失犯罪,完善了入罪、追究责任的范围,是立法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阿法”可分类如下:第一,“不直”罪。所谓“不直”是指司法官故意重罪轻判或故意将轻罪重判的行为。据秦简《法律问答》。记载:“赀盾不直,可(何)论?赀盾。”意为:官吏判处犯人罚盾不公,应如何论处?应罚盾。另有史料记载:“(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②《史记·秦始皇本纪》。第二,“纵囚”罪。所谓“纵囚”是指司法官将应当论罪的故意不定罪处罚的行为。笔者未查到“纵囚”的相关处罚,但“纵囚”比“不直”行为危害性更大,按照朴素的法理分析,“纵囚”的处罚应比“不直”的处罚更严厉。第三,“失刑”罪。所谓“失刑”是指司法官由于过失而定罪量刑不当的行为。秦简《法律答问》规定:“士五(伍)甲盗,以得时直(值)臧(赃),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吏弗直,其狱鞠乃直(值)臧(赃),臧(赃)直(值)百一十,以论耐,间甲及吏可论?吏为失刑罪,或端为,为不直。”[2]上述古代法律类似今日的司法解释,其对“失刑”与“不直”的认定和区分是:过失将货值达百一十的,为“失刑”,如果是故意为之的,则为“不直”。
三、汉代的“见知故纵”制度
“见之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即不举报自己知道的违法犯罪人,主观心态为故意的行为。“见知故纵”之罪不仅适用于司法官员也适用于民众和其他官吏,是一项稳固当局统治者统治的司法制度。司法官员犯此罪,一律加重处罚。如《晋书·刑法志》记载:“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之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知不见不坐”。汉昭帝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纵死罪,弃市。”③《汉书·昭帝纪》。从以上记载可见:处罚程度因官员身份不同而不同,一般对司法官员会加重处罚;“故纵”的对象犯罪程度越高,“故纵”的后果越严重。
“见知故纵”主要是针对监临部主失职放弃监督而设置的,其立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监督,是吏治建设的重大举措,但实施的效果适得其反。根据史书记载:“小吏胃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④《汉书·咸宣传》。。其说明了一项制度的实施需要司法人员的全体配合与贯彻,否则如同废纸。
四、唐代的“故、失出入罪”制度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初的统治者特别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威,要求司法官员依法办事,取信于民。唐朝统治者要求司法官吏依法办案,是封建社会以来“法治”程度相对较高的朝代。为此唐代法律责成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不得任意出入人罪,违者要负刑事责任。
(一)司法官故意出入人罪的责任
1.故意入人罪的责任。第一,故“入全罪”的责任。唐朝律法规定:“若入全罪,以全罪论。”第二,“从轻入重”的责任。唐律规定:“从轻入重,以所剩论。”⑤《唐律·断狱》。意为:法官故意将原本无罪的当事人枉法入全罪的行为,应负当事人全罪的罪责;法官故意将原本轻罪的当事人判为重罪的行为,应按将所处重罪扣除应处轻罪之后的余罪处罚法官。该立法思想很简明,将当事人所负多余的罪责由司法官吏承担,是典型的对等报应原则。
2.故意出人罪的责任。唐律规定:“其出罪者,各如之。”⑥《唐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疏议》释曰:“其出罪者,谓增减、情状,足以动事之类。或从重出轻,依所减之罪科断,死出至徒、流,从徒流出至答、杖,各同出全罪之法,故云出罪者,各如之”。简言之,即,减少了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罪责由司法官吏承担。
(二)司法官过失出入人罪的责任
1.过失入人罪的责任。唐律是这样规定的:“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疏议》曰:“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假有从答失入百杖,于所剩罪上减三等,若入至徒一年,同入全罪之法,于徒上减三等,合杖八之类”。①《唐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失入人罪”的罪责是差额罪刑的70%。
2.过失出人罪的责任。唐律规定:“失于出者,各减五等。”《疏议》曰:“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假有失出死罪者,减五等合徒一年半;决出加役流,亦准此,三流同为一减,合徒一年之类”。②《唐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失出人罪”的罪责是差额罪刑的50%。
综上,从唐代律法立法思想上看,故意“出入人罪”的罪责远大于过失“出入人罪”。故意枉法中将差额罪刑作为枉法官吏的惩罚是典型的同等报复思想;过失“出入人罪”中“失入人罪”比“失出人罪”的惩罚要高,因为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要高。这样的立法符合现代基本的立法原理,由此可见唐代的立法技术已经相当合理、成熟。
五、宋代的司法官吏错案追究制
宋代对司法人员错案追究的规定继承了《唐律疏议》,又有所创新。宋代以文治国,追求公正,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宋代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对于法官的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类。刑事处罚与前文所述相仿,不再赘述。宋代对司法官吏的“行政处分”主要体现在其“任职、升迁制度”,即办错案的司法官吏在任职、晋升时会受到严厉的限制。
(一)丧失晋升机会
根据《宋史·刑法志》记载:“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吏一坐深,或终身不进”。[3]仁宗时规定:“官失入死罪者,终身不得改官。”[4]即,司法官吏过失判他人死罪的,终身不得升迁。该制度的设立有极大的威慑力,功名利禄可谓是有志之士的一生追求,一旦“失入人死罪”就会前功尽弃。该制度的设立让司法官吏提高了对案件的谨慎程度。
(二)不得再出任司法官吏
《宋史·刑法志》记载:“仁宗时,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着皆罚金。”[5]即,对于“失入人罪”的司法官员不但不能被升迁,还不能再出任司法官吏。
上述措施类似于当代中国的行政处分,但宋代的“处分”种类比较单一。将限制晋升或再任司法官吏作为处分内容,这样的设置过于单一。从错案的复杂性来看,这种处分模式缺乏“处罚均衡”。对于司法官吏办理错案给予刑事处罚外,宋代立法明确了办理错案的司法官吏应承担的行政处罚,这是立法体系的完善。
六、明清法律中法官错案责任的追究
明清对法官“出入人罪”的规定较唐代更为全面、具体。此外,明清法律中特有的“辩明冤枉”专门条款,将平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明清法律规定:“凡监察御史,按察司辩明冤枉,须要开具所枉事迹,具封奏闻,委官追问得实,被诬之人,依律改正。罪坐原告原闻官吏。若事无冤枉,朦胧辩明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所枉罪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论,所辩之人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③《明律·刑律·断狱》。不难看出,明清专门的追究法官错案责任的机构,是律法监督部门,其追究系事后的救济措施。明清法律对于法官错案责任的追究一般是同罪处罚,系刑事处罚。“辩明冤枉”制度类似于当代的审判监督程序,其将错案依法改判,使受冤之人的冤情得以伸张,以防止激化社会矛盾。
中国古代诉讼法中关于法官责任制度的规定可谓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法官责任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封建社会君主的统治,是对中国古代法官恣意断案的限制。从西周至明清,法官责任制度不断更新丰富:从只惩罚故意的枉法裁判行为到惩治故意或过失的枉法裁判,主观要件上不断更新丰富;从简单的出入罪者同罪到影响司法官吏仕途的行政考核制度,责任承担方式不断变化增加;从无追究机关到建有具体的追究机构,追究制度更加完善。可见,随着历史的推进,法官责任制度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古代法官责任制度毕竟是封建统治的产物,其本质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追求公平正义。其制度的设计有极大的局限性。
[1]曾宪义.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6.
[2]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出入罪的责任制度[J].政法论坛,1990(1):56-62.
[3][5]丘汉平.历代刑法志[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336,342.
[4]王云海.宋代司法制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