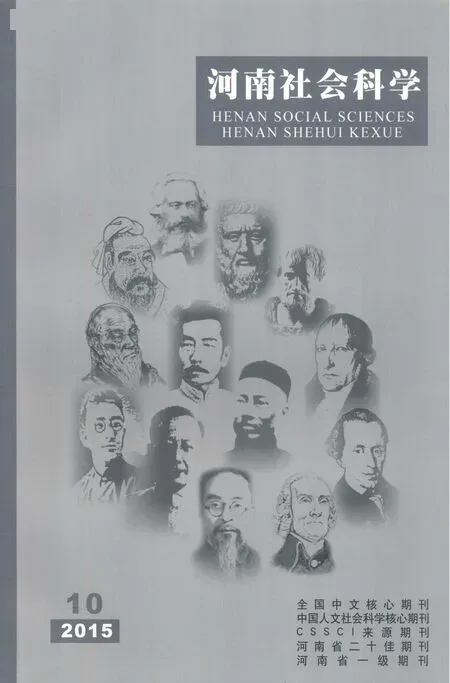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新女性”的自我认同与困惑——《十二金钗》的追问
2015-03-26李萍
李 萍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蜕变,“这给女性带来空前的机遇和挑战”,不仅“女子学校教育的起步,成为从根本上改善女性在资源占有中劣势地位的第一块基石”,而且“职业领域逐步向女性开放,使一部分女性在适应社会劳动分工的前提下,成为能独立谋生的人”[1]。这些受过教育且能够独立谋生的人成为区别于传统社会中被限制在家庭领域的女性,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即“新女性”。
“新女性”们一个个争相做了出走的“娜拉”,抛弃掉传统女性角色,从封建母体中剥离出来。然而,怎样建立新的自我认同,如何在恋爱、婚姻、事业的追求中给自己定位,“新女性”的“新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以庐隐、冰心为代表的第一代“女高师”作家群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追问的真相:出走的女性不是男性启蒙者的同盟而是从属于反叛的男性启蒙者,她们只是男性他者所描述的虚假女性“镜像”的“镜像”,她们必须按照“新”的妇德典范要求自己“美貌、忠贞、温驯、富有献身精神”[2],她们的“新”角色依然被男性主体塑造着和掌控着。
到了1940年代,战争遮蔽了自我的寻觅,一部分出走的“娜拉”走向了革命,以牺牲性别特征为代价,实现了所谓的“儒家大女人”(参见林幸谦《女性主体祭奠》)的追求,融入了主流话语之中,如丁玲、谢冰莹等;一部分在乱世中寻找现世的安稳,在斤斤计较中以爱谋生,在“食”“色”纠缠之中以欲望书写的方式来证明其作为“人”的存在,如张爱玲、苏青等;而同为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内的另一群女子——“东吴系”女作家群却延续着“五四”“女高师”作家群未竟的对“新女性”本质的追问:“生在乱世,女人如何为人,如何为女人?”
领军人物施济美的《十二金钗》(1947)最为典型地展现了1940年代中国“新女性”自我认同的艰难与困惑:有“五四女儿”从“人”到“女人”的认同转向,有被资本改造的“新妻子”对传统“旧小妾”的身份认同,当然也有女作家理想化的女性自我认同表达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充满着艰涩而滞重的沧桑与无奈。
一、“五四女儿”的认同转向:从“人”到“女人”
《十二金钗》中韩叔慧与王湘君是典型的“五四女儿”,前者年轻的时候出国留学,自由恋爱,甚至有一个私生子,为了事业上的成就,一直在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董事”“主席”“妇女届领袖”“女权运动者”。而后者王湘君不仅才貌双全,还有一颗“五四女儿”标志性的“自由恋爱”的心,为了追求爱情,她拒绝了有钱人家的求亲,毅然嫁给了家无恒产的同学胡长年。对“爱情”的选择不仅显现了她们对自己心中美好的“五四爱情”的观念的认同,也是对人生主动权的自我确认。她们相信“男人是人,我们女人就不是人吗”[3],相信子君式的“我是我自己的”女性宣言,相信“在这建国时期,每一个国民都有他艰巨的责任,妇女当然不能例外,尤其是知识妇女,受过高深教育的妇女,她应该站在领导者的地位……”[3]。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第一次“浮出历史的地表”,发出“人”的声音。
然而,新女性在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始终存在着恼人的矛盾:新女性职业角色的在场始终伴随着其家庭角色的缺席。韩书慧,作为一个背叛了传统女性应属的家庭角色的职业新女性,属在室女却不从父;有恋爱和生育的经历,却始终未婚,无法进入家庭获得相应的家庭角色,并且其现在所拥有的职业角色排斥其最基本的家庭角色,她不敢让人们知道自己是赵一德的情人,更不敢让人们知道自己是单身母亲的秘密,作为职业女性她有意规避自己的家庭角色,因为她害怕面对社会的无端责难。这种将事业(职业角色)与家庭(传统角色)对立的思维方式应该说是一种对“五四”“女高师”作家群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对婚姻、对生存焦虑的延承。正如陈衡哲借洛绮思之口所言:“结婚的一件事,实是女子的一个大问题。你们男子结了婚,至多不过加上一点经济上的负担,于你们的学问事业,是没有什么妨碍的。至于女子结婚之后,情形便不同了,家务的主持,儿童的保护及教育,哪一项是别人能够代劳的?”[4]所以韩叔慧与陈衡哲笔下的洛绮思一致选择了以牺牲个人情感幸福为代价来完成“新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
然而随着“五四”的退潮,“五四女儿”们高蹈的理论却遭遇着残酷的现实。一如洛绮思在她成功地成为著名的哲学家之时,内心的失落透过梦境展示出来,她梦到自己成为已结婚生子的瓦德白朗太太,那梦中的感觉是“那么和谐、那么完美”一样,被人们尊称为“韩先生”的39岁女人,“有钱,有势,有名,有地位,有汽车和华丽的洋房……”。她越来越在乎“她没有丈夫和孩子”,在与赵一德破裂的过程中,一种向“父之家”和“夫之家”回溯的姿态和心理越来越强烈。她无法抑制地开始羡慕和垂涎曾经作为“父亲的女儿”的“韩三小姐”称呼,或者想要却又无法获得的“××太太”身份认同。
与之相比,王湘君变成胡太太之后的“倒退”认同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湘君丈夫不幸早逝后,她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和一个“胡太太”的称号在历经人生颠簸后意识到女性即使有才也很难赢得一个漂亮而幸福的人生。女人的风光,在她看来,“却是靠男人的娇宠和金钱而来的”。基于此,她不仅否定了自己过往的人生,更把这种理念推广应用到其女儿艳珠身上,要女儿钓住风流绅士“赵缺德”,以“你有好衣服穿,戴贵重的首饰,坐了汽车到顶豪华高贵的场合走出风头,多少女人用妒嫉的眼光看你,多少男人用爱慕的眼光看你”[3]来引导女儿走上所谓“正路”。
不论是韩叔慧还是胡太太,我们都看到了明显的从独立自主的“人”到依附性的“女人”的认同转向,最具讽刺意味的便是在胡太太笔下,为女性“争人权”的宣言变成了“争生活”的形式,曾经轰轰烈烈地女性解放运动在新的现代环境下成为资本的一种作秀的表演,一切都围绕着胡太太悟出来的真理“金钱”运转,“女性的自我认同”当然不能幸免于此。
二、“新妻子”与“旧小妾”:现代消费社会中资本对女性自我认同的改造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范畴内,女性写作具有颠覆男权社会体制的重大意义,当女性拿起笔开始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女性自我生命的观照,女性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或显或隐总要体现出来,从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认同”,正如戴锦华所说:“写作之于我,是一处没有屋顶的房间。它是一种裸露,又好似一份庇护;是一次规避,又是某种触摸。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5]然而,上文的胡太太却让我们看到女性写作仅仅是一场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空洞而华丽的表演,无关女性解放的任何宏旨。
上海从1843年开埠起,便逐步发展为“远东第一都市”,近百年的殖民化过程,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思潮也逐渐向华人生活圈渗透,资本催生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已成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最亮丽的风景。现代性进程一方面使女性得以走出“厨房、卧室和小孩”传统活动空间和角色扮演,进入公共领域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男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性别定位使得女性在被物化过程中再一次失去了主体性。
在以上论述中,我们已看到资本涮去了胡太太这个“五四女儿”身上的对“人”的自我认同,“饱经世故的胡太太,现在除了钱以外,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在乎,名誉,事业,志向,人格,学问,爱情,理想………全是假的,书呆子骗人的鬼话,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如果有,也不过是可以用来换较多的金钱而已”[3]。在她的“女性认同”训导下,女儿胡艳珠——一个受过新式教育可以独立谋生的现代女性懵懵懂懂同意了母亲的“女性以色靠男人谋利”的价值观念,并意识到“有一点最要紧,就是——钱”,于是放弃了对“兴隆居”的情感眷恋,奔向了“国际饭店”的怀抱。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系统中,有“娶妻娶德”的行为规范,只有“妾”是以色事人、以性谋生。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将女性身体围绕“美丽与色情”圣化,“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的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6]。由此,其对女性身体的管理和干预达到了极致,从头发到脚趾,正如韩叔慧的外甥女李楠孙为了讨得未婚夫的欢心,将直头发烫成卷发,买了眉笔、胭脂、唇膏、皮鞋、皮包。我们从中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一次的“女性认同”吊诡般地以消费时尚的名义被资本置放回传统的“小妾”认同。资本与中国陈腐的性别观念联手再一次剥夺了女性的自我认同,女性成为无限滑动的能指,像一个虚幻的彩泡漂浮在资本的海洋上,空洞洞的一戳就破。
另外,李楠孙崇拜的上海小姐傅安妮,以《现代小姐须知》和《处世哲学》为典范,认同着女交际花的身份,希望在此过程中钓到一位金龟婿,从而拥有一张长期饭票。对这些新女性来说,职业角色不仅不是她们追求的目标,反而是她们努力逃脱的绳索,她们希望凭借资本对自己性别角色的凸显,在男性的权掌中分得一杯羹。我们悲哀地看到,女性已逐渐沦落为一种现代商品,而所谓的“女性认同”也沦落成为一种对传统的“小妾”身份的认同。
如此“古怪”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在争得了做“人”的权利之后,《十二金钗》中的一些金钗却宁要再一次回到“物”的角色里,或许这才是受到当下历史条件制约的关于女性主义解放的真正难题。正如有学者曾言:“女性自家庭走向社会,浅近地看来,固然是挣脱了一重枷锁。在一般初跳出封建的樊笼,刚举步迈向社会的女性眼中,骤然间,仿佛以为从此便跃进了自由的天地。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新的事物之初获得的欢喜;若进一层去观察,应当说:她们不过是由两重奴隶之禁狱的底层,爬上了男性狱囚所居的地面而已。如此,她们不特要分担了现社会男性大众所担负的一切苦难和忧虑;而且,因为她们是女子的关系,在这转换期的社会,更不能不遭遇到一切因性关系而来的,过于优遇或者过于酷待的压迫。”[7]也就是说,女子获取了职业角色不仅不等于女子经济独立,反而意味着女性或将丧失自己的女性角色(如韩叔慧),或者必须背负双倍于男性的社会重担,解放带来的不是自我实现的欢欣,而是无依无傍的自由与繁重的社会负担,高尚的“解放”于是沦为了许多传统女性想要规避的“苦果”。这样的悖论,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亦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轰轰烈烈的20世纪种种革命,风卷残云了社会的角角落落,却似乎独独与“女性的现代自我认同”无关。
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资本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从“三纲五常”的绳索上脱落进资本欲望的囚牢,以一种极新的姿态吊诡般地回归到极旧的位置。胡艳珠、李楠孙、傅安妮这些接受过教育的新女性,被资本蘸透了身体击穿了灵魂,一次最现代的博弈在有着五千年悠久传统的中华历史上沦落为最陈旧的“女为悦己者容”,“新妻子”成功地被现代消费社会中的资本“光荣革命”为“旧小妾”。
三、理想化的自我认同:“独身主义”与献身“大众”
女作家施济美在文中通过插叙式的议论与讽刺的语言表达了对上述“新女性”认同的否定态度,并塑造了余爱群和赵志聪的理想新女性形象:“独身主义”与“献身大众”的新女性。
小说中信奉“独身主义”的教师赵志聪一边唱古怪歌讽刺想成为“旧小妾”的新女性,一边忙于助人为乐,忙于与人为师,忙于阅读《静静的顿河》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护士余爱群也兢兢业业为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这种理想化的自我认同不仅是一种女性自我的身份和价值在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和秩序中的求证和确认,更将女性的自我认同提升到了宏大的人类的高尚境界。
事实上,在施济美的其他小说中单身女主人公形象占据了大半,她们常常以逝去的爱或者疾病放弃组建家庭的可能性。比如《凤仪园》中,风雅聪慧、潇洒美丽的女主人公冯太太拒绝了康平的追求,把他请出了凤仪园,继续着其避世守寡之路;《紫色的罂粟花》中富家小姐赵思佳在自己爱恋的老师离开人世后,拒绝他人的追求,最终为照顾爱人的孩子染病身亡;小说《三年》叙述了司徒蓝蝶为了自己空战中牺牲的爱人,放弃了柳翔,关闭了通向幸福的门;《古屋梦寻》则在淡淡的怀旧气氛中,展示了荷珠和表哥的凄美恋情,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并没有封建家长的横加阻挠,仅仅是因为患病的荷珠自己“我怕有一天会令你伤心”而放弃了可期待的美好爱情,孤独地回家养病了。
这样一种悲剧的爱情处理方式,在笔者看来,实是一种“独身主义”的宣言与践行,是一份对上文中婚姻状态中女性身份认同灾难的无言抗拒。正如施济美自己在解放前夕《申报:自由谈》上的《小雨点》中所写的“很少的女人在嫁后还有她自己,因为太记得自己,就不成个贤妻良母——所以女人多了一个姓之后,多半就失去了个性”[8]。为了保持女性独特的自我认同,女作家施济美自己终身也没有走入婚姻殿堂,这昭示了女性对现实婚姻的怀疑与恐惧,暗示着女性自我认同遭遇的精神症候,“即爱情只能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境界中而始终无法走向婚姻”,同时说明了“现代知识女性对自我命运和人生道路的黯然领悟与悲观洞察”[9]。若想逃脱资本的魔掌,现代女性只能选择无奈的“独身”,尽管作者已经通过韩叔慧揭示此路的荆棘坎坷与辛酸,但两权相害取其轻,只有在“独身主义”的女性认同中,女性才可以捍卫住一番辛苦争取来的“稀薄”的主体性。因此,与其说赵志聪和余爱群坚守的“独身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认同,毋宁说只是独善其“主体”的无奈之举。
此外,赵志聪对大众的关注与余爱群名字“爱群”都象征了施济美的女性们将自我的认同努力与对大众命运的认同联结起来。施济美的小说《永久的蜜月》中到海边度蜜月的丹蔷因救助邻家小孩而被传染,不幸离开人世,悲痛欲绝的丈夫学明放弃了都市安逸繁华的生活,按其嘱托在此地开设医院治病救人,且在梦境中借丹蔷灵魂之口说出“快乐在不停的工作里”“牺牲小我,完成大爱——才是万全的爱”。《野草》则叙述了一对因门第观念被迫分离的恋人宝丽与杜大森多年后重逢,不再留恋狭窄的恋情,大森对宝丽开办孤儿院献身于社会大加赞赏。《巢》中更借用恋人大卫的遗言宣告:“亲爱的,那最重要的不是爱情,是工作;不是刹那,是永久;不是个人,是大众。”[10]
这种献身大众的理想认同意识却是与当时上海的左翼风潮的影响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左翼风潮在上海沦陷以前早已是风起云涌,妇女职业、妇女解放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自然是关注的热点。1935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新女性》伴随着女主角的原型艾霞以及扮演者阮玲玉的自杀,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左”倾色彩浓厚的《女声》杂志断言“阮玲玉的死是死于她以恋爱为人生观”[11],并且认为“妇女们要想走上光明的路,挤进人的地位”,必须“跳出恋爱为生活重心的圈套之外”[12]。于是我们猛然发现此时女性所呈现的理想化人格竟是由革命男权文化所建构和想象的。在施济美等新女性的创作中,女性被“敦促不要沉溺于爱或其他私人感情之中”[13],要求她们“亲爱的,那最重要的不是爱情,是工作,不是刹那,是永久;不是个人,是大众”[10]。这里,新女性被巧妙地经过了去性化(desexualized)而成为与“大众”可互换的指称,成为新的左翼意识形态塑造的理想人格。某种意义上,这种对新女性理想人格的塑造和掌控不仅影响了那个时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东吴系”女作家,而且又通过她们的创作影响了很大一批新新女性(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们更多地致力于自我的社会认同,等到她们完成社会认同时,才发现“女性自我”的基石早已被抽空了。刚逃脱资本枷锁控制的女性却又落入了意识形态的圈套,女性自我认同的进程彻底陷入了悖论和诡计的漩涡之中。
总之,小说试图通过余爱群和赵志聪来完成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们既摆脱了传统家庭旧道德的束缚,是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人,又摆脱了现实物质世界的诱惑,是一个思想高尚的人。但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自我认同中却隐含着“女性性别认同”再一次失落的危险和无奈。如小说的结尾写道:“志聪一个人胡乱吃了晚饭,对着这空落落的大宅,心里头很有点不自在,无精打采的一个人,在屋子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3]独身主义维系的苍凉,献身大众逃逸的失败,“女性认同之路何去何从”,至今仍是女性主义直面并亟待解决的命题。
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认为:“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展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人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14]也就是说,女性一旦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自我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系列纠结的追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我将成为谁?”而写作则是女性承担并试图回应这一系列关于生命和个体诘问的最佳方式。它通过塑造某一类女性人物来表达对自我的特定的认同感,从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女性的“自我认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写作即是女性之于个体之于生命的自我思考、自我观照乃至自我拯救。
在施济美的女性写作中,不论是“五四女儿”们,还是资本环境下的摩登女郎、上海小姐,抑或自食其力的理想化的职业女性,其女性的现代自我认同中都卷裹着重重或新或旧的标识,受“启蒙”而入世,却期望向“传统”回归,打破家庭夫权的藩篱却又陷入资本男权的魔咒,渴求通过“独身”来维系那一点点“个性”却落得个无比苍凉,妄图借“革命”来进行认同上的突围,无奈发现革命竟是更大的陷阱。更不幸的是,这种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自我认同宿命和难题在当下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条件下愈演愈烈,现代女性每一步新的解放都被残酷的现实箍得更紧。但是,无论怎样,黑如磐石的夜已被尖锐的缝隙划破,曙光一丝两丝挤进来,这条艰难地“寻找自我”的道路终究将被女性用被禁锢了千百年的脚一步一步走出来。
[1]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杨莉馨.女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02):80.
[3]施济美.十二金钗[A].王羽.小姐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23.
[4]陈衡哲.小雨点[M]北京:新月书店,1928.
[5]戴锦华.没有屋顶的房间[A].印痕[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9.
[6][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孙师毅.新女性作家[J].良友画报,1934,(12).
[8]雷洁琼.论抗战中妇女职业问题[J].广东妇女,1941,2(6).
[9]王羽.“东吴系女作家”研究(1938—1949)[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10]施济美.巢[J].启示,1946,(4).
[11]伊蔚.阮玲玉自杀之透视[J].女声,1935,3(11).
[12]白蔚.传媒中的女性角色与现代性(1990—1999)[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13]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上海现代女性的构形[A].汪晖,余国良,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177.
[14]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19.